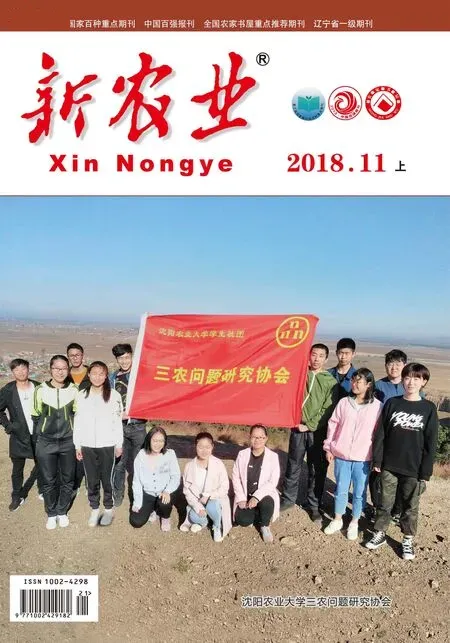我國肉牛業現狀簡析
陳玉艷,劉鴻鶴,李永才,張天姝
(遼寧省獸藥飼料畜產品質量安全檢測中心,遼寧 沈陽 110016)
1 肉牛品種
我國本土主要的肉牛品種包括:延邊黃牛、魯西黃牛、南陽黃牛、晉南牛、秦川牛;因其役用的歷史緣故,本土肉牛生長速度緩慢,平均日增重在1公斤以下,由于生長期長導致肉質差。目前,大型牧場極少育肥本土品種,基本上都是與其他優良品種進行雜交的牛,但是,雜交的代數無法準確跟蹤。散戶的養殖以本土品種為主,含有極少量的雜交血統。
國際上的肉牛品種眾多,在中國常見的包括安格斯、西門塔爾、利木贊、夏洛萊及少量的比利時藍。近三四年以來,國內興起了安格斯養殖熱潮,西北、東北、西南等地區的大型牧場都從澳大利亞直接引進純種安格斯母牛,期望進行安格斯牛繁育并隨之進行公牛育肥,生產高檔牛肉。截止到2018年,進口安格斯數量已經遠超過10萬頭。除安格斯牛以外,國內也有少量的純種利木贊牛或者一代、二代利木贊雜交牛。除去這兩個品種之外,雜交的西門塔爾和雜交的夏洛萊,即使無法追蹤雜交代數,但在目前的育肥養殖形勢下,已經屬于優良肉牛品種。
2 生產指標
肉用繁殖母牛最重要或者唯一的經濟指標便是產犢,除了淘汰前可能進行育肥出售外,肉用母牛不創造其他的經濟效益,產后的母乳僅供犢牛采食。其非常低的產出無法支撐專門化的母牛養殖,多以農戶散養的形式存在,且每日的飼養成本必須控制在10元以下。低文化非專業的從業者、低成本營養不均衡的日糧、非有效管理的人工授精(凍精質量和存放、檔案記錄)等各種客觀現狀,都導致產犢狀況不佳,大概是每3年產2個犢。
育肥肉牛生長速度,是目前絕大多數從業者追求的第一經濟指標,肉質尚未成為主要的效益考核指標。而決定生長速度的第一因素便是品種,追溯繁育母牛的養殖現狀,絕大多數散戶的肉牛品種是沒有保障的。因品種、飼養方式、飼養理念的眾多差異,架子牛從300公斤至出欄,整個育肥期的平均月增重差異巨大,在35~60公斤。即使擁有雜交西門塔爾或者雜交夏洛萊等優良品種的大型育肥場,因在管理、營養和飼養等方面專業知識的欠缺,仍不能保證較佳的生產性能。同理,前面所提到的進口純種安格斯牛,如果進行定向跟蹤回訪的話,飼養效果估計也不盡如人意。
性能指標還包括屠宰率和瘦肉率。但因為不同屠宰場計算方法的差異,以及養殖戶無法直接與屠宰場建立關系(牛販子收牛、賣牛),導致無法收集到這兩個指標的真實數據。另一方面也是目前市場需求使然,若優質牛肉成為主導需求,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指標必將脫穎而出。
3 主要問題
3.1 牛源短缺
因基礎母牛的飼養現狀,當育肥牛行情可觀之時,許多基礎母牛轉而進行育肥、屠宰,導致基礎母牛的質量和數量都下滑。據業內人士估計,全國基礎母牛下滑速度每年在15%~30%,個別地區甚至超過80%。
3.2 環境污染
因肉牛養殖造成空氣、水質和土壤等方面的污染,傳統的散戶院內飼養模式勢必將面臨比較大的挑戰,這取決于政府法律法規的監管力度。
3.2 人員短缺
無論是如今的散戶養殖或是牧場養殖,專業化的從業人員都極度稀缺。推廣科學飼養、規范飼養,對提高生產性能、增加生產效益是極為關鍵的。另一方面,隨著環保壓力的加大、散戶模式向專門化模式的轉變,面臨的首要急迫問題便是從業人員的數量和素質。如何鼓勵專業人員從事專業的工作,需要政府、高校和企業共同努力。
3.4 食品安全
因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肉品及飼料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相對于牛奶和奶牛飼料,牛肉安全性的監管仍然是顯寬松的。這導致飼料市場亂用藥物添加劑的現象層出不窮,養殖者僅著眼于當下收益,而置可能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于不顧。大型飼料企業嚴格遵守法規,以食品安全為前提供給產品;小型企業靈活多變唯利是圖,反倒贏得市場。僅僅依靠市場杠桿來引領肉牛飼養,將掩蓋眾多無法眼觀的隱患,著實令人堪憂。
4 機遇和挑戰
我國肉牛業面臨的最大機遇,便是牛肉需求量的日益增加和供應量的短缺。隨著國民健康意識的增強,牛羊肉的數量和質量都將提上日程。目前,我國人均肉牛消費量為4.7公斤左右,與世界人均10公斤相比仍有很大差距。2016年的牛肉產量為716萬噸,而未來五年牛肉的消費量將達到1000萬噸。進口牛肉雖然來勢洶洶,卻因價格優勢或者肉品新鮮度等原因,未能沖擊國內的牛肉業。
除以上各項問題是肉牛養殖業所面臨的當下挑戰之外,長遠的挑戰是中國必須規范行業,從基礎母牛養殖到餐桌食品,都要建立自己的標準化和科學化繁育、飼料加工、飼養管理和屠宰加工體系,實現肉牛養殖業的穩固發展和不斷完善,而非凡事向外國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