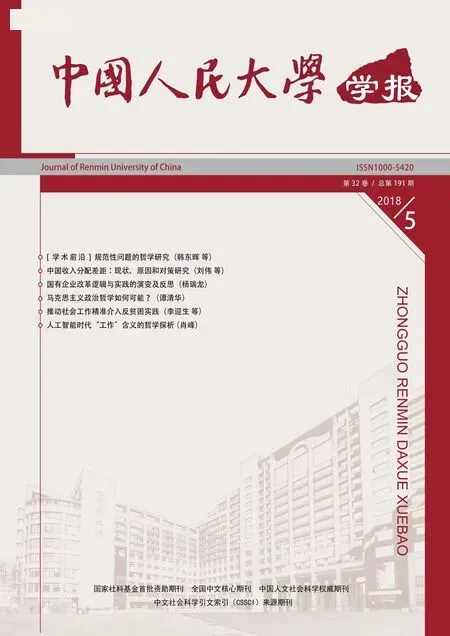試論戰國秦漢文學研究中的慣例方法及其相關問題
徐建委
如何想象或描述戰國秦漢文學,或者如何以“可理解”的形式在當代語境中“再現”戰國秦漢文學?這樣的問題并不好回答。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首先要借助某種類型的敘事架構,因為只有確定了描述或想象的邏輯,建立了一種事物的秩序,才會有“故事”的講述。而史的架構幾乎是目前戰國秦漢文學研究能夠采用的唯一選擇,本文所使用的“戰國秦漢”一詞,就是史學的用語。那么,它是戰國秦漢文學研究唯一有效的架構嗎?恐未必然。但至少在目前,我們還很難擺脫對史學邏輯的依賴。如何講述歷史,也會有不同的敘事模型,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一書有精彩的表述,筆者無須贅述。*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1-43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歷史的描述或想象需要清晰的時間線作為基礎,在時間線基礎上,選擇哪些內容、如何講述它們,則需要一些基本的共識。沒有這些共識,研究者之間就沒有了對話的基礎。這些共識并不是研究中處理文獻或思考問題的方法,而是研究者在開始研究工作之前,就已經按照某種研究的傳統而選定的“做法”,或者可以稱之為“慣例方法”。比如在作品研究中,研究者會很自然地從修辭、技巧、思想以及文學史意義等方面去思考,而沒有反思自己為什么會從這些方面來切入,這就是“慣例方法”的意思。它們是文學研究中的“方法的方法(元方法)”,或者也可以叫“地下方法”,因為它們并沒有出現在研究的表層。文學研究的地上建筑是以這些地下方法為基礎的。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慣例方法”許多源自西方學術傳統,甚至可以說主要來自歐洲19世紀文學史研究的傳統,但對其適用性和有效性罕有清醒的反思。
戰國秦漢文學研究因其材料特點,那些成為研究“默認程序”的“慣例方法”很多都不適用或適用性存疑,茲略舉五條,以供討論:
一、清晰年代的預設
近一百年來,戰國秦漢文學文獻研究往往糾纏于作者、真偽與成書年代這三個問題,遺憾的是,這些問題似乎永遠糾纏不清。它們在被提出之前,研究者默認了這樣一個假定:戰國秦漢古書的主體部分有一個精確的成書年代,但我們幾乎找不出一部這樣的戰國秦漢文獻。
《春秋》三傳、特別是《左傳》成書問題的研究大概可以算這個問題最有名的例子了。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曰:“《春秋》一經,今附于《公羊》、《穀梁》、《左氏》三傳以行。經文大同而小異,三本孰得其真,學者不能無疑。傳文引史釋經,更復彼此離殊,孰得《春秋》著者筆法之真諦,孰得隱、哀間二百四十余年實事之真相,又成千古疑案。二千年來,學者抑揚異致,取舍不同,駁辯既烈,轉益紛拏矣。”[注]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載《洪業論學集》,22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20世紀以來,關于《左傳》成書年代問題的討論尤其熱烈,預言、歲星紀年、冬至日誤差均成為判斷《左傳》年代的“堅實”證據,但三者所得出的結論卻大相徑庭。據預言判斷,《左傳》大約成書于公元前4世紀的某個時刻,衛聚賢的結論是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3年之間,梁啟超判斷在公元前381年之前,劉汝霖則認為應該在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40年之間,趙光賢判斷是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52年之間,楊伯峻的看法則是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386年。還有許多學者曾就這一問題提出過推斷,茲不贅述。[注]黃覺弘:《左傳學早期流變研究》,8-4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新城新藏根據《左傳》中歲星紀年問題,判斷《左傳》成書在公元前365年至公元前329年之間,[注]新城新藏:《東洋天文學史研究》,369-428頁,上海,中華學藝社,1933。陳久金甚至更加精確的定為公元前365年,這與預言得出的結論比較接近。[注]陳久金:《從馬王堆帛書〈五星占〉的出土試探我國古代的歲星紀年問題》,載《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編輯組編:《中國天文學史文集》,48-65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但是,《左傳》中歷日的記載卻直接將此書成書年代下推到了西漢晚期。《左傳》中的歷日往往與魯歷不合,多數先天一二日,因此王韜判斷這些歷日是后人追改,[注]王韜:《春秋歷學三種》,106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而張培瑜更為準確的推算了《左傳》歷日,特別是據兩條“日南至”的記載,做出了這樣的判斷:“西漢太初歷施行期間,《漢書·五行志》所記其時日食絕大多數發生于歷法的晦日。可知是時歷法后天約為1日。《漢書·律歷志·世經》中劉歆用《三統歷》推得,僖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襄二十七年九月乙亥朔(因再失閏,傳書十一月)、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昭二十年正月乙丑朔(失一閏,傳言二月),等等,都與《左傳》說法完全相同。三統四分之法,300年朔差1日。公元前1世紀時《三統歷》后天1日,那么用《三統歷》推算600年前(前7世紀)的歷日,一定會先天1日,這與《左傳》所增歷日先天情況基本相符。也就是說,《左傳》歷日的先天情況與《漢志·世經》用《三統歷》推得的大致相同。說明《左傳》歷日與周歷、《三統歷》有著某種關系。”[注]張培瑜:《中國古代歷法》,182頁,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張先生其實已經判斷出今本《左傳》中的歷日記載很可能是劉歆或其后學據《三統歷》增入,但卻沒有明說。因為還存在另一種可能,即:“這二條日南至資料與以《三統歷》等歷法推算相合,因而可認為是劉歆或者其他人篡入。但也可以作相反的解釋,即《三統歷》等歷法在制定時是把這二條資料當作實測資料考慮在內的,所以它們應與此等歷法符合。但據春秋日食記錄,日食大都發生在朔,而此資料朔日差誤一日以上,是難以解釋的。”[注]陳久金:《歷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歷》,載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編:《科技史文集》(一),19頁,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左傳》新增歷朔有18條,多數先天(包括這兩條“日南至”之朔日)。若《三統歷》僅依據《左傳》新增歷朔來制定,而不考慮《春秋》日食記錄及其他歷朔資料的話,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左傳》新增歷日應為后來增入,增入的時間當是西漢中后期,極有可能就是劉歆。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的結論雖然不能成立,但劉歆確曾染指于《左傳》,恐也是事實。
另外,高本漢據語法判斷《左傳》成書于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間,洪業發現今本《左傳》有避諱“邦”、“盈”的現象,故此書似寫定于漢惠帝時代。
總之,依據不同的材料類型,對《左傳》成書年代的判斷也會有不同。學者們對每一類材料的考證,尤其是對預言、歷法的考證又堅實無比,似無法否定。但這兩種途徑的考證得出的結論卻相差很大。因此,只能說《左傳》是一部累積成書的著作,沒有固定的或單一的成書年代。于是,《左傳》也就無所謂作者、真偽了。
可以說,作者、真偽和成書年代三個問題,在戰國秦漢研究的方法論層面上都是偽命題。戰國秦漢典籍多數都屬于長時段文獻,它們之間排不出一個先后次序清楚的年代序列,任何有這種構想的做法,都將是徒勞的。但為什么我們又熱衷于探索成書年代問題呢?也許還是老套的研究模式在作祟。文學的思想、情感、風格、技巧、歷史位置等問題都需要一個時間的坐標,需要作品背后的作者,也就是需要任何作品都有一個清晰的年代。
二、進化假設和線性的歷史構造
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形成于20世紀初,那是進化論盛行年代。1928年8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發行,卷首傅斯年先生《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云“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注]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先秦卷》,1頁,北京,中華書局,2009。。似乎這是無須特別說明的一個認識,足見當時進化論之風行。那時絕大多數《中國文學史》的敘事中都有進化論的影子。綿延至今,進化論的幽靈一直在文學史研究中徘徊。從《老子》、《論語》到《莊子》、《孟子》,是說理散文的進化;從《詩經》到《楚辭》,是詩歌語言的進化;從永明體到近體詩是詩歌格律的進化;從魏晉志怪到唐傳奇是古小說的進化等等,這樣的想法或敘述幾乎就是文學研究者的常識。另外,許多著作還會提到文體的衰落,整個過程就像一個生物體的生長與衰老。這種簡單的進化論模式,甚至會自動地創建進化鏈,我們每一個受過文學史教育的人,似乎都能摸著樹狀進化圖譜,把詩歌、文章、小說、戲曲的生長軌跡給復述出來,這么清晰的圖譜,其有效性自然值得懷疑。
首先,我們是否相對全面地看到了古代的材料?就戰國秦漢時代的材料而言,今天即便是能夠看到當時1%的材料也是奢望。以《漢書·藝文志》為例,其所錄圖書多數散佚。“兵書略”錄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數術略”錄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這三“略”二百七十九家,近四千卷(篇)文獻中,除《吳孫子兵法》、《魏繚》、《山海經》、《黃帝內經》等四部流傳下來,《齊孫子》出土于銀雀山漢墓外,其他盡數失傳。相對而言,“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中,流傳于后世的略多,但在整個《漢志》當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不會很高。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漢志》所錄僅僅是未央宮藏書,這些書雖然大體可以反映當時精英知識的主要文獻類型,卻不可能是當時的所有文獻的表征,畢竟這批藏書只有一萬多卷,而漢代及其以前的文獻自然遠不止這些。盡管我們不能確知具體數目,但從世界其他文明的同時期文獻流傳量來看,漢代的文獻恐怕絕不止一萬多卷,如亞歷山大時期的圖書整理就有近七十萬卷。因此,依據這么少的材料所看到的進化和線性的歷史,是不是一種“被制造”的進化?
戰國秦漢時代那些流傳下來的文獻與當時的文獻總體相比較,大約也就是一些零星的碎片,如果我們把當時的文獻總體想象成一只50厘米高的瓷瓶,現在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數量不多的幾毫米大的碎片。依靠這么點碎片,是很難復原那個瓶子的形狀的。各種戰國秦漢文學史的講述,恐怕會是我們利用零星文獻臆想出來的一只沒有意義的瓶子。
其次,文字書寫的特點能否等同于語言表達的特點,或者說文字與語言的發展是否具備同步性?進化論思維的潛在邏輯之一,是對早期歷史的“原始”假設。在處理文字的歷史時,中國的殷商時代成了可確證的源頭。于是,另外一個不加反思的慣性思維就出現了:將文字的使用階段與人類的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的發展等同。文字的質樸未必等同于思維和表達的質樸。如果我們考慮到殷周時代之前長達數千年的文明發展的話,就會知道殷周時代的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表達水準并不能看作是那個時代的語言表達水準,那個時代真正體現當時人“文學”水平的應該是口頭文學,而非書面文學。如果我們具體到春秋晚期至西漢初年這一時段,從孔子時代到孟子時代僅僅一百多年,我們先人的文學表達力會出現文學史中所描述的那種飛躍嗎?從文字以來的歷史看,這的確是一段相對較長的時期,但從文明的歷史看,孔子與孟子之間的時差幾乎可以忽略。在書面文字表達成熟的東周時代,孔子時代的文學與孟子時代的文學,乃至荀子時代的文學,會有多大的不同?
再次,我們今天看到的古代文獻是否就是原初的面貌?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對于戰國秦漢文獻來說,抄寫、版刻中的訛變倒在其次,關鍵的問題是西漢晚年劉向的圖書整理。目前傳世先秦秦漢文獻,多數經劉向整理校勘過。群書今本絕大多數以劉向校本為祖本。這次文獻整理重構了絕大多數傳世的先秦秦漢文獻,成為諸多經典文獻流傳歷史中的根本性轉折。與此同時,劉氏父子還構建了一個體系完整、條理清楚的學術圖譜,被班固繼承在《漢書·藝文志》中,成為后人閱讀、理解和想象先秦的起點。更為重要的是,劉氏父子的文獻整理也是我們面對先秦秦漢的視點——即我們在按照劉向、劉歆父子的方式“觀看”那時的文獻。
因此,就目前所能夠掌握的文獻來說,我們既不能確定一些相似的語言特征之間存在連續性的關聯,也無法判斷不同時代的人物之間存在知識方面的承襲,即我們不能在文字能力等同于表達能力這種荒謬的前提下,依據片段的、非原貌的材料來構造線性的文學研究的史學假設。
三、文本內在統一性的假定
戰國秦漢文學研究、特別是涉及具體的作品時,研究者往往假定文本有內在的統一性,即假定文本總體上是一個有唯一“作者”的“完足”的“一次性”作品。即便文本存在前后重復或矛盾,研究者也會從“理解”與“闡釋”的角度加以分析,竭力彌合文本內部的裂隙,呈現其整體的意義。比如《離騷》,多數解讀者首先是假定它是完全屬于屈原一次性創作的作品,當然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們不能無視其他可能性。比如它還很可能是一個復合文本,這其實也不是什么新觀點,胡適的《讀楚辭》(《努力周報》1923年)就已經認為《離騷》等屈原作品類似于《荷馬史詩》,是一些早期的口頭文學,后人將之歸于屈原名下。[注]胡適:《讀楚辭》,載《胡適文集》第三冊《胡適文存二集》,7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后來,岡村繁的《楚辭與屈原——論屈原形象與作者的區別》(《日本中國學報》1966年)亦曾留意《離騷》、《九章》等作品的復合特征。[注]岡村繁:《周漢文學史考》,50-8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近來,柯馬丁在一些學術會議上也提到了這一問題。即便我們不同意上述諸人的看法,至少我們應該承認《離騷》文本的內在統一性是存疑的。[注]關于此問題的詳細辨析參見常森:《屈原及楚辭學考論》,1-13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文本內在統一性假設源于后世對早期文獻流動性估量的不足。同時,后人對漢人整理前代文獻的工作多有忽視,以為《漢書·藝文志》載錄的就是戰國秦漢時代流傳的文獻,而沒有意識到許多經典直到劉向父子校書,才最終成為《漢志》中的卷帙樣式。
劉向校書之前,古書多為開放性文本,因此西漢成帝之前流傳的署名為漢人的典籍,其文并不僅限漢代文獻,甚至不以漢代著作為主。純然為漢人著作的,除了《楚漢春秋》、《鹽鐵論》等少數幾部外,多數西漢文獻實際上是戰國秦漢文獻的匯總,且以戰國文獻為主。艾蘭在《關于中國早期文獻的一個假設》一文中說:
在春秋后期或戰國時代,人們開始將同類文本進行歸納收集,其中包括《詩》、《書》、《禮》,門徒們也開始記錄他們導師的言辭。這些收集起來的文本開始傳播,特別是同一導師的門徒之間,并被聚集為規模更大的文集。這類的文集不一定有順序。更為重要的是,它們的內容往往有一個開放性的結尾。我這么說是為了說明,有文集以后,更短的文集和單篇文章還同時流傳,這些文本也被組合起來進行傳播,也可能經過添加、刪減或修訂。而不同的人對于文本的收集與組合也不盡相同。例如,孔子的《書》和墨子的《先王之書》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但又顯示出差異。
這個推斷的價值之一在于,它有助于解釋自漢代以來一直困擾中國文獻傳統的真偽問題。此外,即使書寫于帛卷上的版本在漢代變得明晰以后,仍然有簡短的“古文”竹書和早期絲帛稿本流傳,并被收藏于皇家圖書館。以上假設說明,這種松散的古文文獻,來自于學術氣氛寬松活躍的戰國時期。它們既是中國文獻的最初形態,也是漢代新訂隸書文本的來源。[注]艾蘭:《關于中國早期文獻的一個假設》,載《光明日報》,2012-01-09。
她的推斷大體不差。除了《史記》和大、小戴《禮記》外,漢代幾部重要的經傳子書《新書》、《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新序》等也基本如此,乃某類或某幾類戰國秦漢文獻的匯總。
同樣,《晏子》、《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等戰國諸子著作因最終定本在漢成帝時期,其中若存有秦代或漢代文獻短章、語句,亦屬正常。總的來看,流傳至今的先秦文本多數為綜合性文本,或曰長時段文獻,不能以作者的時代對應之。此問題前人多有注意,但西漢文本的綜合性問題,迄今并未引起學界足夠之重視,應予特別注意。
從時間角度而言,戰國秦漢文本的綜合性特點,乃是長時段之特點,故知此間多數文本不能將其限定于其“作者”的年代。因此,《春秋繁露》很難與董仲舒畫上等號,其中的文字與思想我們不能預先假設其統一性,事實上,此書幾乎不可能具備內在統一性。
因此,文本內在統一性的缺失,不僅存在于《論語》、《老子》、《孟子》、《莊子》等周秦古書,也存在于《新書》、《史記》、《春秋繁露》、《說苑》等西漢典籍中。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對《離騷》等《楚辭》作品文本復合特征的研究,容易被誤認為否認屈原的真實存在,其實《離騷》文本的復合特征與屈原是否存在是兩個問題。就像我們認定《管子》一書是各種類型篇章的綜合,并非管仲所作,但并沒有否認管仲的存在一樣。
四、“作者”自我表達與全知的假定
“作者”的自我表達與全知假定,這是兩個相互有關聯的問題。文本是作者自我表達的假定,也可以說是“泛創作”假定,它是與文本內在統一性假設相互關聯的另一個“慣例方法”。為什么我們在閱讀古代文本之時,會自然地假定它的制作者有一個創作的目的呢?或自我表達,或塑造人物,總之,我們容易自然而然地認定制作者對文本有著某種掌控的意圖,并以為制作者的自我意識會成為文本形成的動力。這是一種目的論式的研究預設,但并不總是有效的,特別是在戰國秦漢時代,像《史記》這樣的書,其目的性的“創作”很可能也只限于書的層面,即《史記》整體上是有明確的著述意圖的,但具體到每一篇,則編纂和創作孰輕孰重是需要仔細考量的。
目的論式的分析即便放到漢以后,也未必總是有效的。如顏師古《漢書注》雖然采獲二十五六家前人注釋,但幾乎沒有引及東晉以后、特別是南朝的《漢書》學成果,吉川忠夫在《六朝精神史研究》一書中,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是,顏師古對于南朝學術并不欣賞。[注]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236-32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這種思考的預設為:文本的內容和特征可以反映作者的思想。這種假設很多時候是成立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可能。如果我們不從目的論的角度求證,而是仔細分析顏師古《漢書注》的制作過程就會知道,這部書是顏師古利用西晉末年臣瓚的《漢書集解音義》來修訂東晉蔡謨的《漢書注》,與他是否欣賞南朝學術并無關系。所以,文本的內容固然重要,但其物質性、特別是其形成或制作過程,仍然應該是具有優先性的,但由于“創作”思想的影響,文本物質性的研究至今非常薄弱。
我們往往假定古代存在一個著述傳統,進而將其擴大化,很少反思實際情形。這種假設更多地受到了《太史公自序》或《報任安書》的影響,而沒有意識到這也許只是一種夫子自道,并將文王等人牽扯進來,為自己的想法制造了傳統和歷史。
“作者”的全知假設往往存在于“文學史意義”或“影響”研究之中。研究者非常容易將“作者”當成一個對早期傳統和文獻完全了解的人,也會將那些重要的大人物當成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完美作者”。比如我們知道《左傳》與《史記》的關系頗為糾葛,特別是《史記》諸《世家》的記事有許多大異今本《左傳》之處,翻檢梁玉繩《史記志疑》即可略知其大概。那么,這么多差異是否是因為司馬遷見到了《左傳》之外的春秋史料,而據之以編纂諸世家與《十二諸侯年表》呢?近年有如此多的戰國秦漢簡帛文獻面世,每每有驚人發現,如馬王堆、郭店、上博、清華、北大諸文書,均或多或少有一點與史料相關的文獻存在,以一斑而窺全豹,似乎可以斷言司馬遷時代出于《左傳》的春秋史料應有不少。實則這種思考亦有一個先行的假設,即司馬遷是一位類似與現代學者或者說現代意義上的史學家,他會匯總史料,并在史料批判的基礎上擇善而從,編纂一部現代意義上“完美的史書”。但是,司馬遷會在多大程度上進行嚴謹的史料批判呢?我們現在知道,古代的很多大著作是二次加工的成果,《史記》、《漢書》、《史記集解》、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等都是如此。既然已經有了一部完善的《左氏春秋》,司馬遷是否還有必要搜集一些零散的春秋時代的故事呢?只要仔細看看《十二諸侯年表》,就會知道,《史記》的春秋史料就是抄錄自《左氏春秋》,只不過是一部未經劉歆整理過的《左氏春秋》。
我們也會假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敘述的是漢武帝時代對屈原和《離騷》的共識,司馬遷對前代文學傳統也是全面了解的。但是否還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屈原部分是太史公直接抄錄自其他文獻,而非自撰。事實上,其文本的內在矛盾已為許多學者所注意。《文心雕龍》提到的劉安對屈原的評價,也見于《屈原賈生列傳》,故不能排除《史記》中屈原的史料來自劉安《離騷傳》這種可能。司馬遷對屈原的生平也許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還從其他地方重復抄錄了一些,甚至名字都沒有統一起來。再如,當我們討論歐陽修《詩本義》時,總是要強調此書對漢唐《詩經》學、特別是《毛詩正義》的反動,但是,歐陽修在以札記的形式撰寫《詩本義》時,他是否已經閱讀過《毛詩正義》?
五、余論
除上述五個問題外,在文獻考辨中,受到傳統校勘之學的影響,研究者還會有一種發現“原始文本”的考證期待,這也是不切實際的。在文獻電子化的今天,傳統校勘學已經部分地失去了意義。
這些“慣例方法”是我們今天理解歷史的方法。一百多年來的戰國秦漢文學史就是以“現在”來理解的“過去”,使用今天我們認知歷史的方法重建的、想象中的、理所當然的文學史。
當我們用自以為合理的方法來處理戰國秦漢材料之時,這些材料變成了鏡面,我們從中看到的其實是自己的影像,而不是原始的、粗糲的過去。遺憾的是,鏡像化的先秦學術、思想和文學的研究目前依然是主流形態。現在,也許到了打破這面鏡子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