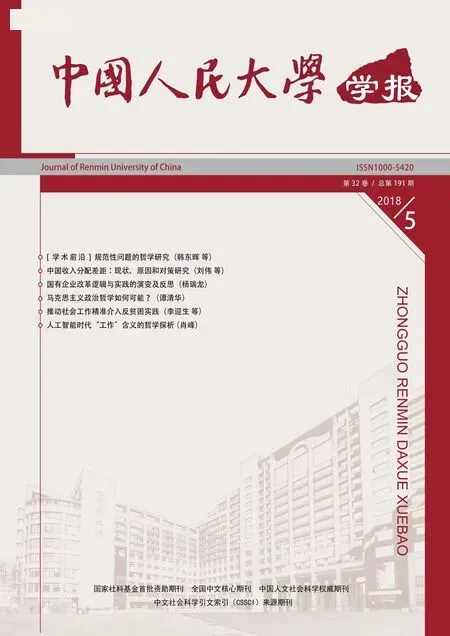文理之爭(zhēng)的背后: 再探阿諾德與赫胥黎關(guān)于文學(xué)教育的論爭(zhēng)
納 海
近年來(lái), 隨著國(guó)內(nèi)大學(xué)文科面臨的種種挑戰(zhàn), 學(xué)界開(kāi)始借鑒西方文科教育與科學(xué)教育的紛爭(zhēng)給我們帶來(lái)的啟發(fā),尤其是英國(guó)維多利亞后期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1880年撰寫(xiě)的《科學(xué)與文化》以及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82年作為回應(yīng)寫(xiě)下的《文學(xué)與科學(xué)》[注]David Roos.“Matthew Arnold and Thomas Henry Huxley: Two Speeches at the Royal Academy, 1881 and 1883”.Modern Philology, 1977 (74.3).,更是引起了國(guó)內(nèi)學(xué)者的關(guān)注。[注]米廣寧:《“科學(xué)與文化之爭(zhēng)”——赫胥黎與阿諾德的對(duì)話(huà)》,載《教育隨想》,2008(2);單中惠:《試析十九世紀(jì)英國(guó)科學(xué)教育與古典教育的論戰(zhàn)》,載《清華大學(xué)教育研究》,2000(2);高曉玲:《馬修·阿諾德的知識(shí)話(huà)語(yǔ)》,載《國(guó)外文學(xué)》,2013(3)。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lái)看,大部分的研究都把二人的爭(zhēng)論視為“學(xué)科”的分歧。當(dāng)然,阿-赫之爭(zhēng)首先是對(duì)大學(xué)教育中人文學(xué)科和自然科學(xué)不同看法的爭(zhēng)辯,這點(diǎn)毋庸置疑,而且他們各自所秉持的理論對(duì)當(dāng)今國(guó)內(nèi)大學(xué)教育也有相當(dāng)重要的意義。但如果細(xì)讀赫胥黎、阿諾德的兩篇文章,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在“學(xué)科”的表象下是他們二人各自所代表的思想傳統(tǒng)的重大分歧,是在深層含義上對(duì)于“知識(shí)”和“真理”的不同理解。這場(chǎng)爭(zhēng)論為20世紀(jì)斯諾(C.P.Snow)提出“兩種文化”的論斷奠定了基調(diào)。由于這兩篇文章有許多互相呼應(yīng)的概念,而兩位作者將這些概念不斷地界定,因此細(xì)察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就尤為有趣。本文從細(xì)讀這兩個(gè)文本入手,梳理他們各自所秉持的關(guān)于“知識(shí)”的理念,特別是要透過(guò)《文學(xué)與科學(xué)》的語(yǔ)義層面考察阿諾德獨(dú)特的思想境況。
一、赫胥黎的“科學(xué)精神”
首先,阿諾德與赫胥黎關(guān)于教育的觀點(diǎn)并非絕然不同。從19世紀(jì)初期開(kāi)始,阿諾德就一直倡導(dǎo)將科學(xué)內(nèi)容引入大學(xué)教育;而赫胥黎也堅(jiān)持認(rèn)為,科學(xué)教育有著教化德性的功用。他們二人都希望擺脫過(guò)于功利、遷就當(dāng)時(shí)商業(yè)社會(huì)發(fā)展的、帶有典型中產(chǎn)階級(jí)烙印的庸俗文化,著力培養(yǎng)理性、全面、有益于社會(huì)整體風(fēng)尚的優(yōu)秀文化。他們的不同在于各自的側(cè)重:赫胥黎不愿被當(dāng)作“科普”作家,一心要塑造專(zhuān)業(yè)科學(xué)家的形象,因而他的著作多是比較專(zhuān)門(mén)的專(zhuān)業(yè)論著;阿諾德提倡在人文教育中融合科學(xué)、客觀的研究方法,將“批評(píng)”精神引入文學(xué)領(lǐng)域。然而從19世紀(jì)80年代開(kāi)始,他們二人之間論爭(zhēng)的聲音似乎掩蓋了合作的聲音,二人就科學(xué)教育與古典教育展開(kāi)了深入激烈的討論。在1880年寫(xiě)就的《科學(xué)與文化》中,赫胥黎認(rèn)為科學(xué)知識(shí)爆炸式的增長(zhǎng)乃是這個(gè)時(shí)代的最重要特征, 因此傳統(tǒng)的古典教育不再擔(dān)當(dāng)培育社會(huì)精英的責(zé)任。他認(rèn)為阿諾德所謂的文化——即通過(guò)學(xué)習(xí)“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思想和言論”,從而“追求全面的完美”[注]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wú)政府狀態(tài)》,185頁(yè),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2。——無(wú)非是“包含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對(duì)人類(lèi)生活的批評(píng)”[注]③⑤ Thomas Henry Huxley.Collected Essays.Vol.3 .Hildesheim: Georg Olims Verlag, 1970, p.142,145-151,154.。文化是對(duì)人類(lèi)生活的批評(píng),赫胥黎對(duì)此并無(wú)異議,但他否認(rèn)這種文化必須要通過(guò)閱讀文學(xué),特別是古典文學(xué)來(lái)達(dá)到:即使學(xué)習(xí)了希臘、羅馬,以及東方的古代文明,并了解了現(xiàn)代文學(xué)所能告訴我們的一切,我們?nèi)匀徊荒苷f(shuō)獲得了應(yīng)有的“文化”身份。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雖也重視古典文化的學(xué)習(xí),但那時(shí)候的古典知識(shí)正相當(dāng)于19世紀(jì)的科學(xué),對(duì)人有一種啟迪、開(kāi)化的作用,因此決不能把文藝復(fù)興時(shí)代重視希臘羅馬語(yǔ)言的事實(shí),作為19世紀(jì)末期依然高舉古典語(yǔ)言大旗的借口。③
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和19世紀(jì)對(duì)待古典文學(xué)態(tài)度的差異,在于時(shí)代精神的不同。赫胥黎指出,當(dāng)今時(shí)代的最大特征是大量日益增長(zhǎng)的自然知識(shí),這些對(duì)于自然不斷深入的認(rèn)識(shí)不僅有益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更是成為新時(shí)代的一種“思維范式”,赫胥黎稱(chēng)這種范式為“科學(xué)的精神”。同時(shí)赫胥黎認(rèn)為希臘精神其實(shí)一向是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探索的,由此他把文化守成主義者的發(fā)難反推回去[注]赫胥黎說(shuō):“我們都知道在論辯中,‘你也如此’這樣的論證是沒(méi)有什么說(shuō)服力的,否則科學(xué)教育也會(huì)反擊現(xiàn)代的人文主義者,說(shuō)他們雖然聲稱(chēng)要以‘文化’之名建立一種‘對(duì)生活的批評(píng)’,但實(shí)際上他們只不過(guò)是一些研究語(yǔ)言文字的專(zhuān)門(mén)家(specialists)。”此處的論說(shuō)非常值得玩味,因?yàn)橐环矫婧振憷枵f(shuō)“你也如此”這種論證沒(méi)有說(shuō)服力,另一方面他實(shí)際應(yīng)用的就是這樣一種邏輯:人文主義者說(shuō)科學(xué)家是專(zhuān)門(mén)家,其實(shí)他們自己也并不能挑起傳承文化的重任。,認(rèn)為在現(xiàn)在這個(gè)時(shí)代,如果還僅僅讀希臘羅馬,恰恰是缺乏科學(xué)精神,教條地承襲古代文化而無(wú)視自然科學(xué)的發(fā)展,談不上“對(duì)生活客觀、公允的批評(píng)”。由此,赫胥黎把論證的焦點(diǎn)又重新放到“文化”上來(lái):“我們須得像我們中間最優(yōu)秀的人那樣,有一種堅(jiān)定不渝的信念,認(rèn)為只有按照科學(xué)的方法來(lái)自由調(diào)動(dòng)理性,才是達(dá)到真理的唯一途徑。除非如此,否則我們就徒有傳統(tǒng)文化守成者的虛名”。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shí),赫胥黎認(rèn)為目前那些保守派實(shí)在夠不上稱(chēng)為文化的繼承者。當(dāng)然,他也認(rèn)為文科也不可盡廢,因?yàn)椤皢螌W(xué)科學(xué)就像單學(xué)文學(xué)一樣,只能培養(yǎng)出一些跛腳的文化人”⑤。由此可見(jiàn),赫胥黎并沒(méi)有認(rèn)為科學(xué)比人文學(xué)科更重要,然而不論學(xué)什么,都要秉持一種科學(xué)客觀的態(tài)度,以“達(dá)到真理”為最終的目的。此處的真理是人類(lèi)運(yùn)用理性,對(duì)可以觀察到的實(shí)驗(yàn)數(shù)據(jù)加以分析從而得到的關(guān)于自然界的認(rèn)識(shí)。這些認(rèn)識(shí)可以幫助人類(lèi)過(guò)上更好的生活。同時(shí),追求這種客觀真理的過(guò)程,可以培養(yǎng)人的誠(chéng)實(shí)、審慎、客觀等品質(zhì),以更好地了解自然。
二、阿諾德關(guān)于文學(xué)的三重理解
1882年,阿諾德在《文學(xué)與科學(xué)》中回應(yīng)了赫胥黎對(duì)文學(xué)的看法,并從三個(gè)層次論述了自己對(duì)文學(xué)的定義。
首先,他援引了古希臘哲學(xué)家柏拉圖的見(jiàn)解。雖然他同意柏拉圖關(guān)于教育的目的——“使人的靈魂變得清醒, 正直,充滿(mǎn)智慧”,但總體上他覺(jué)得柏拉圖為哲學(xué)辯護(hù)的理論是不能用于維多利亞時(shí)代維護(hù)文學(xué)教育的。阿諾德并非一味沉迷于對(duì)歷史的留戀,他認(rèn)為先進(jìn)的工業(yè)社會(huì)、特別是像美國(guó)這樣的工業(yè)社會(huì),科學(xué)技術(shù)的意義決非尋常。但他卻不能因此就同意那些科學(xué)家“削弱文科在大學(xué)的主導(dǎo)地位,并將這種主導(dǎo)地位讓位給自然科學(xué)”的主張,盡管他意識(shí)到這種重心的轉(zhuǎn)移是目前的重要趨勢(shì),已經(jīng)一發(fā)不可收拾。[注]⑦ R.H.Super(ed.).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Vol.10.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55,63.
接下來(lái),阿諾德重新將文化定義為“對(duì)世界上過(guò)去最優(yōu)秀的思想和言論的了解”[注]這是阿諾德引述赫胥黎的原文,而赫胥黎在文中的“最優(yōu)秀的思想和言論”參見(jiàn)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wú)政府狀態(tài)》,185頁(yè),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2。。他認(rèn)為赫胥黎扭曲了自己的原意:“最優(yōu)秀的思想和語(yǔ)言”不等同于“文學(xué)”,“文學(xué)”更不僅是“美文”。赫胥黎這兩步錯(cuò)誤的聯(lián)系,讓阿諾德的教育理念變成了僅關(guān)乎人感官的、膚淺的“審美”體驗(yàn),是以享受為目的的一種貴族教育。阿諾德反擊說(shuō),自己所設(shè)想的“文學(xué)”絕不僅僅是所謂的美文,而是應(yīng)包括歷史、哲學(xué)、地理、自然科學(xué)的“文獻(xiàn)”。“當(dāng)我說(shuō)‘了解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我不僅指語(yǔ)言和文字,而包含了整個(gè)希臘,整個(gè)羅馬的生活、思想史,他們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以及我們能從他們中學(xué)到什么樣有用的價(jià)值。這才是我所說(shuō)的理想狀態(tài)。我所謂通過(guò)‘文學(xué)’達(dá)到對(duì)人類(lèi)生活客觀、公允的批評(píng),指的就是我們盡可能地接近這樣一個(gè)理想。”[注]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wú)政府狀態(tài)》,57-58頁(yè),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2。這便是阿諾德對(duì)于“通識(shí)教育”的一種解釋?zhuān)鼘?duì)我們今天的教育思想也起到了很深遠(yuǎn)的影響。然而讀者不禁會(huì)問(wèn):阿諾德的解釋能回答赫胥黎的問(wèn)題嗎?這樣把“文學(xué)”解讀為“文獻(xiàn)”的方法,能夠達(dá)到赫胥黎所說(shuō)的“了解自然世界”嗎?盡管阿諾德說(shuō)文學(xué)不等于美文,但僅僅了解科學(xué)方面的文獻(xiàn)并不等同于了解最新的科學(xué)發(fā)現(xiàn),也不意味著就能夠在一定條件下獨(dú)立進(jìn)行科學(xué)研究。[注]事實(shí)上阿諾德本人對(duì)于科學(xué)的確涉獵極少。這和赫胥黎所倡導(dǎo)的科學(xué)教育還是有很大距離的。[注]赫胥黎不僅本人對(duì)科學(xué)深感興趣,還是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的積極推動(dòng)者。他還為現(xiàn)代經(jīng)驗(yàn)主義的先驅(qū)者之一休謨(David Hume)編寫(xiě)了介紹性的傳記。見(jiàn)后文。阿諾德前面論述了這樣一種觀點(diǎn),即大部分人只需要了解科學(xué)發(fā)現(xiàn)的結(jié)果,而不需要清晰地掌握科學(xué)發(fā)現(xiàn)的“過(guò)程”,但是這樣培養(yǎng)出來(lái)的學(xué)者,只能做到了解前人的發(fā)現(xiàn),并不能如赫胥黎所說(shuō),“按照科學(xué)的方法來(lái)自由調(diào)動(dòng)理性”,從而“達(dá)到真理”[注]Thomas Henry Huxley.Collected Essays.Vol.3.Hildesheim: Georg Olims Verlag, 1970, p.152.。可見(jiàn),阿諾德的這番回答并不能令赫胥黎滿(mǎn)意。
然而要讓“過(guò)程”成為現(xiàn)代教育的主導(dǎo),這在阿諾德看來(lái)是不能接受的。他的理由如下:科學(xué)的種種發(fā)現(xiàn),從過(guò)程到結(jié)果都很“有趣”,但這種知識(shí)往往是不成體系、互無(wú)關(guān)聯(lián)的。如果只學(xué)習(xí)這種碎片化知識(shí),那無(wú)疑忽視了“人性”。人與生俱來(lái)的潛能和欲望,它不僅希望將散碎的知識(shí)在一定體系內(nèi)部結(jié)合起來(lái),更希望使那些智性層面的認(rèn)識(shí)與道德判斷和審美體驗(yàn)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⑦這種“關(guān)聯(lián)”的工作,非得由文學(xué)來(lái)承擔(dān)不可:“每個(gè)人都知道,我們渴求將所學(xué)的知識(shí)加以整合,將它們與一般規(guī)律相聯(lián)系。如果不能這樣做,而只是不斷地掌握每個(gè)知識(shí)碎片,不斷積累各種數(shù)據(jù),那是多么令人沮喪和疲倦”[注]。為了說(shuō)明這點(diǎn),他引用了柏拉圖《會(huì)飲篇》中的一段寓言,借狄?jiàn)W提瑪之口,來(lái)論述人天性中渴望“永久地占有美”,這是人的“本能”。他說(shuō):“科學(xué)結(jié)論確實(shí)很有趣,也很重要,我們所有人都應(yīng)該了解。但我想說(shuō)的是,假使我們?nèi)P(pán)接受了這些信息,我們也仍還停留在知識(shí)和智性的水平上。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依然會(huì)有一種不可遏制的愿望,想要把這些知識(shí)與道德力量和審美趣味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然而這些關(guān)聯(lián)的工作,科學(xué)是不能幫我們完成的,我們也不能指著科學(xué)去完成。”[注]R.H.Super(ed.).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Vol.10.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p.64-65.
這里阿諾德對(duì)“文學(xué)”的定義有別于“文獻(xiàn)”的含義。“文獻(xiàn)”所能給讀者的知識(shí)依然需要一個(gè)“支點(diǎn)”[注]高曉玲:《馬修·阿諾德的知識(shí)話(huà)語(yǔ)》,載《國(guó)外文學(xué)》,2013(3)。來(lái)將其與我們的倫理生活關(guān)聯(lián),而這種“關(guān)聯(lián)”又必須由“文學(xué)”來(lái)完成,這個(gè)語(yǔ)境下的文學(xué)顯然承擔(dān)了人類(lèi)想象力的任務(wù),那么一切能夠啟發(fā)想象力的作品都可稱(chēng)之為文學(xué)。阿諾德之所以強(qiáng)調(diào)想象力,是因?yàn)樗⒉粷M(mǎn)足于科學(xué)提供給我們的智性能力,而是追求道德、審美層次的真理。他們二人之所以產(chǎn)生分歧,根本在于他們對(duì)“知識(shí)”和“真理”的理解不盡相同。赫胥黎所謂的知識(shí),正是他強(qiáng)調(diào)的關(guān)于“事物”的認(rèn)識(shí),是人類(lèi)通過(guò)理性的方法,對(duì)客觀世界的一種了解和掌握。了解了這樣的知識(shí),在赫胥黎看來(lái),就能夠通達(dá)真理,促進(jìn)人類(lèi)的進(jìn)步。而阿諾德認(rèn)為真理有著更為豐富的內(nèi)涵,它不僅包括對(duì)于客觀“事物”的認(rèn)識(shí),也包含對(duì)于道德秩序的訴求,包含對(duì)“美”的欣賞和對(duì)復(fù)雜而深刻的人性的洞察。這一系列涉及人類(lèi)主觀體驗(yàn)的認(rèn)知活動(dòng),僅靠自然科學(xué)知識(shí)是無(wú)法完成的。
三、文學(xué)想象力 —— 希臘精神與希伯來(lái)精神的相遇
阿諾德關(guān)于文學(xué)內(nèi)涵的討論,必須放在他整個(gè)文化批評(píng)中考察。在《文化與無(wú)政府狀態(tài)》一書(shū)中,阿諾德指出“文化”就是“對(duì)完美的追求”,并且“文化心目中的完美,不可能是獨(dú)善其身。個(gè)人必須攜帶他人共同走向完美,必須堅(jiān)持不懈、竭其所能,使奔向完美的隊(duì)伍不斷發(fā)展壯大,如若不這樣做,他自身必將發(fā)育不良,疲軟無(wú)力”。人類(lèi)要想接近這樣的完美狀態(tài),就必須努力獲取“美好”與“光明”,“讓美好與光明蔚然成風(fēng)”。[注]“美好”偏重道德風(fēng)尚的培養(yǎng),而“光明”則象征著那種不帶偏見(jiàn),一心想要探究事物本來(lái)面目的愿望。為何思考力與行動(dòng)力,或這本書(shū)中所談的希臘精神與希伯來(lái)精神,這二者必須結(jié)合才能接近完美?阿諾德認(rèn)為這是由于人性復(fù)雜,有著多重的需求:
假如人性不是那樣一種復(fù)合體,假如人性只有道德這一面,只有可謂道德的一組本能,或者說(shuō)人性中以道德表現(xiàn)最為突出,壓倒了其他——假如是這樣的情形,我們無(wú)疑可以說(shuō),《圣經(jīng)》與人的全部需要一樣寬大深厚。然而人性還有一個(gè)方面,而且是很顯著的一面,那就是智性,以及可稱(chēng)為智力的一組本能和力量。[注]
對(duì)于智性與道德,阿諾德希望“充分地估量?jī)烧撸怪_(dá)到和諧”[注]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wú)政府狀態(tài)》,11-33、113-115、115-117頁(yè),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2。。然而在《文化與無(wú)政府狀態(tài)》中,阿諾德倡導(dǎo)的是希臘精神,他的討論主要針對(duì)的是英國(guó)各階級(jí)中那些注重實(shí)利,埋頭苦干而不關(guān)心所走的道路正確與否的人,以及那些受清教思想影響、只知道謹(jǐn)小慎微地拯救自己靈魂、而不愿動(dòng)用自己全部的心智去探究周遭事物的人,因此他通過(guò)宣揚(yáng)注重“意識(shí)的自發(fā)性”(spontaneity of consciousness)的希臘精神來(lái)糾正英國(guó)思想領(lǐng)域?qū)Α皣?yán)正的良知”(strictness of conscience)的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這是阿諾德文化批評(píng)第一時(shí)期的代表。那個(gè)時(shí)期出現(xiàn)的一些關(guān)鍵詞匯如:“批評(píng)”(criticism)、“好奇心”(curiosity)、“思維的自由”(free play of the mind)等,都強(qiáng)調(diào)人運(yùn)用自身的創(chuàng)造力和理解力,去盡力探究外部環(huán)境和人類(lèi)歷史,并且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應(yīng)成為這些思想?yún)R聚和碰撞的載體。不難看出,這樣的一種“現(xiàn)代精神”與赫胥黎所提倡的科學(xué)態(tài)度是不謀而合的,兩人都提倡摒棄偏見(jiàn)和迷信,用盡可能理性客觀的態(tài)度審視這個(gè)世界。然而阿諾德的思想在他進(jìn)行宗教和圣經(jīng)批評(píng)時(shí)期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此時(shí)期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人的道德培育,認(rèn)為圣經(jīng)首先是關(guān)于人類(lèi)倫理道德的經(jīng)典,是詮釋和彰顯正義的典范,此時(shí)期可以稱(chēng)之為他的“希伯來(lái)時(shí)期”。[注]Joseph Carroll.The Cultural Theory of Matthew Arnol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92-93.
1882年的《文學(xué)與科學(xué)》中提出的關(guān)于文學(xué)的功用,是阿諾德文化批評(píng)中出現(xiàn)的兩個(gè)傾向——希臘精神和希伯來(lái)精神——的一次整合。既然文學(xué)能夠?qū)⒅切苑懂犞械闹R(shí)與道德力量和審美趣味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那么文學(xué)必然不完全等同于這三個(gè)范疇中的任何一個(gè)。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阿諾德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倡的文學(xué),有可能獨(dú)立于智性、道德、審美這三大范疇,又能在這些范疇中穿梭、聯(lián)絡(luò),那么它所承擔(dān)的實(shí)際是浪漫主義思想家所提到的想象力的功用。早在1853年,阿諾德就在《詩(shī)歌研究》中引用亞里士多德說(shuō)到詩(shī)歌比歷史“更加嚴(yán)肅崇高,更接近真理”,接著他又說(shuō),“最優(yōu)秀的詩(shī)歌,其內(nèi)容和形式之所以?xún)?yōu)秀,在于它們能夠很好地把握真實(shí)的和重大的道理”[注]R.H.Super(ed.).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Vol.9.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171.。在《文化與無(wú)政府狀態(tài)》中他提出,最好的文學(xué)承擔(dān)的正是“文化”的責(zé)任:“文化以美好與文明為完美的品格。在這一點(diǎn)上,文化與詩(shī)歌氣質(zhì)相同,遵守同一律令”[注]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wú)政府狀態(tài)》,18頁(yè),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2。。
文學(xué)之所以必要而且崇高,因?yàn)樗軌驇椭藗兌床斓奖瓤陀^知識(shí)更廣闊的真理。在《文學(xué)與科學(xué)》一文中,阿諾德繼續(xù)就“真理”的概念進(jìn)行界定。他所謂真理并非僅是赫胥黎說(shuō)的對(duì)世界的客觀認(rèn)識(shí),而是基于這種客觀認(rèn)識(shí),在主觀上對(duì)世界的一種理解和把握。按照經(jīng)驗(yàn)主義的設(shè)定,人們對(duì)世界的認(rèn)識(shí),基于各種感官所接收到的刺激:視覺(jué)、聽(tīng)覺(jué)、觸覺(jué)、味覺(jué)和嗅覺(jué),除此之外無(wú)法把握外部世界,甚至無(wú)法把握自身。因此,像“上帝”、“愛(ài)”、“正義”、“道德”等既不能被感知也無(wú)法科學(xué)推導(dǎo)出來(lái)的抽象概念,要么被貶低為迷信與幻象(比如休謨《人類(lèi)理解研究》的最后部分所說(shuō)),要么被庸俗化(比如在功利主義哲學(xué)中)。然而起源于德國(guó)的浪漫主義則認(rèn)為,人類(lèi)雖然無(wú)法直接感知,但可以通過(guò)直覺(jué)或想象力直接通達(dá)更高層次的認(rèn)識(shí),比如世界的本原。既然阿諾德認(rèn)為人類(lèi)既有智性需求,又有道德需求,那么他也必然需要滿(mǎn)足這些需求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文學(xué)。他對(duì)文學(xué)的討論繼承了浪漫主義傳統(tǒng)中對(duì)于“想象力”作為一種思維能力的探討。從浪漫主義在英國(guó)的開(kāi)端柯?tīng)柭芍魏腿A茲華斯,到浪漫主義詩(shī)學(xué)的倡導(dǎo)者雪萊,從維多利亞前期既秉持著德國(guó)理想主義的理念、又敏銳地意識(shí)到“勞作”對(duì)于當(dāng)代社會(huì)的重要意義的卡萊爾,到維多利亞中后期道德感極強(qiáng)的美學(xué)批評(píng)家羅斯金,他們都曾對(duì)“想象力”做出過(guò)論述,并且從不同層面討論過(guò)想象力作為一種人的認(rèn)知手段,有一種整合、轉(zhuǎn)化、乃至創(chuàng)造的能力,是人內(nèi)心直覺(jué)與外界感官刺激之間的一種媒介。阿諾德所說(shuō)的文學(xué)具有的“關(guān)聯(lián)”能力,與這些論述是一脈相承的。
阿諾德的詩(shī)學(xué)觀念受華茲華斯影響最大。華茲華斯在1802年版本的《抒情歌謠集》序言中說(shuō)道,“詩(shī)”的反義詞并非“散文”,而是“科學(xué)”。因此華氏下面對(duì)于“詩(shī)”的論述應(yīng)適用于一切訴諸想象力的作品。對(duì)于何為詩(shī)人這一問(wèn)題,他這樣回答:“詩(shī)人的對(duì)象是全人類(lèi)。他有著比常人更為敏銳的感受力,更為熱情和細(xì)膩,比一般人更懂得普遍的人性;他還有更為寬廣的靈魂,他為自己所擁有的情感和意志力感到欣喜,也為自己的生命力感到喜悅。一切宇宙中存在的事物,他都能從其中感受到相似的情感和意志力;如果他無(wú)法直接感受,他就會(huì)去創(chuàng)造這情感與意志力”。他指出,想象力能夠不通過(guò)真實(shí)事件、而僅通過(guò)語(yǔ)言文字來(lái)調(diào)動(dòng)讀者的深層情感。正像阿諾德回答赫胥黎有關(guān)文學(xué)是否只能起到修飾生活的作用,華茲華斯也警惕著詩(shī)歌會(huì)淪為玩弄語(yǔ)言的借口:“有人會(huì)說(shuō),詩(shī)歌乃是詩(shī)人自己并不真懂的話(huà),詩(shī)人寫(xiě)詩(shī)無(wú)非就是一種娛樂(lè),他們所在乎的,無(wú)非是一種‘品味’。”對(duì)于這樣的問(wèn)責(zé),華茲華斯回應(yīng),“詩(shī)歌的目標(biāo)是傳達(dá)真理,不是單個(gè)、具體的,而是普遍的,真正產(chǎn)生影響的真理;它們不依靠外界的證據(jù),而是被情感帶入人們的心靈”[注]。
這顯然為后來(lái)阿諾德所持詩(shī)歌作為一種對(duì)生活的批評(píng)的論點(diǎn)埋下了種子。而華茲華斯對(duì)于詩(shī)人與科學(xué)家職責(zé)與才能的區(qū)分,更成為阿諾德80年后論述文學(xué)與科學(xué)之間有機(jī)聯(lián)系奠定了基礎(chǔ)。華茲華斯認(rèn)為科學(xué)家尋求的是客觀、有距離感的真理,而詩(shī)人所表達(dá)的適用于全人類(lèi),他讓真理變成了時(shí)時(shí)與我們相伴的朋友:
詩(shī)人是人性的基石和守護(hù)者……而詩(shī)歌則是一切知識(shí)的起源和終結(jié),它像人心一樣永恒。如果科學(xué)家的成果有一天會(huì)改變我們的生活狀態(tài)……那么詩(shī)人也決不會(huì)袖手旁觀,而是會(huì)追隨著科學(xué)的腳步,將鮮活的生命力注入科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中……如果真有一天,那個(gè)現(xiàn)在被稱(chēng)為科學(xué)的東西有了血和肉,詩(shī)人一定會(huì)借助天賜的靈感幫它完成這個(gè)變形(transfiguration),并會(huì)張開(kāi)雙臂歡迎這個(gè)變形后的科學(xué),成為人類(lèi)的重要組成部分。[注]W.J.B.Owen(ed.).Wordsworth&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1798.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65-166,166.
在華茲華斯看來(lái),詩(shī)歌可以讓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學(xué)事實(shí)與人的生活發(fā)生密切的關(guān)系,成為人類(lèi)可以感知的事物。將人的智性轉(zhuǎn)變?yōu)榍楦校瑢⒕唧w、個(gè)別的知識(shí)轉(zhuǎn)變?yōu)槠毡榈娜祟?lèi)經(jīng)驗(yàn),這種作用力正是使詩(shī)歌成其為詩(shī)的想象力。
阿諾德對(duì)于華茲華斯的推崇,有他自己所寫(xiě)批評(píng)文章《華茲華斯》為證[注]文章寫(xiě)于1879年,當(dāng)時(shí)作為阿諾德自己編訂的《華茲華斯詩(shī)集》的序言。該文在阿諾德去世后被收入《文學(xué)批評(píng)集》(Essays in Criticism)的第二集中。。然而華茲華斯的詩(shī)學(xué)觀念雖然深深影響了阿諾德,但他絕不是阿諾德理解“想象力”的唯一來(lái)源。實(shí)際上,19世紀(jì)許多詩(shī)人和評(píng)論家都將想象力看作是人類(lèi)接近“真理”——或許也可稱(chēng)“最終理念”——的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比較有代表性的還有柯?tīng)柭芍巍⒀┤R、卡萊爾和羅斯金。柯?tīng)柭芍螌?duì)于想象力的敘述散見(jiàn)于《文學(xué)生涯》中, 而比較集中的論述出現(xiàn)在第13章的結(jié)尾:
我所論之想象力,可分為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第一層次的想象力,指的是人類(lèi)洞察世界的原動(dòng)力和主要機(jī)制,是在有限的腦海中,展現(xiàn)出無(wú)限的自我意識(shí)永不停止地進(jìn)行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而第二層次的想象力是第一層次的呼應(yīng),與之同時(shí)存在于自我意識(shí)中,而不同的只是其發(fā)揮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它(指第二層次)將我們所見(jiàn)所感進(jìn)行消解、驅(qū)散,從而進(jìn)行再創(chuàng)造;即使不能再創(chuàng)造,它也能整合我們的主觀感受,使之理念化。即使我們觀察的對(duì)象是固定,甚至僵死的,它也能給它們帶來(lái)生命的活力。[注]Samuel Taylor Coleridge.Biographia Literari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04.
安格爾(James Engell)認(rèn)為,柯?tīng)柭芍嗡摗暗诙哟蔚南胂罅Α睂?shí)際是詩(shī)性的想象力,是個(gè)體內(nèi)在創(chuàng)造力的集中體現(xiàn)。因此,柯?tīng)柭芍螌?shí)際是賦予了詩(shī)歌(和其他一切藝術(shù))一種道德的感召力:“這個(gè)層次的想象力通過(guò)創(chuàng)造出新的意象和圖景,調(diào)和了人類(lèi)自我意識(shí)和外部世界的矛盾”。貝特在專(zhuān)著《柯?tīng)柭芍巍分兄赋鲞@“第二層次”實(shí)際是想象力在藝術(shù)中的自覺(jué)運(yùn)用:“通過(guò)這兩個(gè)層次,想象力實(shí)際上首先把外部的自然世界整合起來(lái),繼而投射到自我意識(shí)中去。”[注]W.Jackson Bate.Colerid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58-159.阿諾德所言文學(xué)對(duì)于科學(xué)認(rèn)識(shí)的轉(zhuǎn)化和整合,使之影響我們的道德和審美判斷,在理念上是與柯?tīng)柭芍蜗嗤ǖ摹?/p>
事實(shí)上, 將詩(shī)人提升至宗教或道德領(lǐng)袖的高度,在浪漫主義文學(xué)及社會(huì)批評(píng)中幾乎是一個(gè)慣例。雪萊在《詩(shī)辯》(ADefenseofPoetry)中區(qū)分了“故事”與“詩(shī)”:前者只是一些將分散的,支離的事實(shí)拼湊起來(lái),而后者則是按照“人性中永恒不變的法則”來(lái)進(jìn)行的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當(dāng)說(shuō)到“知識(shí)”與“詩(shī)”的聯(lián)系時(shí),雪萊說(shuō):“我們不斷地產(chǎn)生科學(xué)、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新知識(shí),多到我們不能將它們充分運(yùn)用。在這種對(duì)數(shù)據(jù)的積累和運(yùn)算的過(guò)程中,我們失去了所謂的‘詩(shī)性’……我們所缺少的是一種創(chuàng)造的動(dòng)能,來(lái)設(shè)想和想象我們已經(jīng)認(rèn)知的世界;我們?nèi)鄙僖环N將想象的理念付諸行動(dòng)的沖動(dòng);我們?nèi)鄙偕钪械摹?shī)’。”[注]想象力的作用,除了產(chǎn)生新知識(shí)外,更重要的則是“在我們的腦海中催生出一種愿望,這種愿望能按照一定的韻律和順序,把我們的知識(shí)整合起來(lái)。而這種韻律和順序,不妨叫作‘美’與‘善’”。正因?yàn)檫@樣,雪萊賦予了詩(shī)人神圣的地位:“詩(shī)人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會(huì)的創(chuàng)立者,人生百藝的發(fā)明者,他們更是導(dǎo)師,使得所謂宗教,這種對(duì)靈界神物一知半解的東西,多少接近于美與真”[注]Percy Bysshe Shelley.The Major Wor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95,696-697.。20年后,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論英雄與英雄崇拜》一書(shū)中寫(xiě)下“論詩(shī)人作為英雄”一章,重申了雪萊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我們?cè)谠?shī)人身上能看到“政治家、思想家、立法者和哲學(xué)家”的影子,而詩(shī)人向我們傳達(dá)的訊息則是“神圣的奧秘”,是普通人難以有所洞察的。[注]Thomas Carlyle.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Lincoln: Nebraska UP, 1966, pp.80-81.
四、“想象力”的解構(gòu)
文學(xué)啟迪想象力,這是阿諾德為“文學(xué)”所做的辯護(hù)。然而阿諾德必須回答,想象力的這種關(guān)聯(lián)作用是如何被文學(xué)作品完成的。阿諾德并沒(méi)有試圖用理性的“事實(shí)”來(lái)說(shuō)服讀者,而是用具體的文學(xué)作品作為例證,來(lái)調(diào)動(dòng)讀者的“想象力”,用讀者閱讀體驗(yàn)中的想象力來(lái)驗(yàn)證自己關(guān)于想象力的論述,這是阿諾德這篇文章最為高明之處。他所舉的例子之一是關(guān)于人的忍耐力:人們常說(shuō)說(shuō)“隱忍是一種美德”;而荷馬史詩(shī)中關(guān)于赫克特之死,阿波羅也說(shuō)“命運(yùn)給凡人安上了知道容讓和忍耐的心靈”[注]《伊里亞特》24卷49行。此處的上下文是,阿克琉斯殘忍地將赫克特的尸體綁在車(chē)后,圍繞著帕特羅克羅斯的墳塋拖拉奔跑。阿波羅看到此情景很生氣,認(rèn)為阿克琉斯既然已經(jīng)為好友帕特羅克羅斯報(bào)仇,就應(yīng)適可而止,給赫克特應(yīng)得的葬禮,而不應(yīng)過(guò)度沉溺于失去好友的痛苦中。此處關(guān)于希臘文的理解得益于北京大學(xué)英語(yǔ)系劉淳副教授的指點(diǎn),特此表示感謝。。阿諾德認(rèn)為,荷馬史詩(shī)是文學(xué)表達(dá),對(duì)讀者有著更為強(qiáng)烈的感染力。然而這段論說(shuō)奇特之處在于,阿諾德在本段將要結(jié)束的時(shí)候,再一次引用荷馬史詩(shī)來(lái)闡明自己關(guān)于文學(xué)的信念,他認(rèn)為文學(xué)作為一種對(duì)生活的體察,“能夠使我們堅(jiān)強(qiáng),能夠提升我們的境界,豐富我們的情感,并啟發(fā)我們的思維”[注]這個(gè)論斷也是阿諾德所一直堅(jiān)持的。在《詩(shī)歌研究》一文中他寫(xiě)道:“我們必須理解詩(shī)歌更高的作用,它能夠完成比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更重要的使命。人類(lèi)越來(lái)越會(huì)發(fā)現(xiàn),我們讀詩(shī),是因?yàn)樵?shī)歌能夠幫我們理解生活,能夠安撫我們,支撐我們”。,因?yàn)椤懊\(yùn)給凡人安上了知道容讓和忍耐的心靈”。阿諾德為何要重復(fù)這個(gè)引文?我們且看第二次引用的上下文:
荷馬對(duì)宇宙的理解恐怕是離奇、怪誕的;但是現(xiàn)代科學(xué)告訴我們,‘世界并不為人類(lèi)所控制,而人也絕非世間萬(wàn)物的中心’。當(dāng)我們聽(tīng)到這句話(huà)時(shí),我自己卻找不到比荷馬這句詩(shī)更能安慰我的話(huà)了:‘命運(yùn)給凡人安上了知道容讓和忍耐的心靈’。[注]R.H.Super(ed.).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Vol.10.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68.
再次引用時(shí),阿諾德特別利用了這句引文的含義。這一句出現(xiàn)在《伊利亞特》24卷的開(kāi)頭:赫克特死后,阿克琉斯拖著他的尸體轉(zhuǎn)了三圈,而這句話(huà)是阿克琉斯因失去好友而殘忍地對(duì)待赫克特的尸體時(shí),阿波羅對(duì)阿克琉斯的指責(zé)。他說(shuō),人類(lèi)也許還有更可怖的痛苦,比如喪子之痛,但這并沒(méi)關(guān)系,因?yàn)槊\(yùn)之神賦予了我們一顆隱忍之心。聯(lián)系史詩(shī)的語(yǔ)境,阿諾德的用意似乎清晰起來(lái):荷馬想象中的宇宙,當(dāng)然不符合當(dāng)今的科學(xué)觀念,但荷馬的詩(shī)句卻能給失去好友的阿克琉斯極大的安慰。而我們今天也在阿諾德的文章中參與了閱讀荷馬的體驗(yàn),而我們同樣也能得到極大的安慰。阿諾德在上述引文中想說(shuō)而沒(méi)說(shuō)出來(lái)的似乎是,荷馬對(duì)古代世界的理解是離奇的、怪誕的(grotesque),正如今天的詩(shī)人,他們并不能像科學(xué)家那樣對(duì)這個(gè)世界做出最客觀最科學(xué)的描述,但文學(xué)家能夠撫慰我們的心靈,這是不分古今的。阿克琉斯的處境是失去了好友帕特羅克羅斯,那我們呢?我們的痛苦正是現(xiàn)代科學(xué)關(guān)于世界起源、人類(lèi)進(jìn)化和物種關(guān)系的冷冰冰的事實(shí)。這雖不是喪子,但進(jìn)化論所揭示的人類(lèi)起源卻足以讓我們感到“喪父”。阿諾德似乎說(shuō),閱讀荷馬不但能了解古人之痛,更能彌合今人的心靈創(chuàng)傷,看來(lái)文學(xué)的功效的確不可小視。
在閱讀阿諾德的過(guò)程中,讀者也跟著他的思路閱讀了荷馬,參與了文學(xué)想象力幫助我們撫平心靈創(chuàng)傷的過(guò)程,阿諾德用文學(xué)作品本身證明了文學(xué)的作用。然而我們似乎同時(shí)覺(jué)察到一個(gè)論述的缺陷:這個(gè)引語(yǔ)起到的作用是告訴我們文學(xu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現(xiàn)代科學(xué)對(duì)我們?cè)斐傻拇驌簦⒅Z德先前所持論點(diǎn)是,文學(xué)(或想象力)可以將科學(xué)成果與道德和審美追求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消解”和“關(guān)聯(lián)”終究是不同的。這究竟是阿諾德疏忽所致,還是由于他出于無(wú)奈才把話(huà)題轉(zhuǎn)向了現(xiàn)代科學(xué)對(duì)人類(lèi)精神世界的消極影響呢?其實(shí)無(wú)論動(dòng)機(jī)如何,我們都可以在這種話(huà)題的轉(zhuǎn)移中看到,無(wú)論阿諾德從哪個(gè)角度來(lái)論述文學(xué)性思維的重要性,他都無(wú)法抵制科學(xué)話(huà)語(yǔ)勢(shì)不可擋的巨大力量,無(wú)法否認(rèn)科學(xué)發(fā)現(xiàn)和科學(xué)的思維方式正對(duì)人們的思想進(jìn)行強(qiáng)力地改造和沖擊。這也是阿諾德給我們的重要啟迪之一。
五、再論“文學(xué)”與“科學(xué)”
我們站在21世紀(jì)的歷史潮頭,如何來(lái)解讀阿諾德與赫胥黎的這次論爭(zhēng)?阿諾德論證文學(xué)的內(nèi)在必要性,主要是基于“人性”這一概念。這一傳統(tǒng)在20世紀(jì)由李維斯(F.R Leavis)所繼承。在回應(yīng)斯諾(C.P.Snow)的《兩種文化》時(shí)李維斯指出,斯諾之所以得出“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告訴我們,和其他知識(shí)分子相比,大多數(shù)科學(xué)家都是無(wú)信仰者”,以及由此得出 “大多數(shù)科學(xué)家在政治上都持左派觀點(diǎn)”這樣的結(jié)論,是因?yàn)閷?duì)歷史的簡(jiǎn)化,而這來(lái)源于斯諾對(duì)于人性的狹隘理解。[注]F.R.Leavis.Two Cultures?The Significance of C.P.Snow. London: Hatto & Windus, 1962, pp.23-24.同樣,《文學(xué)與科學(xué)》一文論證的核心也是人性的永恒。阿諾德說(shuō):“只要人性一直如此,那么人文學(xué)科就會(huì)一直保持它的吸引力”。[注]R.H.Super(ed.).The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Matthew Arnold.Vol.10.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72.然而“人性一直如此”嗎?他的論敵也許不這么認(rèn)為,而且這在他們眼中正是阿諾德論證的弱點(diǎn),因?yàn)橐院振憷杷淼目茖W(xué)主義者眼中的“人”與“人性”,并不是永恒、固定的。即使是阿諾德緊緊抓住的“本能”,如果放在達(dá)爾文的語(yǔ)境中,也是隨時(shí)處在變化當(dāng)中。達(dá)爾文的《物種起源》將“本能”定義為一切不必經(jīng)過(guò)后天習(xí)得,并且沒(méi)有任何主觀目的的行為。某個(gè)物種的本能絕不是放之四海皆準(zhǔn)的、普遍的,相反,它隨著物種所處的生長(zhǎng)階段,或它所在的地理位置緊密相關(guān),因?yàn)檫@些因素都會(huì)導(dǎo)致“本能”的變異。[注]Charles Darwin.Origin of Spe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69-171.赫胥黎作為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的積極推廣者,必然接受了達(dá)爾文關(guān)于本能進(jìn)化的學(xué)說(shuō)。既然“本能”是進(jìn)化所得,那么人性也在進(jìn)化,時(shí)刻受到人類(lèi)所處的自然、政治和經(jīng)濟(jì)生態(tài)制約。其實(shí)現(xiàn)代社會(huì)對(duì)于人性的認(rèn)識(shí),早在達(dá)爾文之前就發(fā)生了改變。羅伊·波特(Roy Porter)在分析英國(guó)啟蒙思想的著作《現(xiàn)代世界的興起》(TheCreationoftheModernWorld)中將屬于現(xiàn)代的、“科學(xué)”的人性觀念追溯至休謨。休謨認(rèn)為,人性中的各種特點(diǎn)和規(guī)律,都是可以通過(guò)科學(xué)分析認(rèn)識(shí)到的。他將洛克的經(jīng)驗(yàn)主義運(yùn)用到極致,提出了“人是何物”的問(wèn)題,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主體,休謨認(rèn)為都沒(méi)有現(xiàn)成的答案。“自我”意識(shí)建立在不斷變化的、對(duì)自我感知的基礎(chǔ)上。因此,決定人類(lèi)道德問(wèn)題的,不是“理性”(reason),而是需要充分了解人的“情感”(passions)。休謨的人性論為之后的道德哲學(xué)發(fā)展開(kāi)創(chuàng)了一個(gè)新的角度。我們不難從達(dá)爾文論述道德的一段文字中,看到休謨的影響:
因?yàn)槿祟?lèi)都渴望獲得幸福,因此對(duì)一切行為的表彰或批評(píng)都基于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即它們是否會(huì)推動(dòng)人們尋求幸福。既然幸福是人類(lèi)所有美好事物的核心,那么幸福的最大化也就間接地成為評(píng)價(jià)正義與不義的標(biāo)準(zhǔn)。[注]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393.
可見(jiàn),道德標(biāo)準(zhǔn)也不是永恒或普遍的,達(dá)爾文認(rèn)為道德和人的幸福感緊密相關(guān)。赫胥黎傳承了休謨和達(dá)爾文的衣缽[注]赫胥黎曾為休謨寫(xiě)了一本介紹性的簡(jiǎn)傳《休謨》。參見(jiàn)T.H.Huxley.Hum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09。,也吸收了他的前輩們有關(guān)人性道德方面的思想,他并不否認(rèn)道德的重要性,但他所推崇的科學(xué)教育,正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人類(lèi)社會(huì)所能達(dá)到的、物質(zhì)與精神并重的幸福感。
赫胥黎在其名作《進(jìn)化論與倫理》[注]嚴(yán)復(fù)譯作《天演論》。中,闡述了自然狀態(tài)中“物競(jìng)天擇”的自然法則,該法則也適用于人類(lèi)社會(huì)的初始階段。然而他指出,人類(lèi)社會(huì)的倫理秩序,乃是通過(guò)科學(xué)和文化知識(shí)不斷地制約自然中的競(jìng)爭(zhēng)法則。[注]也就是說(shuō),赫胥黎并不像阿諾德那樣對(duì)人性充滿(mǎn)了樂(lè)觀、浪漫的想象,也不認(rèn)為人的“天性”中自然有向善的本能。他認(rèn)為人類(lèi)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幾百萬(wàn)年前自然狀態(tài)生活中的“趨利避害”的本性,而這里的“利”和“害”是生存層面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也就是說(shuō)“利”意味著飽足、舒適,“害”意味著危險(xiǎn)、艱苦。人性中如此強(qiáng)大的自然基因,決定了人類(lèi)社會(huì)的“倫理化”進(jìn)程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學(xué)知識(shí)和人文理想一樣,承擔(dān)著引導(dǎo)人類(lèi)邁向更理想狀態(tài)的任務(wù):
在所有的家庭和政體中,人都要約束其自然屬性,或者法律和習(xí)俗來(lái)幫助人們進(jìn)行制約。人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也不斷地受到農(nóng)業(yè)、牧業(yè)、和手工業(yè)的影響。當(dāng)文明向前進(jìn)步時(shí),這種影響和制約也在不斷加深,直到高度發(fā)達(dá)的科學(xué)和人文知識(shí)使得人能夠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自然屬性。這是一種從前只有魔法師才有的控制能力。[注]
在赫胥黎的視野中,科學(xué)與人類(lèi)的道德追求非但不相抵觸,反而是互相促進(jìn)的。科學(xué)進(jìn)步的直接結(jié)果是人類(lèi)的整體道德的進(jìn)步:“天文學(xué),物理學(xué),化學(xué),這些學(xué)科都會(huì)經(jīng)歷這個(gè)(從模糊到清晰的)過(guò)程,直到它們有足夠的力量來(lái)影響人類(lèi)事務(wù)。這同樣適用于生理學(xué),心理學(xué),倫理學(xué),政治學(xué)。然而在不久的將來(lái),它們一定會(huì)帶來(lái)人類(lèi)道德行為方面(the sphere of practice)的重大變革。”[注]H.T.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London: Macmillan & Co., 1925, p.81,84-85,85.
赫胥黎認(rèn)為人類(lèi)倫理生活的進(jìn)步依靠對(duì)自然的認(rèn)識(shí),而阿諾德仍舊表露出來(lái)對(duì)科學(xué)的巨大疑問(wèn)。當(dāng)然,這絕不是說(shuō)他們二人的思想絕不相容。被浪漫主義思潮滋養(yǎng)的阿諾德在早年曾是科學(xué)教育積極的推動(dòng)者,而赫胥黎在《科學(xué)與道德》一文中也明確表示,他自己并不是徹底的唯物論者(materialist)。盡管二人有許多交集,但細(xì)讀《文學(xué)與科學(xué)》和《科學(xué)與文化》這兩篇文章,的確能夠看出二人對(duì)于追求真理(包括認(rèn)知層面和道德層面)的不同態(tài)度,而試圖揭示它們之間的某些復(fù)雜性是本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