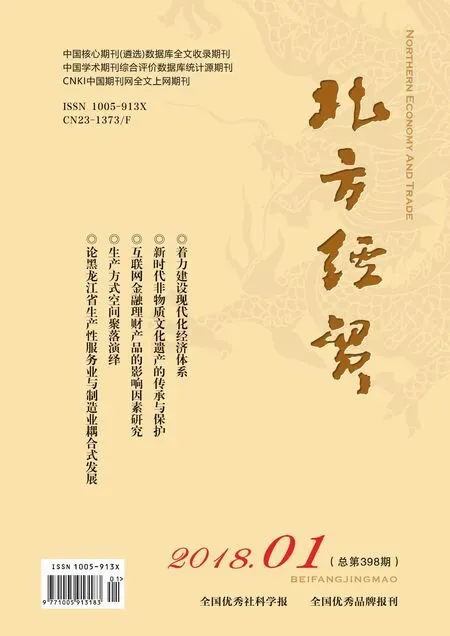共享經濟下消費者購買意愿分析
——基于協同消費理論視角
孫 博,張玉雯
(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南昌330013)
近年來,以Airbnb和Uber為代表的商業模式,拉開了一切物質和人力的、時間和空間的、有形和無形的、商業和非商業的資源進行分享的序幕,同時更宣告了共享經濟的崛起(Zervas et al,2014)。在共享經濟中,人們把私人的、企業的、機構的剩余資源、未利用資源、緊缺資源變成了社會公共物品,變成了可供的社會資源。消費者通過合作的方式,公平、有償地共享但不以擁有所有權為目的消費這一切社會物品和資源。2015年9月,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提出用分享、協作方式搞創新創業,大力發展我國的分享經濟。不同的企業開始了對不同市場的探索及開發。在此過程中消費者租賃需求與意愿對這些企業決策與生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立足于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因素的條件下,筆者推測群聚效應、閑置資源、社會認同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等因素會對購買意愿起到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因而將前者作為自變量展開研究。
一、共享經濟下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因素的理論分析
(一)文獻綜述
共享經濟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Marcus Felson)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Joe L.Spaeth)共同提出,他們以“協同消費”描述了一種新的生活消費方式。2015年蔡斯將共享經濟定義為:共享經濟是過剩產能+共享平臺+人人參與,形成嶄新的“人人共享”模式。這一新型經濟模式的優勢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Princeton’s Alan Krueger參與合寫的文章中發現Uber模式對“合伙人司機”有明顯好處,以及其為成千上百的工作者提供新的經濟機會。Fraiberger S.&A.Sundararajan(2015)則通過構建一個基于P2P耐用品租賃市場的動態模型,論證了共享經濟對不同收入階層消費者產生的福利效應。同時,共享經濟也成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條新途徑(Heinrichs,2013)。目前,共享經濟在中國剛剛興起,其怎樣在中國發展成為學者們研究的重點。趙斯惠(2015)提出O2O環境下的適合共享經濟發展的商業模式結構。王亞麗(2016)則研究了中國供給側改革和共享經濟的關系,拓展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領域。作為所研究因變量的購買意愿,目前學術界較為普遍認同其是消費心理活動的內容,是一種購買行為發生的概率,能夠用來預測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一般認為購買意愿受感知價值、感知風險、感知成本和感知利益四個方面影響。Sweency,Soutar 1&Johnson(2001)發現客戶感知價值對用戶購買意愿存在顯著的影響。高海霞(2003)則指出感知風險與購買意愿呈負向相關。在萬苑微(2011)的研究中發現購買成本對感知價值有顯著影響,感知成本與感知價值負相關,與購買意愿負相關。對于感知利益,Lee和Turban(2011)認為與消費者購買意愿呈正相關。國內外從這四個角度出發的購買意愿研究相對都已經比較成熟,因此這四個因素將被當作本研究中的控制變量進行研究。
(二)理論基礎與機制
共享經濟采用協同模式,其基礎為協同消費理論。該理論是指利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進行資源匹配,整合重構閑置資源,降低消費者購買成本,打破原有商業規則的全新商業模式。
群聚效應作為協同消費理論中的一個因素,是指某件事情的存在已達到一個足夠的力量,使它能夠自我維持,并為往后的成長提供動力的現象。群聚效應使共享平臺不斷擴大,平臺支付運營的固定成本,供給者僅需支付較小的邊際成本,即私有財產的折舊和提供服務的時間與體力,使其相比于傳統經濟下成本更低、價格更有優勢,也可達到滿足消費者自身需求的目的,從而迎新感知價值和購買意愿。協同消費的核心就是合理使用社會閑置生產力,重新分配商品的使用價值。互聯網、移動互聯的興起為共享經濟配置閑置資源的使用權提供了可能。閑置資源供給的多樣性和較傳統市場相對低廉的價格會一定程度上影響消費者的需求和購買成本。社會認同理論是協同消費的關鍵因素,是指當個體認為歸屬于某一社會組織,并以作為該社會組織成員來確定他們自己時,這種由群體定位的自我知覺在行為中便產生心理區辨效應(pspchological distinctive effects)(解天然,2016)也就是說,當消費者所在消費群體對于共享經濟產品或服務的購買認知較為一致時,消費者便產生心理區辨效應,會趨向于和群體保持一致以使自身滿意度增加,因而購買抉擇也會受到影響。在互聯網發達的背景下,共享經濟2.0的交易大多發生于線上,使得交易從人與人接觸到通過媒介完成。Casalo et al(2008)指出虛擬社區中信任關系的建立對社區的經營和發展起著積極作用。通過共享平臺信譽評價體系,人們在與市場中其他信息主體建立相互的信任,而消費者對于建立的信任程度會對其購買意愿產生影響,同時對平臺的維持產生影響。
二、共享經濟下影響消費者購買意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研究設計
本次研究主要以電子問卷形式展開調查,采取分層抽樣、便利抽樣、判斷抽樣、定額抽樣、隨機抽樣等方法獲取調查數據,共發出問卷700份,收回634份有效問卷,收回率90.57%,其基本涵蓋了從70后到00后各年齡段的被調查者;覆蓋全國25個省份。
筆者首先對數據進行信度分析,即可靠性分析,指調查統計結果的穩定性或一致性,度量通常是以相關系數即信度系數表示。對全部數據進行信度檢驗,標準化以后的信度系數為0.953,通過檢驗。對數據進行相關性檢驗,因變量的KMO值0.832,自變量為0.946,控制變量為0.923,且三者的Bartlett的球形度檢驗值均小于0.05。依據Kaiser標準,該數據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對自變量的因子分析中,得出以下結論。群聚效應在第一主因子上具有較高載荷達到0.76以上,因此,將第一主因子命名為群居效應因子。第二主因子上閑置資源的載荷是0.68以上,將其命名為閑置資源因子。第三主因子上社會認同收斂的效果好,故其命名為社會效應因子。在第四主因子上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的載荷都達到了0.79以上,將其命名為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因子。
(二)模型建立
以協同消費理論為基礎設立以下線性回歸模型:

其中,PI為消費者對于消費共享經濟產品和服務的購買意愿,i代表不同樣本,x是控制變量,ε是殘差項。解釋變量源于協同消費理論的四個維度,CM為群聚效應,IR為閑置資源,Soci為社會認同度,Trust為陌生人之間的信任。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1.描述性統計

表1 總體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列式了各個變量的總體基本統計量。各個變量均采用問卷量表均值得到。總體樣本量為634,由于量表采取的是李克特五級量表,取值區間為1-5,分別代表非常不認同、比較不認同、一般、比較認同和非常認同。各個變量的均值基本維持在3.063到3.62之間。從標準差可以看出,樣本取值波動性不大。
針對各個分組樣本的變量均值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得出以下結論:根據年齡進行分組后,80后對共享經濟產品的購買意愿較其他年齡段更高。而隨著教育水平的上升,對共享經濟產品的購買意愿也在逐漸提高。在職業分組之下,企業家的分值普遍偏低,尤其是對于共享經濟產品的購買意愿均值僅為2.55,遠低于其他職業人群,而購買意愿最高的是公務員群體,其次是企業單位群體。原本預期在校大學生將是共享經濟產品購買的主要群體,但從數值中可以看出,大學生購買意愿均值(3.08)并未顯著高于其他職業群體。從收入分組來看,購買意愿最高的群體是年收入10-15萬的人群,購買意愿最低人群是年收入5萬以下的群體,從描述性統計來看收入與購買意愿之間未體現出明顯的線性相關性。

表2 總體樣本和分組樣本線性回歸分析
2.線性回歸分析
為了驗證共享經濟產品和服務影響因素與消費者購買意愿之間的關系,筆者對總體樣本以及按照性別和年齡分組樣本進行基于White標準誤的OLS線性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呈現在表2中。首先,從總體樣本的回歸結果(表2第1列)來看,四個解釋變量對PI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并且均在1%顯著性水平之下拒絕原假設,與理論預期相符,表明協同消費理論四個因素均對共享經濟產品和服務購買意愿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中,在四個變量中,社會認同度(Soci)的系數為0.303,大于其他三個變量,表明它對于消費者購買意愿具有最高的貢獻度,系數排序為社會認同(Soci)、群聚效應(CM)、閑置資源(IR)和陌生人信任(Trust)依次遞減。在性別分組樣本中(表2第2列與第3列),四個因素的作用仍然均顯著為正,總體樣本的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其中,對于男性而言,社會認同感(Soci)對購買意愿的貢獻度大于女性(0.326>0.270),而女性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更大程度影響了其對共享經濟產品和服務的購買意愿(0.250>0.192)。
在年齡分組樣本中,群聚效應(CM)在90后和80后兩個子樣本中均顯著為正,其中,對于80后而言,群聚效應對購買意愿的貢獻度最大(0.370)。對于閑置資源(IR)而言,三個子樣本均顯著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并且對閑置資源的重視程度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遞增,表明年齡越大的群體越具有充分利用閑置資源的傾向。而陌生人傾向(Trust)對購買意愿的貢獻度卻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遞減。社會認同對三個樣本群體來說沒有顯著差異。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模型建立與實證結果驗證得出結論:消費者購買共享經濟產品和服務意愿與協同消費理論四個因素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正相關作用由強到弱排序如下:社會認同、群聚效應、閑置資源、陌生人信任。且該結論在分性別和分年齡樣本下仍保持穩健。在分性別樣本下,盡管對于男性而言社會認同度對購買意愿的作用要比女性顯著,而對于女性而言陌生人的信任則更大程度影響其購買意愿,但并不影響協同消費理論四個要素對消費者購買共享經濟產品和服務的購買意愿的作用仍然是顯著為正的;在分年齡樣本中,群聚效應在80后和90后兩個子樣本中均顯著為正,閑置資源和陌生人信任在三個樣本中均顯著為正,社會認同三個子樣本無顯著差異,總體來說協同消費理論四個要素的作用仍是顯著為正的。
中國共享經濟正處在高速發展階段,共享經濟平臺作為連接供需方的重要樞帶,是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中國的共享經濟平臺并不多,被提供用來共享的共享經濟產品或服務也是極少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共享經濟的發展。筆者認為,基于中國共享經濟發展現狀和上述結論,首先,制定政策鼓勵共享經濟平臺的發展;其次,加大共享經濟產品和服務的范圍;最后,提升共享經濟平臺的服務等級,加大開發力度。
[1] 董成惠.共享經濟:理論與現實[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6(5).
[2] 馮建英,穆維松,傅澤田.消費者的購買意愿研究綜述[J].現代管理科學,2006(11).
[3] 高海霞.消費者的感知風險及減少風險行為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3.
[4] 雷切爾·博茨曼,路·羅杰斯.共享經濟時代互聯網思維下的協同消費商業模式[J].交通與港航,2016(5).
[5] 劉 奕,夏杰長.共享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動態[J].經濟學動態,2016(4).
[6]趙斯惠.基于O2O視角的共享經濟商業模式研究[D].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5.
[7] 羅賓·蔡斯,王 芮.共享經濟:重構未來商業新模式[J].中國房地產,2015(6).
[8] 萬苑微.感知利益、感知風險和購買成本對網絡消費者購買意向影響的研究[D].廣州:華南理工大學,2011.
[9] 解天然.網絡化時代的社會認同機制研究[D].合肥:安徽大學,2016.
[10]王亞麗.供給側改革視角下的共享經濟[J].改革與戰略,2016(7).
[11]Casalo et al.Repurchase behavior in B2C ecommerce—a relationship quality perspective,2008(4).
[12]Fraiberger S.&A.Sundararajan“Peer-to-peer rental markets in the sharing economy”,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Working paper,2015(11).
[13]Heinrichs,H.,“Sharing economy:A potential new pathway to sustainability”,Gaza,2013(4).
[14]Lee,Matthew K.O.and Efraim Turban.A Trust Model for Consumer Internet Shopp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Fall,Vol.2011(6).
[15]Sweency,J.and Soutar,G.N.Consumer perceived value: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 item scale[J].Journal of Retailing,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