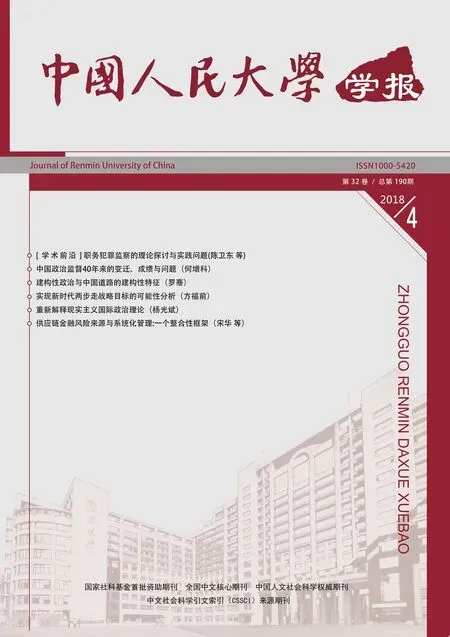職務犯罪調查與刑事訴訟法的適用
魏曉娜
自2016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吹響監察體制改革的號角,歷經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從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三省市到全國的有序推開,直到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以下簡稱《監察法》),歷時兩年多的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暫告一段落。根據中共十九大“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權限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的基本精神,《監察法》第四章圍繞監察委員會“監督”“調查”“處置”三項職責規定了“監察權限”。其中,涉及職務犯罪的各項調查措施與之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措施具有可比性,加上有官方媒體曾提出“監察委員會是實現黨和國家自我監督的政治機關,其性質和地位不同于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注]閆鳴:《監察委員會是政治機關》,載《中國紀檢監察報》,2018-03-08。,因而職務犯罪調查不適用刑事訴訟法。因此,《監察法》甫一出臺,就引起刑事訴訟法學界的格外關注。本文擬從微觀和宏觀兩個視角,將《監察法》提供的職務犯罪調查規制框架與刑事訴訟法進行對比,尋找二者的共性和差異,并在此基礎上對這種差異進行法理上的分析,然后對職務犯罪調查和刑事訴訟法的適用問題作出初步判斷。由于《監察法》施行未久,難以獲得有價值的實踐反饋,因而本文主要采用規范分析方法。
一、微觀視角:職務犯罪調查及其程序規制
《監察法》第四章規定的涉及職務犯罪的調查措施有12類,包括:談話;訊問;詢問(證人);留置;查詢、凍結(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搜查;調取、查封、扣押(財物、文件和電子數據等信息);勘驗檢查;鑒定;技術調查措施;通緝;限制出境。在《監察法》規定的12類職務犯罪調查措施中,除了談話和限制出境外,其余措施都可以在刑事訴訟法中找到對應的類似偵查手段。
例如,留置從改革前的黨內“雙規”措施[注]中央紀委1994年《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2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提供證據的義務。調查組有權按照規定程序,采取以下措施調查取證,有關組織和個人必須如實提供證據,不得拒絕和阻撓。”其中第3項規定:“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以及行政監察中的“兩指”[注]1997年《行政監察法》第20條規定:“責令有違反行政紀律嫌疑的人員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就調查事項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和解釋,但是不得對其實行拘禁或者變相拘禁。”措施轉化而來,是貫徹中共十九大報告“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基本精神的成果。其適用對象既包括涉嫌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也包括涉嫌行賄犯罪或者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對于上述兩類對象,如果監察機關已經掌握部分違法犯罪事實及證據,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且同時具備下列情形之一的,即涉及案情重大、復雜,可能逃跑、自殺,可能串供或者偽造、隱匿、毀滅證據,可能有其他妨礙調查行為的,經審批后,可以采取留置措施。[注]參見《監察法》第22條。從程序上,《監察法》要求留置措施的采取由監察機關領導人員集體研究決定,而且設區的市級以下監察機關采取留置措施,必須報上一級監察機關批準;省級監察機關采取留置措施,雖然不必經過國家監察委員會批準,但也應當向后者報備。[注]《監察法》明確限制了留置的期限,即不得超過三個月,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一次,但延長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省級以下監察機關延長留置期限時,應當報上一級監察機關批準。[注]參見《監察法》第43條。這就把留置的期限嚴格控制在六個月以內。對于被留置人的處遇,《監察法》要求保障其飲食、休息、安全和醫療服務,訊問被留置人時,要合理安排訊問時間和時長。[注]參見《監察法》第44條。被留置人員日后若被依法判處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這種省級以下監察機關采取留置措施決定權“上提一級”的處理,似乎是借鑒了檢察機關自偵案件逮捕“上提一級”的實踐。[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327條規定:“省級以下(不含省級)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報請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從刑期折抵的規定來看,《監察法》也是將留置比照刑事訴訟中的逮捕來處理。
《監察法》為上述12類職務犯罪調查措施設計了不同層次的程序性規制:其一,個別性程序規范,即針對這12類職務犯罪調查措施規定了具體的適用條件和程序階段。例如,在“談話”適用條件中沒有出現“調查過程中”或“被調查人”這樣明顯限定程序階段的表述,也沒有使用“涉嫌”一詞來限定適用對象,其措辭與其他調查措施的適用對象與適用階段都不相同。[注]《監察法》第19條規定:“對可能發生職務違法的監察對象,監察機關按照管理權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關機關、人員進行談話或者要求說明情況。”這意味著,“談話或者要求說明情況”不僅可以適用于正式立案后的被調查人,而且可以適用于正式立案前的監察對象。但除“談話”外,其他11類措施只能適用于監察立案以后。監察立案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防止過度干預被監察對象合法權益的程序性屏障。[注]安徽省合肥市紀委的微信公號“清風合肥”于2018年4月28日發布消息稱,合肥市下轄的巢湖市紀委“從談話對象處提取到一組被刪除的微信聊天記錄”,并以此為線索使談話對象心理松動,交代問題,推進了辦案工作。消息一經發出,立即引發軒然大波,引發多家媒體的批評。批評的焦點之一,就是當地紀委對僅是“談話對象”的監察對象采取侵犯“通信秘密”基本權利的技術性措施。參見《安徽巢湖1至4月處分63人:從被刪除微信記錄提線索》,http://news.sina.com.cn/c/2018-04-28/doc-ifzvpatq7269566.shtml。其二,對關鍵性調查措施的錄音錄像,即進行訊問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證工作時,應當對全過程錄音錄像,留存備查。[注]參見《監察法》第41條。其三,一般性程序要求,即采取訊問、詢問、留置、搜查、調取、查封、扣押、勘驗檢查等調查措施時,調查人員均應當出示證件,出具書面通知,由二人以上進行,形成筆錄、報告等書面材料,并由相關人員簽名、蓋章。其四,一般性的程序禁止規范:嚴禁以威脅、引誘、欺騙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證據,嚴禁侮辱、打罵、虐待、體罰或者變相體罰被調查人和涉案人員。[注]參見《監察法》第40條。最后,以總則部分設置“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原則[注]參見《監察法》第5條。統領全局。
如果以刑事訴訟中的普通刑事案件偵查權為參照,根據程序的嚴格程度或者程序對相關人員的權利保障程度[注]對于職務犯罪,調查機關行使調查權的程序要求越嚴格,對相關人員的權利保障程度就越充分,這是一體兩面。,可以把《監察法》中規定的職務犯罪調查措施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程序的嚴格程度高于刑事訴訟法的調查措施,主要包括訊問、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證措施。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21條引入了錄音錄像制度,但目前僅適用于訊問措施,而且并不做強制性要求,只有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對訊問過程錄音或者錄像才是必須的。根據《監察法》第41條的規定,全程錄音錄像不僅適用于訊問措施,而且擴大適用于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證工作,對于這些重要取證工作,全程錄音錄像不再是建議性的,而是必須履行的程序。因此,對于這些調查措施的采用,《監察法》要求的程序嚴格程度是高于刑事訴訟法的。
第二類是程序嚴格程度相當于刑事訴訟法的調查措施,大致包括詢問、查詢、凍結、勘驗檢查、鑒定、技術調查措施和通緝等措施,適用這些措施的實體條件和程序條件基本比照刑事訴訟法。需要提及的是,技術調查措施和通緝措施,監察機關只有決定權而沒有執行權,仍要交給公安機關執行,客觀上形成了決定權和執行權分離的機制。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將技術調查措施和通緝措施歸入第一類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類是權利保障程度低于刑事訴訟法的留置措施。如前所述,從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審批程序和刑期折抵等規定來看,《監察法》中的留置與刑事訴訟中的逮捕具有較高的可比性,但是,留置程序中提供的權利保障程度明顯低于逮捕程序。其一,在刑事偵查程序中,逮捕存在明確的分權結構,即公安機關提請批捕,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然后交公安機關執行。其二,執行留置和執行逮捕之后均要履行通知程序,即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執行留置的還要通知所在單位),但均設置了例外。對于逮捕的執行后通知程序來說,例外只有一種情況,即無法通知的情形。但這種情形一般不太可能出現在職務犯罪案件中,留置的執行后通知程序的例外情形被重新設計為“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等有礙調查”的情形。比起逮捕程序中被嚴格限定的例外,留置程序中的通知例外明顯寬泛得多。其三,最重要的是,留置和逮捕的性質和功能設定是完全不同的。逮捕是一種強制措施,其首要功能是保證到案。留置則是一種調查案情的手段,留置的適用條件、通知例外情形的設置遵循的都是這個設計邏輯,因此,適用留置的核心條件是調查案件的需要,而案件的嚴重程度、被調查人未來可能判處的刑罰這些在逮捕中主要考慮的因素并沒有在留置程序中受到太多的關注。[注]《監察法》第22條對留置適用條件的設置并沒有限定案件的嚴重程度。
由此可見,除留置外,《監察法》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的吸收、轉化,為大多數職務犯罪調查措施提供了與刑事訴訟法基本相當、個別情況下更嚴格的程序性規制。
二、職務犯罪調查與刑事訴訟的銜接
監察機關對監察對象進行調查后,如果得出涉嫌職務犯罪的結論,就需要移送人民檢察院,進入刑事訴訟。《監察法》從三個方面規定了職務犯罪調查與刑事訴訟的銜接問題。
(一)程序的銜接
監察機關將起訴意見書、案卷材料、證據一并移送檢察機關后,人民檢察院經審查,可以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如下處理:其一,檢察機關認為符合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條件,即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其二,檢察機關對于有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不起訴情形的,經上一級檢察機關批準,應當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其三,經審查,檢察機關認為需要補充核實的,應當退回監察機關補充調查,也可以自行補充偵查。對于補充調查的案件,應當在一個月內補充調查完畢。補充調查以二次為限。其四,在監察機關調查職務犯罪的過程中,被調查人逃匿,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的,由監察機關提請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注]參見《監察法》第47、48條。
不難看出,對于監察機關移送的涉嫌職務犯罪的案件,檢察機關審查、處理的標準與刑事訴訟法的要求完全一致,雖然在個別程序問題上與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的普通刑事案件略有差異。[注]比如,檢察機關對于監察機關移送的職務犯罪案件如果要作不起訴處理,必須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又如,監察機關不服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要求復議。而公安機關如果不服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只能先向原決定機關要求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才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參見《監察法》第47條第4款、《刑事訴訟法》第175條。這反過來又會對監察機關的調查產生影響,如果職務犯罪調查的案件未來有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可能,那么監察機關就不得不考慮檢察機關審查、處理案件的標準。因此,即使職務犯罪調查不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但后者難免對職務犯罪調查有“反射性”地滲透適用。
(二)證據材料的銜接
對于職務犯罪調查過程中收集到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的使用問題,《監察法》第33條首先表明了肯定立場,即依照《監察法》規定的程序收集的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調查人供述和辯解、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一條從形式上突破了《刑事訴訟法》第52條關于行政執法與刑事訴訟證據銜接的規定。因為《刑事訴訟法》第52條對可以直接進入刑事訴訟的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的種類是有嚴格限制的,即限于“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種類,雖然“兩高”在解釋這一條時對“等”所包含的證據種類不盡相同,但基本的共識是不包括言詞類證據。《監察法》第33條卻明確將“證人證言、被調查人供述和辯解”納入其中,這樣一來,就等于肯定職務犯罪調查過程中收集的幾乎所有證據種類,都有資格直接進入刑事訴訟,至少不會因為證據的類別而被排除在刑事訴訟程序的大門之外。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職務犯罪調查過程中收集到的所有證據材料都可以自動進入刑事訴訟。《監察法》第33條第2款從正面提出了進入刑事訴訟的條件,即“監察機關在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時,應當與刑事審判關于證據的要求和標準相一致”。第3款接著規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案件處置的依據。”第2款和第3款相結合,一個是從正面的程序的角度對證據的收集提出要求,另一個是從反面的證據排除規則的角度加以規制,其效果不僅是將刑事訴訟中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的要求和標準運用于職務犯罪調查,而且也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延伸適用于職務犯罪調查。既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適用于職務犯罪調查,未來法院也可以基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排除監察機關收集的證據,那么法院采取的“非法證據”的標準必然會“反射性”地對監察機關的取證活動產生影響,只要監察機關調查職務犯罪案件存在進入刑事訴訟的可能,它就不能不考慮法院采納證據的標準,尤其是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大背景下,這種趨勢只會越來越強化。
(三)人身控制的銜接
從職務犯罪調查到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還有一個問題是對犯罪嫌疑人人身的控制,尤其是在監察機關已經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留置措施的情況下,進入刑事訴訟后如何銜接的問題。對此,《監察法》第47條規定得比較籠統:“對監察機關移送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對被調查人采取強制措施。”2018年5月10日,全國人大公布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十二條(擬增加一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第170條)對此作出具體規定:“對于監察機關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動解除。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內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決定。在特殊情況下,決定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對于被采取留置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根據目前《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的設計,在進入刑事訴訟后,先由檢察機關采取拘留措施作為銜接和過渡,然后再利用拘留的10天(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到14天)期間作出進一步的處理,根據審查的具體情況決定逮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通過上述程序、證據、強制措施三個方面的銜接[注]實際上還有涉案財物的銜接,《監察法》第46條規定:“監察機關經調查,對涉嫌犯罪取得的財物,應當隨案移送人民檢察院。”,立法者希望實現從職務犯罪調查到刑事訴訟程序的平穩過渡。根據上文的分析,在程序的銜接上,檢察機關對于監察機關移送的涉嫌職務犯罪的案件,審查、處理的標準與刑事訴訟法完全一致;在證據的銜接上,職務犯罪調查要遵守刑事訴訟中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的要求和標準,而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延伸適用于職務犯罪調查。所以,在程序和證據這兩個方面,通過刑事訴訟法的“反射性”作用,職務犯罪調查和刑事訴訟程序基本可以做到“無縫對接”。但是,在人身控制方面,刑事訴訟法卻無法通過這種反射機制發揮影響,這使留置成為一塊完全不受刑事訴訟法影響、滲透的“飛地”。
三、聚焦留置:適用還是不適用刑事訴訟法?
通過以上兩部分的分析,大致可以作出一個判斷:監察機關有權實施的絕大部分職務犯罪調查措施,雖然不直接適用刑事訴訟法,但其程序嚴格程度或者權利保障程度與刑事訴訟法基本相當。這樣的效果是通過兩個途徑實現的:一是《監察法》直接吸收了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將刑事訴訟法的程序要求轉化為《監察法》的要求;二是通過職務犯罪調查與刑事訴訟的銜接機制,使刑事訴訟法在程序、證據方面的要求和標準“反射性”地對監察機關的職務犯罪調查發揮作用,從而使職務犯罪調查的標準與刑事偵查的標準趨于同一。然而,這一判斷有一個例外,這就是留置。
(一)留置性質的再審視
職務犯罪調查過程中的留置措施該不該適用刑事訴訟法的標準?有論者從留置權行使主體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監察委員會是實現黨和國家自我監督的政治機關,不是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其依法行使的監察權,不是行政監察、反貪反瀆、預防腐敗職能的簡單疊加,而是在注重監督的基礎上,既調查職務違法行為,又調查職務犯罪行為,其職能權限與司法機關、執法部門明顯不同。”[注]鐘紀軒:《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載《求是》,2018(9)。在這樣一種論證邏輯下,答案似乎很明確了。但是,對于留置該不該適用刑事訴訟法的問題,其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另一個前提性問題:留置應當如何定性?這一問題對于其他問題的討論具有基礎性意義。比如,如果把留置定性為一種調查措施,那么留置的條件和程序設置就必須服從調查的邏輯、為調查的順利開展服務。
關于留置的性質,目前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其一,留置是“雙規”的替代物。這一定性的主要根據是中共十九大報告“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的表述。從這個角度看,留置的出現意味著“雙規”的消失,無論目前的它是多么不完美,但一項以往在法治視野之外運作的權力現在開始走入法治的視野,僅此一點就是中國法治的一大步。即便個別部門法治出現了暫時性倒退,也不能埋沒其積極意義。其二,留置是監察機關在調查嚴重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過程中采用的調查措施,其主要法律依據是《監察法》第41條“調查人員采取訊問、詢問、留置、搜查、調取、查封、扣押、勘驗檢查等調查措施”的規定。從《監察法》對留置條件的設置來看,“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可能有其他妨礙調查行為”之類的表述恰恰反映了調查的邏輯和需要。其三,留置是刑事訴訟中強制措施的對應物,類似于逮捕。其主要法律依據有三:一是前述《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十二條關于留置與刑事訴訟強制措施銜接的規定;二是《監察法》中規定的留置的審批程序借鑒改革之前檢察機關自偵案件逮捕“上提一級”的做法;三是留置比照逮捕折抵刑期的處理。
然而,目前關于留置性質的幾種觀點都存在嚴重的視角問題。也就是說,上述幾種對于留置性質的界定,均著眼于大體相似的觀察視角,即立足于公權力之運作,其基本立場是權力本位的。這一觀察視角的主要問題在于,它無視中國社會治理方式在過去40年間所發生的重要變化。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的治理大體經歷了政治治理模式[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尚未建立之時,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首先是解構舊的體制和社會關系,而這主要是通過大規模政治動員的方式完成的。例如,為了鞏固新生的政權,打擊各種敵對勢力,中共中央發起了“鎮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行政治理模式[注]在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基本穩固、新的生產關系的基礎初步建立之后,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已經從變革舊體制轉變為維持并改進現行體制。相應地,社會治理方式也在發生轉型,除“文化大革命”特殊時期,大規模的政治動員日益少見,行政治理的功能逐漸凸顯。在政治治理模式下,政府通過政治動員把自身和社會的支持力量結合在一起,而在行政治理模式下,政府和社會力量相對地分離,以相對獨立的方式對社會加以管理。這種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要通過行政手段實現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社會各階層成為被管理和行政的對象,行政手段成為社會控制、實現國家各項政策目標的最主要手段。參見鄭永年:《中國模式》,24-25頁,杭州,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并逐漸向法治治理模式轉型的過程。政治治理模式和行政治理模式的共同特點是權力集中。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個副產品。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一個如影隨形的威脅是民族生存問題。在極端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凝聚個體的力量以保證國家、民族的生存無疑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其結果是國家和集體的力量受到了格外的強調,國家的話語、集體的話語輕易地超越了個體的權利話語。所以,從價值取向上,政治治理模式和行政治理模式都是國家本位、集體本位的,同時也是權力本位的。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啟動了經濟體制改革。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經濟關系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具有根本性,可能引發政治法律制度、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連鎖效應。在現實層面,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民主化、法治化日漸成為中國政治實踐的主題。自中共十五大以來,“依法治國”成為基本的治國方略,“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入黨的文件,這標志著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開始發生重大轉變。此后,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一系列正式文件開始頻繁出現“依法治國”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表述。這一政治動向很快反映于國家立法。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憲法中正式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在憲法中增加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2012年3月,經過激烈討論,“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最終寫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更是史無前例地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主題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的部署。這些動向釋放出了強烈的信號:中國正在實現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中國社會也即將從以往的政治治理模式、行政治理模式轉向法治治理模式。
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留置性質的界定,需要改變以往政治治理模式、行政治理模式下權力本位的思維慣性,轉而采取一種與法治治理模式相適應的權利本位視角加以重新審視。如果立足權利本位,不難看出,留置的實質在于限制、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它所干預的是《憲法》第37條保障的人身自由權,是一種干預公民憲法權利(基本權)的行為。[注]類似的觀點參見陳衛東:《職務犯罪監察調查程序若干問題研究》,載《政治與法律》,2018(1)。因此,職務犯罪調查是否適用刑事訴訟法,并不取決于權力行使主體即監察委員會的性質,甚至職務犯罪調查是否適用刑事訴訟法這一問題本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留置的屬性如何界定,當前的法律體系是否提供了與其屬性相匹配的程序性保障。
(二)基于留置性質的制度標準
留置的性質,決定了它應當依據什么樣的原則構建、應當提供什么樣的程序保障和救濟管道。人身自由是人類最古老的基本權利之一,同時,剝奪人身自由長期以來也被國家當作打擊違法犯罪和維護社會安全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與人格尊嚴、肢體完整等權利不同,人身自由權并非絕對不可干預,法治社會所要提供的僅僅是一種程序性保障。法治社會所否定的不是剝奪自由本身,而是“非法的”和“任意的”剝奪。為此,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關規定以及我國的立法法,一項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措施應當符合以下標準:
其一,法律保留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是公法上的基礎性原則,19世紀末為德國學者奧托·梅耶首創,意指一些特定的事項必須由法律予以規定,行政行為若無法律依據,不得為之。“法律保留”之主旨在于維持法律規范的效力,避免行政行為侵犯立法機關之權限,同時也防范立法機關怠于行使職權,放任行政機關之作為。[注]吳萬得:《論德國法律保留原則的要義》,載《政法論壇》,2000(4)。法律保留原則在我國立法中也有明確的要求。《立法法》第8條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隨著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監察法》,法律保留的問題基本解決。法律保留原則所防范的,不僅是對人身自由“非法的”剝奪,也包括“任意的”剝奪。為此,法律應該明確規定留置的具體適用對象、適用條件和程序,一方面是為公權力的行使劃定清晰的邊界,防范權力濫用;另一方面也提供可預測性,使得被調查人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
其二,比例原則。比例原則被譽為公法領域的“皇冠原則”,既適用于立法,也適用于司法,其基本要求是國家采取的剝奪或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措施必須與所調查行為的性質和嚴重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說,較高強度的剝奪、限制基本權利的措施只能適用于對較嚴重行為的調查,對較輕的違法犯罪行為只能適用較輕程度的剝奪、限制措施。如果較低強度的限制措施可以達到法律目的,就沒有必要采用較高強度的限制措施。[注]德國學者將比例原則又細分為三個具體的原則:“(1)妥當性,即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實現所追求的目的;(2)必要性,即除采取的措施之外,沒有其他給關系人或公眾造成更少損害的適當措施;(3)相稱性,即采取的必要措施與其追求的結果之間并非不成比例(狹義的比例性)。”參見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238-239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從比例原則出發,會發現目前留置條件的設置還存在較大的改進空間。從后果上看,留置是一種可以長達6個月的較為嚴重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而從《監察法》設置的適用條件看,不僅可以適用于涉嫌“職務犯罪”的嫌疑人,還可以適用于涉嫌“嚴重職務違法”的嫌疑人,并未如刑事訴訟中的逮捕一樣僅適用于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較為嚴重的案件,這與留置帶來的剝奪人身自由的嚴重后果相比是不成比例的。除留置外,《監察法》也沒有設置其他可以替代留置的、程度較輕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因而也無從落實必要性原則。
其三,法官保留原則。法官保留原則是指將特定的公法上事項保留由法官行使,并且也是僅法官始能行使的原則。[注]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78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至于何等公權力事項需要保留由法官行使,也即在法官保留原則的適用邊界問題上,各國存在差異,但干預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措施應保留給法官裁決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共識。中國1998年已經簽署、尚未批準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對此項原則也有反映。該條第3款規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見法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員。”同條第4款規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釋放。”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一般評論(General Comments),第3款的要求僅適用于涉嫌刑事犯罪的場合,而第4款由法庭審查剝奪人身自由是否合法性的要求更為絕對,適用于所有情形,無論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注]曼弗雷德·諾瓦克:《民權公約評注》,175、17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留置作為職務犯罪調查過程中使用的一種剝奪人身自由的措施,顯然是具備公約第9條第3款和第4款的適用前提的,但目前留置的決定和延長完全由監察機關決定,而“監察委員會是實現黨和國家自我監督的政治機關,不是……司法機關”[注]鐘紀軒:《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載《求是》,2018(9)。,這與上述兩款的要求有著明顯的差距。
所以,留置基于其剝奪人身自由的屬性,應當具備上述原則施加的制度要求,至于其是否適用刑事訴訟法,則并不是問題的關鍵。畢竟上述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有的已經得到較好的貫徹,比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比例原則,有的迄今尚未落實或者頗具爭議,比如法官保留原則。
四、宏觀視角:職務犯罪調查的結構
監察委員會依憲依法成立后,無論是將其性質界定為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還是政治機關,它所行使的是國家公權力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監察委員會行使國家公權力,尤其是采取職務犯罪調查措施,干預了公民基本權利,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經典政治哲學告訴我們:“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5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現代國家對權力的控制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實現:一是制約,二是監督。中共十九大報告也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為了監察權的健康良性運行,需要引入一定的監督、制約機制,優化職務犯罪調查的宏觀結構。
立法者并非沒有意識到監察權力同樣需要規范行使,《監察法》第七章以專章規定了“對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的監督”,從監督的主體和來源上看,主要包括權力機關的監督、民主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又通過登記備案、回避、申訴、責任追究等方式和機制強化內部監督。然而,總體來看,第七章構建的監督體系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除了權力機關監督外[注]《監察法》第53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聽取和審議本級監察委員會的專項工作報告,組織執法檢查。縣級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舉行會議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或者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就監察工作中的有關問題提出詢問或者質詢。”,其余的外部監督主體均缺乏制度化的參與管道,而且不專業,這樣的外部監督注定是無力的。二是過于倚重內部監督,第七章構建的幾種具體化的監督機制均屬內部監督。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即開放性不足,缺乏切實可行的外部監督制約機制。當然,職務犯罪調查作為收集證據的關鍵階段,以保密為原則無可厚非,然而,若完全排除外部的監督制約,職務犯罪調查的權力運行結構就會出現問題。因此,為了保障監察權的健康良性運作,有必要在保證職務犯罪調查順利進行的前提下實現程序的有限、有序開放。這種有限、有序開放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實現:
(一)檢察監督
《憲法》第12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均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受其監督,由此形成與西方三權分立制度截然不同的一元權力架構。這種權力架構的弱點是缺乏有力的制約機制,為了防止權力腐敗和濫用,就必須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下設立專司法律監督職能的機關。[注]朱孝清:《中國檢察制度的幾個問題》,載《中國法學》,2007(2)。這個專司法律監督的機關就是人民檢察院。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推進,“依法治國”“尊重和保障人權”先后入憲,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范圍幾乎覆蓋了所有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實施領域,不僅包括三大訴訟法[注]除刑事訴訟法外,民事訴訟法經2007年、2012年兩次修正后,涉及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條文擴展為7個(第14、208、209、210、212、213、235條)。行政訴訟法2014年修正后,有3個條文涉及檢察監督(第11、93、101條)。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修改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決定,增加了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規定,豐富和發展了檢察監督的方式和范圍。根據該決定,《民事訴訟法》第55條增加一款,作為第2款:“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在沒有前款規定的機關和組織或者前款規定的機關和組織不提起訴訟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前款規定的機關或者組織提起訴訟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支持起訴。”同時,《行政訴訟法》第25條增加一款,作為第4款:“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還覆蓋了行政執法領域[注]在行政執法領域,例如,《人民警察法》第42條規定:“人民警察執行職務,依法接受人民檢察院和行政監察機關的監督。”《治安管理處罰法》第114條第2款規定:“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辦理治安案件,不嚴格執法或者有違法違紀行為的,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權向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行政監察機關檢舉、控告;收到檢舉、控告的機關,應當依據職責及時處理。”,甚至延伸到立法領域。[注]在立法領域,2015年修正的《立法法》第99條第1款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根據2006年《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第32條的規定,如果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同法律規定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送有關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根據國務院頒布、2002年開始施行的《規章制定程序條例》第35條和《法規規章備案條例》第9條的規定,如果檢察機關認為規章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或者地方性法規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或者國務院各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發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政決定、命令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可以向國務院書面提出審查的建議,由國務院法制機構研究后按照規定的程序處理”。而綜觀《監察法》全文,在一部授權以多種調查措施干預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中,并未設置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條文,這使職務犯罪調查成為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盲區。值得注意的是,《監察法》第60條構建的申訴機制[注]《監察法》第60條規定:“監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被調查人及其近親屬有權向該機關申訴:(一)留置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解除的;(二)查封、扣押、凍結與案件無關的財物的;(三)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措施而不解除的;(四)貪污、挪用、私分、調換以及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五)其他違反法律法規、侵害被調查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受理申訴的監察機關應當在受理申訴之日起一個月內作出處理決定。申訴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處理決定之日起一個月內向上一級監察機關申請復查,上一級監察機關應當在收到復查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作出處理決定,情況屬實的,及時予以糾正。”明顯借鑒了《刑事訴訟法》第115條的規定,然而卻有意地排除了檢察機關的外部監督,使得申訴機制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內部監督機制。這種對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系統性排除,不僅與檢察機關“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發生沖突,也不利于監察權的健康良性運行。
(二)律師介入
職務犯罪調查與普通刑事案件的偵查相比,有一些技術性特征。例如,普通刑事案件的偵查思路往往是從“案”到“人”,而職務犯罪案件發生后,無“現場”(至少對于調查人員而言現場已不復存在)、無被害人,其偵查思路往往是從“人”到“案”,所以職務犯罪調查更為倚重口供,也更依賴于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控制,這也是留置被《監察法》設定為調查措施的根本原因。但是,越是這種“近身”調查(例如訊問),而且越是封閉的“近身”調查,風險就越大。
在普通刑事案件偵查中,如果偵查人員對口供過于偏愛,也會產生類似的問題。為了杜絕這種傾向產生的風險,現行刑事訴訟法多管齊下,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檢察監督外,還引入一系列的程序規則予以防范,例如,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作為證據收集的一般原則,要求拘留、逮捕后及時送看守所,要求拘留、逮捕后的訊問在看守所進行,等等。[注]參見《刑事訴訟法》第50、83、91、116條。尤其是經過兩次立法修正,現行刑事訴訟法從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就允許辯護律師介入偵查。上述防范風險的措施,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外,在《監察法》提供的職務犯罪調查框架中,基本上都是缺失的。目前的職務犯罪調查,不僅缺乏有力的外部監督和制約,而且還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程序,這是一個重大的結構性缺陷。
但是,這一結構性缺陷可以通過一種成本較低的方式彌補,即可以參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犯罪嫌疑人被監察委員會“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允許辯護律師介入職務犯罪調查程序。“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的時間設定,既充分照顧到偵查犯罪的需要,又為封閉的偵查程序打開一個有限的窗口,由專業的、有組織紀律和職業倫理約束的辯護律師介入,有助于防范執法風險,保證職務犯罪調查活動不至于跑偏。參考比較立法例,在設置專門反腐機構的國家或地區,從犯罪嫌疑人被拘捕開始,無一例外地都允許辯護律師介入。[注]在香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第10A條關于逮捕后的程序規定,被拘捕人士從被拘捕開始即可要求通知、會見律師,在律師出現之前可以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即在拘捕時律師即可介入整個案件。在新加坡等地反貪專門機構的偵查權同時受專門法律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制,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并不因反貪而缺位。參見熊秋紅:《監察體制改革中職務犯罪偵查權比較研究》,載《環球法律評論》,2017(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監察法》第31條還引入了目前仍在試點、即將通過修正案的進入刑事訴訟法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眾所周知,保證認罪認罰的“自愿性”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生命線”,也是該制度立足的根本。為了保證認罪的“自愿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第5條明確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法律幫助的權利,并要求辦案機關承擔起相應的保障義務,要求法律援助機構根據人民法院、看守所實際工作的需要,通過多種形式提供法律幫助。[注]《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第5條規定:“對于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機關,賦予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法律幫助的義務,并要求法律援助機構根據人民法院、看守所實際工作需要,通過設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駐值班律師、及時安排值班律師等形式提供法律幫助。人民法院、看守所應當為值班律師開展工作提供便利工作場所和必要辦公設施,簡化會見程序,保障值班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沒有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值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法律幫助。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符合應當通知辯護條件的,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在一個封閉的、缺乏任何外部監督制約環境下取得的口供,無法保證其自愿性,也使得職務犯罪調查階段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踐陷入“合法性”困境。
《監察法》的出臺和監察委員會的成立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從反腐的有效性來看,監察委員會整合了多重反腐力量、反腐力量更集中、獨立性更強、政治地位更高,可以期待在反腐方面會有更大的作為。從推進依法治國角度來看,《監察法》的出臺,以留置取代“兩規”,使得以往很大程度上在幕后運作的反腐運動走上前臺,進入國家立法,成為嚴格在法律規范下進行的活動,也成為大眾評判、社會監督的對象,這本身就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一大步。因此,我們應該抱以足夠的耐心,客觀看待這一新生事物暫時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畢竟依法治國的巨輪已經啟航,所有零部件都將調整、磨合自己來適應、咬合這座巨輪的動力系統,推動巨輪安全駛向未來。同時,立法者也應當保持開放的心態,傾聽各方面的聲音,使新生的監察制度走上良性健康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