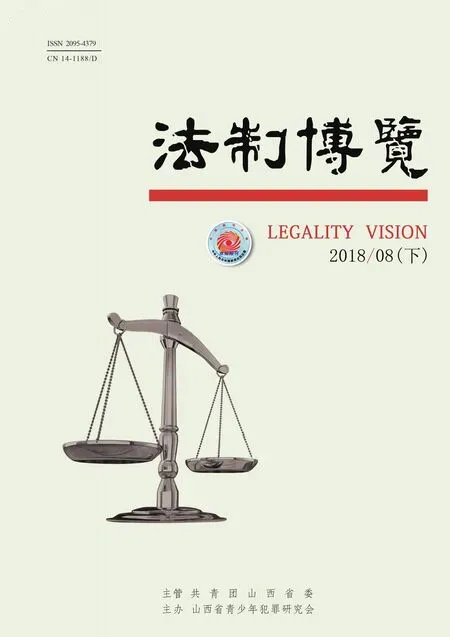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機制研究
紀澤東
1.北方民族大學法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2.寧夏工商聯,寧夏 銀川 750001
調解,古來有之,不僅用來解決國內民商事糾紛,也被用于解決涉外經濟案件。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外交檔案記載:光緒三十年(1904)公記茶棧李雨亭被控拖欠俄商阜昌行借款及擔保借款,福防廳受理該案之后,“飭據福防同知呂渭英事同兩造齊到南臺商會,經會董多人委婉調停,勸令阜昌行買辦劉世逸體念李雨亭虧累為難,所欠茶銀核計減讓”。[1]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步入新時代,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深度和廣度也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此同時,中國企業與境外企業的經濟糾紛也將步入增長期和多發期,如何更好的化解經濟貿易糾紛,確保“一帶一路”倡議順利實施,需要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間的經濟貿易,是“一帶一路”經濟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企業與阿拉伯國家企業之間的經濟貿易糾紛解決機制也同樣是“一帶一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商事調解機制,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豐富、完善我國涉外商事糾紛解決的途徑、方法。
一、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的性質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商事調解,是我國涉外商事調解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第二條對人民調解的定義,涉外商事調解可以定義為:當分屬不同經濟體的商事主體之間發生商事糾紛時,根據任意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的請求,商事調解組織在當事人全部同意的情況下,在當事人平等協商的基礎上自愿的達成調解協議,解決其商事貿易糾紛的活動。它具有以下特征:⑴涉外性或者外部性。根據商事糾紛主體是否屬于同一個經濟體,將商事糾紛劃分為內部商事糾紛和涉外商事糾紛。因歷史等原因,我國領土范圍內,存在著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四個經濟體,我國涉外商事調解主要解決的商事糾紛是中國大陸地區的商事主體與港澳臺以外的其他經濟體的商事主體之間產生的經濟貿易糾紛。⑵平等性。涉外商事糾紛的當事人是不同經濟體的商事主體,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⑶自愿性。涉外商事調解依托于當事人之間形成的合意,由其共同的意思自治決定。⑷民間性。也稱非官方性,涉外商事調解是一種私力救濟的糾紛解決方式,是不同經濟體的商事主體之間基于解決商事糾紛的合意而進行的活動,調解過程不依賴于公權力。⑸非復雜性。涉外商事調解所能解決的經濟貿易糾紛是依據商事糾紛主體之前達成的協議,權利義務清晰或者能夠明確,在調解過程中,經過當事人之間的相互妥協讓步能夠解決。(6)可重復性。涉外商事糾紛調解失敗后,當事人之間只要存在合意,就可以提請調解組織進行調解。
二、涉外商事調解同其他涉外糾紛解決途徑的主要區別
調解、仲裁、訴訟是請求第三方解決民商事糾紛的三種主要方式,同樣是請求第三方解決涉外商事糾紛的三種主要途徑。但涉外調解與涉外仲裁、涉外訴訟卻有著顯著不同的功能取向。
首先,性質不同。涉外調解屬于民商事主體請求第三方給予私力救濟的方式,是意思自治原則在跨經濟體的平等民商事主體之間的實踐和運用,是全球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中一種非公權力治理。涉外仲裁、涉外訴訟屬于司法或準司法的救濟途徑,依托單一經濟體自身公權力或不同經濟體公權力間的協助對當事人給予救濟。
其次,商事糾紛的復雜情況、復雜程度各不相同。涉外調解中,調解組織基于當事人共同解決問題的誠意,在調解組織的協助下,經過各自利益取舍,尋求最大公約數以解決爭議,這就決定了糾紛不可能復雜,涉外調解功能的定位、調解組織的地位也決定了涉外調解糾紛的難度和復雜度不能過于困難和復雜。涉外仲裁、涉外訴訟,則是在仲裁機構、法院的主持下依據證據、評判是非、確定責任,多為當事人之間無法協商,難以達成妥協的糾紛,較涉外調解中的糾紛更加困難、復雜。
第三,管轄依據不同。涉外調解中,調解組織的管轄權來自于當事方一致的意思表示;而在涉外仲裁案件中,仲裁機構的案件管轄權來源于當事人之間達成的書面仲裁協議或者仲裁條款;在涉外訴訟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管轄權根基于司法主權,允許當事人協議管轄,但只能就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的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與此同時,不得違反民事訴訟法有關于級別管轄以及專屬管轄的相關規定。
三、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的現狀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主要指的是中國大陸地區同阿拉伯國家商事主體之間發生的商事貿易經濟糾紛,依據任意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的請求,商事調解組織在當事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組織、引導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涉外商事糾紛的活動。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是我國涉外商事調解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多元化商業糾紛解決的重要方式和途徑,主要就中國大陸地區與22個阿拉伯國家的商事主體之間發生的非復雜的商事經濟貿易糾紛,在相關商事糾紛調解組織的調解下,在自愿的情況下平等協商,從而達成調解協議,化解經濟貿易糾紛。近幾年,國內外商事糾紛調解組織蓬勃發展,各地先后發起成立了中國—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中心、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義烏市涉外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解中心、香港調解會、香港和解中心、新加波國際調解中心等,他們都在積極參與中阿商事調解工作。
目前,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中國—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中心秘書處建設需要進一步充實和加強。中阿商事調解中心作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開展商事糾紛調解的主要機構,自身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寧夏分會(寧夏博覽局)會務處具體承擔中阿商事調解中心秘書處辦公室工作[3],受人員編制等制約,秘書處缺乏專職及專業人員從事中阿商事調解推進工作。二是中阿商事調解合作框架有待進一步充實。全球共有22個阿拉伯國家,主要分布在西亞、北非地區,中國同全部22個阿拉伯國家建立外交關系。[2]如前所述,中阿商事調解中心秘書處與7個國家建立了商事調解合作關系,阿拉伯國家覆蓋率僅為31.8%。三是涉及阿拉伯國家商事糾紛調解機構之間的合作仍需要進一步加強。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大,涉外商事調解機構數量將持續增加,調解機構的發起主體千差萬別,彼此之間合作的意識不強、合作的層次較低,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還未建立。四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商事糾紛調解的互惠性還不強。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商事調解中心為例,其所調解的涉外商事糾紛,絕大多數調解案件由外方當事人發起,中方當事人被動接受,涉外商事調解單向運行,互惠性不強。五是涉外商事糾紛調解還沒有納入到人民調解的框架之下。社會各界對人民調解的認識還不深入,將商事調解與人民調解對立,呼吁為商事調解立法,未能充分認識到《人民調解法》在調解領域的根本法地位,未能在人民調解的大背景下,就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人民調解進行深入探索,僅就商事調解論商事調解,缺少理論及法律支撐。
四、完善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機制的建議
(一)加強國家層面統籌規劃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中國與中亞國家、中國與南亞國家、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中國與非洲國家、中國與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共同構成了“一帶一路”貿易藍圖,涉外商事調解機制作為“一帶一路”多元法律保障機制的有機組成部分,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統籌規劃,協調推進中國與不同地區之間商事糾紛調解機制建設工作,建立健全涉外商事調解體系,構筑兼容并蓄,各有側重的保障體系。由司法部牽頭,協調有關部門,以《人民調解法》為依托,推進我國涉外商事調解工作。
(二)建立健全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網絡
中阿商事調解中心秘書處應加強與阿拉伯國家有關調解組織的協商,建立健全聯合調解機制,力爭實現中國與22個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全覆蓋。加強同國內涉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機構的整合,建立完善涉阿拉伯國家商事糾紛聯動機制。
(三)加強阿拉伯國家法制研究
整合國內力量,對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了解,從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文化等領域,多維度、多層次開展調查研究,設立阿拉伯國家大數據庫,運用大數據分析、研判阿拉伯國家法治環境變化情況,保障涉外商事主體合法權益。
(四)發揮涉外商事調解的功能作用
我國涉外商事調解互惠性不強的問題,揭示出我國涉外商事主體運用調解解決商事糾紛的意愿還不強烈,涉外商事調解未能形成有效的市場規模和市場效應,對解決我國涉外商事糾紛的貢獻還不大,涉外商事調解市場繼續培育和發展。應進一步充實和加強調解機構,充實相關人員、完善調解機制;需要進一步加強宣傳引導,讓涉外商事主體認識、了解涉外商事調解的優勢,豐富其糾紛解決方式和途徑;需要進一步加強機構間合作,為涉外商事主體提供優質的服務,滿足當事人的業務需求。
(五)加強中阿商事調解中心秘書處建設
中阿商事調解中心秘書處作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推進的核心機構,應進一步增強其實力,完善工作機制,充實工作人員。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應將中阿商事調解中心秘書處的人員編制、機構設置從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寧夏分會(寧夏博覽局)剝離,以寧夏內陸型經濟試驗區建設為依托,整合相關力量,現行先試,大膽創新,建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事調解的法律高地,構建涉外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為中國與阿拉伯國家貿易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