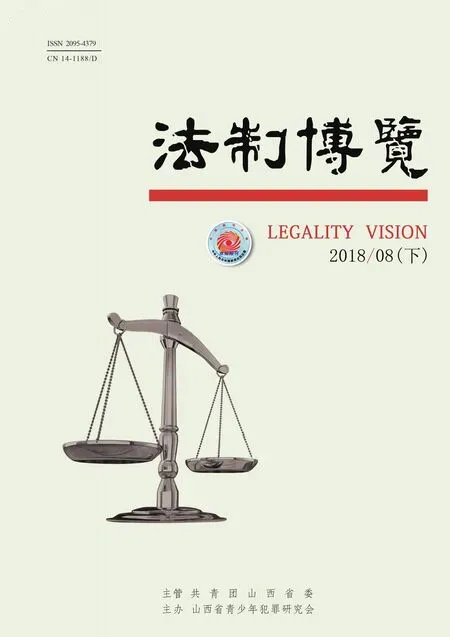淺論好意施惠引發的侵權責任
安勝美
內蒙古科技大學,內蒙古 包頭 014010
一、研究問題及意義
好意施惠是一種熱心幫助他人,旨在增進雙方情誼,在生活中極為常見的做好事行為,如好意搭乘、見義勇為、照看孩子等。雖然是出于好意,有良好的動機,但是往往事與愿違。例如,邀請朋友出去吃飯或者一塊搭車出去游玩——一塊吃飯或者出行游玩這本是好意,既可以溝通交流又可以相互間聯絡感情,但卻往往事與愿違,可能會出現朋友之間矛盾產生、一方爽約等問題。這對于好意施惠人來說,其實是善意的,但是往往“好心辦了壞事”,這就導致施惠人善意的內心與事實形成鮮明的對比。
例如,“小明、小芳在公交車上相識,小明擔心自己到站時未醒,請求小芳在A站把自己叫醒然后下車,小芳便同意。公交車到達A站時,小明沉睡,小芳也未醒。故小明沒能在A站下車,由此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小明要求小芳賠償損失。對此,應如何處理?”從上文中可看出,小明、小芳之間應為“好意施惠關系”。可見,好意施惠行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故對好意施惠關系及其引發的糾紛侵權處理的探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狀況
好意施惠關系指雙方當事人之間無意設定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而由當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道德風尚的實施而使另一方受恩惠的法律關系。好意施惠關系的概念最早是來源于德國判例學說①,德國學者迪特爾·梅迪庫斯在《德國民法總論》一書中闡明法律行為這一概念時,將這些統稱為好意施惠行為,并且指出該行為是不能產生法律后果和侵權行為的。我國臺灣學者王澤鑒先生將此譯為“好意施惠關系”,黃立先生譯為“施惠關系”。好意施惠關系在我國法律法規及理論研究上沒有相關規定,在實務上也尚未有判例可供參考。我國大陸學者對此也鮮有研究,只有王澤鑒先生在其所著的《債法原理(一)》中對好意施惠關系有所論述。
三、好意施惠之性質認定問題
(一)“好意”的事實界定
1.無償性。這是判定好意的首要外觀。例如我們平時說到的索取對價,這就不是我們所說的無償。雙方的約定內容一定是對受惠人有益的,而不是對受惠人強制設置權利義務關系,在日常活動中,以主動邀請或者進行具體恩惠的形式展開一種施惠行為,雖然有時會支付一定費用,但通常出于情誼維系,非支付對價之意思,應屬于“無償”范疇。如果施惠是其他目的的實現手段或組成部分也不構成“無償”,即若是行為與金錢的有償交換,也不可能稱之為好意施惠。
2.約定性。雙方二人有一定的約定,此約定是指雙方一種意思表達,而不是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這與合同法上達成合意完全不同。
(二)法律性質界定
究竟怎樣才能更好的給好意施惠行為定性?假如說好意施惠不是民事法律行為的話,那它是以什么樣的概念存在于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它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那么關于該行為的法律性質及因該行為產生糾紛后的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在理論傷沒有統一的規定,在實踐中操作也非常紛雜。
好意施惠在民法上并沒有嚴格的界定。根據傳統通說,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合同關系說:認為好意施惠基于主體意思表示而締結的一種法律關系。
2.關系契約說:認為好意施惠雙方形成的契約關系式因一定事實過程而成立,非主體意思。
3.就好意施惠與無因管理來說
無因管理與好意施惠的概念非常相近,但是絕對不能將其等同化。
筆者認為,而無因管理是一種法律事實,屬于事實行為,為債的發生根據之一。無因管理之債的產生是基于法律規定,而非當事人意思,而好意施惠不是法律事實。在事實行為中雖然意思表示不是其構成要件,但是當事人還是有意思表示的,只不過這個意思表示不對事實行為的成立產生影響。故好意施惠關系不是民事法律關系,這是由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事實之間的邏輯關系定位所決定的。
4.就好意施惠與無償合同來說
(1)雙方當事人之間是否有產生法律上的與約束力——效果意思,即以書面或口頭刑事的表示行為所推斷的效果意思。
(2)解釋當事人之意思表示應斟酌當事人利益關系和公平原則。
(3)結合交易習慣來理解。交易習慣,是指某種存在于交易中的行為習慣和語言習俗。這種習慣或者習俗通常出現在某個特定的交易參與人階層,該交易階層的成員通常都遵守這些習慣和習俗。對好意施惠與無償合同區分之關鍵,是對當事人主觀意思的識別。施惠人為意思表示時知道或應知道而沒有明示排斥交易習慣者,可以認為意思表示者愿意遵從交易習慣,從而使雙方之間本為好意施惠的關系變成無償合同關系。當事人自愿負法律上之義務,法不禁止,這也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則。
由于好意施惠關系和合同關系不具備相同的意思表示效果,故好意施惠不是合同關系。
而筆者認為,好意施惠行為是一種普通的社會關系,但行為人不具有發生一定私法意義上的意思表示,其不是我們所認為的民事法律行為,而只是一種事實行為,沒有讓自已做出的行為獲得法律上強制約束的意思,而他的價值追求是增進情誼以及出于良好的目的性。所以筆者認為,這就不能從法律角度來評議好意施惠行為的性質歸屬問題,但是在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中,好意施惠行為仍有存在重要的注意義務,很有可能會引發事與愿違的后果,這便有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同時也會產生侵權行為。因此,筆者認為,當好意施惠行為因違反注意義務而造成受惠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損害而引發侵權糾紛時,法律將會介入其中進行調整與改善。
四、好意施惠之侵權與歸責原則
由于好意施惠關系引起的損害在我們身邊經常發生,施惠人給受惠人造成損害,受惠人給施惠人造成損害,此情況是經常發生的,但是這畢竟是好意施惠行為,施惠人的侵權責任在構成要件上要區別于我國《侵權責任法》中普通的侵權行為,例如在過錯責任的判別中應歸屬于行為人故意或重大過失的情形。所以,解決由于施惠行為引發侵權行為怎么辦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對好意施惠行為進行討論,不是為了理論上的探討和爭辯,而是為了追尋實務中由于好意施惠的行為引起的糾紛解決,從而實現施惠者與受惠人之間的利益平衡,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
(一)歸責原則
按照《民法總則》的相關規定以及結合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來看,侵權行為分為一般侵權行為和特殊侵權行為兩類。一般侵權損害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構成要件,缺一不可:違法行為、損害事實客觀存在、行為人有過錯、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有因果關系。侵權行為法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為主要目的,對因侵權所造成的損害可以基于此請求進行懲罰與賠償。故,當施惠人的行為造成對受惠人的損害并符合侵權行為四大構成要件時,筆者認為完全可以引用侵權行為法的相關規定來請求保護。
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歸責原則主要包括過錯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在我們的學習中,好意施惠行為造成的損害,我們認為應重點學習歸責原則的認定問題,以便于更好的解決日常生活中的糾紛問題。目前,持“過錯責任”和“無過錯責任”二者說法均有之。對于好意施惠引發糾紛的通說,大部分地區認為應當采取過錯責任的規則原則處理,這可分為“重大過失”和“一般過失”兩大類。“重大過失”說認為,施惠人對損害的發生原則上僅在具有重大過失時才應該進行責任承擔;“一般過失”說認為,在好意施惠行為關系中,原則上,施惠人應就其實施的行為造成他人的損害,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在對他人生命身體健康的注意義務上,我們不能因施惠者為好意施惠而應當從輕或者減輕,將其僅限于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
我們認為,惟施惠人在主觀上存在過錯時才應承擔責任。關于好意施惠行為關系,在排除適用公平責任原則的情況下,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主旨在損害之合理分配,這是基于對生命價值至高無上的尊重與敬仰,施惠人與受惠人享有同等的權利,二者也應承擔同等的注意義務。
(二)責任承擔
對于在好意施惠的情況下侵權責任是否可以從輕或減輕,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當然,這也留給我們更多思考的空間進行繪畫和構建。
筆者認為:首先,就好意施惠行為關系本身而言,是具有積極的社會價值,法律應避免懲罰好意施惠行為;其次,好意施惠致損害,雖其轉變為侵權行為,但這并不排斥其內含善良、友好的道德歸屬,減輕賠償難道不是更符合公序良俗的闡明?難道這沒有符合當下社會倫理道德價值的觀念嗎?最后,從利益平衡的角度來看,受惠人本因受惠而享有利益收獲,施惠人也并未因此而獲取對價補償,在受惠人受損的情形下,適當減輕施惠人責任,可謂利益均衡。
就減輕責任方式而言,當在施惠人過錯形態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受損利益性質、雙方當事人關系性質、雙方經濟狀況等。實踐中,好意施惠致損害案件,施惠人的“過錯”常表現為過失,在受惠人財產利益受損的狀態下,好意人僅就重大過失承擔責任;在受惠人人身權益受損狀態下,施惠人就所有過失承擔責任。同時,均具有減輕之優待,一般過失減輕程度自當大于重大過失減輕之程度。
總之,好意施惠引起的糾紛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經常發生,對好意施惠行為法律問題的研究,并沒有深入的進行探討,在實踐中反映出的問題也屢見不鮮,依然是法律規定的一大空白。好意施惠行為與我們日常交往聯系密切,又是我們中華傳統美德所倡導的熱心幫助、積極為善的彰顯,我們現在應該解決好由于好意施惠引起的糾紛問題。筆者認為我國應盡快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盡快彰顯引發糾紛的解決方法,從而達到利益平衡和社會秩序穩定。
[ 注 釋 ]
①德國 判例學說將這類行為稱為 Gefalligkeitsverhaltrt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