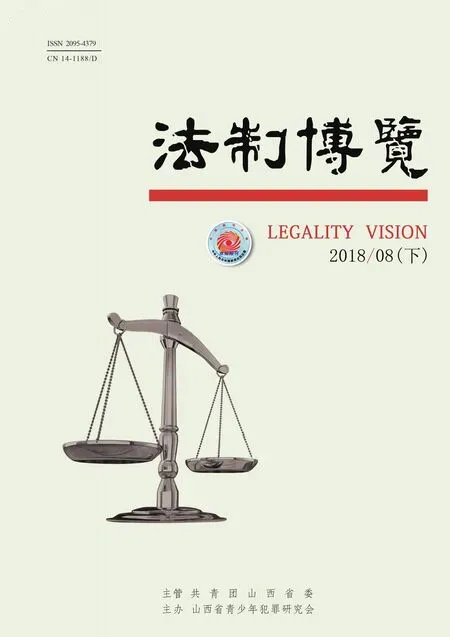看清廷的監察制度發展及對當代之借鑒
李 鵬
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3
一、清朝監察制度概覽
《欽定臺規》是我國古代最為完整的一部監察法規,也是清朝監察制度發展的產物。始纂于乾隆八年,共四十二卷,非常全面的規定了都察院的職責和任務,職官的選拔,紀律,獎勵和懲罰。
清朝在繼承了明朝的監察制度(都察院)的基礎上,擴大都察院官員的權力,允許其“風聞言事”,康熙認為:“國家設言官,專司耳目,凡政治得失,民生利弊,必須詳切條陳,直言無隱,司為稱職。”到雍正時期,將六部的六科給事中劃入都察院管轄。至此,唐代以來的臺(御史臺,明清改為都察院)諫分離,明朝的科,道并行的監察體系不復存在,形成了以中央都察院為核心,地方十五道監察御史為輔助,全部監察權力集于中央的監察體系。
二、清朝監察制度無法發揮效能的原因
回顧整個清王朝,監察制度的發展與吏治腐敗并行這種矛盾的現象一直存在。清朝吸收借鑒了前朝的監察制度,是我國古代史監察制度的集大成者。有數據統計,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八年間,一、二品官員貪污腐敗的經濟案件共有108件,但僅乾隆年間一、二品官員經濟犯罪就有65人,占清代總數的41%。這一方面展現了乾隆從嚴治吏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監察制度已相對完善的運行機制下,貪污腐敗仍屢禁不絕,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尤其是在乾隆末年之后,監察體制對于抑制官場的腐敗風氣已如杯水車薪。這其中的原因又包括:
最高權力的參與。清朝腐敗是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大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意。皇上自身就是“進貢制度”的受益者,但卻不許州官收貢,或是限制其收貢。這種政治生態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腐敗是伴隨在其骨子里的,不可分割。
議罪銀和捐納。議罪銀形成于乾隆時期,就是針對一些有侵吞公物,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的政府高級官員,繳納一定的財物即可抵免其罪過的制度。一般繳納的銀兩少則萬兩,多則數十萬兩,而當時的二級公務員(現在的正部級)一年的薪資也只有一百八十兩,這之間的差距既暗含了議罪銀只針對高官,另一方面也能看出當時官員通過貪污腐敗所獲的臟銀之重。
捐納即買官賣官的制度。清朝建國后(順治年間)就開始出現了捐納的案例,后來便一發不可收拾。乾隆年間,道員一職的價位是13120兩,知府10640兩,知州4820兩,知縣3700兩。這些明碼標價的職位并非天價,因此有許多富裕的商人通過這種途徑入仕,而一旦當他們的一只腳邁入了官場,其商人本性便又隱隱發作,第一件事便是撈回其成本,最簡單高效的方式便是出售其轄內的官職,層層捐納,或是貪污腐敗,像蛀蟲一樣,自上而下,逐漸蠶食大清的政治生態,使大清的末日提前到來。
三、清朝監察制度對當代的啟示
歷史是一面鏡子,盛衰之理盡收其中。
(一)建立獨立、權威的監察機關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前提。清朝施行了獨立、垂直的管理體制,保證監察機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以實現對各級官員的有效監督。目前我國最新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對上級監察委員會負責,這一點區別于之前監察部的雙重領導,既要受上一級的監督,又要受本級人民政府的監督,實則為各級地方政府過多干涉轄內行政機關獨立行使監察職能提供機會,侵蝕監察機關的權力。
(二)科學的監察官員選任制度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關鍵。古人云“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監察職能的最終實施要依靠廣大的監察官員來完成。清代學者顧炎武曾說“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這樣的制度設計使得監察官員有著廣闊的晉升空間,可以激勵監察官更好的履行自己的職責,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擺正自己的位置,當下的監察委員會可在此處有所借鑒。
(三)嚴密的反監互察機制是充分發揮監察效能的必要措施。監察官是反腐的最后一道防線,那么要是監察官自身出了問題又該如何解決?為了發揮監察官員的作用,防止監察官員弄權行私,清朝也實行了反監互察機制,這種制度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監察系統內部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制約,從而制約監察權力的濫用。為此,我們也應當借鑒如此,改變過去那種線性組織管理體系,逐步形成全國各級監察機關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相互配合的工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