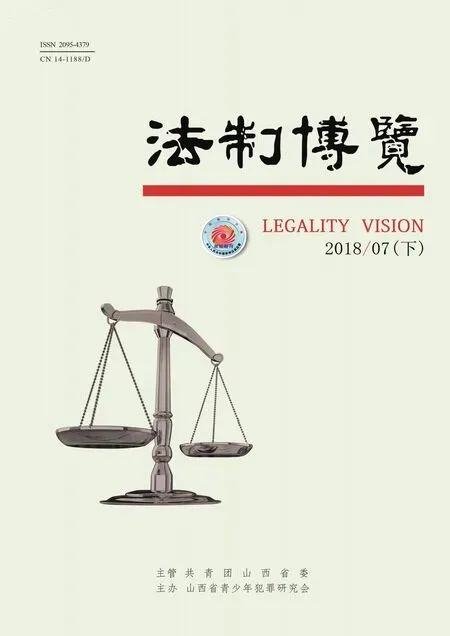論中國古代法中禮與法關系的演進
宋一楠
江南大學法學院,江蘇 無錫 214000
中國古代禮與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古代“法”的概念主要體現在對刑罰的裁判與實現上,而禮更多的是一種道德規范,強調等級尊卑,要求人們發自內心地去遵守。禮法關系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夏、商、西周三代處于混一狀態,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分離,經過秦及漢初的艱難發展,到西漢中期漢武帝時代又結合在一起。[1]
一、夏商周禮治制度下的禮法混一
法律產生受宗教、道德的極大影響。法律與道德、宗教由混合到分化,是其進化的普遍規律。中國法“法出于禮”的特點也印證了這一現象。
早在夏商,從祭祀活動中發展起來的禮文化已逐漸演變為一種以宗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用以區分貴賤親疏的規范秩序。周初,周公制禮作樂,形成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的行為規范,稱為“周禮”。這種制度既包含了強制手段也包含了非強制手段,是禮與法的混合,僅就行為規范這一點來說,禮與法律無異。這時的禮混雜了其他很多形式的社會規范。此時的“法”也無后世所稱法律的含義,《爾雅·釋沽上》:“法,常也。”指常循之法式,也即習慣,更能體現法律特征的其實是“刑”。
而至于禮與刑的關系,如晉大夫叔向描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所謂的“事”,就是違禮的情況。說明西周實行的禮治存在著“失禮入刑”的原則,禮和刑皆是禮治的組成部分,同時也進一步說明刑是維護禮的手段之一,當時并沒有獨立的、相對穩定的刑罰體系,刑是依附于禮而存在的。[1]禮刑的結合也體現了禮法的混一。之后隨著統治階級司法經驗的豐富,西周中期定《呂刑》,特定違禮的情形和相應的刑罰開始能夠大致對應,“法”的概念也逐漸同刑罰及相關制度相結合,在與禮分化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二、春秋戰國時期禮法的分離
春秋戰國時期,西周禮治制度式微。禮崩樂壞下,儒法兩家提出各自的社會治理主張,一個主張德治和仁政,一個主張法治和刑罰。但其實無論是儒還是法,其思想內核都脫胎于西周的禮治,是經過揚棄,從中分化出來的禮和法。
儒家主張“克己復禮”,突出傳統禮治體系中的德禮教化,形成儒家之禮。法家強調禮治中的“政刑”,主張用強制、嚴苛的制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鄭子產鑄刑書、晉鑄刑鼎、李悝制法經、商鞅變法,各國制定成文法的法律實踐活動都使原來依附于西周禮治體系的刑與法在制度實體和思想理論上都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形成了法家之法。[1]
禮法分離,各自對西周禮治進行繼承與革新,但盡管如此,二者文化的實質核心并非對立,對立的只是它們的社會治理主張。法家不排斥禮所蘊含的對貴賤、尊卑、長幼、親疏的區分,不僅如此,反而力圖以法律來建構尊卑有別的差別性社會。商鞅變法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可見,法家反對的只是儒家所主張的無用的禮。同樣,儒家也不否認政刑在國家治理上的作用。《論語·子路》:“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所反對的也僅是法家試圖用刑罰來治理社會的主張,認為這樣治標不治本。
儒法兩家的對立在秦朝時達到頂峰。秦覆亡后,漢承秦制,在基本沿襲秦朝法律制度的同時,逐漸開始重視儒家之禮的教化作用,禮法的關系再次發生變化。
三、西漢中期及之后禮與法的結合
漢代雖基本承襲秦朝法制,但漢代統治者開始將儒家思想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漢武帝時期開啟禮法結合的端倪,其中董仲舒所倡導的“春秋決獄”,即是指運用經典《春秋》所載事例及其體現的道德原則作為司法審判的依據,用“禮”來進行“法”的裁判。董仲舒所提的儒家理論,與春秋初期的儒家大不相同,是一種已被改造了的以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為基礎的封建政治思想體系。他主張德刑并用,側重于儒家德治教化的統治原則。以禮入法,禮法結合,是這一時期禮法關系最為顯著的特征。
所謂的禮法結合,即是指以禮作為法的指導思想,禮所蘊含的倫理道德、綱常規矩成為法必須體現的道德精神。法家之法中對秩序、規則的注重,再無發揚之余地,因為法律、刑罰的適用可以根據禮的解釋而變化。禮法結合首先以“以禮為主”為前提。這一轉變的原則在后世歷代中都不斷被確認與加強。魏以“八議”入律,晉律“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唐代《唐律疏議序》載:“夫禮,民之防也,刑,禮之表也。二者相須猶口舌然。禮樂禁于未萌之前,刑制于已然之后。”標志著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終完成。
禮法的結合誕生了一種絕佳的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社會制度,人們的思想由禮來直接規范,行為由以禮為原則的法來規范,禮法共同為社會的穩定服務,禮法關系的演進在這一階段愈趨穩定,直至清末外來的沖擊迫使這一制度開始近代化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