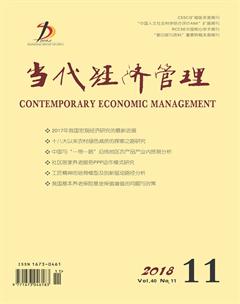2017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的最新進展
陳享光 李振新
摘 要 2017年我國經濟學界對我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宏觀經濟波動、全要素生產率、宏觀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宏觀調節與財政政策轉型、人民幣國際化與開放宏觀經濟等問題上,并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創新的見解,為認識和解決我國宏觀經濟問題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
關鍵詞 經濟增長;經濟波動;宏觀金融穩定;開放宏觀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8)11-0001-07
宏觀經濟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縱觀經濟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的主要問題集中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問題、宏觀經濟波動問題、全要素生產率問題、宏觀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宏觀調節與財政政策轉型、人民幣國際化與開放宏觀經濟等問題上,并在這些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問題研究
王少平和楊洋[1]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和經濟新常態下的數量關系。他們構建了由 GDP、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宏觀經濟變量組成的協整系統,應用 KPSW理論分解出2001~2014年我國 GDP的長期趨勢和短期沖擊。研究得出以下結論:一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出現結構性下移,尤其是2010~2014年期間發生大幅度下滑;二是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性下移主要歸因于資本積累不足,勞動力優勢逐步喪失,以及技術進步的速度下降等經濟因素;三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穩定在6%至7.5%之間,概率為91.5%。因此,經濟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重視促進和培育長期經濟增長因素,同時適度地實施刺激性政策以應對GDP的周期性下滑。
陶新宇等[2]利用1999~2015年中國地級市面板數據構建了中國經濟結構指數, 研究了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之謎。研究發現:首先,從國家的角度來看,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呈現倒“U”曲線;其次,就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城市而言,經濟結構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仍然不同。東部城市率先進入“結構性減速”渠道,中心城市的經濟增長正處于加速和減速的過渡時期,西部城市的經濟結構仍處于“結構性加速”通道;再次,中國各區域城市形成了一個獨有的經濟結構與GDP同步提高的“雁陣”模式。因此,他們認為,國家應當充分考慮各地區的經濟特征,保持中西部的經濟結構優勢,警惕東部地區經濟結構失衡的風險,實現全國經濟結構優化調整。
馬勇和陳雨露[3]使用1981~2012年世界68個國家的動態面板數據來實證檢驗金融杠桿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金融杠桿水平以及金融杠桿波動對經濟增長均存在著顯著影響,金融杠桿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金融杠桿的門檻約為1.468,金融波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負線性關系。根據閾值預計,我國將于2019~2020年左右進入“次高速”階段,金融杠桿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作用。因此他們建議,在即將步入“次高速”階段,應積極加快經濟的轉型升級,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支撐點,同時繼續推進金融去杠桿化,避免金融杠桿大幅波動對宏觀經濟產生猛然沖擊。
劉瑞祥等[4]對1995~2011年世界投入產出表數據進行分析,試圖找到對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新解釋,研究發現:第一,隨著國際分工體系的建立,中國經濟順利融入全球價值鏈,對外經濟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具體來看:中國對東亞經濟的依賴正在下降,而對美國等經濟體的經濟依賴正逐漸增加。第二,通過全球生產網絡逐步融入世界經濟。不同生產地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不盡相同。當前中國逐漸融入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但是由于中國在價值鏈中主要從事加工貿易,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因此他們認為,中國應該通過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從而擺脫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同時加快轉變以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更加注重完善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避免扭曲最終的消費需求結構。
邵宜航和李澤揚[5]試圖從理論上解釋空間集聚通過影響企業創新、企業研發、企業進入與退出等企業動態演變進程進而作用于經濟增長,他們使用擴展的熊彼特式縱向創新的內生增長模型,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挖掘中國制造業企業2000~2007年的地理信息,構建空間集聚指標,實證檢驗空間集聚、企業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發現,企業空間集聚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目前大部分企業空間集聚已經開始出現負向效應,主要原因是空間集聚提高了周邊地區的地租成本,并造成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緊張,這將通過降低創新公司的利潤來減少對企業創新的激勵。因此他們認為,應當著力發揮空間集聚對企業創新和經濟增長的激勵作用,同時抑制土地使用成本的過快上漲、避免高地價對企業創新的擠出效應,并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等政策。
白俊紅等[6]構建了包含研發要素的動態特征與GDP增長的理論模型,以此來研究研發要素的動態特征對GDP增長的作用機制。他們使用引力模型來測量中國各省的研發人員和資本因素的流動數據。最后,他們利用2000~2013年中國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中國地區之間的經濟行為存在著相互影響;研發要素在地區之間的流動可以影響鄰近地區的經濟增長,而這是通過相鄰地區之間的空間知識溢出效應來實現的。因此建議,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時,需要通盤考慮周邊地區的發展策略,積極搭建區域協作平臺;同時,完善區域間要素流動機制,促進知識因素的自由流動,從而促進中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
二、宏觀經濟波動問題研究
項后軍等[7]闡述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對經濟波動的理論機制,并利用動態GMM的方法對2003年以來我國地方債務對經濟波動的傳導渠道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了如下結論:第一,地方政府投資項目所需資金龐大,往往需要舉債來解決,如果債務融資不穩定,將會造成地區經濟增長的波動;第二,鑒于地方政府財政能力較弱,而地方債務的大部分投資于基礎設施、城市改造等回報周期長的項目,因此,土地財政收入成為地方債務的主要還款渠道;第三,地方政府在任期內存在政治晉升的激勵,而在任期將滿時經濟行為則會趨于保守,導致政治周期通過舉債動機的強弱對經濟的不穩定性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為了緩解區域經濟波動,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有必要規范地方政府的債務融資行為。
仝冰[8]利用混合頻率數據構建了DSGE模型,并對模型重新估計并進行方差分解。該研究發現,特定投資的技術沖擊是中國經濟不穩定的重要來源之一。因此,他建議中央銀行應當在貨幣規則中增加對投資品價格的反應,進而改善宏觀調控的績效。
方福前等[9]通過構建經濟波動作用于技術創新的理論機制,并利用 SYS-GMM估計的方法探討了2005~2014年中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與經濟波動的關系。研究發現:第一,中國的經濟波動對工業企業的技術創新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第二,金融市場通過預期收益機制作用于兩者之間的關系,同時這種影響存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差異性。他們認為,2010年是中國技術創新模式的轉折點,從此開始,中國的技術進步模式在逐步向自主創新轉變。因此在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持續下行、經濟波動加劇的背景下,加快向自主創新模式的轉變,同時加快金融對自主創新型企業的支持具有合理性。
高然和龔六堂[10]構建了一個簡化的DSGE模型來研究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我國住房市場的不穩定性主要來自于房地產需求沖擊;第二,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行為的存在不僅會放大房地產市場的波動,而且還會導致實體經濟部門的波動;第三,土地財政導致無謂的社會福利損失,合理的土地供給政策能夠減少這種損失程度。因此,地方政府應當拓寬收入來源的渠道,逐漸降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同時合理的運用土地供給政策有助于緩解社會福利損失。
王頻和候成琪[11]建立了由兩個異質性家庭和兩個異質性生產部門組成的DSGE模型。為了研究預期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房屋交易成本沖擊和房價預期沖擊被引入到模型中。研究發現:第一,確實存在著預期沖擊對房地產市場和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第二,住房價格的預期對耐心家庭和缺乏耐心家庭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價格預期對缺乏耐心家庭的影響尤其明顯;第三,公眾的期望會影響政府房地產行業調控政策的有效性,而錯誤的預期會導致政府政策的失敗。他們進而認為政府應該引導公眾形成產業調控政策的正確預期,進而改善相關政策的實施效果,減緩經濟波動。
邵全權等[12]試圖通過統一的DSGE框架來研究風險沖擊和保險的存在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社會保險制度的存在可以熨平宏觀經濟波動,減緩非預期沖擊下的風險對經濟變量的影響;降低保險賠付的免賠率,增強保險領域的良性競爭,可以有效地緩解經濟波動。因此,適時地降低保險賠付的免賠率,增強保險市場的反壟斷執法能力,既能促進保險業的良性發展,又能有效地發揮保險對宏觀經濟的保障功能,減緩經濟的短期波動。
張翔等[13]通過建立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并利用1998~2015年的季度數據來研究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金融化對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研究認為:國際市場金融化嚴重地影響了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同時這一影響渠道在金融危機前后是不同的。金融危機前主要是通過信息渠道對經濟波動產生平抑效應,而在金融危機后則主要通過美聯儲的量化寬松等外部因素對經濟波動產生放大效應。相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沖擊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弱于國際商品市場的價格沖擊。因此,他們建議應加強對國際資金流動監控,推動建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預警機制,以便及時識別金融資本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不利影響,有效應對國際商品市場金融化對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
三、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影響因素問題研究
賈俊雪[14]通過異質性企業家模型來分析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要素配置和TFP的作用機制。結果發現,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在全要素生產率中的作用首先是上升然后則是下降,并且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有一個最佳門檻。因此,我國應當轉變傳統的、粗放式的投資模式,合理規劃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政策,進而可以更有效地發揮投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確保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
朱軍[15]構建了兩國DSGE模型,采用“貝葉斯估計”方法討論了1992~2014年以來中國技術演化的實現路徑。他們發現技術吸收和效率提升是中國GDP增長和TFP改善的重要來源。“技術吸收加本土技術創新”該模型對中國的經濟現實有更強的解釋。中國技術存量對GDP增長具有明顯的“前瞻驅動”效應,一般來說,其對GDP的促進作用要延緩至下半個周期。也就是說,當美國的技術創新不確定時,美國技術創新提升了我國的TFP,但是卻阻滯了我國本地技術的增長效應。因此他們認為,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不應該盲目地完全追隨發達國家,也不能夠完全寄希望于自主創新,這兩種方法的有效整合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
余泳澤[16]考慮到省際勞動力投入質量和資本折舊率方面的差異,分別對勞動和資本進行了同質化和異質性處理,然后對1978~2012年我國的TFP進行了估算分析。研究發現,第一,從1979年到2012年,中國TFP的年均增長率為2.073%,其中規模效率提高和技術進步是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最重要因素;第二,改革開放以來,TFP大部分年份都呈現正增長,2008年以后TFP開始逐漸下降;第三,當前我國TFP低下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企業投資的無效性。他們因此建議,應逐漸改變中國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推動企業技術進步,合理規劃產業布局,避免無效投資和產能過剩問題。
程惠芳和陳超[17]旨在研究不同知識資本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構建了一個綜合指標體系來測度國內知識資本及細分項指數,通過份額加權法測度國外知識資本及溢出項指數,進而把國內外知識資本納入開放經濟的內生增長模型中,最后利用組間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GM-FMOLS)對1981~2010年全球130個經濟體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國內外知識資本溢出是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但不同類型的知識資本對不同創新類別的TFP有不同的影響。因此,優化知識資本投入結構有利于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而促進創新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蔡躍洲和付一夫[18]構建了包含技術效應、結構效應以及要素結構效應的宏觀TFP增長率分解模型,并從宏觀、行業和相應的子行業層面重新計算中國的TFP增長率。研究發現,第一產業的增長主要取決于技術進步效應,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各個子行業的技術進步效應,而結構效應則可以忽略不計。但2005年后,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技術進步支撐作用迅速減弱;而結構效應則顯著地促進產業的增長。因此他們認為,短期內要更注重要素結構,陸續淘汰行業中的落后產能,中長期內則要重點提高產業技術進步水平,為經濟增長提供長久動力。
宣燁和余泳澤[19]以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集聚作為提升微觀企業生產率的主要內容,他們從生產性服務業空間專業化集聚和多樣化集聚兩個維度出發,綜合考慮生產性服務的空間集聚對企業生產力的溢出效應的影響。研究發現:首先,城市專業服務業空間專業化和多元化集聚可以顯著地促進企業TFP效率的提高。其中,城市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取決于空間多樣化程度。其次,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集聚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有很大的影響,國有企業的作用更為顯著。第三,專業化空間集聚和多元化空間集聚對生產服務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與城市規模成正比;城市規模越大,對TFP的影響越明顯。因此,有必要通過政策引導加強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集聚,關注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對中國工業企業的作用。同時,關注不同規模城市的等級分工,大中城市增加生產性服務業的多元化集聚,而在中小城市,主要是增加專業集聚。
黃先海等[20]構建了兩部門的ACF生產函數的估計框架,并實證分析了我國的經濟改革對TFP的作用程度。研究發現,結構性經濟改革促進了企業內部的要素流動,從而提高了制造業企業的生產率水平。具體來看,首先,國有部門優化重組促進部門內的要素流動,從而優化了資源配置,通過提高部門內部生產率,最終導致制造業整體生產率的提高;其次,國有企業的重組也將促進不同部門之間的要素流動水平,進而導致制造業生產率的提高。因此他們認為,應當繼續對某些行業的國有部門實行優化重組,促進企業生產率水平,同時做優做強國企,提高制造業整體的全要素生產率。
四、宏觀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
蘇治等[21]在 GVAR模型框架下,利用1992~2016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數據探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聯性,基于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對不同類型貨幣政策的影響進行了比較和解釋。最終發現:首先,中國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是一致的,即規模水平和周期波動視角下,我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都存在嚴重背離的現象。其次,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互動是不對稱的,實體經濟的溢出效應更為明顯。第三,基于價格的貨幣政策優于數量型貨幣政策,以減少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分離程度。因此他們建議,中央銀行需根據實際經濟發展形勢擇機而動,貨幣政策的調整方式應慢慢地從數量型轉向價格型,從而減緩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黃先海等[22]通過擴展的Bernanke理論模型,構建了面板數據FAVAR模型。基于此,研究新常態下我國中央銀行的傳統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等綜合業務的特征。最終發現,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的不同組合對企業投資具有明顯的調節效應,這種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應對不同特征企業具有顯著差異。因此他們認為,新常態下央行為實現定向調節目標,應基于貨幣政策對特征企業的定向調節效應而進行選擇性操作。
程方楠和孟衛東[23]主要研究如何協調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以及如何在宏觀審慎與貨幣政策協調過程中制定各自的政策規則。他們構建了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將房價波動嵌入該模型中,從而將宏觀審慎政策和貨幣政策置于統一的分析框架之下,從理論上分析了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研究發現:第一,從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角度來看,宏觀審慎政策應側重于根據信貸主體選擇相應的政策手段,從而維持金融穩定,而貨幣政策則應注重維持國家價格水平的穩定;第二,宏觀審慎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規則都應遵循標準的泰勒規則;第三,從實施宏觀審慎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兩者高度依賴政策執行的“方向”和“力量”。倘若運用不合理,可能導致政策沖突。因此,他們認為,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應該合理匹配,以實現金融和價格的雙重穩定目標,并盡量減少社會福利的損失。
馬勇等[24]首先構建出一個綜合性的整體金融周期指數,然后將新凱恩斯模型擴展為開放經濟下的包含金融周期的八方程模型,最后,實證分析了貨幣政策對金融周期和金融不穩定性的具體影響。他們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是金融周期明顯地影響經濟周期;其次是宏觀經濟不穩定性很大一部分來自于金融周期的波動;第三,中央銀行應將金融周期和金融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的考慮。
袁越和胡文杰[25]在理論層面區分了貨幣政策沖擊對資產價格泡沫中基礎價格和泡沫價格的不同影響。他們充分利用1997~2016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中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數據,使用變系數向量自回歸(Time-Varying Coefficients SVAR)模型來研究我國貨幣政策沖擊對股市泡沫及經濟系統中的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研究發現,“逆風而動”的貨幣政策存在保持政策有效性的邊界,一旦超過這一邊界,貨幣政策就會通過影響實際利率的傳導路徑助長投資性泡沫的擴大,而且我國外生性的緊縮性貨幣沖擊正在導致股市價格的進一步擴張。我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會加劇股市泡沫這一現實,這就要求央行的政策制定需要更細致的考量,這將有助于央行在市場利率提升過程中提高其宏觀調控能力。
何國華和李潔[26]通過構建包含金融摩擦與跨境資本流動的DSGE模型,分析了本幣匯率的預期變動對金融體系的風險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并比較不同貨幣規則下的社會福利狀況。最終發現:第一,一國本幣升值的預期對基金部門的風險行為影響較大,它使得部門對金融風險的偏好上升;第二,升值預期和跨境資本流動的結合降低了本國無風險利率,提高了借貸利率,導致一國銀行部門杠桿率上升;第三,貨幣政策目標在包含利差平滑時,可有效減緩社會福利的不穩定性,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相比之下,盡管杠桿調節也可以減緩福利波動,但是這并不會引起整體福利水平的升高;而資產價格穩定不但提高了整體福利的不穩定性,還會降低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最終他們認為,在一定條件下,貨幣政策目標可以包含利差平滑以及杠桿調節,而絕不應該包含資產價格的穩定。
孫國峰和何曉貝[27]在信用貨幣理論和貸款創造存款(LCD)機制基礎上,探討了銀行在信用貨幣體系下的作用,并指出信貸供給是由信貸需求和貨幣政策共同決定的。然后,他們通過構建的 DSGE模型來研究存款利率零下限在負利率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研究發現,存款利率的降低對負利率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產生了負面影響,而如果一旦銀行端的利率傳導能夠保持暢通,存款利率可以有效地穿透零利率區間,負利率政策可以穩定信貸供應,從而抑制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因此,中央銀行能夠利用負利率政策來有效抑制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但前提條件是存款利率能夠突破零下限。
五、宏觀調節與財政政策轉型
汪昊和婁峰[28]根據2012年中國的投入產出表和城鄉居民調查數據,構建了社會核算矩陣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重新計算了中國主要的財政工具的再分配效應。結果發現,首先,中國的財政再分配并未縮小收入差距,但增加了各級收入差距。因此,他們認為應優化財政收入結構,逐步增加直接稅的比例,減少間接稅的征稅。其次,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適當提高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第三,優化個人所得稅制,實現從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的轉變。四是優化間接稅制,降低間接稅的累退性,并增加其累進性。
陳登科和陳詩一[29]構建了包含金融摩擦與“超低利率”的DSGE模型,并基于此綜合地計量了財政支出的各類乘數。研究發現:中國財政支出的投資乘數最大,其次為產出乘數、就業乘數、最后是消費乘數,這印證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以投資驅動為主的事實;此外,他們還發現金融摩擦與“超低利率”之間存在彼此加強的交互效應。因此,我國財政支出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需要更加注重金融摩擦以及基準利率降低的事實,否則可能低估財政支出的效果,甚至可能導致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最終將破壞當前“去庫存,調結構”戰略部署的有效性。
李丹等[30]結合我國基本財政—政府負債特征建立了非線性財政反應函數,進而研究不同經濟狀態下的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問題。研究發現:首先,非線性財政反應函數合理地刻畫了基本財政—政府負債的動態特征,能夠實現政府債務可持續性的量化研究;其次,政府債務負擔率的二次項函數能比較好地擬合我國財政的反應特征,且很好地擬合了我國“財政疲勞”的現實;再次,我國財政調整的“儲備渠道”尚未達到最優儲備存量;最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中國的財政空間開始縮小,特別是在2007年金融危機之后。因此,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時應當充分考慮“財政疲勞”跡象,有效協調財政緩沖建設與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力度之間的關系。
王瑞民和陶然[31]使用1994~2009年的中國縣級財政數據,并根據財政收入來源進行分解。從人口的人均財力和經濟支持人口的兩個角度,研究了不同類型的轉移支付的金融均等化效應。同時,比較了縣級和省級轉移支付均等化效應的異同。研究發現,縣級層面的轉移支付的分配效應當注重財政供養的人口因素,合理地平衡財政供養人口的人均財力;省級轉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應尚未轉移到縣級。因此,他們認為,國家應根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財政目標,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制定最低財務保障標準。省政府應主要確定適合本省的財政收支標準,省級以下的轉移支付應在省級協調。這樣可有效減少轉移支付分配中因尋租而造成的效率損失與分配不公問題。
王方方和李寧[32]構建的向量自回歸(SV-TVP-FAVAR)模型包含隨機波動率的時變參數,從結構角度研究從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三季度,中國財政政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時變影響,進而對不同時期我國應采取的不同政策措施進行比較研究。實證結果發現:首先,從財政支出總額的角度來看,財政政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時變效應確實存在;其次,從財政支出內部的結構層面以及稅收內部結構層面來看,在不同的經濟時期,不同類型的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具有不同且不斷變化的敏感性。因此,他們認為,在經濟疲軟時期,政府應當實施擴張性財政支出政策,并輔以減稅政策;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政府應該把重點放在收緊財政支出政策上,并輔以增稅政策。
席鵬輝等[33]研究了增值稅稅收分成的變化引起的財政沖擊對產能過剩行業和稅收征管水平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政府在面對地方財政壓力時,會傾向于引入能夠給政府帶來較高稅收收益的企業,盡管這部分企業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產能過剩的行業,這就會使得地方財政壓力反而變成了一種財政激勵;第二,增值稅分成減小并不會帶來征管力度的弱化;第三,地方政府之所以會引進產能過剩企業,是因為產能過剩企業入駐本地,可以有效地彌補增值稅分成降低所導致的稅收收入的減少;第四,中央為化解產能過剩而制定的政策很容易被財政壓力所引起的對地方財政的激勵而難以實際地產生作用。他們認為企業應該關注地方政府財政激勵在減產過程中的作用;當行業形勢有所好轉時應繼續堅持供給側改革,并且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注意產能過剩行業的轉移軌跡;中央政府應積極發揮宏觀調控的職能,妥善布局新興產業結構。
谷成和曲紅寶[34]利用2003~2013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腐敗對中國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腐敗對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阻礙作用主要通過降低公共支出效率來實現,因此有效地發揮財政支出的作用需要繼續提高腐敗治理力度;在穩定稅負條件下合理規劃稅收結構,科學制定勞動、資本以及消費稅率等措施都會有效地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因此,國家應根據實際經濟發展制定財政政策;在穩定稅負的條件下提升直接稅的比重,降低對勞動所得的征稅力度,加大對資本所得的課稅并加大反腐力度,這將有助于優化中國的稅收結構,促進長期經濟增長。
六、人民幣國際化與開放宏觀經濟問題研究
于恩鋒和龔秀國[35]從歷史的視角出發,通過計量模型考察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對SDR利率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國債收益率的標準差和變異系數均表明,人民幣的納入可以顯著降低SDR利率的波動幅度,提高其穩定性。因此,他們認為中國應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繼續加強國債市場建設,提高政府債券收益率曲線。
彭紅楓和譚小玉等[36]構建了人民幣國際化總量指數,并細分為絕對程度和相對程度兩種指數,然后,通過面板回歸模型和Bootstrap面板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仍然處于較低水平,但發展態勢良好,受制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水平較低等限制性因素,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到了阻礙。因此,他們認為,在保持經濟和貿易穩定增長的條件下,中國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同時,要進一步加強金融市場建設,提高金融體系運行效率和市場監管有效性,為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創造有利條件。
李政[37]采用滾動的協整VAR模型來構建動態的總體溢出指數、方向性溢出指數和信息溢出表,從三個層面研究“811匯改”的影響。最后發現:第一,整個匯率價格體系的總體溢出在“811匯改”后呈現明顯上升趨勢,系統的聯動水平顯著提高;第二,在“811匯改”之前,自2013年以來,中間價格與其他價格之間的方向性溢出在不斷減低,“811交易所改革”后,中間價格的方向溢出有明顯的上升趨勢;第三,“811匯改”后中間價格與單個匯率價格之間的溢出結構產生明顯的改變,CNY等在岸市場的影響更加突出;第四,在“811匯改”后,中間價接受信息溢出的規模基本沒有改變。因此,他們認為應該在適當的時候逐步優化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報價機制,并強調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對其他價格的影響,進一步加強中間價格的基準地位。
楊榮海和李亞波[38]對我國的資本開放度進行了多角度計算,并采用“貨幣錨”模型來衡量貨幣國際化程度,將模型數據分為2001第一季度~2009第四季度、2010第一季度~2015 第一季度兩個階段,進而研究了資本開放的影響以及人民幣國際化“貨幣錨”的現狀。最終研究結果表明,人民幣已然成為全球大多數國家,尤其是與中國有密切經濟往來國家的“貨幣錨”,如果中國繼續推進資本賬戶的開放進程,這將加快人民幣“貨幣錨”的進程。因此,中國應當對資本賬戶開放持穩健態度,逐漸讓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經濟往來中,優先使用人民幣作為計價、結算、儲備和投資貨幣。
鄧富華和霍偉東[39]使用2009年至2014年期間,包括中國在內的178個國家或地區的跨國面板數據,并利用Heckman的兩階段選擇模型和傾向得分匹配方法來克服樣本的自選偏差,深入研究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在解決人民幣跨境貿易中的作用。研究發現,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有利于增加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的使用。其中,服務貿易協定的促進作用更強;對“南北型”FTA的提升作用要大于對“南南型”FTA的提升。因此他們認為,中國應當加快推進國內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逐步完善國內體制機制的改革,有效對接國際經貿新規則,建立自由貿易區戰略的重要保障,同時注重與發達國家的談判,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陳創練等[40]構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同時包含利率改制、匯率波動與國際資本流動的理論模型,并采用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模型(TVP-VAR)模型動態地刻畫變量隨時間變遷的互動時變機理。研究表明,利率限制了匯率和國際資本流動的傳導;匯率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相對平穩;國際資本流動的匯率相對較強。因此他們認為,應當科學合理地開放資本賬戶,有序推進我國利率改制、匯率改革,最后實行資本賬戶開放政策。
[參考文獻]
[1] 王少平,楊洋.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與經濟新常態的數量描述[J].經濟研究,2017,52(6):46-59.
[2] 陶新宇,靳濤,楊伊婧.“東亞模式”的啟迪與中國經濟增長“結構之謎”的揭示[J].經濟研究,2017,52(11):43-58.
[3] 馬勇,陳雨露.金融杠桿、杠桿波動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7,52(6):31-45.
[4] 劉瑞翔,顏銀根,范金.全球空間關聯視角下的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7,52(5):89-102.
[5] 邵宜航,李澤揚.空間集聚、企業動態與經濟增長:基于中國制造業的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7(2):5-23.
[6] 白俊紅,王鉞,蔣伏心,李婧.研發要素流動、空間知識溢出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7,52(7):109-123.
[7] 項后軍,巫姣,謝杰.地方債務影響經濟波動嗎[J].中國工業經濟,2017(1):43-61.
[8] 仝冰.混頻數據、投資沖擊與中國宏觀經濟波動[J].經濟研究,2017,52(6):60-76.
[9] 方福前,邢煒.經濟波動、金融發展與工業企業技術進步模式的轉變[J].經濟研究,2017,52(12):76-90.
[10] 高然,龔六堂.土地財政、房地產需求沖擊與經濟波動[J].金融研究,2017(4):32-45.
[11] 王頻,侯成琪.預期沖擊、房價波動與經濟波動[J].經濟研究,2017,52(4):48-63.
[12] 邵全權,王博,柏龍飛.風險沖擊、保險保障與中國宏觀經濟波動[J].金融研究,2017(6):1-16.
[13] 張翔,劉璐,李倫一.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金融化與中國宏觀經濟波動[J].金融研究,2017(1):35-51.
[14] 賈俊雪.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與全要素生產率:基于異質企業家模型的理論分析[J].經濟研究,2017,52(2):4-19.
[15] 朱軍.技術吸收、政府推動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J].中國工業經濟,2017(1):5-24.
[16] 余泳澤.異質性視角下中國省際全要素生產率再估算:1978—2012[J].經濟學(季刊),2017,16(3):1051-1072.
[17] 程惠芳,陳超.開放經濟下知識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國際經驗與中國啟示[J].經濟研究,2017,52(10):21-36.
[18] 蔡躍洲,付一夫.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中的技術效應與結構效應——基于中國宏觀和產業數據的測算及分解[J].經濟研究,2017,52(1):72-88.
[19] 宣燁,余泳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研究——來自230個城市微觀企業的證據[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7,34(2):89-104.
[20] 黃先海,金澤成,余林徽.要素流動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來自國有部門改革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7,52(12):62-75.
[21] 蘇治,方彤,尹力博.中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聯性——基于規模和周期視角的實證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17(8):87-109.
[22] 歐陽志剛,薛龍.新常態下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對特征企業的定向調節效應[J].管理世界,2017(2):53-66.
[23] 程方楠,孟衛東.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搭配——基于貝葉斯估計的DSGE模型[J].中國管理科學,2017,25(1):11-20.
[24] 馬勇,張靖嵐,陳雨露.金融周期與貨幣政策[J].金融研究,2017(3):33-53.
[25] 袁越,胡文杰.緊縮性貨幣政策能否抑制股市泡沫?[J].經濟研究,2017,52(10):82-97.
[26] 何國華,李潔.跨境資本流動、金融波動與貨幣政策選擇[J].國際金融研究,2017(9):3-13.
[27] 孫國峰,何曉貝.存款利率零下限與負利率傳導機制[J].經濟研究,2017,52(12):105-118.
[28] 汪昊,婁峰.中國財政再分配效應測算[J].經濟研究,2017,52(1):103-118.
[29] 陳登科,陳詩一.中國財政支出乘數研究——基于金融摩擦與“超低利率”的視角[J].金融研究,2017(12):17-32.
[30] 李丹,龐曉波,方紅生.財政空間與中國政府債務可持續性[J].金融研究,2017(10):1-17.
[31] 王瑞民,陶然.中國財政轉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應:基于縣級數據的評估[J].世界經濟,2017,40(12):119-140.
[32] 王方方,李寧.我國財政政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時變效應[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7,34(11):132-147.
[33] 席鵬輝,梁若冰,謝貞發,蘇國燦.財政壓力、產能過剩與供給側改革[J].經濟研究,2017,52(9):86-102.
[34] 谷成,曲紅寶.財政政策、腐敗與經濟增長:理論分析與現實考察[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7(4):70-83.
[35] 于恩鋒,龔秀國.人民幣“入籃”對SDR利率的影響——基于歷史的視角[J].國際金融研究,2017(1):78-88.
[36] 彭紅楓,譚小玉.人民幣國際化研究:程度測算與影響因素分析[J].經濟研究,2017,52(2):125-139.
[37] 李政.“811匯改”提高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基準地位嗎?[J].金融研究,2017(4):1-16.
[38] 楊榮海,李亞波.資本賬戶開放對人民幣國際化“貨幣錨”地位的影響分析[J].經濟研究,2017,52(1):134-148.
[39] 鄧富華,霍偉東.自由貿易協定、制度環境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J].中國工業經濟,2017(5):75-93.
[40] 陳創練,姚樹潔,鄭挺國,歐璟華.利率市場化、匯率改制與國際資本流動的關系研究[J].經濟研究,2017,52(4):6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