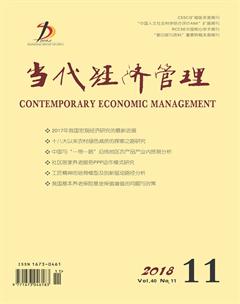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析
丁存振 肖海峰

摘 要 根據(jù)聯(lián)合國商品貿(mào)易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庫數(shù)據(jù),通過靜態(tài)和動態(tài)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指數(shù)從整體和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兩個層面分析了1995~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狀況。結(jié)果表明:中國與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以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為主,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輔,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雖然不高,但總體呈現(xiàn)逐漸上升趨勢;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以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且與中東歐地區(qū)和西亞及中東地區(qū)以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與其他地區(qū)以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統(tǒng)計(jì)期內(nèi)中國與沿線國家整體和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均主要來源于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中國與西亞及中東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主要由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引起,與其他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由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引起。
[關(guān)鍵詞]中國;“一帶一路”;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貿(mào)易規(guī)模
[中圖分類號]F752.7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8)11-0046-07
一、引 言
2000多年前的古代“絲綢之路”開辟了東西文化交流和貿(mào)易互通往來的通道,具有深遠(yuǎn)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多重影響的絲綢之路正在成為人們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絲綢之路經(jīng)濟(jì)帶”和“21世紀(jì)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倡議是新時期我國提出,積極應(yīng)對世界經(jīng)濟(jì)形勢變化、深化改革開放、統(tǒng)籌國內(nèi)外兩大市場的重大舉措(余妙志和梁銀鋒等,2016[1];何敏等,2016[2]),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yīng)。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付明輝和祁春節(jié),2016)[3]。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以下簡稱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總額達(dá)到595.26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貿(mào)易總額的25.62%。“一帶一路”的提出為我國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利契機(jī)(何敏等,2016)[2]。但現(xiàn)階段,有關(guān)“一帶一路”的研究,多關(guān)注能源、礦產(chǎn)、制造業(yè)等產(chǎn)業(yè),對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關(guān)注相對較少。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jìn),一些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雙方的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情況,如何敏等(2016)[2]利用RCA指數(shù)和TCI指數(shù)分析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競爭性和互補(bǔ)性,付明輝、祁春節(jié)(2016)[3]采用GL指數(shù)和RCA指數(shù)研究了2000~2014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區(qū)域結(jié)構(gòu)、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和比較優(yōu)勢等問題,部分學(xué)者注意到了各地區(qū)間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的重要性。
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持續(xù)加深使得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日漸盛行,并成為國際貿(mào)易的主要增長方式。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貿(mào)易與合作成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重要引擎,但有關(guān)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析較少,學(xué)者們僅從中國與單個國家或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齊曉輝和劉億,2015[4];佟光霽和石磊,2017[5])或靜態(tài)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的角度分析(付明輝和祁春節(jié),2016)[3],并沒有很好地解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的關(guān)系。故本文以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作為切入點(diǎn),借助靜態(tài)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測度指數(shù)(GL指數(shù))、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測度指數(shù)(GHM指數(shù))、動態(tài)的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指數(shù)(BI指數(shù))以及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測度指數(shù)(BI指數(shù)和HI指數(shù))從整體和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兩個層面較為全面地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狀況進(jìn)行分析,進(jìn)而為“一帶一路”背景下開展和深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間的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提供理論基礎(chǔ)及現(xiàn)實(shí)依據(jù)。
二、研究方法、研究范圍與數(shù)據(jù)說明
(一)研究方法
1.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測度指數(shù)——GL指數(shù)
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指數(shù)(Grubel-Lloyd指數(shù),簡稱GL指數(shù))由Grubel和Lloyd(1975)[6]提出,是目前通用的測度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的指標(biāo)(劉雪嬌,2013;馮宗憲和蔣偉杰,2017),本文運(yùn)用該指數(shù)測度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
2.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測度指數(shù)——GHM指數(shù)
根據(jù)貿(mào)易特征不同,可將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為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和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通過測度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可以反映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工格局。測度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常用的方法是Greenaway et al.(1994)[7]提出的GHM指數(shù):
3.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指數(shù)——BI指數(shù)
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指數(shù)(簡稱BI指數(shù))由Brülhart(1994)[10]提出,用于反映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的動態(tài)變化。本文運(yùn)用該指數(shù)測度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一段時期內(nèi)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的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
4.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測度指數(shù)——BI指數(shù)和HI指數(shù)
GHM指數(shù)為靜態(tài)的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指數(shù),無法衡量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的動態(tài)變化趨勢,為測度一段時期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的類型,本文采用Thom和McDowell(1999)提出的HI指數(shù)和BI指數(shù)比較法,其中BI指數(shù)為Brülhart(1994)[11]提出的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指數(shù),HI由式(6)計(jì)算:
當(dāng)BI大于HI時,說明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以水平型為主,反之,則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以垂直型為主。
(二)研究范圍
“一帶一路”是個開放區(qū)域,當(dāng)前還沒有準(zhǔn)確的空間范圍。借鑒以往學(xué)者(付明輝和梁銀鋒等,2015;何敏和張寧寧等,2017)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界定,將沿線國家劃分為6個地區(qū),共包括64個國家(見表1)。
(三)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主要采用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進(jìn)出口貿(mào)易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來源于UN Comtrade數(shù)據(jù)庫。根據(jù)以往研究,將SITC商品分類號前三位數(shù)相同的商品作為相同產(chǎn)品,前三位數(shù)相同商品的雙向貿(mào)易定義為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Grubel和Lloyd,1971)。依據(jù)SITC Rev.3分類標(biāo)準(zhǔn)界定的農(nóng)產(chǎn)品共包括4類、22章、66組農(nóng)產(chǎn)品,其中,0類為食品和活畜,共10章36組農(nóng)產(chǎn)品;1類為飲料和煙草,共2章4組農(nóng)產(chǎn)品;2類為非食用原料,農(nóng)產(chǎn)品為其中的7章共22組;4類為動植物油、油脂和蠟,共3章4組農(nóng)產(chǎn)品。
三、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析
(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規(guī)模和結(jié)構(gòu)
1.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規(guī)模不斷擴(kuò)大
根據(jù)UN Comtrade數(shù)據(jù)庫數(shù)據(jù),1995~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雙邊貿(mào)易額不斷擴(kuò)大,農(nóng)產(chǎn)品進(jìn)出口貿(mào)易總額從1995年的64.978 6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595.264 8億美元,增長了9.16倍,年均增長率8.76%;進(jìn)口總額從1995年的37.408 3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370.810 9億美元,增長了9.91倍,年均增長率9.14%;出口總額從1995年的27.570 3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224.453 9億美元,增長了8.14倍,年均增長率8.18%。進(jìn)口額增長速度高于出口額增長速度,因此貿(mào)易逆差也不斷擴(kuò)大,由1995年的9.838 0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146.357 0億美元(見表2)。
2.區(qū)域間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規(guī)模差異較大
通過表3可以看出在不同年份,各地區(qū)國家在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規(guī)模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區(qū)域性明顯。自1995年起,東南亞一直作為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各地區(qū)中貿(mào)易量最大的國家,2015年貿(mào)易量高達(dá)402.18億美元,占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量的67.56%,其次為蒙俄地區(qū),占比13.24%,再次為南亞(6.20%)、中東歐(6.08%)和西亞及中東地區(qū)(5.22%),占比最小的為中亞(1.69%)。從貿(mào)易額年均增長速度上看,各地區(qū)也表現(xiàn)出較大的不同,其中,年均增長速度最快的是中東歐地區(qū),約為17.86%,2015年的貿(mào)易額相比于1995年增長59.89倍,其次為南亞(10.68%)、西亞及中東地區(qū)(9.66%),再次為東南亞(9.05%)、蒙俄地區(qū)(8.97%),增長速度最慢的是中亞地區(qū),約為4.82%。
3.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類別較為集中
從2015年的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類別較為集中,從總體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主要集中在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約占農(nóng)產(chǎn)品總貿(mào)易額的53.08%,其次為2類(非食用原料)農(nóng)產(chǎn)品,約占農(nóng)產(chǎn)品總貿(mào)易額的34.39%,再次為4類(動植物油、油脂和蠟)農(nóng)產(chǎn)品,約占10.65%,最后是1類(飲料和煙草)農(nóng)產(chǎn)品,約占1.88%。分區(qū)域來看,六大地區(qū)中除蒙俄地區(qū)外,其他5個地區(qū)(中亞、東南亞、南亞、中東歐、西亞及中東)與中國最主要的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均集中在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僅是占比不同,其中,中國與西亞及中東地區(qū)的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中在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占比最高,高達(dá)59.97%。中國與六大區(qū)域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占前兩位的均為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和2類(非食用原料)農(nóng)產(chǎn)品,與總體情況相同(見表4)。
(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分析
1.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分析
表5顯示了1995~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從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區(qū)表現(xiàn)出略微的不同,但總體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以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為主,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輔,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雖然不高,但總體呈現(xiàn)逐漸上升趨勢。分區(qū)域來看,2015年中國除與蒙俄地區(qū)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與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他5個地區(qū)(中亞、東南亞、南亞、中東歐、西亞及中東)與中國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相比于1995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從2015年的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的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最高,GL值達(dá)到了0.304 3,其次為南亞地區(qū),GL為0.290 3。六大板塊中,與中國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發(fā)展最快的為南亞地區(qū),GL值由1995年的0.044 5增長至2015年的0.290 3。其次為西亞及中東地區(qū),GL值由1995年的0.066 0增長至2015年的0.229 5。
2.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分析
表6顯示了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可以看出各地區(qū)不同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不同。整體來看,中國除與蒙俄和中亞1類(飲料和煙草)為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之外,與其他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以及“一帶一路”其他地區(qū)各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均以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為主。具體來看,中國與蒙俄地區(qū)四類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并不高,但其1類(飲料和煙草)農(nóng)產(chǎn)品的GL指數(shù)高達(dá)0.74,表明中國與蒙俄地區(qū)的飲料和煙草主要以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其他幾類農(nóng)產(chǎn)品的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均不高,以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為主;與中亞地區(qū)1類(飲料和煙草)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GL指數(shù)為0.58,表明中國與中亞地區(qū)的飲料和煙草也主要以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2類(非食用原料)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也較高,GL指數(shù)為0.41,其他幾類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則較小,以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為主;與東南亞地區(qū)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GL指數(shù)為0.49,表明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食品和活畜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較高;而與其他3個地區(qū)(南亞、中東歐和西亞及中東)的各類產(chǎn)品的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都較低。
(三)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分析
1.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分析
表7顯示了1995~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的主要類型。從結(jié)果可以看出,中國與各地區(qū)不同年份表現(xiàn)出來的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并不相同,在多數(shù)年份中,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國家以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且與蒙俄地區(qū)、中亞地區(qū)、東南亞地區(qū)、南亞地區(qū)以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與中東歐地區(qū)和西亞及中東地區(qū)以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具體來看中國與不同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中國與蒙俄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GHM指數(shù)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由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轉(zhuǎn)變?yōu)榈唾|(zhì)量垂直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后又轉(zhuǎn)變?yōu)楦哔|(zhì)量垂直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中亞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GHM指數(shù)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變化趨勢,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由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轉(zhuǎn)變?yōu)楦咚降乃叫彤a(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之后再度轉(zhuǎn)變?yōu)楦哔|(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GHM指數(shù)同樣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但均表現(xiàn)為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由高質(zhì)量高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轉(zhuǎn)變?yōu)榈唾|(zhì)量垂直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后又轉(zhuǎn)變?yōu)楦哔|(zhì)量垂直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南亞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GHM呈不斷下降趨勢,但均大于1.25,說明中國與南亞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一直以來均以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中國與中東歐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GHM指數(shù)波動較為頻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由低水平的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轉(zhuǎn)變?yōu)楦哔|(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之后轉(zhuǎn)變?yōu)榈唾|(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2015年轉(zhuǎn)變?yōu)楦咚降乃叫彤a(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西亞及中東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GHM呈波動上升趨勢,多數(shù)年份里以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2015年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由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轉(zhuǎn)變?yōu)榈退降乃叫彤a(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
2.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分析
表8顯示了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從結(jié)果可以看出,中國與各地區(qū)不同種類的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不盡相同,但多數(shù)農(nóng)產(chǎn)品以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具體來看,中國與蒙俄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中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為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且為高水平的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1類(飲料和煙草)為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2類(非食用原料)和4類(動植物油、油脂和蠟)農(nóng)產(chǎn)品均為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中亞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中0類(食品和活畜)、1類(飲料和煙草)和4類(動植物油、油脂和蠟)農(nóng)產(chǎn)品為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0類(食品和活畜)、1類(飲料和煙草)為低水平的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4類(動植物油、油脂和蠟)為高水平的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2類(非食用原料)農(nóng)產(chǎn)品為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且為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四類產(chǎn)品均以為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其中1類(飲料和煙草)為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0類(食品和活畜)、2類(非食用原料)、4類(動植物油、油脂和蠟)為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南亞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四類產(chǎn)品均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其中0類(食品和活畜)為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1類(飲料和煙草)、2類(非食用原料)、4類(動植物油、油脂和蠟)為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中東歐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四類產(chǎn)品均以為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其中0類(食品和活畜)、1類(飲料和煙草)為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 2類(非食用原料)、4類(動植物油、油脂和蠟)為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中國與西亞及中東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四類產(chǎn)品均以為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其中0類(食品和活畜)、2類(非食用原料)為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 1類(飲料和煙草)、4類(動植物油、油脂和蠟)為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
(四)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析
1.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析
表9顯示了1995~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情況,從整體BI值可以看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主要由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引起,但各地區(qū)略有不同,其中,中國與蒙俄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BI值僅為0.040 5,說明其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中主要是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引起的,而中國與中亞、東南亞、南亞、中東歐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BI值均為0.25以上,與西亞及中東地區(qū)的BI值也達(dá)到了0.17,說明中國與其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中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析
表10顯示了1995~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各類農(nóng)產(chǎn)品在不同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是不同的。其中,對于東南亞來說,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BI值為0.25,說明其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中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起了部分作用,而其他幾類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中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的作用較大;對于其他地區(qū)來說,各類的BI值均小于0.20,說明中國與蒙俄、中亞、南亞、中東歐、西亞及中東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主要由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引起;從動態(tài)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指數(shù)BI和HI對比來看,除中亞地區(qū)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BI大于HI,其他各地區(qū)各品種的BI均小于HI,說明中國與大多數(shù)地區(qū)大多數(shù)種類的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來源于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而與中亞地區(qū)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則主要由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引起。
(五)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分析
表11為1995~2015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動態(tài)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以及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分析。首先,從BI指數(shù)上看,中國與各地區(qū)國家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BI指數(shù)均相對較小,說明中國與各地區(qū)國家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主要來源于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其次,從各地區(qū)BI指數(shù)的比較上看,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國家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BI指數(shù)最大,說明“一帶一路”地區(qū)中,中國與東南亞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中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作用最大。再次,從BI指數(shù)和HI指數(shù)比較上看,中國與蒙俄、中亞、東南亞、南亞以及中東歐地區(qū)的BI指數(shù)值均小于HI指數(shù)值,說明中國與這些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由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引起,中國與西亞及中東地區(qū)的BI指數(shù)值大于HI指數(shù)值,說明中國與西亞及中東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主要由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引起。
四、主要結(jié)論及啟示
本文通過靜態(tài)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測度指數(shù)(GL指數(shù))、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測度指數(shù)(GHM指數(shù))、動態(tài)的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指數(shù)(BI指數(shù))以及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測度指數(shù)(BI指數(shù)和HI指數(shù))從整體和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兩個層面較為全面地分析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狀況。結(jié)果表明:
第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以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為主,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輔,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雖然不高,但總體呈現(xiàn)逐漸上升趨勢;從與不同地區(qū)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類型看,中國除與蒙俄和中亞1類(飲料和煙草)為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之外,與其他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以及“一帶一路”其他地區(qū)各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均以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為主。
第二,從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以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且與蒙俄、中亞、東南亞以及南亞地區(qū)以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與中東歐和西亞及中東地區(qū)以低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從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類型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多數(shù)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以高質(zhì)量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為主。
第三,從整體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主要來源于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從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邊際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各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增量同樣主要由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引起。
第四,從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類型來看,中國與蒙俄、中亞、東南亞、南亞以及中東歐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由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引起,中國與西亞及中東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主要由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引起;從分類別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類型來看,中國與大多數(shù)地區(qū)大多數(shù)種類的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來源于垂直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而與中亞地區(qū)0類(食品和活畜)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增量則主要由水平型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引起。
基于以上研究結(jié)論,本文認(rèn)為在“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深入推進(jìn)國內(nèi)農(nóng)業(yè)“走出去”和“引進(jìn)來”的背景下,一方面,應(yīng)把握“一帶一路”發(fā)展機(jī)遇,構(gòu)建有效的農(nóng)產(chǎn)品合作機(jī)制,優(yōu)化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政策,加深與沿線國家農(nóng)業(yè)領(lǐng)域合作。另一方面,當(dāng)前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雖以產(chǎn)業(yè)間貿(mào)易為主,但應(yīng)加強(qiáng)雙邊互利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的發(fā)展,提升與沿線國家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水平;在促進(jìn)與沿線國家高質(zhì)量的垂直型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的基礎(chǔ)上,發(fā)揮與不同地區(qū)國家比較優(yōu)勢,積極發(fā)展水平型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
[參考文獻(xiàn)]
[1] 余妙志,梁銀鋒,高穎. 中國與南亞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的競爭性與互補(bǔ)性——以“一帶一路”戰(zhàn)略為背景[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6,37(12):83-94,112.
[2] 何敏,張寧寧,黃澤群.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競爭性和互補(bǔ)性分析[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6(11):51-60,111.
[3] 付明輝,祁春節(jié).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現(xiàn)狀與比較優(yōu)勢分析[J].世界農(nóng)業(yè),2016(8):180-185.
[4] 齊曉輝,劉億. 中國與中亞5國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內(nèi)貿(mào)易研究[J]. 世界農(nóng)業(yè),2015(7):29-34.
[5] 佟光霽,石磊. 基于產(chǎn)業(yè)內(nèi)的中俄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實(shí)證分析[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問題,2017,38(6):89-100.
[6] GRUBEL H G,LLOYD P J. 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5,6(3):312-314.
[7] GREENAWAY D,HINE R,MILNER C. Country-Specific Factors and the Pattern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 the UK[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94,130(1):77-100.
[8] AZHAR A K M,ELLIOTT R J R. On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in Intra-Industry Trade[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6,142(3):476-495.
[9] BOJNEC,STEFAN. Pattern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 Products During Transition[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01,39(1):61-89.
[10] BR?譈LHART M.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Measurement and Relevance for the Pattern of Industrial Adjustment[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994,130(3):600-613.
[11] THOM R,MCDOWELL M. Measuring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9,135(1):4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