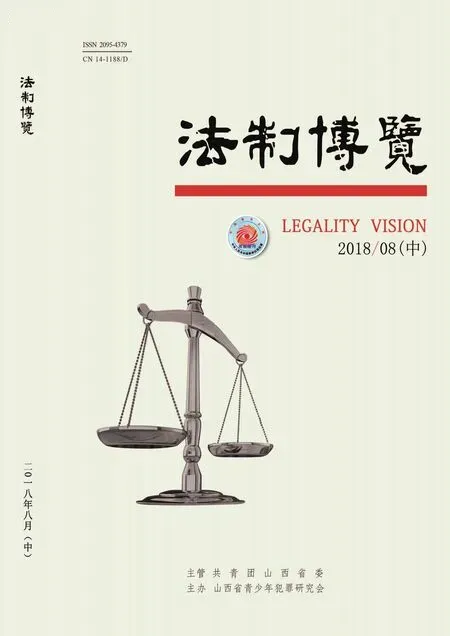論跨境網購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
任玉嬌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631
一、建構跨境網購消費者合同法律適用規則的必要性
(一)《法律適用法》第42條的進步與局限
《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以下簡稱《法律適用法》)第42條規定,消費者可以在商品、服務提供地或消費者經常居所地中進行選擇,從而適用選擇的法律對其進行保護,這與《法律適用法》第41條的立法理念不同。第41條體現的是合意選擇,而第42條是單方選擇。民事活動中的“意思表示”尤為重要,尤其在合同這一需要雙方意思表示達成一致的民事法律行為中,更加必要。當事人對法律適用所達成的合意選擇,也應當得到尊重。因此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1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這種選擇最為優先,選擇的范圍也相當廣泛,當事人可以選擇與合同有聯系地的法律,如合同訂立地、合同履行地或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等等,也可以選擇其他與合同沒有絲毫關系的其他任意國家、地區的法律,不論選擇的法律對當事人的保護水平是高還是低。
而消費者合同與普通合同有很大不同,具有其特殊性。消費者作為合同當中的弱方當事人,應當給與特殊的照顧,這在國際私法中被稱為弱者地位的保護,因此純粹的“當事人意思自治”這一立法理念并不適合消費者合同,更為恰當的是賦予消費者更為有利的地位。《法律適用法》第42條確實賦予了消費者更為有利的地位,即消費者單方選擇的權利,這使得消費者可以在經常居所地法律或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中進行選擇,此種單方選擇改變了“當事人意思自治”這一傳統的連接因素,限制了合同關系中的強者,將權力讓渡給了合同關系中的弱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合同關系因地位強弱不等而導致的某些不公平結果,這種理念無疑是我國國際私法立法的一次進步。
《法律適用法》第42條雖然在立法理念上有所進步,體現了對消費者弱者地位的保護,但是評價法條不應只從立法理念出發,而更應該從多方面予以評價。下文從法條適用的結果、適用過程可能出現的情況兩方面予以分析,判斷第42條保護消費者弱者地位這一立法理念是否能夠實現。
首先,從法條適用的結果維度分析。《法律適用法》中的弱者不僅出現在第42條,還分別出現在第25條、第29條以及第30條。不論這些主體成為“弱者”的原因如何,《法律適用法》均不同程度的對他們進行了保護,但第42條與其余三條有所不同。第25條、第29條、第30條均出現了“有利于保護”這一表述,如第30條規定,“監護,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國籍國法律中有利于保護被監護人權益的法律。”此種規定所適用的法律,必然是其中保護水平相對較高的那一個,這從結果上體現了對被監護人的保護。但是第42條并沒有出現“有利于保護”消費者這樣的表述,條文僅僅賦予了消費者單方選擇權,單方選擇權是否真正“有利于保護”消費者,有待商榷。消費者在沒有專業知識和專業指導之下所選擇的法律,并不一定有利于對其自身權益的保護。若消費者選擇了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那么即使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法律對其保護更為有利,也不會予以適用,而只能適用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也即不論消費者選擇的法律保護標準高或低,都將直接適用其選擇的法律,這種狀況下,第42條并沒有真正地保護作為弱方當事人的消費者。
其次,從法條適用過程可能出現的情況這一維度分析。在消費者合同中,尤其在跨境網購消費者合同中,經營者極有可能通過格式條款確定法律適用法。此時,消費者若簽訂了該合同,便做出了法律適用的選擇。此種情形雖然從表面來看,可以視為消費者的選擇,但是實質卻是純粹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在消費者合同中,應當對作為弱者的消費者進行保護,但是沒有限制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將其重新置回弱者的身份,此種狀況下消費者失去了被保護的機會。這與第42條的立法理念相悖。再者,一般經營者在格式合同中確定的法律適用法對經營者更有利,消費者的被動選擇,導致其適用了對自身不利的法律,而第42條并沒有對此進行限制,這種結果與國際私法保護弱者地位的理念相悖。如某經營者在格式合同中確定商品、服務提供地法為法律適用法,但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法更有利于對該消費者的保護,該消費者簽訂了格式合同,即放棄了對其更有利的適用法的保護。
(二)跨境網購適用《法律適用法》第42條的矛盾
《法律適用法》第42條規定,若消費者選擇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則適用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若經營者在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沒有從事相關經營活動,則適用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這里有兩個概念:“商品、服務提供地”和“從事相關經營活動”,如何理解這兩個概念非常重要,但法律并沒有明確的解釋。在網購中,商品、服務提供地不同于普通消費者合同中的商品服務提供地,必須做其他理解。本文做如下嘗試:
1.商品、服務提供地為可能購買地,也即商品能到達地。可能購買地指的是商品售出的對象地,也就是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地點,不特定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地點,其實就是商品服務能夠被提供到的地點。如果將商品服務提供地做以上理解,會有以下結果:一、消費者選擇適用的法律范圍過廣。只要網絡能夠到達之處,即為商品服務提供地,但是相對于發生糾紛的這一特定消費者合同而言,并不是所有的商品服務提供地都與之有關聯。如果不對消費者選擇的范圍加以限制,就加大了經營者承擔法律責任的很多不確定性。二、假設經營者在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沒有從事相關經營活動,法律適用的結果是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但是適用哪一個商品、服務提供法律,這種選擇由誰決定,選擇的依據是什么,會帶來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因此,將商品、服務提供地理解為可能購買地或商品能到達地,以此適用第42條會產生很多矛盾。
2.商品、服務提供地為商品存儲地。網購在發展,快遞業也隨之發展,電商平臺為了加快商品到貨的速度,紛紛建立了倉庫以儲存商品。當消費者購買商品后,能夠提供商品的地點,是倉庫地,因此將商品、服務提供地理解為商品存儲地。消費者合同成立后,經營者一般就近發貨,如果最近的倉庫沒有此類商品,一般選取其他倉庫的商品進行發貨,因此商品存儲地不限于一地。當商品、服務提供地有多個的時候,論述過程與結果同上,矛盾重重。
3.商品、服務提供地為實體店。網購打擊了線下市場交易,很多商家迅速改變銷售策略,采用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進行銷售,當消費者通過網購購買商品時,其實商品、服務提供地為線下的實體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網絡經營者都經營實體店,事實上大多數商家并沒有實體店,另外,當某些經營者經營的實體店為多家,且處不同國家時,又會產生第一點論述的問題,依舊矛盾重重。
綜上所述,跨境網購消費者合同直接適用《法律適用法》第42條矛盾重重,有必要建構跨境網購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
二、如何建構跨境網購消費者合同法律適用規則
(一)對美國《統一計算機信息交易法》相關內容的分析
1.立法者認為在信息交易中,選擇法律的權利極其重要。當事人不熟悉彼此國家法律時,即使選擇與交易無任何關系的中立第三方國家的法律也在情理之中。但從《統一計算機信息交易法》第104條可以得知,當事人協議選擇法律并不是完全不受限制,即該選擇不得違反直接適用的法律,特別是公共基本政策。
2.第109條(b)款規定,一些特殊的合同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時,確定適用的法律。如訪問合同或規定拷貝的電子交付合同,比較難確定信息提供方所在地,即便可以通過網址獲得也無法確認其真實性,但許可方所在地卻容易確定,因此應適用締約時許可方所在地的法律。
(二)對歐盟《電子商務指令》相關內容的分析
《歐盟電子商務指令》第2條規定,當某網上商人在該成員國內注冊機構時,應遵守的法律是信息供應商本國的法律,其他成員國的法律對該信息供應商的活動無效。此規定不僅明確了法律適用,而且防止了公司在其他規定較松的成員國設立服務器的現象,從而防止規避所在地的法律。根據《歐盟電子商務指令》第3條,可知信息服務應當受到信息提供者機構所在國家的法律管轄。
(三)建構跨境網購消費者合同法律適用規則的建議
通過上述國外相關立法之比較,本文認為跨境網購消費者合同的法律適用規則應當為:網購消費者合同,適用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沒有協議選擇的,適用當事人所在地的法律。訪問合同或規定拷貝的電子交付合同,適用締約時許可方所在地的法律;要求以有形介質交付拷貝的消費者合同應適用向消費者交付拷貝的地方或本應向消費者交付拷貝的地方的法律。
如果當事人所在地的法律更有利于消費者,則適用當事人所在地的法律。當事人所在地指:于經營者而言,在其只有一個營業地時,為營業地;在有一個以上營業地時,為管理中心所在地;在沒有營業地時,為其成立地或主要注冊地。在其他情況時,為其主要居所地。于消費者而言,指消費者經常居所地。兩者比較,適用對消費者最有利的法律。
上述規定可以解釋為:一、消費者和經營者有選擇法律的權利,但是這種選擇權受到限制。一方面這種選擇對于經營者來說并不存在不確定性,就避免了消費者選擇范圍過大的問題;另一方面,這種選擇傾向于保護消費者,選擇的法律對消費者的保護不得低于當事人所在地法律的保護水平。二、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時,特殊合同特殊規定,如果當事人所在地法律更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則適用當事人所在地的法律。而一般合同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時,適用當事人所在地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