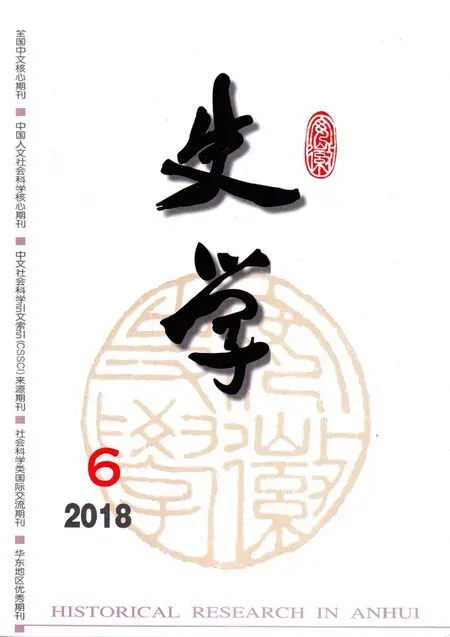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政黨的改造與變質
張 東
(中山大學 歷史學系,廣東 廣州 510275)
近代日本政治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發展,從藩閥政治到大正民主、政黨政治,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經過“舉國一致”內閣而過渡到法西斯統治。各政治階段的特征固然重要,階段間轉換的過程與邏輯亦不能忽視。對于日本法西斯統治的形成,學界多關注軍部與右翼勢力的沖擊、天皇制的精神構造、意識形態統制等,但對于政黨在此過程中的處境及應對等方面的研究不夠充分。[注]國內代表性專著有楊寧一:《日本法西斯奪取政權之路: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研究與批判》,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崔新京、李堅、張志坤:《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蔣立峰、湯重南:《日本軍國主義論》上、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代表性論文有李玉:《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形成及其特點》,《世界歷史》1984年第6期;李玉:《三十年代日本急進的法西斯主義運動與中間階層》,《世界歷史》1987年第3期;武寅:《三十年代日本財閥與法西斯勢力的關系》,《世界歷史》1985年第11期;高洪:《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的精神專制》,《日本學刊》2005年第4期;張勁松:《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思想專制述論》,《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構成》,《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徐平:《戰前日本軍部法西斯體制確立原因新探》,《日本學刊》1991年第3期;張景全:《二戰前日本的現代化與法西斯化》,《日本問題研究》2012年第1期;胡月:《論日本法西斯統治的“國民組織化”》,《沈陽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等。政黨是堅持抗爭以求恢復憲政之道?還是追隨軍部甘愿做政治配角?抑或洞悉政治趨勢爭取主動?考察九一八事變后政黨的自覺與自主意識,對于我們理解日本法西斯統治的形成與構造是至關重要的。
一、政黨聯合及其破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社會中的法西斯氣氛濃厚,10月發生的“錦旗革命事件”更刺激了軍隊中青年將校的激進思想[注]又稱“十月事件”,1931年10月發現的軍部激進派政變計劃,陸軍的橋本欣五郎等櫻會干部與民間右翼的大川周明、西田稅等聯合,動員步兵、海軍航空隊等人,試圖暗殺若槻禮次郎首相,推舉荒木貞夫組成軍人內閣。,使之“轉向國體原理探尋‘革新’之道”,同時,也使井上日召、橘孝三郎等民間右翼分子“確信軍中有政變計劃,認為時機已到準備行動”。[注]斎藤三郎:『右翼思想犯罪事件の綜合的研究:血盟団事件より二·二六事件まで』,東京:司法省刑事局1936年版,第123—128頁。
鑒于局勢,政黨內有提出“聯合內閣”論者,如內務大臣安達謙藏稱:“民政黨單獨內閣不足以駕馭議會,不應再拘泥于一黨一派”,“借此機會舉國一致,修正原有政策”。[注]立憲民政黨史編纂局編:『立憲民政黨史』下巻,東京:立憲民政黨編纂局1935年版,第894—895、898、899頁。起初,若槻禮次郎首相對此表示認同,認為“關東軍無視政府命令,或是因為政黨內閣是一黨一派,只代表了部分國民意見”。[注]若槻禮次郎:『明治·大正·昭和政界秘史:古風庵回顧録』,東京:読売新聞社1950年版,第383—384頁。但在隨后的議員懇談會上,若槻禮次郎首相認為“聯合內閣”是“無責任的表現”,不同政黨聯合組閣會使政策紊亂。[注]立憲民政黨史編纂局編:『立憲民政黨史』下巻,東京:立憲民政黨編纂局1935年版,第894—895、898、899頁。21日,安達謙藏公開聲明:“基于國民信念與決意,有必要政黨聯合組成國民內閣”。[注]立憲民政黨史編纂局編:『立憲民政黨史』下巻,東京:立憲民政黨編纂局1935年版,第894—895、898、899頁。翌日,山道襄一干事長不得不向全國各支部及所屬議員發出通告,安撫人心,“聯合內閣”問題暫告一段落。但由于安達謙藏堅持主張,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首相以內閣不統一為由辭職。
1931年12月13日,犬養毅內閣成立。翌年2月的眾議院議員選舉中,政友會獲得大勝,犬養毅首相信心滿滿:“內閣的政策綱領得到了國民絕對信任”。[注]犬養毅伝刊行會編:『犬養毅伝』,東京:犬養毅伝刊行會1932年版,第366頁。但實際上,由于腐敗、政策無力及選舉舞弊等,此時民眾對政黨的態度十分消極,“中央及地方議會的憲政精神變弱,國民對議會的感情日漸消退”[注]永井柳太郎編纂會:『永井柳太郎』,東京:勁草書房1959年版,第339頁。,“政友會與民政黨好像突然間就成了國民之仇敵”。[注]鈴木梅四郎:『政界の根本的浄化』,東京:実生活社出版部1932年版,第15—16頁。及至5月,發生了五一五事件[注]5月15日,青年海軍將校10名、陸軍士官候補生1名、農民決死隊部分成員等,分別襲擊永田町首相官邸、政友會本部、牧野內大臣官邸、日本銀行、警視廳、三菱銀行以及東京市區周圍的變電所,首相犬養毅被殺。,政黨政治就此結束。之后,政友會內部要求擁護憲政,但其呼聲“不過是對過去威勢的挽歌”。[注]野村重太郎:『軍部·官僚·政黨:政界の三大勢力を解剖す』,東京:今日の問題社1936年版,第34頁。而且,五一五事件的兇犯得到輿論同情:“青年人士作為忠良國民用非常手段打破現狀是可以諒解的”[注]精華書房:『五·一五事件と各紙の論調』上巻,東京:精華書房1932年版,第2頁。,陸軍方面的公訴狀也寫道:“政黨財閥及特權階級腐敗墮落,忘卻國家存立之本,輕視國防,紊亂國政,外失國威,內則國民精神頹廢,農村疲敝”[注]九州日報社編輯局編:『五·一五事件:陸海軍公判記録』,福岡:九州日報社1933年版,第63頁。,隨后在軍隊及各地方掀起的“減刑請愿運動”更使政黨陷于被動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輿論中流行“非常時”一詞,它泛指經濟危機、持續擴大的對華侵略以及國際上的日益孤立等內外局勢。1933年前后,部分輿論認為“非常時”已經緩和,尤其是政友會,希望恢復“憲政常道”。而軍部則有意強化“非常時”的危機意識:“有人認為‘非常時’是捏造的或虛幻的,否定其存在,這是不懂內外時勢、或茍且偷安缺乏進取心、或有不純動機拒絕改變現狀之表現”。[注]陸軍省新聞班:『非常時に対する我等國民の覚悟:日露戦後三十年』,1935年版,第29頁。對此,1933年10月,政友會的浜田國松在日比谷公會堂批判軍部“獨斷而無視輿論,破壞民眾自由與國家秩序”。[注]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の國家構想 1871—1936』,東京:巖波書店1996年版,第225頁。
為扭轉局面維持政治地位,政友會與民政黨先后有三次聯合。
1932年5月26日,海軍大將齋藤實組閣,標榜“不偏一黨一派,舉國一致,尊重議會,重視政黨,排除弊病以革新政界”[注]池田美代二:『新日本の展望』,東京:國民教育會1936年版,第101—102頁。,政友會與民政黨表示支持。但在10月,齋藤實內閣召開五相會議(首相、陸相、海相、藏相、外相)[注]五相會議,是因為“我國行政機構分化,閣僚過剩,閣內不統一的弱點”,五一五事件后,為“克服閣僚過剩的內閣制度缺陷”,齋藤內閣成立初,即有內務、大藏、商工、農林、鐵道等五大臣會議。參見:山崎丹照:『內閣制度の研究』,東京:高山書院1943年版,第404—414頁。,調整國防、外交與財政,以及編成來年預算,政黨被排除在決策之外。政友會與民政黨心有不滿,欲借此契機謀求聯合。兩黨以反法西斯、擁護議會政治、恢復政黨信譽為口號展開交涉,政友會以文相鳩山一郎、久原房之助、望月圭介等為中心,民政黨以富田幸次郎、俵孫一等為中心。而在12月9日,陸軍省發表“軍民離間”聲明:“關于最近預算問題,不少‘軍民離間’的言論,或認為1936年危機是軍部的宣傳、或認為過去戰役中戰死的都是民眾而無高級指揮官、或認為軍部為了軍事預算犧牲農林問題等,試圖破壞民眾的國防意識”,“誘導農村對軍部的反感,危及國防及國家安全”(海軍當局亦聲明同意),這更加速了兩黨聯合。
齋藤實內閣為維持“舉國一致”,同時避免政黨舉措刺激軍部,委派中島久萬吉商相出面斡旋兩黨聯合。12月25日,兩黨干部召開懇談會,出席者有政友會的床次竹二郎、望月圭介、久原房之助、山本條太郎,民政黨的町田忠治、賴母木桂吉、川崎卓吾等。中島久萬吉就兩黨聯合發出聲明:“一、現今國民對政黨缺乏信任,此為更始一新之秋,政民兩黨忘卻以前干戈,舍棄一黨一派轉而合作;二、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疏通意見,協力應對時局。”[注]白木正之:『日本政黨史 昭和篇』,東京:中央公論社1949年版,第173頁。
然而,政友會與民政黨并無具體的聯合對策,此后不久,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再次提出“憲政常道”,主張政黨單獨組閣。隨著中島久萬吉商相辭職、政友會內部因綱紀問題出現混亂及派系對立加劇,民政黨也趁機煽動紛爭,1934年3月,政友會禁止干部出席第三回聯合懇親會,兩黨第一次聯合即告失敗。
1934年7月,齋藤實內閣辭職,岡田啟介繼任組閣,民政黨參與政權而政友會在野。面對即將到來的臨時議會,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表示有意再啟政民聯合,久原房之助與山本條太郎作為交涉委員向民政黨提出協議。而在10月1日,陸軍省新聞班發布了《國防的本義及其強化的提倡》,要求國民“貫徹盡忠報國之精神,養成為國而忘我精神,芟除無視國家之國際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真正達至舉國一致精神”。[注]陸軍省新聞班:『國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934年版,第15頁。該冊子引起日本社會各界熱議,政黨表示不滿。10月2日,民政黨在干部會上決議:“在憲政國家,陸軍發表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等指導意見,著實令人吃驚”;政友會亦在3日的總務會上表示反對軍部變革經濟機構并使國家統制一元化的建議,認為軍部有壓迫其他機構之嫌。[注]近代日本史研究會編 :『満洲事変前後』,東京:白揚社1943年版,第254頁。
11月,政友會的久原房之助、山本條太郎,民政黨的富田幸次郎、賴母木桂吉等4人作為交涉委員發表聯合聲明:“清算以前感情與行動,排除政權爭奪、黨派舊弊”,“支持舉國一致,研討適當國策”。[注]立憲民政黨史編纂局編:『立憲民政黨史』下巻,第975頁。29日,兩黨所屬議員在議院內食堂舉行懇談會,山本條太郎稱兩黨聯合猶如明治維新時的薩長聯合,“其歷史意義將會永久銘記在我國憲政史上”。[注]政友會卅五年史編纂部編:『政友會卅五年史』,東京:政友會卅五年史編纂部1935年版,第418頁。同時,兩黨會見軍部、財界代表,交換意見,自省以求恢復信譽。
但兩黨政策、尤其是對農村政策有其差異,1934年11月,在第66回議會上,政友會議員提出“爆彈動議”[注]在眾議院的預算總會上,政友會的東武提出緊急動議,討論災害追加預算問題,要求中止審議。,不僅使內閣措手不及,民政黨等亦感到吃驚、意外和憤怒。與此同時,12月,岡田啟介內閣決議設置內閣審議會,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明確反對,望月圭介、秋田清、水野錬太郎等3人因加入審議會而選擇退黨,但民政黨企圖利用審議會加強與內閣合作,強化政策實施,黨內也開始反對兩黨聯合。在1935年“天皇機關說事件”中,政友會借機攻擊岡田啟介內閣,在倒閣問題上,兩黨分歧更為明顯。6月,民政黨干事長川崎卓吾向政友會干事長松野鶴平正式告知決裂。政友會加強在野黨意識,標榜“憲政常道”,兩黨繼續對立,第二次聯合亦無果而終。
1936年二二六事變后,廣田弘毅組閣,寺內壽一出任陸相,試圖以“廣義國防”、“庶政一新”擺脫自由主義與“姑息因循”。[注]本城広信:『今次の異動に見る陸軍の新動向と庶政革新』,東京:秀光書房1936年版,第2頁。9月,寺內壽一陸相與永野修身海相共同向內閣提出《行政機構改革意見書》,要求“明征國體觀念”、“暢達民意”[注]三浦徹:『軍部·官僚·政黨第七十議會を衝く』,東京:明報社1936年版,第34、32、33頁。,實則欲縮小議會權限。政黨對此表示不滿,11月7日,社會大眾黨聲明:“這不是革新,而是舊軍閥的反動”。[注]三浦徹:『軍部·官僚·政黨第七十議會を衝く』,東京:明報社1936年版,第34、32、33頁。民政黨少壯派主張抵抗,70多名議員結成“憲政擁護有志議員會”,決議:“宣揚立憲政治本義,消滅法西斯思想;排斥現役軍人干政;發揮議會和政黨機能”。[注]三浦徹:『軍部·官僚·政黨第七十議會を衝く』,東京:明報社1936年版,第34、32、33頁。11月、12月,政友會與民政黨在各地召開大會“確立政黨政治”、“反對現役軍人干政”。翌年5月19日,兩黨聯合召開協議會,并設置“倒閣本部”,之后兩黨召開大會,有500多人參加。但隨著廣田弘毅內閣及其后任林銑十郎內閣辭職,兩黨即失去抗爭對象。《讀賣新聞》在11月18日批判政黨對民眾的啟蒙太少,認為“有必要在全國掀起護憲運動”,“政黨今日處于守勢,與民心隔離,只有改正這一點,方是護憲之道”。[注]海津澄夫:『軍部と議會政治の動向』,東京:有恒社1936年版,第26頁。兩黨雖然表現激憤并發表聲明,但依舊延續其“不作為”風格,最后一次聯合同樣沒有取得實質成果。
二、從政黨“大同團結”到一國一黨
1932年5月政黨政治結束后,“舉國一致”成為日本政治上的“大義名分”,這雖有助于政黨間休止政爭、聯合共處,但也使政黨內統制成為問題,尤其像派閥對立的政友會。此時,政友會內主要有鈴木喜三郎的總裁派、反總裁派的床次竹二郎派、久原房之助派及舊政友會派,各自成員間又有一定流動性,床次竹二郎、久原房之助為應對時局,基于原有觀念而提出政黨改造主張。[注]床次竹二郎(1866—1935),近代日本官僚、政治家,1913年任鐵道院總裁,翌年加入政友會,歷任內相、鐵道相、郵政相等,1924年脫離政友會成立政友本黨,五年后重回政友會,1934年因違反黨的決議加入岡田啟介內閣,再被除名。久原房之助(1869—1965),近代日本實業家、政治家,創立久原礦業所,金融恐慌后加入政友會,歷任郵政相、政友會干事長、內閣參議等,1939年成為最后一任總裁,二戰后遭“公職追放”,后為日蘇及中日邦交恢復做出貢獻。
1933年12月,在第65回議會上,床次竹二郎發表“大同團結”演說:“最近形勢惡化,軍縮會議停頓,國聯機能喪失大半,各國經濟對立競爭激化”,認為日本應“立中庸大道,引導時勢,戒焦慮輕躁以免激化形勢”[注]床次竹二郎:『挙國一致論』,東京:國際経済研究所1934年版,第3、15—17頁。,同時注重政黨的作用:“議會政治下,政黨是自然存在的,不應受到排斥。為發揮議會機能,政黨自身必須探尋更生之道,革新議會政治”,因此他提出政黨“大同團結”,“不再拘泥于過去情感與細枝末節,直視國情,基于國政根本和國策之道,與軍部等政治勢力同心協力”,“避免激化社會對立的反軍部、反政黨及勞資沖突等事項,實現和諧統一”。[注]床次竹二郎:『挙國一致論』,東京:國際経済研究所1934年版,第3、15—17頁。
其實,早在1926年,床次竹二郎就批判日本政黨的私利權欲:“以巨額財力者為中心,附和勾結,以奪取政權為主”,稱之為“巨額本位”或“權勢本位”[注]床次竹二郎:『政黨の現在と將來政黨改造の重大時期』,1926年版,第12—13、13、14—15頁。,認為政黨應以政策為本位。他將政黨分為橫斷黨和縱斷黨,橫斷黨就是“各階級、民族自行團結起來形成政黨”,限于某一階級或民族,如勞動黨、農民黨、地主黨、商工黨、階級政黨等;縱斷黨是“沒有階級民族區別,各方同志集合形成政黨”[注]床次竹二郎:『政黨の現在と將來政黨改造の重大時期』,1926年版,第12—13、13、14—15頁。,以國民全體利益為目的。他認為“政黨應從全局出發,增進國家福利,不能囿于部分利害,調解勞資關系,公正裁決農民與工商的利害相爭,國民融合一體”,支持縱斷黨,因為“橫斷性組織不僅無用,反而誘發混亂糾紛”。[注]床次竹二郎:『政黨の現在と將來政黨改造の重大時期』,1926年版,第12—13、13、14—15頁。
基于歷史發展,床次竹二郎認為:“明治時代是在國際社會中發現自國的貧弱,發憤圖強,為建設強國而努力;大正時代是勃興之后的沉靜期,更注重內容而非形式,深刻反省,安靜沉思,積蓄思考;而昭和新時代是走出沉靜之山,再度邁進新興之域,從外到內發揚日本獨自的文化價值”。[注]床次竹二郎述:『全日本の青年諸君に告ぐ令旨拝戴満拾周年に方り』,東京:社會基調協會1930年版,第42—43頁。在昭和期的“新興之域”,其政黨的“大同團結”既要舍棄政黨之前的行徑與私情、消除政黨內的派系斗爭、政黨間的爭權奪利,還要與軍部等政治勢力實現合同協作,也就是要實現整個政治勢力的“大同團結”。
“大同團結”反對黨內派系斗爭,但其本身亦有為派系爭權所用之嫌疑。床次竹二郎“過去數年憧憬政權,有些歇斯底里之感”,“其人格不過是粉飾野心的道具”。[注]馬場恒吾:『現代人物評論』,東京:中央公論社1930年版,第86頁。犬養毅組閣時,床次竹二郎與鈴木喜三郎競爭內務大臣,最終卻是中橋德五郎出任。犬養毅死后,床次竹二郎與鈴木喜三郎競爭總裁,無奈再次敗選。在“舉國一致”政治中,如果政黨能夠再度崛起,床次竹二郎或有機會通過“大同團結”使自己處于政治中心。但在岡田啟介組閣后,床次竹二郎加入內閣,“大同團結”運動也因此失去了基礎。
在政友會內,與床次竹二郎達成某種共識的是久原房之助。1934年3月,支持“大同團結”的議員(以床次派與久原派為中心,政友會82名、民政黨52名)召開懇談會,準備聯合政友會、民政黨以及國民同盟等政黨所屬議員,在打倒鈴木喜三郎派的同時,實現政界重組,但這未能成功。與政黨“大同團結”并行,久原房之助醞釀并提出一國一黨論,它可以說是“反總裁派、達成政治野心的手段,但它并不只是權力斗爭的手段”,一國一黨論與“國風”政治理念相關,“是久原房之助對整個日本政治的設想,權力斗爭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注]奧健太郎:『久原房之助の一國一黨論——斎藤內閣期を中心に』,『法學政治學論究』(46), 2000。
在1932年政友會選舉獲勝時,久原房之助(此時為干事長)向犬養毅建言:“以日本國風政治理念容納他黨人才入閣,實現聯合內閣,以增強政治力,恢復國民信任。”[注]久原房之助:『世界維新と皇國の使命』,東京:翼賛出版協會1942年版,第39—40、42—43、43頁。另一方面,對于眾議院內的絕對多數,他認為政友會“有了統制基礎,父母對子女之情是日本帝室的源泉,選舉公平亦如此。公平會影響到整個政治,統制就能成為強大的日本式一國一黨之基礎”,“日本式的大和公平之心,與帝室恩寵一樣,實現和諧氛圍下的統一之力”。[注]大野慎:『久原房之助と宇垣一成』,東京:東京パンフレツト社1935年版,第19—20頁。他認為德意志、意大利是“信念國家”,“政治基礎不是個人主義、民主主義,而是信念主義”,“基于信念的話,獨裁是必然的,亦即一國一黨”,也就是說,“他的‘信念’是自信之念,相信只有某種信念才能拯救國家,信念之外的東西即不必要”。[注]森川肇:『立ち上つた久原房之助:これから何をするか』,東京:時局評論社1938年版,第36頁。
1933年5月,久原房之助正式表述一國一黨論,認為“之前的‘憲政常道’和兩黨制被視為金科玉律,應檢討反思”,兩黨“爭斗尖銳化,為了取勝而不擇手段,為求財源而暴出種種丑聞,肆意捏造,互相攻擊,如仇敵相爭”,“兩黨制在任何國家都不是最理想的,尤其是東洋,像日本這種沒有異族、自古即是萬世一系帝室,更不能在家族制國民中生造對立”。[注]久原房之助:『皇道経済論』,東京:千倉書房1933年版,第57—58頁。后來他說,“我對于名稱并不在意,就理念來說,我的主張不是德意志、意大利那樣的一國一黨,而是基于日本國風,追求總意之結晶,發揚宇宙之本真,形成自然的舉國一致,與其稱一國一黨,不如叫一國一家。”[注]久原房之助:『世界維新と皇國の使命』,東京:翼賛出版協會1942年版,第39—40、42—43、43頁。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國內整備戰爭體制,久原房之助認為“政黨愈發遠離政局中心,政黨聯合不足以統合整個政治,要實現真正的舉國一致不能僅靠政黨,軍官民應渾然一體,實現國民的地域性組織化,網羅各方面的政治要素”[注]久原房之助:『世界維新と皇國の使命』,東京:翼賛出版協會1942年版,第39—40、42—43、43頁。,因此提出國民協議會構想,并嘗試以一國一體代替一國一黨,即以地方代表、職能代表、國民代表(眾議院議員)為主體,加之貴族院議員、文武官吏等,“在政治上公正反映國民總意,通過協議消解一切黨派對立及朝野官民對立,實現一國一體之實”。[注]水島彥一郎:『更生政友會の展望』,東京:猶興書院1939年版,第85—86頁。
某種意義上說,政黨“大同團結”、一國一黨論都有“恢復政黨勢力”之意,在當時看來,“政黨政治是批判政治、責任政治,不是最優政治,也不是最壞政治,是相對安全的政治形式”[注]山田文吾:『一國一黨は果して可能か』,東京:昭和書房1938年版,第14、24—26頁。,但各黨都不能單獨掌握政權,或實現政黨聯盟,以壓制其他勢力;或拉攏宇垣一成、平沼騏一郎、清浦奎吾等政界巨頭。在這過程中,政黨本欲強化自身,結果卻是受到削弱,不自覺地脫離原本政治位置,逐漸喪失自立性,潛隱著自我解散的危險。例如松岡洋右,他認為政黨聯合實質上就是政黨解散。1933年12月8日,他發表聲明脫離政友會:“凡阻礙國民合衷協同者,皆應清算,消除一切黨派政爭、階級斗爭及其他各方面對立”,希望“各方人才擺脫舊有束縛,基于超黨派立場,以無私精神盡奉公赤誠”。[注]松岡洋右:『非常時に際し全國民に愬ふ:一國一黨論·政黨解消論』,東京:文明社1934年版,第1—4頁。
此時輿論中亦有一國一黨論,1937年12月中旬,頭山滿、一條實孝公爵、山本英輔大將3人聯名發表檄文,呼吁成立舉國政黨。檄文中表示,“萬世一系天皇乃國家中心,億兆歸一,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君民一體、忠孝一致乃我國體之本義”,批判政黨政治為“西洋思想的余毒”,“我皇國之中,政黨存在的義理在于舉國協贊天業恢弘之國策,報國之大道,這與西洋式的權利和利益政黨有著本質不同,西洋政黨是基于國民各階層分立,而皇國政黨則是基于全體國民的精神一致,當前時局尤為緊要,應在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實現國民結合”,最后提出建議,“國民作為一國一家的成員參與國務,這是基于道義立國之原則,日本國民以政治奉公為本分,政黨應于此覺醒,超越彼此不同而渾然一體,達成強力政黨之新組織,反映全體國民意志,否則,政黨將被歷史原則徹底粉碎”。[注]山田文吾:『一國一黨は果して可能か』,東京:昭和書房1938年版,第14、24—26頁。
同時,輿論中亦有對一國一黨論的批判:“獨裁政治的一國一黨是以權力破壞和排斥他黨”,“必須排斥以愛國主義為名操縱國政的一國一黨”;[注]山枡儀重:『憲政よ何処へ』,東京:寶文館1934年版,第40—41頁。而且,一國一黨涉及到國體:“以私人團體之勢力限制國務大臣的行動自由,這與天皇神圣的根本之義是不相容的”,“黨閥、官閥、軍閥、及幕府等私閥,皆應受到排斥”,“天皇作為天照大神的代表成為國家政治中心,但德意志、意大利沒有這種存在,其政治力只能求于私人團體”[注]藤井清治:『神國日本の全貌:帝國憲法の謹解と八紘一宇の還元 國體明徴の斷案』,東京:世界平和研究會1939年版,第51—52頁。,試圖通過批判一國一黨和“明征國體”,將日本的天皇統治與德意志納粹、意大利法西斯區別開來。
三、新黨運動與永井柳太郎
“舉國一致”內閣由軍部與新官僚主導,其政治決策與民意相脫離,“舉國一致下的國民并非實際的國民,而是假設虛擬的國民”[注]戸坂潤:『現代日本の思想対立』,東京:今日の問題社1936年版,第115—124頁。,內閣需要強有力的政治統制基礎。此時政界逐漸有一共識:若要獲得民眾支持,就必須形成“超越一切政黨和階級斗爭”的新型政黨。[注]永井柳太郎編纂會:『永井柳太郎』,第341頁。
1936年11月,日德防共協定成立,日蘇關系緊張,軍部急需強化國防,寺內壽一陸相、永野修身海相也希望有新黨支援。12月,陸軍的林銑十郎大將、海軍的安保清種大將、金融界的結城奉太郎、民政黨的永井柳太郎、昭和會的山崎達之輔、政友會的中島知久平、前田米藏、新官僚的后藤文夫等,在荻窪的有馬賴寧家中會談新黨事宜,即“荻窪會議”。新黨運動多以近衛文麿為中心,“(日本社會)上下結合才能實現革新,其門第家世很合適”,“(他)應擔負起革新的宿命”[注]麻生久伝刊行委員會編:『麻生久伝』,東京:麻生久伝刊行委員會1958年版,第478頁。,秋山定輔、秋田清、麻生久、龜井貫一郎等積極推動。秋田清認為,“新黨應符合舉國、單一、強力等條件,在其指導精神、組織機構、運營方針下產生新的機軸,只有解散原有政黨才能謀求新黨”。[注]秋田清伝記刊行會編:『秋田清』,東京:秋田清伝記刊行會1969年版,第632—634頁。也就是說,要打破原有政黨傳統,在憲法內避免與軍部沖突,形成全體主義的統合性政黨。
1937年9月,日本以“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為契機[注]國民精神総動員本部:『國民精神総動員運動』,東京:國民精神総動員本部1940年版,第2頁。,進一步強化國民統制。1938年10月,日軍攻陷武漢,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如社大黨聲明:“消除我國內對立、派閥、斗爭,實現全國民強力舉國一致,期待大革新政黨出現,實現國民再組織。”[注]內務省警保局編:『社會運動の狀況〔第14〕』,東京:日本資料刊行會1940年版,第570頁。新黨運動與國民再組織運動互相交織在一起,甚至說,“新黨運動不過是國民再組織運動的一個表現”。[注]高橋亀吉:『東亜建設戦と財政経済の再編成』,東京:千倉書房1939年版,第139頁。1939年1月4日,近衛文麿內閣辭職,新黨計劃與國民再組織運動暫時擱淺。
1940年6月25日,畑俊六陸軍大臣向全體將校訓話:“強化國內體制”、“實現真正的舉國一致政治”。[注]三島助治:『軍部の目標』,東京:國民政治経済研究所1942年版,第155、156頁。29日,澤田茂參謀次長在全國新聞通信代表招待會上也表示,“熱切期望新體制”。[注]三島助治:『軍部の目標』,東京:國民政治経済研究所1942年版,第155、156頁。7月22日近衛文麿第二次組閣,新黨運動與國民再組織運動合流并具象化為新體制運動。隨后,近衛文麿首相發表《基本國策要綱》,“基于國體本義,庶政一新,確立國防國家體制基礎”。[注]大政翼賛會奈良県支部:『翼賛綱要』,1941年版,第21—22、23—27頁。8月28日,新體制準備委員會成立并召開會議,近衛文麿首相致辭:“國民組織的目標是集結國家與國民之總力,一億同胞成為一體而盡大政翼贊之臣道”, 實現“下意上達、上意下達”,他批判過去的政黨“代表個別、局部利益”,而“國民組織運動則超越自由主義下的政黨政治,其本質是舉國性的、全體性的和公共性的,以促使國民集結總力為目的,涵蓋整個國民生活”,是“超政黨的國民運動”,“不允許部分的、對立的抗爭性政黨運動”,同時,新體制也不允許“一國一黨”,因為“一國一黨是將部分作為全體,將國家與黨同一化,將反對黨的東西視作反對國家,從而將黨的權力地位永久化,黨首永久把持權力,有違一君萬民之國體本義”。[注]大政翼賛會奈良県支部:『翼賛綱要』,1941年版,第21—22、23—27頁。新體制運動正式展開,各政黨也相繼解散。
在新黨運動中,值得注意的是民政黨的永井柳太郎。他1920年加入憲政會,作為黨內左派人物、“大眾政治家”,積極提出普選等進步主張,在加藤高明內閣及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任外務參與官、浜口雄幸內閣任外務政務次官,1931年出任民政黨干事長。九一八事變后,他在演說及論文中力倡政黨重建和改革議會,主張基于國民全體的強力政黨,推進革新政策,并常與官僚、軍部人士會談。之后,在齋藤實內閣中任拓務大臣、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中任郵政大臣等,積極參與新體制運動。
永井柳太郎在1936年談到時局動向:“不管是納粹還是法西斯,都是基于大眾生活要求而再建國民生活,如此在今日世界方有其生命力”,“墨索里尼被稱為獨裁政治家,但法西斯黨與當時其他政黨相比,政策更貼近大眾生活要求,法西斯黨絕不是單純獨裁政治的成功”,“若政黨的議案與大眾生活沒有關系,政治就只能是少數資本家與野心家的政治。墨索里尼超越了一般政黨,直接與大眾交涉”,因此“墨索里尼才被信賴為大眾代表”。[注]永井柳太郎述:『時局の動向を語る』,東京:談論社1936年版,第15—16、20、25—27頁。他又進一步闡釋“政治即正義”:“若沒有國民支持,斷不能實現強力內閣。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有其強力,就是因為與國民一同戰斗。因此,他們的獨裁政治雖與十八世紀那種與國民無涉的貴族獨裁政治形似,但本質不同”,基于此,他認為日本政治應是:“激進派、漸進派、國家社會主義、統制主義等不同政黨政派與國民大眾一道戰斗,這樣才會有其生命力,政治運動應遵循一君萬民的建國精神”。[注]永井柳太郎述:『時局の動向を語る』,東京:談論社1936年版,第15—16、20、25—27頁。為實現政黨改造,永井柳太郎為民政黨建議:“一是政策立黨,改變政黨與大眾的物質金錢關系,從倫理與精神上確立政策,不能與大眾生活理想與要求脫節”,“基于一君萬民再建日本的立法機構、行政機構、經濟機構等,對外擴充強化國家存立基礎,對內實現勤勞大眾的生活保障”;“二是黨費公募”,因為“選舉經費是政黨的一大問題,之前政黨迎合財閥,動輒出現謀利行為,不能維持政黨獨立之精神”;“三是排斥權力爭奪,以政策為中心”。[注]永井柳太郎述:『時局の動向を語る』,東京:談論社1936年版,第15—16、20、25—27頁。
在二二六事件后,永井柳太郎認為,“現在日本有兩個方面需要改變,對內來說,之前的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著眼于特定階級的利益,常區分城市與農村,這無形中蹂躪了勤勞大眾,應一掃積弊,以一君萬民大義為基礎重建國民生活。對外來說,過去數世紀亞洲處于白人統治之下,日本應解放亞洲,建設自主亞洲”,“人心一新思想安定,才能使諸如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危險消失”。[注]永井柳太郎:『私の信念と體験』,東京:岡倉書房1938年版,第266、270、278、279、282、285、450頁。“政府通過輿論理解國民生活理想與要求,國民也通過議會理解政府的舉措,二者通過議會達成渾然一體,共同實現政策。政府與國民之間,通過議會實現溝通。”[注]永井柳太郎:『私の信念と體験』,東京:岡倉書房1938年版,第266、270、278、279、282、285、450頁。但他認為當時日本議會的狀況和效用并不好,阻礙了政治機能的發揮,所以需要改革,恢復國民對議會、政黨及政治的信任。而且,應清除黨派弊病,“必須把低劣的政爭實現倫理化,消除國民質疑,貫徹公黨實質與責任,實現純真政黨”。[注]永井柳太郎:『私の信念と體験』,東京:岡倉書房1938年版,第266、270、278、279、282、285、450頁。所謂公黨精神,就是“政黨向天下宣告并反省自身存在的必然性,清算黨內斗爭,超越一切黨略斗爭、階級斗爭,動員日本所有資源、資本、勞動力,在國家統制、指導與保護下建設新經濟組織,擴大強化生產力,實現分配公正,提高國民生活,以此突破難局,只有這樣,政黨才能成為新日本建設的原動力,受到國民大眾支持,成為真正的公黨。”[注]永井柳太郎:『私の信念と體験』,東京:岡倉書房1938年版,第266、270、278、279、282、285、450頁。
因此,永井柳太郎提出國家主義大眾黨,認為“一戰之后,伴隨經濟不穩、私企無能,社會不安及革新氣氛加劇,有必要實現國民經濟的公益統制和再組織”。[注]永井柳太郎:『私の信念と體験』,東京:岡倉書房1938年版,第266、270、278、279、282、285、450頁。也就是說,在他看來,需以國家主義重建議會政治,“對內確立全體主義經濟機構,重建國民生活,對外爭取日本國民在世界的生活權”[注]永井柳太郎:『私の信念と體験』,東京:岡倉書房1938年版,第266、270、278、279、282、285、450頁。,強調國家統制、全體國民共存共榮,以貫徹產業合理化與社會化,防止階級斗爭。他也曾指出自由主義的缺陷:“否認國家與個人是一體的,認為國家是為保障個人追求欲望自由的機構,個人行動與國家行動屢有矛盾”、“個人、各階級追求利益,階層間不免激烈對抗”、“可能產生金權政治,動搖國民思想”、“多數黨擴張黨勢,政黨分立抗爭,即便政黨聯合執政,也不免短命內閣”。[注]永井柳太郎:「戰時下に於ける新政治體制とその指導精神」,『興亜論集——世界に先駆する日本』,東京:照文閣1942年版,第234—239頁。
1940年大政翼贊運動開始時,民政黨總裁町田忠治等干部對于解散政黨持懷疑態度,但隨后有40余名黨員退黨,其退黨宣言被視為永井柳太郎所作:“政黨處于休眠狀態,喪失了指導國民和推進政治發展的見識和氣魄。為打破現狀,必須體察國民精神的真髓,把握國民的生活要求”,“個人或政黨都必須立于國家主義大眾,實現強力政治體制”[注]永井柳太郎:『私の信念と體験』,東京:岡倉書房1938年版,第266、270、278、279、282、285、450頁。,并建議總裁早日解黨,與政府共同行動。退黨后,永井柳太郎發起集會并命名為“新體制促進俱樂部”,積極配合大政翼贊運動。
小 結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進入所謂的“非常時”,局勢不穩。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政黨政治結束,軍部與新官僚主導“舉國一致”,民眾對政黨的態度消極。政黨一方面受到軍部、官僚與右翼勢力的壓迫緊逼,一方面試圖恢復民眾信任,既有維護憲政之大義名分,又有重回政治中心之現實追求。政友會與民政黨嘗試聯合,但因私利與理念分歧未能實現,也不能與官僚、軍部等真正決裂對抗。政黨人士提出“大同團結”、一國一黨、組建新黨等主張,期待超政黨的舉國一致強力政府,意欲強化自身,反陷入悖論,以至更加邊緣化,逐漸失去自立性,立憲政治下的多數決等原理被消解在“舉國一致”、“一君萬民”之中,政黨變質為“代表民意”監督和批判政府的消極性組織。政黨的“轉向”固然是受到軍部強權的影響,但它也與近代日本天皇制下政黨的性質和政治位置密切相關。一國一黨論與天皇制亦有矛盾,在國民泛政治化中,政黨解散并走向大政翼贊體制。可以說,在九一八事變后的“非常時”中,政黨的自我改造有恢復憲政的期待與色彩,但它也從內部破壞了政黨存在的正當性,從而促進了法西斯統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