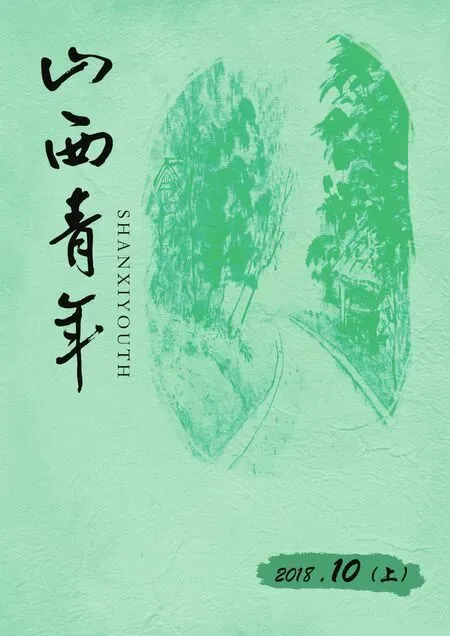郭店簡《老子》思想探究
孫明姚
(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
郭店簡《老子》甲中開篇則說:“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三言以為辯不足,或命之或乎屬。視素保樸,少私寡欲。”這就說明了治國的三大要素:絕智棄辯、絕巧棄利、絕偽棄慮。但僅有這三點遠遠不夠,還須做到“視素保樸,少私寡欲”才行。即保證自己清心寡欲質樸無華的心性。只有做到以上這些,才能治理好國家。而傳世本《老子》第十九章中則是說:“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亡有。”在此處,治國要素發生了變化,變成了:“絕圣棄智”、“絕仁棄義”。之后又提到了知足知止的重要性:“夫亦將知足,知足之以靜,萬物將自定”、“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我好靜而民自正”、“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為人處世與治理國家一樣,皆須做到知足知止,方可長久以待。知足知止就是無論做任何事都要有個度。郭店《老子》中就明確提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無孰病?甚愛必大費,厚藏必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咎莫大乎欲得,禍莫大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從這里就可以看出老子認為最大的禍患與過錯都在于人們的不知足,因此把握好度,知道滿足,這樣才不會招致危難,才可以長久的平安。
二、“自然無為”的思想
郭店簡《老子》甲中提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能為百谷下,是以能為百谷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江海之所以能成為百谷王,是因為它能讓自身處于百川之下。而圣人之所以能處身于民前,則是因為他將自身置于人民的身后,圣人之所以能夠在人民之上,是因為他能用謙虛的態度來對待人民,圣人在人民之上,人民不會以之為負擔,圣人在人民之前,人民不會覺得有妨害。因此天下的人民都樂于推舉而不會感到厭惡。正是由于圣人或天子的不爭之道,所以天下才沒有能夠與之爭相上下的人。從這段文字就可知道圣人或天子只有遵循“自然”之法則,不爭勝,不逞能,不強求,天下自然就歸屬于圣人或天子了。“無為”思想也在郭店《老子》中多次出現。如:“道恒無為而無不為”、“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是以圣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也,為而弗恃也,成而弗居。夫為弗居也,是以弗去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等等。圣人之所以要實行無為而治,是因為萬物的根本“道”就是無為的,圣人應該遵循萬物之根本來治理國家。萬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圣人不應該將其分割和區別對待,而應該順應歷史順應自然來實行無為而治。郭店《老子》甲開篇就提:“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三言以為辯不足,或命之或乎屬;視素保樸,少私寡欲。”“三言”即:“絕智棄辯”、“絕巧棄利”、“絕偽棄慮”,它們都不屬于無為的范圍,都是應該被棄絕的。這樣才能保證樸素的心性,達到無為的至高境界。
三、“仁義”理論觀
郭店簡《老子》丙本中提到:“故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慈。國家昏亂,安有正臣。”傳世本《老子》中提到的則是:“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兩種版本雖是一字之差,但有“安”與沒“安”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意思。傳世本的意思大致是:大道廢弛了,仁義也就出現了;智慧產生了,就會有過度的虛偽;六親不和諧,就產生了孝慈的現象;國家昏亂不堪,就是由于有了忠臣的出現。這似乎有些說不通,太過牽強。難道大道不廢就不會有仁義?智慧不出現就不會有虛偽?六親和諧就不會出現孝慈的現象?國家安定就不會有忠臣的出現?再來看看郭店簡《老子》中這段話的含義:失去了大道,怎么還能有仁義呢?六親不和諧,怎么能看出孝慈呢?國家一旦昏亂,就會缺少正直的臣子。這樣鮮明的對比,郭店《老子》與傳世本《老子》二者豈不正好相反,相互矛盾?可見,在郭店簡中并不反對仁義,老子對“仁義”是持有一種肯定態度的。同樣,與老子“自然”、“無為”思想相同,這“仁義”之思也有其深刻而鮮明的社會背景。在那樣一個禮崩樂壞、動蕩不安的社會大背景大現實下,老子與孔子等圣人一樣,也在積極地尋求一個治國救世的方法,他根據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等多方面多角度分析來提出“仁義”、“孝慈”等觀點。“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用善良的人的方法去同樣善待他,而對待不善之人,也要以善良之心去善待他。這正是“仁義”精神的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