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gè)體價(jià)值與文化身份
——女性藝術(shù)家李青萍解讀
韋俏勛
一、引言
在中國(guó)近代藝術(shù)史中,李青萍是少有的從民國(guó)一路走來(lái),畢生堅(jiān)持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女性藝術(shù)家之一。對(duì)于一個(gè)幾經(jīng)沉浮、身負(fù)榮譽(yù)與污名的藝術(shù)家而言,對(duì)于一個(gè)心頭烙滿時(shí)代的創(chuàng)傷,情感的缺失、在時(shí)代浪潮中欲展現(xiàn)自身而不得的女性而言,繪畫成為幫助李青萍承受痛苦、宣泄對(duì)生命的熱愛和憤恨的依仗,這使得她比以其他女性藝術(shù)家走得更遠(yuǎn),使得她的經(jīng)驗(yàn)滲出語(yǔ)言之外,使得藝術(shù)成為表現(xiàn)她自身更有力的字句。
女性和藝術(shù)家作為李青萍身上兩個(gè)最重要的身份特征,成為理解其藝術(shù)的全新視野:她的藝術(shù)生涯是否因其女性身份而蒙受打擊或得到優(yōu)待?她的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達(dá)出獨(dú)特的聲音,并將女性這一群體的獨(dú)特經(jīng)歷灌注于畫面中?她又是如何看待與處理“女性”與“藝術(shù)家”這兩種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相互排斥的身份的?
二、藝術(shù)才華的隱與顯
女性身份對(duì)于李青萍而言是個(gè)含義特別豐富的主題:入行和早期的成功發(fā)端于社會(huì)對(duì)女性作為獨(dú)立個(gè)體的肯定,但女性與藝術(shù)明星的相互交纏導(dǎo)致其藝術(shù)生涯的阻斷,也消解了身上的銳氣,轉(zhuǎn)化為對(duì)于藝術(shù)世界的持續(xù)探索。
40年代以前,李青萍的藝術(shù)進(jìn)路似乎沒有因其性別而蒙受損失。順利進(jìn)入上海新華藝專學(xué)習(xí)、海外教學(xué)中順利舉辦畫展并出版畫集、回國(guó)后多次舉辦畫展聲名大振、被日本文藝界譽(yù)為“中國(guó)畫壇第一嬌娜”。她的作品得到較高地位的藝術(shù)家的指點(diǎn)和認(rèn)同,使其才情得以在更大、更開放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涌現(xiàn)。徐悲鴻成為李青萍早期藝術(shù)生涯中的重要指路人,來(lái)自名家的評(píng)價(jià)和賞識(shí)進(jìn)一步提升李青萍的知名度。
然而,40年代以后多次身陷囹圄的經(jīng)歷證明,明星與女性身份相互綰結(jié),使她的藝術(shù)行為遭到嚴(yán)重質(zhì)疑。1946年9月,李青萍被國(guó)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逮捕,并以“漢奸嫌疑”起訴。審訊的提問意味深長(zhǎng)[1]:“這幾年中來(lái)來(lái)去去,是否與人相共?又在此兵荒馬亂中怎樣生活?”“有人檢舉,你曾拜儲(chǔ)民誼為干爹?”“否則(指不拜干爹)不容易跑來(lái)跑去。”問訊大多集中在對(duì)女畫家經(jīng)濟(jì)獨(dú)立和自由方面的質(zhì)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huì)對(duì)女性成就的雙重道德評(píng)價(jià):在接受男女平等觀念的同時(shí),社會(huì)仍以家庭價(jià)值的視線作為女性終身成就的標(biāo)準(zhǔn),因此這樣一個(gè)衣著時(shí)髦、社交頻繁的女性的成功或許得益于不為人知的曖昧隱私。可見,新舊交替的社會(huì)地位和男權(quán)主導(dǎo)的政治秩序相互加持,本能地排斥女性超越男性藝術(shù)成就的可能性。
和女性藝術(shù)家多湮沒于家庭俗務(wù)中的趨勢(shì)不同,李青萍終身未嫁且筆耕不輟,時(shí)代造成的厄運(yùn)賦予她對(duì)于精神世界的持續(xù)關(guān)注,獲得異乎尋常的表現(xiàn)力。創(chuàng)作于1984年的《我的天地》,深邃混沌的背景上空同時(shí)存在兩個(gè)月亮,似乎在暗示畫家當(dāng)時(shí)所面臨的現(xiàn)實(shí)處境,孑然一身、渺小無(wú)依,偏安于自己的小世界中也許更為安全。1952年后,李青萍先后因拒絕參加“鎮(zhèn)反”被遣反、因“重大特務(wù)嫌疑”被拘捕,從此展開了二十余年靠撿破爛和賣水為生的生活。她通過從垃圾堆撿來(lái)的廣告顏料在廢舊雜志上持續(xù)作畫,如所作《戲劇人物》,用當(dāng)時(shí)常見的紅色顏料在雜志封面作畫足見她對(duì)藝術(shù)的熱愛與堅(jiān)持。
在李青萍的藝術(shù)生涯中,女性身份似乎并非始終發(fā)生作用。但她遭受的種種苦難都在說明,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xiàn)的對(duì)女性發(fā)展和行為的懷疑,造成了其藝術(shù)發(fā)展的轉(zhuǎn)折。因此,女性這一身份先是隱性的存在,而后變成一個(gè)包袱,最后也成了臺(tái)階。
三、女性特質(zhì)的可見與不可見
回到藝術(shù)實(shí)踐本身,李青萍的作品中是否流露出女性的特質(zhì)?她本人對(duì)女性身份有何認(rèn)識(shí),又作何反應(yīng)?一批數(shù)量可觀的畫作有意無(wú)意地流露出她對(duì)愛情、婚姻和家庭的向往,成為對(duì)于兩性關(guān)系的隱晦表達(dá)。與此同時(shí),日記隨筆中流露出強(qiáng)烈的主體意識(shí),解釋了其作品中試圖淡化女性標(biāo)簽的另一種努力。
1.可見:婚姻與家庭的兩性隱喻
40年代及之后的牢獄之災(zāi)和政治因襲,使李青萍疏離于感情生活,終身未嫁沒有孩子的經(jīng)歷使她陷入情感身份的僵局,并始終對(duì)這種身份和關(guān)系好奇不已,情感的缺失使她嘗試通過藝術(shù)去理解和表達(dá)愛的具體形態(tài)。以下將分為兩性關(guān)系和家庭關(guān)系兩部分進(jìn)行論述。
在李青萍的作品中,身體被抽象成流動(dòng)的存在,脫離了具象的束縛,強(qiáng)調(diào)的是兩性之間緊密依靠、互相慰藉和平等的關(guān)系。《二人情》以自由的筆觸、強(qiáng)烈的色彩和極具沖擊力的構(gòu)圖呈現(xiàn)出男女情感中相互依戀密不可分的狀態(tài),由黃、綠、紅的形、線、點(diǎn)組成的背景與中央充滿動(dòng)態(tài)感的紅、綠線條和諧并置,似相互纏繞的兩股火焰,其中人臉依稀可辨。畫面具有強(qiáng)烈的表現(xiàn)性效果,畫家對(duì)于愛、自由、依戀的情緒穿行其中。同類作品還有《伴侶》《擁吻》等。婚姻是愛情在更高的原則下的錘煉和鞏固,對(duì)此李青萍有著自己的思考。《婚禮》是一場(chǎng)盛大婚禮的記錄,畫面中女子的修養(yǎng)和姿態(tài)毫不遜色于身旁男子,畫家對(duì)女子服飾和姿態(tài)相對(duì)細(xì)致的描摹,不僅透露出對(duì)于美滿婚姻的艷羨,也可視為平等自由等女性意識(shí)的表征。另一幅《婚禮》將藝術(shù)家的認(rèn)知和觀念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色彩成為渲染畫面情緒的重要手段。下方大紅色涂抹,幾筆若有若無(wú)的黑色刮蹭似是人形,目光向上,墨綠色平涂與下方構(gòu)成平衡感,一松一弛形成動(dòng)靜張力——喜慶與壓力并存,和諧與未知接踵而至。更有意味的是,這種色彩和構(gòu)圖間的內(nèi)在沖突在畫家的“留白”中得到了緩解和釋放,中部不作色直接透出木板的原色使畫面更為透氣,使畫家的情緒鋪寫表現(xiàn)出一種節(jié)奏性。
“昏禮者,將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以繼后世也,固君子重之”(《禮記·昏義》),兩性結(jié)合不僅是當(dāng)下個(gè)體生命的事,還勾連著延續(xù)未來(lái)子胤的人倫內(nèi)涵。這種內(nèi)涵影響著李青萍,孩子成為她母性表達(dá)的土壤和誘因,呈現(xiàn)出她作為女性,期待家和事興、子孫環(huán)繞的傳統(tǒng)的一面。《天倫》中深色背景之上成人圍繞構(gòu)筑出的堡壘,為孩子開辟出安全自由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選取明度更為柔和的紅色,猶如溫床凸顯畫家的柔軟,寥寥幾筆勾畫的白色人形雜陳其間,使整個(gè)畫面熱鬧且充滿希望。同類作品還有《兒孫繞膝》,圍繞母與子主題進(jìn)行的創(chuàng)作將畫家對(duì)親子關(guān)系的理解表達(dá)得更為徹底。
李青萍在藝術(shù)中構(gòu)筑了自己兩性身份、家庭身份的種種可能,折射出對(duì)愛情和親情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型的畫作表現(xiàn)的是畫家對(duì)宜室宜家、生育的希望,而非她作為個(gè)體的自我價(jià)值,體現(xiàn)出李青萍思想中根植于心的傳統(tǒng)家庭觀念。
2.不可見:消解身份的另一種努力
李青萍的日記隨筆和部分作品中,透露她的男女平等觀念甚至淡化女性身份的傾向。
她在日記中寫道“對(duì)國(guó)家有貢獻(xiàn),至少不做社會(huì)的寄生蟲,要做女中典型的先行者,男女都是社會(huì)的建設(shè)者[2]。”相信男女平等,進(jìn)入社會(huì)接受教育,有職業(yè)、經(jīng)濟(jì)獨(dú)立,李青萍像男性一樣在社會(huì)上尋求成功的機(jī)會(huì),以社會(huì)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代替以往家庭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作為終身成就的標(biāo)準(zhǔn),這可能是我們?cè)谒挠行┊嬜髦袔缀醪荒芡ㄟ^作品辨認(rèn)其女性身份的原因。40年代齊白石先生評(píng)價(jià)“青萍畫”時(shí)說:“李青萍小姐畫無(wú)女兒氣。”30年劫難使李青萍的繪畫轉(zhuǎn)向一種“粗糙”的表現(xiàn)手法,從她對(duì)色彩的把控和運(yùn)用中我們?nèi)阅芨惺艿匠脚约?xì)膩、柔軟的一面:其一,她能在很小的畫幅中表現(xiàn)出很大的氣勢(shì),如《相逢在南洋》,扁長(zhǎng)筆觸上下延伸拉大畫面的縱向視覺空間,符號(hào)化的人形因?yàn)椴煌脑O(shè)色和姿態(tài)生動(dòng)感人,在紅、綠、黃的碰撞之中,李青萍留下了空間,增加了畫面的節(jié)奏感,從而增大了作品的張力。其二,李青萍通過深淺、刮擦、涂抹等方式,能用簡(jiǎn)單的色彩或同一顏色構(gòu)成層次豐富的畫面,《朝圣者》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條件所限,畫家僅有黑白二色和極少的紅色油彩,卻能在一塊做鞋幫的布料上描繪出一群行走在陰陽(yáng)兩界的人,表現(xiàn)出對(duì)生的渴望以及自由的向往。
3.可見與不可見:女性群體的記憶與超越
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研究生吳靜在李青萍藝術(shù)展研討會(huì)上說道:“李青萍所走過的路是20世紀(jì)很多女性所經(jīng)歷的共同道路,民國(guó)解放的整體構(gòu)架就是從維新、辛亥、五四一路下來(lái),西方的平等觀念逐漸進(jìn)入了民國(guó)女性的事業(yè),她們既被喚醒,又在自身的泥沼當(dāng)中掙扎得更加痛苦,所以矛盾在她們身上體現(xiàn)得非常明顯……但是李青萍堅(jiān)持下來(lái)了,因?yàn)樗龑?duì)生活和藝術(shù)形式的選擇是非常果決的,一生把藝術(shù)奉為生命,在那個(gè)時(shí)期的女性藝術(shù)家甚至是所有畫家當(dāng)中都是不多見的。”[3]
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從民國(guó)一路走來(lái)的女性藝術(shù)家,李青萍是中國(guó)早期現(xiàn)代主義運(yùn)動(dòng)的一個(gè)延續(xù)。民國(guó)時(shí)期第一代女藝術(shù)家(如潘玉良、蔡威廉)注重人物表情、心緒和精神氣息的捕捉與勾勒,“為現(xiàn)代女性美術(shù)提供了一種表達(dá)圖式”[4]。此后,涌現(xiàn)出關(guān)紫蘭、丘堤、郁風(fēng)等一批女畫家,以不同于唯美、細(xì)膩的表現(xiàn)性、精神性和極具辨識(shí)性的個(gè)性化畫風(fēng)馳騁畫壇,卻也都因?yàn)榧彝セ驎r(shí)代的原因最終退出藝術(shù)舞臺(tái)。50至70年代對(duì)女藝術(shù)家,甚至新時(shí)代女性這個(gè)群體而言,都是一個(gè)曲折迂回,自我懷疑的時(shí)代,包括文學(xué)界的張愛玲在內(nèi),女性文藝從業(yè)者的女性身份遭到了最大程度的質(zhì)疑,也造成了大批藝術(shù)家藝術(shù)生涯的斷裂,或是尋求更為安全的表達(dá)方式。高度一統(tǒng)化體制下的小心翼翼、不得自由對(duì)80年代“文藝解放”后的創(chuàng)作也造成了影響,導(dǎo)致李青萍畫面中始終籠罩的憂傷壓抑氣質(zhì)。
與此同時(shí),“女性表達(dá)開始進(jìn)入自覺自為的新階段”[5],“跟著感覺走”的李青萍更是如此,線條、用色、筆觸日漸老練大膽。這在90年代的作品中更為明顯,她筆下的人物和《自畫像》,通過色塊的組合,形成紛繁厚實(shí)的色調(diào)效果,強(qiáng)調(diào)色彩作為一種表現(xiàn)語(yǔ)言的作用,暗示著她屬于30年代奠基的現(xiàn)代藝術(shù)根基,呈現(xiàn)出與同樣活躍于八九十年代的年輕藝術(shù)家(如喻紅、陳淑霞等)不同的發(fā)展路徑。
此外,苦難——這一貫穿李青萍一生的主題,成為她的獨(dú)特性所在:正是因?yàn)榻?jīng)歷并跨越了絕大多數(shù)女性藝術(shù)家從未受到的挫折,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出超越性別的強(qiáng)烈的情緒感和表現(xiàn)力。她的畫面中灰調(diào)子、深藍(lán)、紫、棕等顏色經(jīng)常出現(xiàn),常常伴隨著一個(gè)踽踽獨(dú)行或煢煢孑立的人形,猶如李青萍的人生寫照。劫后重生的李青萍,長(zhǎng)期壓抑的創(chuàng)作欲望被釋放,仿佛打開了抒情的閘口,她把與苦難交往的被動(dòng)和主動(dòng)都體現(xiàn)在畫面上,代表作品有《超脫》《天問》《祈禱》等。以《舞者》系列為例,消除人物的個(gè)體特征,黃色筆觸簡(jiǎn)單勾勒的更像是游蕩在混沌中的靈魂,看似隨意的構(gòu)圖實(shí)則置入了復(fù)雜的心理內(nèi)容:人物圍繞無(wú)所依,或振臂或頷首,構(gòu)成了李青萍自身經(jīng)歷中的不同感受——時(shí)代苦難中藝術(shù)閹割的郁結(jié)、義憤與沉默。對(duì)生活發(fā)自肺腑的熱愛和焦慮,使畫面有了氣象和血色。
可見,時(shí)代認(rèn)同與否定、自我認(rèn)同和堅(jiān)持的復(fù)雜糾纏,顯示出李青萍藝術(shù)的一種特殊形態(tài):早年在時(shí)代潮流中習(xí)得平等意識(shí),憑借豐富的表現(xiàn)力淡化女性的標(biāo)簽;被人遺忘之后又被人記起,仍然在千人一面的時(shí)代大潮中保持自我的身影,但顧影自憐、向往家庭婚姻的心境通過畫面不時(shí)流露。同時(shí),李青萍超越政治形態(tài)和自身性別局限的藝術(shù)堅(jiān)持,使李青萍的藝術(shù)表達(dá)即使在個(gè)人被摒棄的時(shí)代也固執(zhí)地進(jìn)行超越性別的藝術(shù)探索。
四、結(jié)語(yǔ)
女性和藝術(shù)家兩種身份在李青萍身上到底有怎樣的聯(lián)系?
首先,女性身份的影響直觀地體現(xiàn)在對(duì)藝術(shù)生涯的阻力上。從李青萍上世紀(jì)四五十年代的經(jīng)歷中,可以很強(qiáng)烈地感受到成功對(duì)女性審慎的離間,或者那種女性藝術(shù)家的成功,最終無(wú)可避免地陷入男性權(quán)威所帶來(lái)的質(zhì)疑的事實(shí)。雖然李青萍早年的藝術(shù)生涯看似一帆風(fēng)順,但如今人們重新記起和研究其早期藝術(shù)的論據(jù),總離不開她與男性藝術(shù)家交往的經(jīng)歷和評(píng)價(jià),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男性藝術(shù)家的介入,對(duì)于女性藝術(shù)家的脫穎而出,以及作品的保存和流傳來(lái)說是至關(guān)重要的。
誠(chéng)然,李青萍作品中的女性陰柔內(nèi)傾特質(zhì),和關(guān)于愛情、婚姻和家庭的主題會(huì)不時(shí)流露,但這并不意味著對(duì)傳統(tǒng)兩性關(guān)系的俯首稱臣。李青萍自身的追求,彰顯在筆觸的處理和立足現(xiàn)實(shí)與想象對(duì)色彩的洞若觀火,集體陷落下固執(zhí)己見的追求、更體現(xiàn)在她將藝術(shù)家身份貫穿始終的堅(jiān)持中。因此,女性身份在李青萍藝術(shù)中的可見與不可見,反映出李青萍獨(dú)自叩門探索藝術(shù)中的困惑,和對(duì)困惑的反復(fù)咀嚼,這讓她的藝術(shù)和價(jià)值在美術(shù)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當(dāng)囊括性別因素作為一種藝術(shù)分析范疇時(shí),我們難以回避女性身份與李青萍經(jīng)歷之間的暗合,以及作品泄露出的對(duì)此身份的接受和反思,和她從中不斷確認(rèn)自己的獨(dú)立意識(shí)和文化身份的努力。以上論據(jù)沒有哪個(gè)能單獨(dú)充分論證女性身份對(duì)其藝術(shù)的重要影響,或斷言李青萍是一位具有突出女性意識(shí)的藝術(shù)家,但它們加在一起的粘結(jié)與疏離就足以提示,不能忽略女性身份的影響力;同時(shí)也提示著,通過性別因素考察藝術(shù)進(jìn)路,成為探索李青萍藝術(shù)中一條具有啟發(fā)性的路徑。
[1]尚輝. 青萍?xì)堄啊钋嗥妓囆g(shù)展言談會(huì)會(huì)談紀(jì)要[M]//黃德澤. 冷月下的求索:李青萍畫評(píng).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56.
[2]李青萍. 青萍日記九[M]//林陽(yáng). 李青萍畫集. 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4:244.
[3]尚輝. “青萍?xì)堄啊钋嗥季栀?zèng)作品展”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J]. 美術(shù)文獻(xiàn),2015,(09):94.
[4]姚玳玫. 畫誰(shuí)?畫什么——從自畫像看民國(guó)時(shí)期女性西畫的圖式確立[J]. 美術(shù)觀察,2011,(03):104.
[5]姚玳玫. 自我畫像——一條貫穿共和國(guó)60年女性美術(shù)的敘述脈絡(luò)[J]. 美術(shù),2011,(0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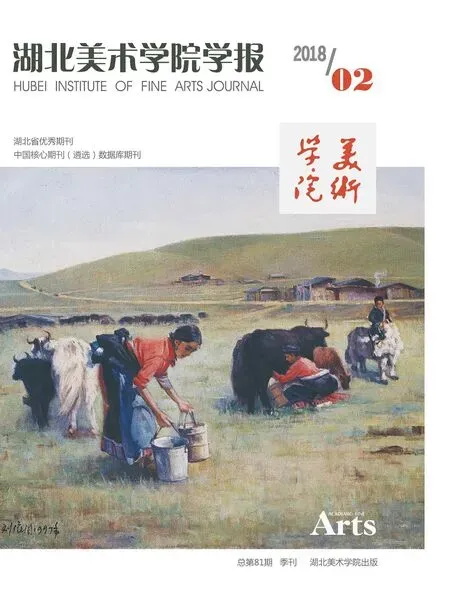 湖北美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8年2期
湖北美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8年2期
- 湖北美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莊子美學(xué)與中國(guó)文人藝術(shù)家的“癡”和“顛”
- 高校園區(qū)商業(yè)建筑空間設(shè)計(jì)的基本關(guān)系分析
——以黌街商業(yè)街為例 - 基于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的“愛購(gòu)”電影APP交互服務(wù)系統(tǒng)設(shè)計(jì)分析
- 當(dāng)代圖片作品與展場(chǎng)空間的交互性研究
- 中國(guó)版畫在當(dāng)代藝術(shù)境遇中的觀念轉(zhuǎn)型
- 人性化設(shè)計(jì)視角下生活陶藝影響因素的四維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