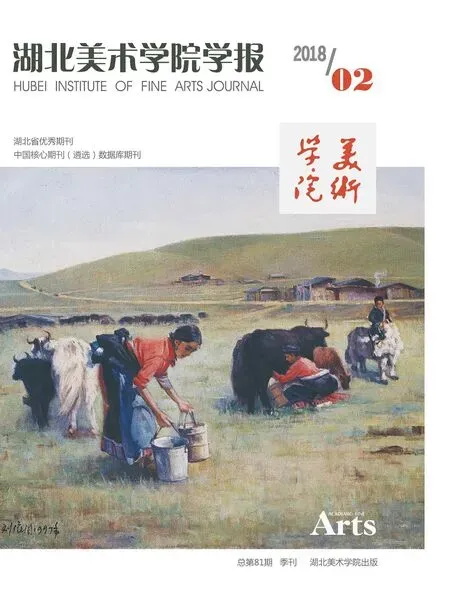當代圖片作品與展場空間的交互性研究
曾 華
展場即展覽空間,對于藝術家來說就是他們賴以生存與世人連接的主要陣地,對于觀者來說,展覽空間從來都是一片汲取靈感與創意的溫床和圣地。展覽空間成就了藝術家,讓藝術家創作的結晶體在其間閃閃發光,照耀著每一個來到展示空間的人們。從莫奈讓自己的睡蓮在紐約美術館綻放開始,白盒子似的展覽方式便拉開了帷幕。藝術的發展在近百年間早已瞬息萬變,就當代藝術而言,其多樣性對每個以當代藝術作為主要展品的美術館來說,都需要依據作品本身的特殊性來進行布展和調節。有的展覽輕則做板換燈,重則挖坑填地去頂,有時甚至為了某一個藝術家的個展而改造美術館或連接兩個畫廊空間。藝術本身的界定因為時代和科技發展的速度而變得越來越模糊,當代藝術作品的邊界也在藝術作品和展示空間的完美融合中不斷的向外延展。
圖片作品本身,因為其平面的特性,策展團隊在照片進入展館時,為了體現出其作品內容的精髓,往往從布展前期就會商定適合作品展陳的地點,結合現場環境與現成品或用現成品做成裝置的方式來進行展出,除作品以外的所有行為都是用來輔助作品內容以讓其產生無限張力。如2018京都國際攝影節中,于2012年去世的中川辛夫的作品選址在日本京都花見小路的盡頭建仁寺中的兩足院內進行布展,其拍攝的花卉植物類靜物作品在現在看來依然前衛張狂。策展團隊選擇了一個有800年歷史的寺廟,同時兩足院內外通透,日式地板上擺放著切割整齊的黑色炭木條,中川的作品就架在木條之上,進入寺廟觀看展覽的觀者,必須脫鞋,要想和作品面對面的對視,必須是日式坐榻榻米的方式半跪。這種因為展覽氛圍的烘托,幾乎沒有人會覺得有什么不妥,同時也是通過作品本身對藝術家有足夠的尊重,用被火燒過的木頭,精致切割,使每一個部件大小一樣,看到這樣黑色炭木上夾著的各類蔬菜植物,那種跨越灰燼然后重生的感受是能夠真實深刻地傳遞到在場的每一個人。再往里面一個房間,可以看見一整個房間地上鋪滿了細碎的黑炭碎片,在屋外的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至于碎炭之上的是一株半人高的百合花(圖1)。百合有些含苞待放,有些已經凋落。這株百合之后便是中川的大幅作品scared book,作品拍攝的感覺猶如花卉綻放般美麗。雖然站在窗邊,但依然可以很強烈地感受到因為布展所選擇的材質而更好烘托出作品內在精神面貌的智慧:黑色的焦炭碎片,雖然暗黑,但卻在陽光下閃耀著光澤,這是一層重生;百合本身含有敬佩之意,百合落地與含苞未放之間是生命重生的第二個通道;像花非花的scared book讓人浮想聯翩,對藝術家本人肅然起敬,身軀不在,精神永能留世這是第三層重生。從展館選址,到布展裝置和現成品的運用,創意迭出,通過本國藝術家作品,結合本國文化傳統,再注入當代藝術模式下的布展方式,非常巧妙地在整個觀展過程中展現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內核。

圖1 中川辛夫作品

圖2 森田具海作品

圖3 沃爾夫岡作品

圖4 Gideon Mendel作品
有一類藝術家會因為要強調自身作品的獨一性,在尺寸、裝裱甚至印刷上特立獨行,并對每個環節嚴格監控,只為自己的作品內容服務,在這個過程中也無不體現出藝術家們超凡卓越的智慧。如日本藝術家森田具海長期圍繞本國的邊界問題來創作的攝影作品(圖2),所記錄的內容是各種鐵質的圍欄、柵欄等,地點選址在警察局附近或政府部門周邊,同時還有廢棄的各種廠房、工廠附近。他的作品給人一種警戒線的直觀視覺感受,其個展布展選用自己定制的鐵柵欄,采用鋁板裝裱,然后固定在木板上,最后掛在鐵柵欄上。作品中可以看到畫面中圍欄里經常有樹枝伸出,選用鋁板加木板的裝裱方式顯而易見,是一種木和金屬的扁平化融合,很好地呼應了畫面內的內容和拍攝的主題;其次自己定做的柵欄也讓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現場定制的柵欄以圍繞成一個矩形在展場正中間排布而并沒有貼墻排布也是為了由內而外,給人以警戒線這樣更直接的感受來進行的布局。
再如享譽全球的圖片藝術家沃爾夫岡·提爾曼斯,其作品把留白運用到了極致,首先是紙上空間的運用,根據拍攝對象在整張構圖中方位的不同,在紙張上進行不同位置的留白。其次是對空間留白的運用在畫廊或展覽空間里,大大小小的照片在白墻上錯落有致地擺放著,其中一面墻上有沃爾夫岡拍攝的蹲著的人物肖像、站著的人物肖像和俯視的人物肖像(圖3),分別置于白墻下方,和與觀者視平線平行的位置和上方,觀者在觀看圖片時,根據人物的空間方位可以由下而上的觀看,卻沒有一點違和感。這些留白會有助于觀者更好地找到圖片中的視覺中心,這是一種平面化的夸張式美學。除此之外,他的一部分作品以城市地點為界限,來探討邊界問題,照片里內容的邊界,與其印在紙上的位置的邊界和照片本身與空間的邊界三位一體,并不會因為某一個展覽而產生一種定式,而是根據每次展覽位置的不同來進行各種視覺上的組合和調節。他的作品既不借助裝置,也不借助氛圍的烘托,僅僅讓圖片作品置于白盒子展館內,視展覽空間本身為一個整體的裝置,以圖片本身來提醒觀者當下圖片作為藝術品的那種獨一性,同時也在對當下琳瑯滿目和花哨的布展方式給予了自己的回音。
說到藝術家把展覽空間視為裝置,是因為這個展覽空間能夠和自己的作品產生呼應,并且更好地展示自己的作品。此處用展示空間,而不用美術館或者畫廊等,是因為當下的各種展覽不一定都會在美術館劃定一個位置來進行展示,很多時候是定在一個城市,然后在城市中找到適合作品展示的位置或地區,再在適合的地區進行細致的布展,例如地鐵站、飛機場、廢棄的工廠、寺廟、博物館、學校等等。南非攝影師Gideon Mendel拍攝的圖像作品Drowning World(圖4),藝術家走訪了被洪水近乎摧毀的六個國家,同時拍下了各國在水中度日的人物肖像照片。這種全球性的題材一向是攝影藝術家在制定拍攝計劃時非常樂于嘗試的方向,在災難面前,人人平等也很好地通過藝術家的鏡頭傳遞了出來。其作品在參加2018京都國際攝影節時,策展團隊選擇了京都三三九前冰房舊址來進行展示。圖像中破敗的場景和照片中肖像人物齊腰深的水位線與所選位置的環境相得映彰,破舊和銹掉的鐵管,地上一灘一灘的積水,觀者進去看作品時,非常容易身臨其境。這樣的選址和作品的陳列,就完全把展示空間當作了一個現成品裝置。現在國際化的大展都在嘗試脫離傳統意義上的展示空間,為了能更好地拓展藝術的邊界,展示空間的選址與藝術家作品之間的聯系被越來越重視。

圖5 Izumi Miyazaki作品
除了選址之外,也有一些策展團隊或者畫廊會根據藝術家作品的內容來拓展周邊的布局,打破平面作品觀看上單一的特性,讓其在空間上獲得新的延展,以此來與觀者進行互動,從而生成一種新的交互。例如日本青年藝術家Izumi Miyazaki在日本ASPHODLE畫廊的個展,其作品本身以藝術家自己為創作元素,可以看作是一種自拍,但是通過數字技術進行空間變換,從而營造了一種荒誕且帶有民族特色的超現實主義風格(圖5)。策展團隊根據其作品的特點,做了一些作品內容與空間布局的互動,將展廳二樓整個房間的一半空間一分為二,有一半是一個封閉的隔層,上方有兩個圓洞,圓洞下是一個白色的綿墊子,觀者可以跪在上面,然后把自己的腦袋伸到洞里,在被封閉的空間中,兩個人同時把腦袋置于其中,就會在空間里相互對視。封閉空間里的隔斷中布滿了棉花,與燈光的節奏配合藝術家大幅的圖像作品——一片藍天,朵朵白云,自己的腦袋斜眼看著一架飛機從頭頂飛過,有種置身于天空中的感覺,讓人過目難忘。
從圖片作品本身出發,作品內容與展示方式相結合,很多時候早已超出了作品本身,這也是為何僅僅從書籍或文獻上是完全無法體驗到一位藝術家匠心獨具的創作的。在當代藝術作品大行其道的今天,本文僅僅以圖片作品作為媒介,探討了其從自身,到圖片作品與裝置與現成品結合,再到圖片作品以展廳作為裝置的布展,最后到內置空間的改變與隔斷來加強與觀者之間的交互。方式有很多,但主要的內核還是圖片作品本身的深度,與藝術家獨具慧眼的觀察角度,根據作品本身所散發的氣質,配合布展方式,把這樣的氣質和感受最大化的傳遞給觀者,能使其在空間中能有超越平時的精神感受,這不正是藝術的使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