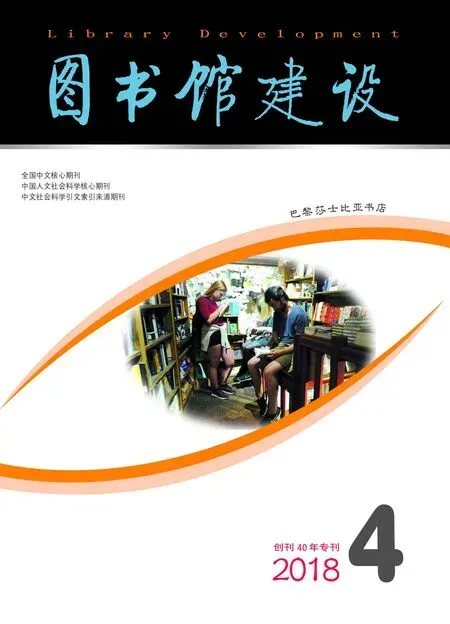回望與《建設》同行的那一程
劉繼維
1978月5月,《圖書館建設》的前身《黑龍江圖書館》被省文化局正式批準定名刊行,成為我國圖書館界創辦較早的專業期刊之一。那時我是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大二的學生,兩年后我來到了省圖書館,1981年走進了編輯部,開啟了第一階段與刊物的同行。
當年的《黑龍江圖書館》季刊,黃軍裝紅領章,素面朝天。刊名題字為集魯迅手體的組合隊。內文以領導講話、會議材料為主,依級別高低排序,首尾相接,魚貫而行,48頁一氣呵成。
初到編輯部,主編為館長楊和生兼任,時而過來坐坐聊聊,審稿編輯的任務是由副主編李修宇完成的。我的主要任務是校對和編務。面對簡易的裝幀,我主動提出可否改換一下面貌。修宇說:“你年輕,還有點兒審美眼光,看著調整調整吧。”于是我找到當時圖書館的美工閆文才設計封面,又到省政府鉛印室與排版的工人師傅商量改進排版事宜,師傅那里存留了一些題頭尾花,我就選擇穿插使用在我們的刊物中。于是刊物就有了脫離文件匯編卻又極其稚嫩的新模樣。
從1981年到1985年,我在編輯部的幾年中,前后換了幾任副主編,李修宇、王科正、趙世良。
趙世良北京人,個性突出,思維敏捷,能言善辯,犀利幽默,高興時能逗得大家開懷大笑,生氣時也能懟得你啞口無言。他北大畢業,又赴蘇留學,是五六十年代少數業內專家之一,上任不長時間就把“副”字去掉了,也是刊物唯一的專職主編。他審稿效率極高,跟我透露說,“把稿件豎著對折,只看前半行就知該文是否能用。”看了前言,便知后語,其思維聯想能力之強,由此可見一斑。
他在任期間刊物的變化比較大,首先是擴容,從48頁擴展到78頁。增加了新內容,開辟了新欄目,突出了學術性,省外專家的文章頻頻露臉。部分稿件編審外委,校對工作也找專業人員承擔。同時注重表現形式,刊物封面每年都有變化,曾經邀請省內著名畫家孟烈為刊物設計了一次封面。此間我的版式設計也有了正式的排版用紙,畫版式是每次付排之前的重要環節,標題如何開,文章如何接轉,字數、頁碼的控制,都需要在此解決。
排版印刷地點幾經輾轉,從工會鉛印室更換到報社印刷廠,我騎車的距離也從南崗延伸到道里,其間還要上下兩個大坡。千字排版的工作量十分繁重,要求編輯每期內容“齊、清、定”后,方能下稿付排。即便如此,撿字工的丟字落段現象,排版過程的改動竄版問題仍時有發生,使得排版工作十分艱巨。為了避免竄動中再出錯誤,付排后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印刷廠的排版車間度過的。“削足適履”這個成語用在此時最恰當,為了幫助工人減輕工作量,許多文章的調整和刪減是我在現場決定的。
自從1839年香港首份華文報章《遐邇貫珍》開始活字印刷起,中國的鉛字印刷大約走過了150年的歷史。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王選發明的激光照排印刷技術,引發了中國印刷行業的一場“光與電”的革命,結束了中國百多年來的“鉛與火”排版業。此時我已調離編輯部,沒能看到廢了武功的排版工人最后離開崗位時的情景,科技在解放勞動力的同時,也讓這一族人失去了飯碗。
趙世良在任時的重大調整,要屬編輯部獨立設置、刊物改為雙月刊并交郵局發行這一系列重大改革了。這一變更,一改以往自辦發行時,輔導部全員打包打卷的手工作坊式的忙亂局面。不過現在回想當年輔導部突擊發行的會戰場面,還是非常溫馨感人的。當時編輯部隸屬于輔導部,部門的工作互有交叉,許多工作都是以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方式進行的,強調彼此間的協作配合,大家的關系也十分融洽。
1985年,我因工作需要調離編輯部,結束了與刊物的第一段行程。
時隔8年,1993年,我又應召回到了編輯部。時任副主編夏國棟主持工作,刊物有了長足的發展。更名為《圖書館建設》,跳出了地域窠臼,開辟欄目,放眼全國,一舉躋身圖書館學核心期刊之列。刊名題字是時任館長兼主編王盛茂回母校北師大參加校慶時,向書法大家啟功先生叩請的兩幅墨寶之一。啟先生外柔內剛、清雋儒雅的字體用于刊首,端莊而顯赫,昔日的拼貼組合走進了歷史。另一幅墨寶是館名,12年后被鑿刻于巨石之上,置于省館新址門前。
回到編輯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參加《中國圖書館建筑集錦》的前期籌備和編輯工作。這一課題立項是夏國棟提出的,得到了國家文化部、省文管會、省圖書館領導的大力支持,同時也得到了全國各級公共、科研、院校圖書館界同仁的積極響應。經過報名、登記、遴選,最終敲定264所圖書館入選。
90年代初,尚處于數字化孕育中的洪荒年代,編輯的工具基本是紅筆、剪刀加漿糊,稿件涂改得無法辨識了,就剪貼、謄抄。編輯這部大型圖冊,雖以照片為主,但文字工作也少不了這些傳統做法。我負責本書建筑圖的編繪工作,這是一項跨學科、跨領域的工作,之前沒有先例。入編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館提供了圖紙,但無質量可言,很多就是藍圖,一些復印件不是深了就是淺了,或是變形了,沒有幾張可以直接使用的。于是我只得重新繪制,仗著自己學過建筑制圖,又有繪圖工具,總算如期完成了90多張平面圖、立面圖的繪制任務。
編此書的一項副業就是刊物的封面有了著落。改革開放之后,全國各地圖書館界迎來了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期,新館建設如雨后春筍。將《建筑集錦》征集來的各館圖片每期一登,十分新穎。刊物順勢開辟了館員繪畫攝影欄目,一時間,刊物有了幾分文藝色彩。只可惜那個年代有相機、能揮毫的館員十分有限,稿源不足,難以為繼,欄目沒能走遠。與如今人人拍,隨手拍相比,雖只間隔十幾二十年,卻恍如隔世,數字化帶給世界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
1998年末,夏國棟高就副館長,編輯部交由我負責。此時正處于跨世紀的當口,計算機逐漸普及使用,出現了用軟盤傳遞的電子稿件,于是手寫稿、打印稿、電子稿并行,稿件管理分開進行。編輯部增設了計算機,學會使用計算機成為這一階段的首要任務。
這期間,我為《建設》設計了刊標,并重新設計了封面。按學術期刊的要求,本刊的編排也朝著更加專業、更加正規的方向發展。每篇學術論文增加了“摘要”“關鍵詞”“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的標注,更加強調“參考文獻”的提供與標注。
2001年,新世紀的第一期,《建設》再換新顏,以端莊大氣的大16開本面世,內頁增至112頁,擴大了欄目設置,增加了發文數量。2000年11月,武漢大學召開“首屆中美數字時代圖書館與情報學教育國際研討會”,一大批國內外圖書館學專家聚集于此,我聞訊報名參會,并對會議進行了全程采訪,形成“會議采風”“大會發言摘要”“小組討論和自由發言摘要”“人物訪談”“大會發言選登”等一組稿件,在新世紀的首刊用30個版面刊發,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和彰顯了本刊的學術性。一些重要發言和人物采訪是根據現場錄音回來整理的。這也是本刊首次采用數碼相機和數字錄音設備進行的會議采訪。
這一年,我被提升為館長助理兼辦公室主任,編輯部的接力棒傳到了畢紅秋手中,我結束了第二階段與《建設》8年的同行。
兩進兩出,相伴十多年,《圖書館建設》編輯部是我在省圖書館工作時間最長的部門,也是我人生中極其重要的一筆財富。它錘煉了我的文筆,拓展了我的思維,提升了我的素質,強化了我的能力,讓我受益終生。
在慶祝建刊四十周年之際,回望與之同行的這段路程,倏然發現消失了幾個身影,他們是:趙世良、李修宇、楊和生、王盛茂。他們每個人無論專職還是兼職,都為刊物的生存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此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
如今,《建設》在新生力量的合力打造下,已是圖書館界的知名品牌,學術地位不斷攀升,集聚了四海八荒的諸神上仙,令我這個曾經的同道為之興奮與鼓舞。回望步履清晰,展望路途漫長,祝今日之《建設》再上層樓,續寫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