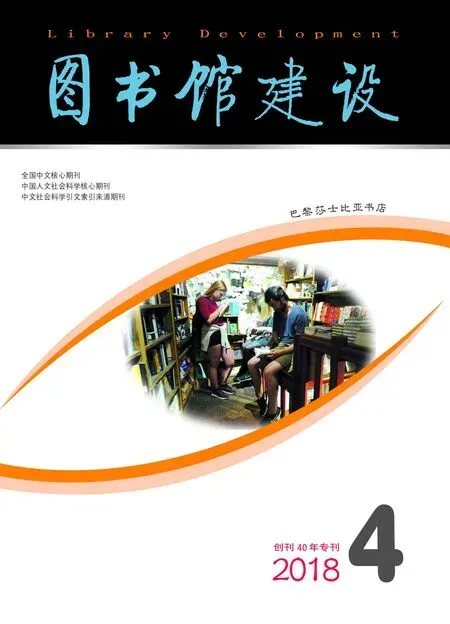《圖書館建設》與我的第一篇“C刊”
謝 歡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23)
每一個人的一生,都蘊含著無數個“第一”,第一次說話、第一次走路、第一次獨自遠行、第一次戀愛……,“第一”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但往往都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對于一位學人而言,第一篇學術論文、第一本學術專著、第一次學術會議、第一場學術報告……肯定也是讓其記憶深刻的!而我發表的第一篇CSSCI來源期刊(簡稱“C刊”)論文正是在《圖書館建設》上!所以說,《圖書館建設》于我而言,自有其特殊的情感。
2007年,我進入蘇州大學社會學院圖書館學專業學習,與大多數人一樣,我也是因為調劑進入這個專業。在收到錄取通知書之前,我從未聽過這一專業,不知圖書館學是何物。不過,既來之,則安之。進入大學以后,學習尚算勤懇,大一結束后,通過一年的學習,對于圖書館學不僅沒有感到排斥,反而有點喜歡上了她。而在學習之余,也慢慢地接觸學術研究,開始看一些專業期刊。不過那時候對于學術期刊并沒有明確的概念,所謂看期刊,大多只是胡亂翻一下,而不少期刊上的學術論文對于當時的我而言,更是晦澀難懂。但是正如俗話說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學術期刊上的文章翻得多了,自然很容易受其感染,內心的“名利之心”也開始萌發,希望什么時候自己的名字也能以鉛字的方式印在這些刊物上。于是,偶爾也會找幾個題目練練筆。
2009年5月,我與檔案學專業的兩位同學合作申請了大學生國家級創新型實驗項目“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現狀及其推進策略——以江蘇省為例”,我主要負責該項目中圖書館與政府信息公開的研究。其時,2008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頒布實施,其中第16條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在國家檔案館、公共圖書館設置政府信息查閱場所,并配備相應的設施、設備,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獲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行政機關應當及時向國家檔案館、公共圖書館提供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因此,該項目后成功立項,我們也獲得了3萬元的經費支持。于是,在當年暑假,我們決定赴南通、揚州、徐州等地調研,檔案學專業的同學重點關注檔案館及行政機關政府信息公開情況,而我則負責圖書館政府信息公開情況的調查。當時計劃的調查對象主要包括圖書館領導、圖書館工作人員以及當地居民,調查的主要內容及方法包括:(1)以政府信息需求者的身份到圖書館(包括訪問圖書館主頁)親身體驗圖書館政府信息服務情況;(2)對圖書館領導以及具體負責政府信息服務的工作人員就圖書館開展政府信息服務相關問題進行訪談;(3)對當地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從公民的角度去了解圖書館政府信息服務工作的相關情況。此后,我又調研了南京、蘇州等地圖書館政府信息服務情況。通過這些調研,我掌握了不少一手數據,于是,基于這些數據我撰寫了《公共圖書館政府信息服務現狀及措施研究——基于江蘇省公共圖書館政府信息服務的調研》一文。文章寫好后,也請指導老師周毅教授、高俊寬老師審閱,兩位老師面對這篇稚嫩的習作,認真審閱并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對這篇文章又進行了修改,修改好之后,決定向《圖書館建設》投稿。
當下,人文社科研究人員對于“C刊”可謂“愛之深責之切”,很多學者以及科研管理部門在認定學術成果時,只承認發表在“C刊”上的成果。而在當時,說實話我對于“C刊”所知寥寥,而之所以選擇向《圖書館建設》投稿,是因為那兩年《圖書館建設》對于政府信息公開這一話題非常關注,發表了好幾篇相關論文,于是我就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投了過去!大約一個月以后,我收到了《圖書館建設》編輯部發來的“退修通知”,通知中要求修改的內容已不大記得了,不過應該不是什么大的改動。在我修改好后,我還是將文章連同修改意見交請高俊寬老師審閱,在高老師認為已經符合修改要求后,我再一次將稿子寄回編輯部。不過此時的心態已不像投稿時,而是多了許多期待與不安!2009年11月3日,我終于收到了《圖書館建設》編輯部發來的正式錄用通知郵件,當時看到這一郵件的激動心情,至今仍歷歷在目,畢竟這是我第一篇被核心期刊(“C刊”)錄用的論文,而我當時只是一位大三的本科生。在拙文被錄用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每次去學校圖書館期刊閱覽室,第一件事都是去查一下新的一期《圖書館建設》有沒有刊出,上面有沒有我的文章。終于,在2010年第3期,我的那篇文章刊發出來!收到樣刊那幾天,每天都會把樣刊拿出來翻上幾次,現在想來,也著實好笑!不過,這確實是一位大三學生的真實經歷!
或許是這篇文章的激勵,我在大學本科階段又陸續發表了七八篇論文(其中有3篇發表在“C刊”之上),據說我在蘇大社會學院留下的這一紀錄至今仍未被打破。而這些學術成果,也為我后來成功保研南京大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后我又繼續深造讀博,博士畢業后留校從事圖書館學教學與科研,這些成就的源頭或許都要得益于《圖書館建設》的那篇文章!所以,每每念及此,我都要感謝《圖書館建設》,敢于刊發一位大三學生的文章,這在很多學術期刊看來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由此也反映了《圖書館建設》對于青年的關心與扶持!這份關心與扶持我在2014年和2017年又有所感受。
2014年9月19日至21日,我至蘇州參加“‘公共圖書館與社會進步’國際學術座談會暨紀念蘇州圖書館建館百年”會議,同時舉行的還有“2014年圖書館學博士生論壇”。在21日博士生論壇那天,我作了《1956年“圖書館為科學研究服務”方針的歷史審視》匯報,匯報最后提到要加強中國圖書館事業中的“十七年史(1949—1966)”研究。我匯報甫一結束,《圖書館建設》的畢洪秋主編就找我說我對于加強“十七年史(1949—1966)”研究的建議很有意義,她很感興趣,約我寫一篇專題文章。當時,我正忙于博士論文的撰寫,為了集中精力撰寫博士論文,我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基本不再寫和博士論文關聯不大的文章,也很少投稿。當時,本想婉拒畢主編的好意,但盛情難卻,于是就有了《圖書館建設》2015年第3期《存史觀變:圖書館史領域的“十七年史”研究》一文,收到樣刊時,讓我意外的是編輯部把我的文章排在了當期第一篇,真是受寵若驚!而在2017年,《圖書館建設》的現任主編肖紅凌老師又請我擔任《圖書館建設》的審稿專家,負責審閱圖書館史、目錄學方向的投稿,同時還請我協助籌劃該刊“數字人文”研究專欄,前幾日又約請我為《圖書館建設》創刊四十周年寫些東西,這些都讓我倍感殊榮!
《圖書館建設》前四十年我雖然只見證了其中的四分之一,但是在這十年辰光,我從讀者到作者再到審稿者,身份雖然在變化,但是對于《圖書館建設》的感恩之心始終沒有變!我也由衷地期待能有機會見證、參與《圖書館建設》下一個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