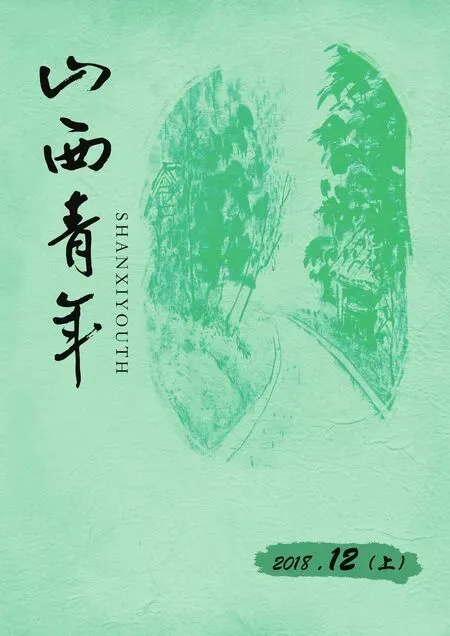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現實人的解放與全面發展
溫 韜 徐 菁
(1.德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云南 德宏 678400;2.中共芒市委黨校,云南 德宏 678400)
一、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關于“現實人”的理論
眾所周知,馬克思吸收了黑格爾辯證法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合理思想,開創性地建立了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主要特色的馬克思哲學。后人追隨馬克思的腳步,以其思想為基礎,結合人類的歷史實踐,延續并發展了馬克思的理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其深刻地揭示了人、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
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唯物史觀、實踐的觀點、矛盾分析法等鮮明的旗幟區分于傳統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哲學,既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又反對將精神、意識等近乎虛無的東西置于世界的始基。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的理論,揭示的是人、物以及人所創造之物本質和發展規律的理論,自始至終都與人類有著密切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揚棄了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費爾巴哈雖然正確揭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但終歸只將人的本質置于形而上學的話語體系中來討論,他認為人的本質是包含在團體之中,包含在人與人的統一之中,卻沒有以實踐和歷史的觀點將人的本質置于現實的社會中來探討。因此,費爾巴哈的“人”只是一個概念上的人,他的人本學不過是一種關于“類”的形而上學理論。而馬克思主義人學,不僅將人的本質視作個體的抽象概念,更將人置于現實社會中,視作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受到現實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支配,人對自然、社會同樣有著認知和物質的需要,人的實踐活動能夠充分體現這種關于人總體性的觀點。區別于傳統西方理性主義人學形而上學式的思辨和邏輯,也區別于非理性主義人學將意志、精神、存在等非物質的東西作為討論人本質的出發點,馬克思主義人學強調,人的本質必須在人的社會中討論,也必須擯棄主客二元對立的觀點,用總體性原則來指導研究人的本質問題。人在馬克思主義中,不再單純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理性邏輯中的符號,也不是擁有固定屬性的人。而是在現實中,可以為經驗所觀察、認識,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發展的以主體勞動實踐為特征的社會人。
既然人的本質依賴于運動、變化、發展的人類社會,人類社會又包羅萬象,人與人無時無刻不與他人發生著聯系,那就意味著人的本質也絕非是靜止和孤立的。那么對于人和人類的發展方向就絕不能是單向度的,人和人類的發展路徑也絕不可能擁有固有的模式。
二、克服異化的路徑
馬克思主義關注人和社會的問題,從人的本質可以看出,人與社會的發展是相互依存的。人的主體性實踐構建出社會形態和社會關系,由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人的勞動實踐其實就是自我建構和實現的過程。
馬克思認為,人的主體性意味著人的勞動實踐也就是人的類本質活動應當是自由的、自覺的,但是由于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和生產關系,人的勞動實踐活動變得不自由、不自覺了,而變成了一種“非滿足勞動需要,只是滿足勞動需要以外的一種需要手段”。異化的勞動揭示人類本質的異化,在這樣的勞動實踐中,勞動的實現以物(產品)的形式呈現;人與人的關系,被代替為物與物的關系;人勞動實踐的目的不再是自我的構建與完善,而是特定的、對象化的物。因此,在這樣的生產關系中,人必然是要尋求自由和解放的。
現代社會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類對自身的優越感也與日俱增,人類對自身能力的自信也達到了歷史的高峰。然而,在這些看似美好的現實中,人的異化卻沒有停止。當人們在為自己占有物數量增加和業績提高而歡呼的時候,當人們在社會中實現那被物化、被對象化了的目標而獲得地位或戰勝對手的時候,“幽靈般的對象性”游蕩在現代人的工作之中,人勞動實踐的主體性地位依然被對象化的物所占據。在物質文明發達的社會中,被異化的人感到的是空虛和壓抑。盧卡奇認為人為了要實現自由和解放,就必須要克服異化,必須從總體性上來認識人類。盧卡奇高度評價了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將黑格爾哲學中的歷史傾向推到了邏輯頂端,并指明了“實踐的革命方向”,盧卡奇認為無論是歷史事件還是人都必須置于一個相互聯系,各要素均統一的社會總體中來認識,單純的知識經驗堆積是不能形成總體的,必須由具有總體性的人發揮主體性構建起總體。由此可見,在現實中盧卡奇的總體性是歷史的和主客統一的,其在《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認為“一旦主體作為自我生產和自我保持連續性的社會化人類時,那么一切物化和異化就會自然消解。”
馬爾庫塞將現代人的異化進一步用“單向度的人”來加以闡釋。他認為,在現代工業社會生活的人們以生存為目的,以永恒化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為單向度的追求目標,對技術理性崇拜卻缺少反思,技術理性在社會中無處不在,社會的一切運動變化均受其左右,是為單向度的社會,而人們單純地以物質財富和安逸的生活狀態作為追求,個人依附于物和關系而存在,主體性漸漸被淡忘,是為單向度的人。
社會人構建起的技術理性力求建立起整體統一的社會,驅逐異己思想,同化異己力量。人們以看似理性、看似合理的方法對個人進行非理性、非合理地社會控制,人的理性實踐在社會化過程中由于喪失了主體性而變成了非理性實踐,在單向度的社會中,個人與公共的界限變得模糊,各要素的對立變為一體,不同抉擇變為同一。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否定和批判的存在地位被剝奪了,在這種單向度的社會與單向度的人之中,反思與創造尚且屬于稀罕物,實現個人的超越性(Transzendenz)或者說實現個體人或人的類意義更是無從談起。因此打破單向度,實現人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的自由和解放便成為了被技術理性禁錮著的人們的當務之急。
存在主義哲學家們將超越性賦予很高的地位,本體論上是一種近乎世界本質的存在,現實層面上是人存在的表達途徑。其中海德格爾認為:“超越就是最本質的存在,超越表示主體的本質,表示主觀性的基本結構,超越構成自我。”①薩特則認為:“人經常超越自己,當人在投出自己、把自己消融于自己之外的時候,他就造成了自己的存在。”②
可以看出,存在主義哲學家們對超越性的描述是以現象學方法為基礎,其描述是抽象的,對超越性的論證是形而上的,如此單純的精神自在之物是虛無縹緲,難以認識的。因此,要想對超越性進行透徹的認識還應當回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人主體性實踐的層面來理解。盡管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的觀點有缺陷,但依然能夠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超越性論證的借鑒。
馬爾庫塞和其他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認為,在歷史活動中,人的主體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人的自由應當是終極追求的目標,它不僅僅是是非異化人的特征,更是人本體本質存在的前提。人的需求需要辨析,人的追求動機不應由非主體因素所刺激產生,而必須源自于人自身自發、自愿的行動。因此,人要想實現超越性就必須首先在現實中實現人的多向度,進而實現自由與解放。
人的類自由必然首先由個體人的自由開始,而多向度的實踐彰顯著人在現實中主體性的發揮,尋求個人的全面發展,運用理性進行否定之否定,不斷革新認識也就變得理所當然。所以的人的全面發展便成為了個人實現自由與解放的必由之路,而個人實現自由與解放也與人的類本質實現自由息息相關。從人的類本質的自由角度來看,由于個體和群體的關系不僅僅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人的本質蘊含在社會關系當中,其中更兼有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所以,人的類本質要實現自由,不僅僅要由個人的自由與覺醒作為推動,更重要的是在現實社會中,在各類關系中醞釀出關于人類命運、人類存在意義的自由意識。這種意識首先是社會的,因為只有社會才能定義人類,這種意識需要在社會中達成共識;其次這種意識是人類的,因為它涉及人類的自然生存和生活的終極追求。
人是現實中的人,本質是其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關系是人整體性的直接表現,其各要素的和諧是人實現自由與解放的先決條件。因此,自洽的人不應當被現實和社會關系所羈絆,在精神尺度上淪為單向度。
三、追求人的全面發展
個人和人類都擁有著需求,在理性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這種需求異化為對自然的征服欲和對物狹隘追求,并將勞動實踐產品作為確認自身的標準。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中闡述道:“以人的主體性和對自然的征服欲與統治權為主旨的文化啟蒙精神只可走向反面。”當人們運用理性改造自然,獲得發展之后,理性的膨脹限定人們的眼界,人在繼續認識、發展的時候,理性變得一家獨大,人類企圖以理性為絕對標準來丈量世界,過分的自信令人變得盲目和單向度,個人和人類的發展掉入了理性的泥淖。按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含蓄說法,人類生活在“神話—啟蒙—神話”的西西弗斯式的循環之中。
在理性的泥淖中,現實生活層面的人的生存狀態是被異化的,人的需求被局限為對象化的物,因此可以理解為人被自身創造出來的東西所禁錮,失去了自由。實現人自由解放這一目標需要克服異化,消除異化在于人在精神層面消除單向度。所以,追求并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多向度便成為了人的根本需求。
人的全面發展既包括個人的全面發展也包括人合類性的和諧發展。個人的全面發展最早由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正式提出,主要包含現實人在社會關系總和中的全面發展;個人在能力方面的全面發展以及在之后的著作中提到的人與社會全面契合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也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觀點之一。馬克思認為,人是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最終占有自己的本質。所以個人在認識、能力、實踐方面的全面發展就變得勢在必行。
盧卡奇以總體性的觀點來考查人類社會與個人,人的交往和實踐都是相互聯系的,并被人的主體性統御。而實現人實踐的主體性是人克服異化,實現自由與解放的先決條件。這就要求個人能夠駕馭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在總體性中做出清醒的認識和恰如其分的決斷。這其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異化和物化表現的是人在認識和實踐方面局限性的體現,個人寧愿失去主體性而依附于物、關系,成為異化的人以獲得社會關系各要素的認可,這本身就是人全面發展欠缺的體現。因此,人的全面發展是克服異化的內在要求。
人本質實現的前提是實現自由,是打破單向度實現多向度。在思想上,肯定與否定并存,批判與繼承兼有,既有揚棄又有超越。單向度的社會并不是看似有序,其實并不是自由與解放的,人的視線被局限在一定的角度,人的認識被限定在某一領域,人的自我學習和自我認識是缺失的,取而代之的是填鴨式的信息灌輸。因此,人的全面發展是實現人的本質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自始至終都在追求全人類的自由與解放,人類的解放首先源自于個體的覺醒和個體的解放,而個體的發展是否屬于自發地合類性發展便是為實現人類解放所必須要考慮的事情了。人類社會是多元而復雜的,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個體的合類性發展必然帶有全面性,即個人的全面發展。因此,個人的全面發展也是人類社會全面發展的前提。
弗洛姆以精神分析法得出人類“生存兩歧”的困境,這其實就是具有普遍性的人性的異化。人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與脆弱,為了生存,人們將自身與自身以外的東西對立起來,犧牲自我的主體性來填平自身與世界的溝壑以克服孤獨,自愿投身于制度、異化的生產關系和與人本質分離的種種客觀標準即逃避自由。異化了的人性令人們將自身的生存依靠變為自身之外的某種力量或者物質,而不是應然的自己。人的全面發展是人本主義的體現,人或者人類是我們一切實踐活動的靶向,馬克思尋求的人的解放其實也就是精神的解放,是達成個體、社會、人類關系的最終和諧,人類本質的實現與人本性的復歸,是人類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矛盾的化解,最終將人作為目的而存在從而使得在各個維度上實現人、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
注 釋:
①[德]海德格爾.論根據的本質[A].海德格爾選集(上)[C].上海:三聯書店,1996:169.
②[法]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A].存在主義哲學[C].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