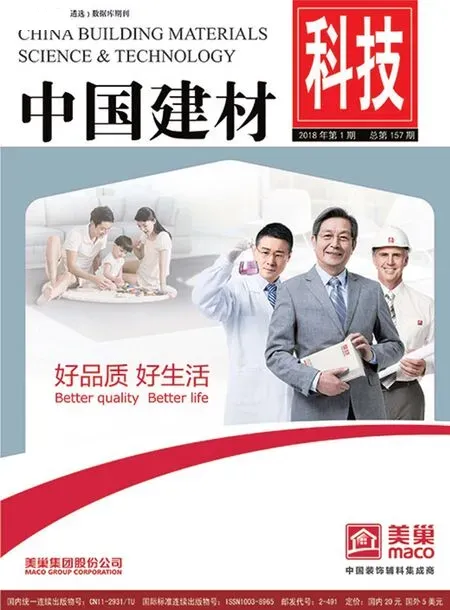剪紙藝術在建筑空間表皮上的數(shù)字化轉換
在建筑出現(xiàn)之前,我國古代先民在居住的巖洞墻壁上繪制了與人類生活相關的馴養(yǎng)、狩獵、舞蹈、祭祀、戰(zhàn)爭等場景圖畫來美化生活環(huán)境。之后,隨著文明的發(fā)展,人們的居住方式因地理、氣候等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差異而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言“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穴居和巢居成為原始先民的主要居住方式。之后,隨著建筑技術的進步,我國北方的穴居或半穴居的居住方式演化為窯洞式住宅及地面式住宅。我國南方早期的干欄式建筑形式演化為木構架建筑形式。隨著結構性建筑出現(xiàn)及裝飾技藝的發(fā)展,人們采用顏料涂繪或雕刻的方法將圖畫與紋樣裝飾于建筑物之上,建筑物上的裝飾開始以獨立的形態(tài)出現(xiàn)并依附于建筑物上,建筑裝飾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向及多變的裝飾效果與藝術風格。
1 剪紙在建筑上的應用
民間藝術中的剪紙藝術自誕生起,就成為建筑裝飾的主題之一,其形態(tài)樣式隨著建筑工藝、材料的演化不斷更新、發(fā)展,并廣泛的應用于建筑空間設計。剪紙藝術在我國的發(fā)展歷史悠久,自西周成王剪桐葉為“圭”封弟以來,剪紙就在人們的世俗生活與理想世界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剪紙作為意識的物化形態(tài)在形成的過程中經歷了諸多演變。早期的剪紙多以鏤、刻、剔、剪的技藝在絹帛、金銀箔、皮革、樹葉等薄型材料上剪刻紋樣,題材有動物、人物、花卉、符咒等,多用于婚喪、巫祝等民俗活動中。隨著紙張的出現(xiàn),剪紙逐漸普及,剪紙技法逐漸趨向成熟,其題材、內容日益多元化,被廣泛應用于建筑裝飾,成為建筑裝飾的主題之一。宋代,隨著造紙工藝的完善,剪紙成為一項專門性的藝術活動,出現(xiàn)了剪紙的專業(yè)藝人,南宋周密所著《志雅堂詩雜鈔》中載有:“舊都天銜,有剪諸色花樣者,極精妙。又中原有余承志者,每剪諸家書字,畢專門。其后有少年能于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類,極精工。”隨著這一時期建筑建造技術的完善、作為建筑外立面的重要裝飾構件的門窗樣式趨向成熟,在門窗上裝飾剪紙圖樣逐漸流行起來。明清時期,建筑的實用性與裝飾性并重,門窗的工藝技術多樣,裝飾手法多變,剪紙在建筑的外立面上的應用達到了高峰。在中國的南方與北方、宮廷與民間窗花剪紙成為裝飾建筑外立面的重要手法,因地域、文化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應用于宮廷的套色剪紙,應用于民間的單色剪紙,應用于北方的彩色窗花,應用于南方的貼金剪紙等類型,大量的角花、團花等圖形被用作裝飾,有植物、動物、文字、故事等多重題材。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建筑的形式、結構、材料、技術等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剪紙除了被直接用于建筑裝飾,其圖形樣式、形式美法則、制作工藝及技術也被廣泛應用于建筑設計中,尤其是在建筑的外立面設計上體現(xiàn)出獨特的風格與韻味。
2 剪紙在建筑空間表皮上的體現(xiàn)
剪紙藝術在建筑上應用經歷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同建筑環(huán)境。剪紙藝術在傳統(tǒng)建筑上的演化首先得益于傳統(tǒng)木構架建筑的產生。木構架建筑形式主導了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形式與建造工藝,木構架建筑的支撐主要由梁柱完成,因此,在墻體上采用大面積的鏤空裝飾成為可能。建筑因其所在地區(qū)的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差異,其外立面裝飾呈現(xiàn)出不同的風格樣貌,在我國,傳統(tǒng)建筑外立面裝飾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門、窗、花墻等。 東漢《說文解字》中對門的解釋為“門,聞也,從二戶;戶,護也,半門曰戶。”對窗的解釋為“在墻曰牅,在屋曰囪。窗,或從穴。”門與窗最早出現(xiàn)于建筑中,主要用于出入門戶及通風采光,其功能性占首要地位。木構架建筑中,門的樣式多為板門及槅扇門。槅扇門又稱格門。唐代,隨著建筑工藝的成熟及門窗工藝的逐漸發(fā)展,門窗的樣式不再受到建筑形式的制約,疏朗簡潔的方格、直欞隔扇形式的門窗成為建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宋代,隨著建筑柱身比例的增高,建筑開間的擴大,門窗的結構逐漸趨向復雜,格門成為門的主要樣式,大量用于皇家及民間建筑中。格門在之后的歷史進程中,出現(xiàn)了槅心和裙板等構件[1],逐漸豐富完善,形成了中國古代建筑門的主要樣式——隔扇。隔扇由縱向的邊挺和橫向的抹頭構成木框骨架,內部分別由上至下設置絳環(huán)板、格心、裙板,格心部分多采用鏤空圖案的欞格構成,絳環(huán)板、裙板上雕刻有裝飾圖案。傳統(tǒng)建筑的窗由窗欞和窗框構成,窗欞是窗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窗欞形式多樣,從構造可分為直欞窗、檻窗、支摘窗、什錦窗、橫披窗、空窗等類型。傳統(tǒng)建筑中的門窗造型多樣、其鏤空的窗欞通過多樣的連接組合構成了虛實結合的空間效果,展現(xiàn)了其與剪紙藝術一脈相承的藝術淵源。而花墻則是將墻面與門、窗、剪紙造型藝術相結合而產生的又一建筑形式。
近年來,建筑設計在現(xiàn)代藝術思潮的推動下,呈現(xiàn)出多樣的、多維的面貌。建筑與剪紙藝術相結合,成為其發(fā)展方向之一。在現(xiàn)代建筑設計中,剪紙藝術在建筑上的應用主要體現(xiàn)為在建筑外立面——建筑表皮上的鏤空設計。建筑表皮上的鏤空設計不僅起到隔絕并聯(lián)通建筑內外環(huán)境的功能,還起到防風、隔熱等使用功能的要求,并滿足設計師及使用者對建筑裝飾性、藝術性、個性的體現(xiàn)。2009年,世界博覽會在中國上海舉行,世博會國家場館建設風格多樣、異彩紛呈,建筑的外立面成為表達設計主題及民族精神的最好途徑。韓國館、波蘭館、俄羅斯館等均以剪紙作為建筑外立面設計主題來體現(xiàn)其國家、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凹凸、鏤空的建筑表皮融合了不同國家的民族符號,帶給人們不同的視覺體驗。數(shù)字化技術的實現(xiàn)、建筑材料、建筑技術的更新使得剪紙與建筑表皮的融合成為現(xiàn)實。剪紙造型、剪紙構成方法、剪紙制作工藝與技術等數(shù)字化技術的實現(xiàn)將設計思維在建筑表皮上得到了徹底的解放[2]。
3 剪紙造型數(shù)字化在建筑表皮上的轉換
我國傳統(tǒng)建筑的表皮裝飾造型主要來源于門、窗、花墻等裝飾造型,門、窗的槅心與窗欞的裝飾紋樣多樣,就外框造型來講,有方形、圓形、扇形、八角形、葫蘆形、瓶形、花型等,而槅心與窗欞的紋樣造型則有規(guī)則紋樣及繪畫性紋樣。如規(guī)則性的回紋、工字紋、雲(yún)紋、花結紋、冰裂紋等。而繪畫性紋樣在造型上則更為隨意,題材也更多樣。現(xiàn)代建筑表皮的剪紙造型則更多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構成藝術及設計思潮的影響,造型大膽、簡潔。僅以單純的圖形進行有序的組織即可形成具有強烈時代感、現(xiàn)代感的圖形[3]。數(shù)字化圖庫的建立可將這些圖形、圖樣以數(shù)字化參數(shù)的形式儲存起來,并通過計算機技術直接轉化為可用的數(shù)字資源。同時,新的圖形軟件的開發(fā)也將有助于設計師在數(shù)字化模式下完成建筑表皮的設計及修改。世博會波蘭館的設計就采用波蘭傳統(tǒng)的民間建筑圖形作為設計母題,在保留圖形歡樂、愉悅的氣氛的基礎上,對傳統(tǒng)圖形加以改造,將圖形加以簡化、現(xiàn)代化。
4 剪紙構圖數(shù)字化在建筑表皮上的轉換
中國傳統(tǒng)建筑立面上的鏤空裝飾——門、窗、花墻等的裝飾構成均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圖形的構圖圖式,內容豐富多樣。傳統(tǒng)門、窗的欞格連接構成方法與剪紙的圖形構成方式有諸多共通之處。剪紙圖形的重復、對稱、節(jié)奏、韻律等形式美法則被廣泛應用于建筑門窗的格心設計中。重復是傳統(tǒng)門窗格心設計的基本圖式。相同或相似的物象通過重復排列,使對象特征突出、形式統(tǒng)一,強化了人們的視覺印象。重復構成方式被廣泛應用于中國傳統(tǒng)門窗的基本構成中,它采用水平或垂直的單一方向的二方連續(xù)構成形式,或采用水平、垂直兩個方向的四方連續(xù)構成方式,形成穿插錯落、富有節(jié)奏、韻律感的圖形圖樣。對稱也是剪紙圖形重要的構圖形式之一,我國南北朝時期的“對馬”、“對猴”剪紙造型即體現(xiàn)了早期中國人的世界觀與哲學觀。對稱的欞格結構具有均勻、協(xié)調、莊重、完美的視覺效果。剪紙的對稱形式分為點對稱和軸對稱,在圖式內容上體現(xiàn)為完全對稱與相對對稱。對稱構圖中,為避免由于絕對對稱而產生單調、呆板的感覺,在整體對稱的格局中加入一些不對稱的因素,增加了構圖的生動性和美感。重復與對稱窗欞的網格狀的骨架結構連接起了多樣的圖形單元,構成了規(guī)則化的圖形樣式,循環(huán)往復的圖案造型精巧雅致、賞心悅目,傳達出含蓄、理性的情感,在建筑門窗及剪紙構圖中廣為應用。除了規(guī)則化的槅心與窗欞構圖之外,富于變化性的圖畫樣式也在槅心與窗欞設計中廣為應用,看似隨意,實則遵循著一定的規(guī)律。圖形所有的筆畫相連,表達出個性化的主題。在現(xiàn)代建筑表皮設計中,構圖形式在繼承傳統(tǒng)構圖形式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并引入現(xiàn)代化的設計構圖理念,使構圖形式更加符合現(xiàn)代化建筑的特點。
傳統(tǒng)建筑的門窗作為建筑表皮的一部分在造型樣式、空間結構等方面與傳統(tǒng)剪紙紋樣形成了高度的契合,剪紙的構圖及鏤刻技藝對其影響顯而易見。這使得建筑外立面尤其是門窗的設計呈現(xiàn)出裝飾樣式多元化,風格華麗、細致。剪紙藝術在二維的平面上通過剪、切、割、鏤、雕等技藝將平面圖形與三維空間聯(lián)系起來,陰線與陽線共用,陽線線條相連,陰線線條相斷,圖形的實與虛實現(xiàn)了多樣的空間變化。
5 剪紙制作工藝及技術數(shù)字化在建筑表皮上的轉換
數(shù)字化技術的應用使得剪紙與建筑有機結合,剪紙在建筑表面的應用成為可能,并更加精確、更加便利。建筑表皮與剪紙藝術的數(shù)字化結合主要體現(xiàn)為以下幾種形式。
5.1 鏤刻
鏤刻非常注重線面的處理及形象的表現(xiàn),作為一種雕刻技藝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現(xiàn)在器物裝飾上,后被廣泛用于石、木、金屬、紙張、布帛等裝飾領域。作為剪紙藝術的基本技法之一,鏤空有助于在局限的空間中創(chuàng)造形象,在畫面中構造新的空間。剪紙的鏤刻應用于建筑,使得建筑表皮被賦予了新的藝術形象,同時又獲得了空間。
5.2 折疊
折疊是剪紙制作工藝中的關鍵技術環(huán)節(jié)之一,在剪紙過程中,紙張通常都要經過折疊來形成不同的軸線,鏤刻通常都是在經過折疊的面上來完成,折疊所形成的面成為剪紙圖形的構圖空間,剪紙的折疊方法通常有對稱折疊與非對稱折疊,不同的折疊方法決定著剪紙展開后所形成的面貌。
5.3 拉伸
剪紙作品在經過折疊、鏤刻等工藝之后,需要將折疊的紙張拉開,展開和未展開的造型都將成為建筑表皮的設計靈感來源之一。在展開的剪紙上,不同面上的鏤刻效果得以完整呈現(xiàn)出來。此外,剪紙作品的展開本身也是剪紙作品的藝術手法之一,如我國民間剪紙中的剪紙掛飾就是采用折疊、剪切、拉伸等步驟,使得剪紙作品形成垂掛的效果。因此,拉伸使得剪紙作品完成了由二維空間向三維空間的轉變。這種剪紙的表現(xiàn)方法被廣泛應用于建筑設計中。如石墨烯剪紙材料變形拉伸的應用為二維剪紙。
5.4 造型
在現(xiàn)代建筑設計中,剪紙的造型也發(fā)生了變化,剪紙圖形依據(jù)設計主體和思想進行改變,在現(xiàn)代建筑設計中,抽象理性的剪紙圖形與具象含蓄的剪紙圖形共同構成了剪紙圖形。
剪紙作為中國最具特色的民間藝術之一,來源于早期的巫神信仰,現(xiàn)今,剪紙作品在室內裝飾中較少出現(xiàn),但其沉郁的藝術風格與鮮明的民間圖案成為現(xiàn)代藝術的靈感來源,剪紙圖形設計、制作靈感被廣泛應用于建筑外皮鏤空面的設計中。鏤空的建筑表皮使得光線進入室內,形成色彩斑斕的視覺體驗。建筑表皮被賦予紙張的可鏤空、可折疊、可拉伸、可造型等特性,數(shù)字化技術與剪紙藝術構思相結合,剪紙造型要素在建筑表皮上得到衍生。
[1]孟琳.傳統(tǒng)建筑中木門窗裝飾與式樣演變分析[J]高職論叢2010-12-15
[2]公琪.從剪紙到建筑表皮空間造型要素的轉譯[D]長春工業(yè)大學 2016-04-01
[3]魯杰.中國古建筑藝術大觀:門窗藝術卷[M]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