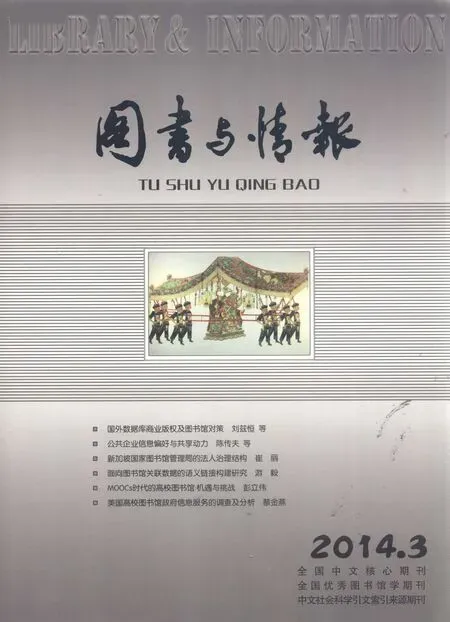挪威版權(quán)延伸性集體許可制度探析——以挪威國(guó)家圖書館Bokhylla計(jì)劃為例
2014-02-27 06:46:39劉茲恒,溫欣
圖書與情報(bào) 2014年3期
關(guān)鍵詞: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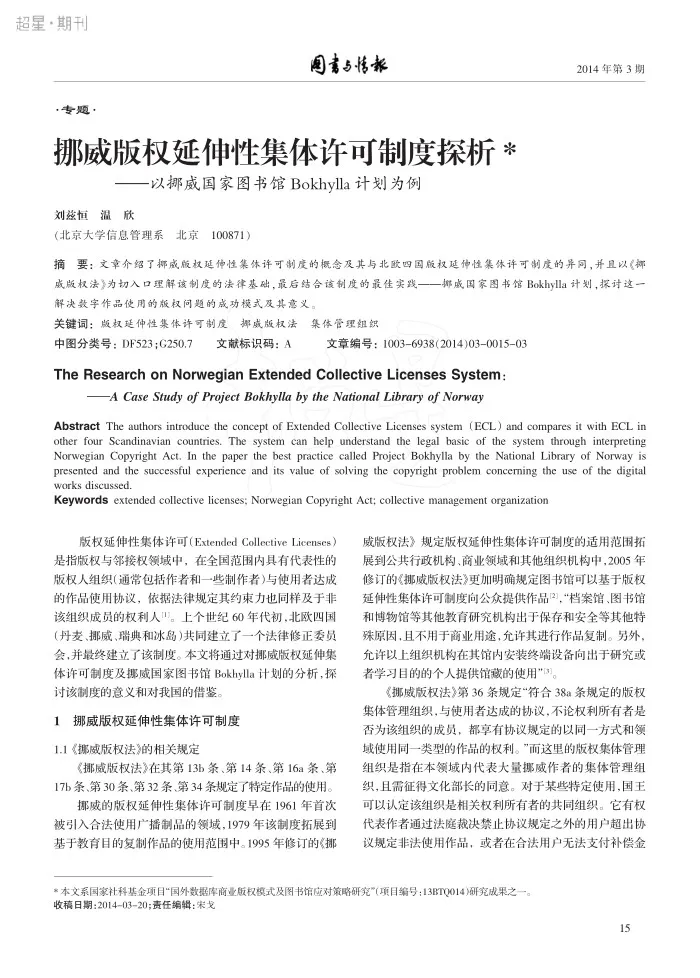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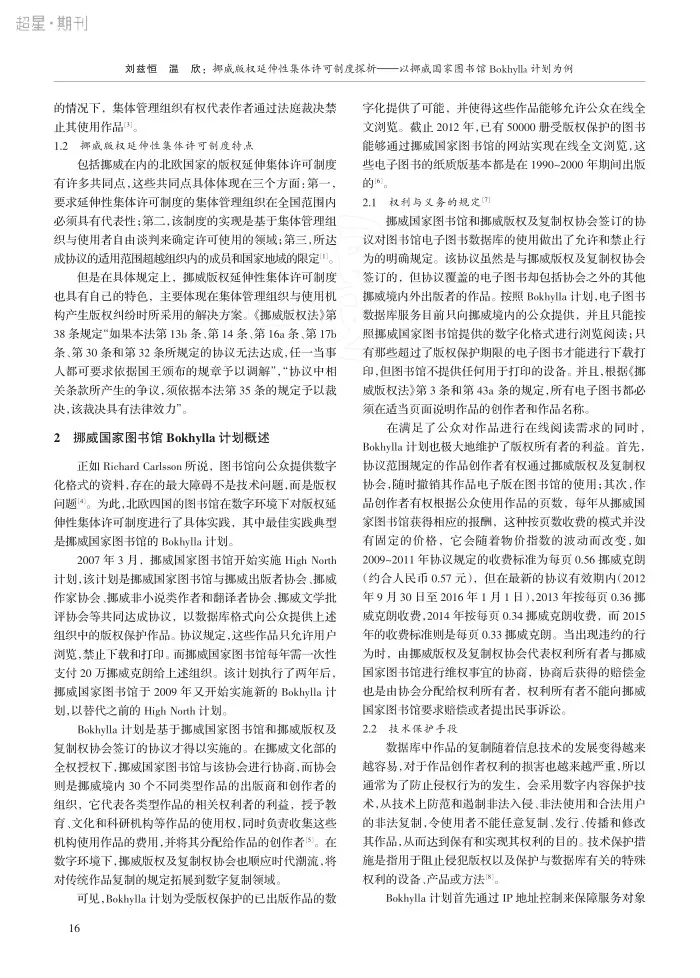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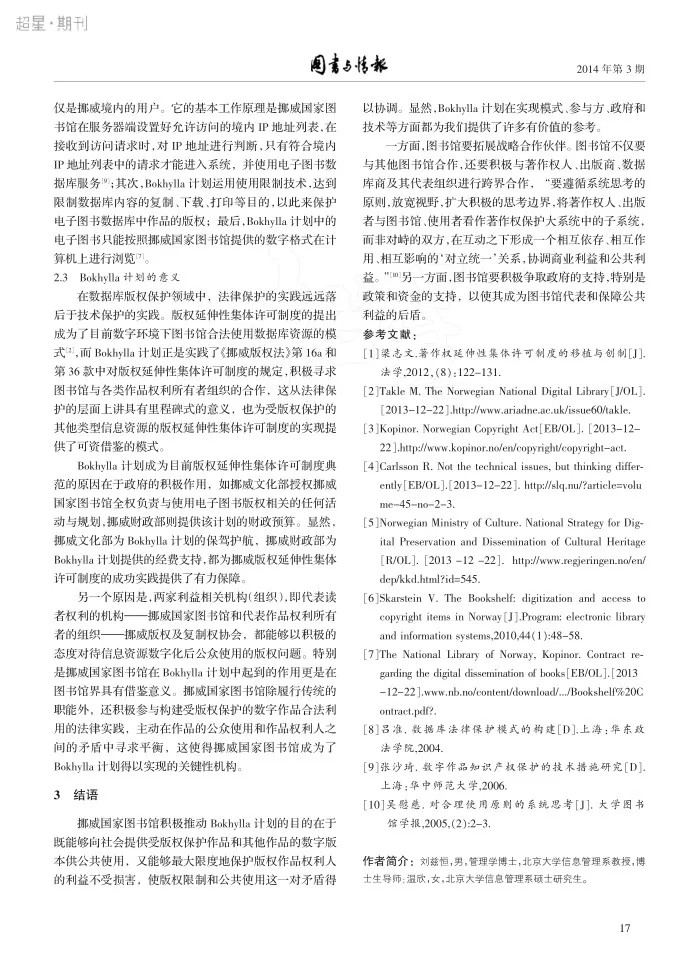
猜你喜歡
遼金歷史與考古(2019年0期)2020-01-06 07:44:44
學(xué)術(shù)論壇(2018年4期)2018-11-12 11:48:50
法大研究生(2018年2期)2018-09-23 02:20:40
世界憲法評(píng)論(2017年0期)2017-12-06 09:10:10
中國(guó)衛(wèi)生(2016年7期)2016-11-13 01:06:26
中國(guó)衛(wèi)生(2016年11期)2016-11-12 13:29:18
中國(guó)衛(wèi)生(2016年9期)2016-11-12 13:27:58
中財(cái)法律評(píng)論(2016年0期)2016-06-01 12:17:10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2期)2015-07-31 18:10:50
時(shí)代法學(xué)(2015年6期)2015-02-06 01:3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