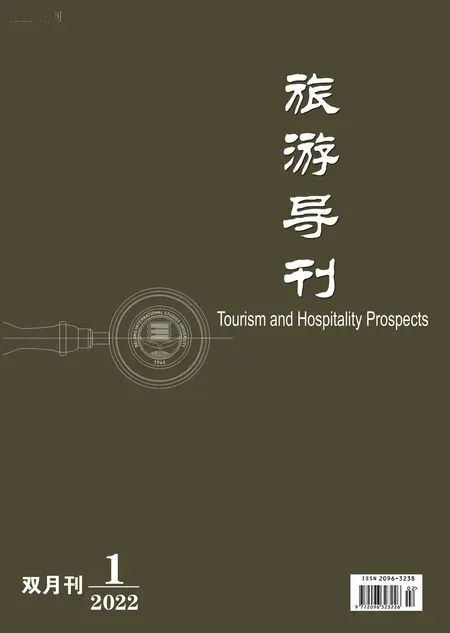社會關(guān)系視域下的VFR旅游主體互動:研究綜述與理論框架
白 凱 璩亞杰
(1.陜西師范大學(xué)旅游與環(huán)境學(xué)院 陜西西安 710062;2.上饒師范學(xué)院體育學(xué)院 江西上饒 334000)
引言
探親訪友(Visi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旅游(以下簡稱VFR旅游)研究始于Jackson在20世紀(jì)90年代發(fā)表的一篇論文《VFR旅游:是否被低估了?》。此前,VFR旅游在學(xué)界和業(yè)界均未獲得足夠的重視,原因在于:人們主觀地認(rèn)為,與其他旅游類型相比,VFR旅游的研究價值、經(jīng)濟(jì)價值微乎其微;其發(fā)生超出了旅游市場營銷的影響范圍,很難受到外部旅游的消費(fèi)刺激與影響;統(tǒng)計(jì)、測量VFR旅游的經(jīng)濟(jì)貢獻(xiàn)率、市場規(guī)模有一定技術(shù)難度。
從20世紀(jì)90年代開始,VFR旅游在全球范圍內(nèi)迅速增長,在有些地區(qū),VFR游客已成為主要客源,如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等,VFR旅游的規(guī)模效應(yīng)和經(jīng)濟(jì)貢獻(xiàn)日益凸顯。這也刺激了學(xué)界對該研究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大量VFR旅游研究的成果不斷出現(xiàn),VFR旅游的市場規(guī)模、旅游者行為特征、VFR旅游對目的地經(jīng)濟(jì)影響及營銷策略等均成為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
進(jìn)入21世紀(jì),VFR旅游研究者開始關(guān)注東道主(Host)的角色與作用,此類研究主要聚焦于東道主對VFR旅游活動的影響,同時強(qiáng)調(diào)東道主在接待VFR旅游者過程中自身利益的損害。這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VFR旅游中主客關(guān)系互動的探討,但其深度還明顯不夠,缺乏對二者關(guān)系類型的分析,也未觸及二者互動關(guān)系的深入關(guān)聯(lián)研究。
顯然,VFR旅游者與其東道主在目的地的社會關(guān)系是明晰VFR旅游與其他旅游類型區(qū)別的關(guān)鍵所在。以此為研究起點(diǎn),本文意欲在兩個層面推動VFR旅游的研究發(fā)展:首先,從社會關(guān)系視角重新審視VFR旅游的概念、VFR旅游的類型以及VFR旅游中東道主的概念;其次,以華人VFR旅游子群體為理論分析對象,建構(gòu)社會關(guān)系視域下VFR旅游的主體互動機(jī)制,明確VFR旅游主體互動的基本特征與運(yùn)行方式。
一、理論分析起點(diǎn)
1.VFR旅游與VFR旅游者
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VFR旅游研究的不斷深化,關(guān)于如何定義VFR旅游的爭論不斷升級,歸總而言,3種視角的定義可供借鑒:①目的論的VFR旅游定義,主要從旅游者動機(jī)角度來定義VFR旅游。如TsaoFang等學(xué)者認(rèn)為,VFR旅游是“以探親訪友作為主要旅行目的的旅游”。McKercher指出,這種類型的旅行參與者,大多數(shù)的主要目的是探親訪友,該目的是VFR旅游定義中必須要提到的。②住宿類型論的VFR旅游定義,主要依據(jù)旅游者的住宿類型來定義VFR旅游。如King指出,VFR旅游應(yīng)該主要以旅行者的實(shí)際住宿類型來界定和劃分。Boyne等人認(rèn)為,“VFR旅游就是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常住地,暫時和自己的親朋好友住在一起,或者是為了在旅行過程中有一個住的地方而和自己的親朋好友住在一起,旅行距離要遠(yuǎn)離自己的常住地15公里以上”。Kotler等人指出,“VFR旅游者,顧名思義,就是住在親朋好友家的人”。③目的與住宿類型論結(jié)合的VFR旅游定義。如Backer于2007年提出的“旅行目的或(和)住宿類型與探親訪友相關(guān)的旅游就是VFR旅游”。
若按照目的論來界定VFR旅游,那些以探親訪友為主要旅行目的、且和親朋好友住在一起的人即為VFR旅游者;但那些雖和親朋好友住在一起,其目的不是探親訪友而是旅游的人,則會被排除在外。若按照住宿類型論來界定VFR旅游,其涵蓋范圍比目的論的VFR旅游更為狹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VFR旅游者都會和親朋好友住在一起,有些人在探親訪友和旅游的同時,會選擇商業(yè)性的住宿設(shè)施。若從技術(shù)統(tǒng)計(jì)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目的論”還是“住宿類型論”的VFR旅游定義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定義所指的VFR旅游者范圍不能完全涵蓋現(xiàn)實(shí)意義中的VFR旅游者。Backer提出的目的與住宿類型論結(jié)合的VFR旅游定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bǔ)了目的論定義與技術(shù)論定義的缺陷,也回應(yīng)了許多學(xué)者對于VFR旅游市場被低估的討論,但忽略了VFR旅游者與VFR旅游東道主之間的社會關(guān)系聯(lián)結(jié)。
那么,應(yīng)該如何來看待VFR旅游者呢?作為一個經(jīng)驗(yàn)性概念,“VFR旅游”如同“旅游”概念一樣,其概念內(nèi)涵、外延與邊界均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在該限制下,人們常常將討論集中于一些無爭議的核心部分(如純粹的旅游者),而漠視那些邊緣事物(如順帶旅游者)。審慎地看,VFR旅游中的旅游者角色、探親者角色和訪友者角色必然存在一定的交叉過渡地帶。為此,根據(jù)Bellman和Zadeh的論斷——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模糊現(xiàn)象也是可以被界定的,最基本的原則是將模糊現(xiàn)象界定在限定條件和目標(biāo)范圍之內(nèi)。要明晰探親者、訪友者與旅游者是如何邊緣交叉的,需要再次回到概念產(chǎn)生的起點(diǎn),即分析VFR旅游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VFR旅游者與目的地的某個人或某些人之間存在明確或隱含的社會關(guān)系,該社會關(guān)系在一定程度上誘發(fā)或促使VFR旅游產(chǎn)生。由此,筆者認(rèn)為可以這樣來定義VFR旅游,即“探親訪友者與旅游者的身份界定僅為一線之隔,當(dāng)某個人的親友關(guān)系節(jié)點(diǎn)與旅游目的地相重合,且離開自己的常住地而到達(dá)旅游目的地,有明確的旅游行為,并與目的地親友產(chǎn)生一定的互動,即為VFR旅游者”。簡化的VFR旅游者角色概念空間如圖1所示。

圖1 簡化的VFR旅游者角色概念空間Fig.1 Simplified conceptual space of VFR tourist role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繼續(xù)分析VFR旅游者的類型劃分。該方面論述較為典型的有:Seaton和Tagg將VFR旅游者分為3類,即拜訪朋友的旅游者、拜訪親戚的旅游者、拜訪親戚和朋友的旅游者,并認(rèn)為拜訪朋友的VFR旅游者停留時間較短,而拜訪親戚的VFR旅游者停留時間相對較長。Morrison等認(rèn)為至少可以從4個角度來審視VFR旅游,即旅行目的、旅游動機(jī)、旅游活動和住宿形式。Moscardo等人將旅游地域、停留時間、住宿形式作為VFR旅游者類型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Backer將VFR旅游者劃分為3類,即PVFRs(旅行目的是VFR,并且住在親朋好友家)、EVFRs(旅行目的是VFR,但住在商業(yè)住宿設(shè)施)和CVFRs(旅行目的不是VFR,但住在親朋好友家)。Backer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并完善了統(tǒng)計(jì)漏洞問題,技術(shù)操作層面更加全面,但如上文分析所言,過分強(qiáng)調(diào)統(tǒng)計(jì)功能的分類,必然會忽略現(xiàn)象背后的深刻關(guān)聯(lián),即忽略了VFR旅游形成的核心——目的地親友社會關(guān)系的節(jié)點(diǎn)。為此,本文將引入社會關(guān)系理論對其加以重新審視。
回顧以往的社會關(guān)系理論,雖然龐雜,但其中最典型且最為學(xué)者們認(rèn)可的是黃光國于1987年總結(jié)提出的人際關(guān)系類型(情感性關(guān)系、混合性關(guān)系、工具性關(guān)系)。其中,情感性關(guān)系通常是指個人和家人之間的關(guān)系,混合性關(guān)系是個人和親戚、朋友等熟人之間的關(guān)系,工具性關(guān)系則是個人為了獲取某種資源和陌生人所建立的關(guān)系。該關(guān)系類型不僅適用于華人社會,同樣適用于其他社會類型。VFR旅游與其他旅游的區(qū)別在于,其不是簡單的“人—地”(旅游者與目的地)互動關(guān)系,更確切地講,是“地”承載之上的“人—人”(VFR旅游者與接待其旅游來訪的東道主)互動。以此為邏輯起點(diǎn),在華人行為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首先是判斷他人與自我之間的關(guān)系類型。因此,用黃光國社會關(guān)系理論可以將VFR旅游類型明確地劃分為3類,即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的VFR旅游、混合性關(guān)系情境的VFR旅游和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的VFR旅游,下文將對其進(jìn)行詳細(xì)論述。
2.VFR旅游中的東道主
在目的地接待過程中,VFR旅游的“東道主”(Host)扮演著重要角色,其重要性首先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貢獻(xiàn)上,同時東道主(Host Friends and Relatives,接待探親訪友)也是VFR旅游者“觸手可及”的旅游信息來源,也是旅游目的地?fù)矶率鑼?dǎo)和消費(fèi)滲透的導(dǎo)引者。因此,一些旅游目的地企業(yè)和營銷組織認(rèn)為,應(yīng)積極保持與當(dāng)?shù)鼐用竦挠行贤ㄅc聯(lián)系,使當(dāng)?shù)鼐用窀邮煜け镜芈糜萎a(chǎn)品,并鼓勵當(dāng)?shù)鼐用裱埶麄兊挠H朋好友來當(dāng)?shù)芈糜巍;诨拥谋匾裕琕FR旅游必然會給東道主帶來一定的負(fù)擔(dān),如Shani 和Uriely就曾以以色列埃拉特市居民為例,說明VFR旅游分別從空間、經(jīng)濟(jì)、生理和社會心理四個方面給東道主帶來的負(fù)面影響,這些影響主要有隱私被泄露、高額的額外支出、勞累的體力勞動、輾轉(zhuǎn)于工作和接待之間帶來的精神壓力及感到自己在被來訪親友壓榨時的不快。然而,東道主也會在該過程中獲得一定的樂趣,如可以享受與自己認(rèn)為重要的人在一起的快樂、為自己熱情接待而感到自豪、為自己生活的地方受到關(guān)注而自豪、與客人一起外出旅游的樂趣、當(dāng)他們回訪客人時也可以得到同樣熱情的接待等。
為了說明東道主在VFR旅游中的角色,也為了揭示東道主角色對目的地旅游企業(yè)和旅游營銷組織的重要意義,Young等人提出了兩個維度的東道主分類模型:一個維度說明東道主對旅游者吸引力的大或小;另一維度說明東道主對當(dāng)?shù)芈糜萎a(chǎn)品的口碑營銷力度的大或小,由此而產(chǎn)生的東道主類型分別被命名為“大使”“空談?wù)摺薄爸辛⒄摺焙汀按盆F”。Shani和Uriely依據(jù)“利他/利己傾向”和“接待區(qū)域”兩個維度,把東道主分成了4種類型:①專注于在家里熱情招待來訪客人;②繼續(xù)保持平日里的生活習(xí)慣;③做客人的導(dǎo)游;④成為自家門口的旅游者。以上研究成果過于注重應(yīng)用層面的VFR旅游影響與結(jié)果,重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了旅游目的地,強(qiáng)調(diào)了東道主對VFR旅游的經(jīng)濟(jì)貢獻(xiàn),忽略了VFR旅游關(guān)系聯(lián)結(jié)的另一方旅游者,而這恰恰是解釋VFR旅游主體互動機(jī)制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
為了更加清晰地說明東道主與旅游者關(guān)系情境下的互動機(jī)制,有必要從社會關(guān)系視角對VFR旅游中的東道主的概念也進(jìn)行再次界定。本文認(rèn)為,VFR旅游的東道主是為了響應(yīng)VFR旅游者的請托,在特定關(guān)系情境下與VFR旅游者產(chǎn)生一定互動的目的地資源支配者,其支配給VFR旅游者的資源包括時間、旅游信息、住處和禮物等。
二、華人社會中VFR旅游者與東道主的社會互動
關(guān)系主義方法論認(rèn)為,關(guān)于個人的任何事實(shí)都必須放在情境脈絡(luò)中加以理解。華人社會是關(guān)系社會,在華人社會里最重要的情境脈絡(luò)就是不同的社會關(guān)系,個人能夠隨著社會關(guān)系脈絡(luò)的轉(zhuǎn)變而做出適合于該關(guān)系脈絡(luò)的行為。在前文中,我們從社會關(guān)系視角對VFR旅游做了類型劃分,分別是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的VFR旅游、混合性關(guān)系情境的VFR旅游和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的VFR旅游。基于該分類,筆者認(rèn)為在華人文化背景下,分析不同情境關(guān)系類型中的VFR旅游者與東道主社會互動的過程更具意義。
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是社會學(xué)研究領(lǐng)域進(jìn)行社會分析的基本單位,是微觀社會學(xué)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社會互動一詞最早由德國社會學(xué)家齊美爾提出,他認(rèn)為社會學(xué)研究對象應(yīng)是與互動內(nèi)容相對應(yīng)的互動形式。我國學(xué)者鄭杭生則提出,社會互動是指社會上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通過信息的傳播而發(fā)生的相互依賴性的社會交往活動,即社會互動是個體間的社會交往。在中國,其社會運(yùn)行的深層支配力量是“人情”“面子”“關(guān)系”和“報”所構(gòu)成的一整套社會機(jī)制,該社會機(jī)制對中國人的社會行為產(chǎn)生著實(shí)際影響。由此,黃光國認(rèn)為中國人的社會行為中,社會交往的核心是“資源交換”,而“資源交換”的兩端是“資源分配者”與“資源請托者”,其論斷的理論參照來自笛卡爾式的“主客二元對立”理論。溯源推廣,該論斷不僅能適用于華人社會中的社會互動關(guān)系分析,同樣也適用于其他類型社會中的社會互動關(guān)系分析。
反觀中國社會的構(gòu)成與發(fā)展脈絡(luò),黃光國所提出的上述論斷,即社會互動關(guān)系中的資源請托者和資源支配者,更能反映中國文化的特質(zhì)。作為社會互動機(jī)制中的二元主體,VFR旅游者與東道主的社會互動必定會遵循上述運(yùn)行機(jī)制。同時,結(jié)合Bales對小群體社會互動階段的劃分(定向階段——情境辨識的問題、評價階段——態(tài)度確定的問題、控制階段——行動選擇的問題),筆者認(rèn)為VFR旅游者與東道主的社會互動過程也必然會存在上述特點(diǎn)(見圖2)。

圖2 VFR旅游者與東道主互動機(jī)制Fig.2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VFR tourists and the hosts
1.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社會互動
“情感性的關(guān)系通常是一種長久而穩(wěn)定的社會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可以滿足個人在關(guān)愛、溫情、安全感、歸屬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像家庭等主要社會團(tuán)體中的人際關(guān)系,都在情感關(guān)系之列。”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家庭是最主要的集體或團(tuán)體,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人而言,甚至也是唯一的集體或團(tuán)體。當(dāng)今世界,社會快速變遷,隨著科技日趨發(fā)達(dá)、知識與信息的急速增加、思想觀念的開放與道德價值觀的重組,家庭生活與組成形式也受到了巨大沖擊,特別是在中國文化不斷擴(kuò)大影響與延展的社會環(huán)境中,家庭呈現(xiàn)出一些新的特點(diǎn)。但是,由于中國傳統(tǒng)觀念與文化的影響,中國人的家庭觀念與西方人的家庭觀念依然存在著本質(zhì)的差異。“中國人特別珍視家庭的親情,喜歡不分你我,對父母百依百順,對子女無私奉獻(xiàn),家人之間沒有任何隱私。在西方,‘家’是高度私人的領(lǐng)地,更享有法律上的保護(hù),各人的臥室必須經(jīng)過敲門獲準(zhǔn)其他家人才可進(jìn)入。這種差異體現(xiàn)出西方人‘利己’、中國人‘利他’、西方人崇尚個體、中國人崇尚集體的思想。”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對朋友的分類是非常復(fù)雜的,有半面之交、一面之交、布衣之交、車笠之交、患難之交、酒肉之交、肺腑之交、膠漆之交、八拜之交、金玉之交、君子之交、一人之交等。在西方,朋友雖然也有親疏遠(yuǎn)近之別,但不像中國人區(qū)分得如此復(fù)雜,平等是朋友關(guān)系的主要原則。所謂肺腑之交、膠漆之交、八拜之交、一人之交等就屬于情感性關(guān)系的范疇。在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們雖然不再遵循古代對朋友的分類,但實(shí)質(zhì)上依然與之對應(yīng)。
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VFR旅游,多見于感情親密、關(guān)系要好的親人和朋友對東道主及其所在目的地的拜訪。此種關(guān)系情境下的VFR旅游者或東道主都可以在對方那里尋找并感受到溫情、安全感、歸屬感,滿足自己情感方面的需要。當(dāng)然,在情感性關(guān)系中,除存在情感成分外,還存在工具成分,只是情感成分要明顯多于工具成分。所謂工具成分,就是個體利用雙方關(guān)系來獲取其所需要的物質(zhì)資源,如VFR旅游者在目的地旅游期間借住在親友家里而不是住在酒店里,東道主在VFR旅游者來訪期間為招待好對方而需要付出很多平時不必要的花銷。
“報”的規(guī)范是一種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規(guī)范,也是任何文化公認(rèn)的基本道德律。中國文化中的需求法則、公平法則或人情法則都是“報之規(guī)范”的衍生物。這些法則的差異,在于它們適用的人際關(guān)系范疇不同,“報”的方式和期限也有所不同。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報之規(guī)范”便是“需求法則”。在中國式家庭中,依照需求法則進(jìn)行交往的情感性關(guān)系,也同樣遵循“報之規(guī)范”。如果雙方是屬于親密社會中的情感性關(guān)系(譬如家人之間),在過去長久的生活史中,他們對彼此的榮辱都有共同的經(jīng)驗(yàn),知道彼此的“里子”,在進(jìn)行社會互動時,便很少有“做面子”的必要。這種關(guān)系中的VFR旅游者在拜訪東道主時,東道主以“需求法則”對待來訪的旅游者,他們會盡最大努力滿足VFR旅游者在旅游過程(包括旅游前和旅游中)中的所有需要,沒有能力滿足的要求,東道主也沒有必要為了“面子”而“打腫臉充胖子”。
不管是對親人還是密友,東道主按照評價階段所確定的“需求法則”,在控制階段會“積極”地招待VFR旅游者。他們非常歡迎親友的到訪并樂意付出實(shí)際行動做好對親友來當(dāng)?shù)芈糜蔚慕哟ぷ鳌K^“有朋自遠(yuǎn)方來,不亦樂乎”,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東道主接待來訪的親友總是出于自身義務(wù)或完全的自愿。親友來訪前詢問當(dāng)?shù)氐穆糜涡畔r,他們會將其所知曉的旅游相關(guān)信息告知親友,甚至?xí)鲃訋椭鷣碓L的親友安排好旅游路線并盡可能收集旅游所需的各種信息,到訪期間也樂意帶親友到當(dāng)?shù)氐穆糜尉包c(diǎn)游玩并愿意為親友做當(dāng)?shù)氐摹皩?dǎo)游”。
2.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社會互動
與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相對應(yīng)的是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黃光國在解釋工具性關(guān)系時認(rèn)為,“個人在生活中與他人建立工具性關(guān)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得他所希冀的某些物質(zhì)目標(biāo)。由于工具性關(guān)系中的情感成分甚為微小,個人以公平法則和他人交往時,比較能依據(jù)客觀的標(biāo)準(zhǔn)做出對自己較為有利的決策”。中國社會長期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發(fā)展脈絡(luò)導(dǎo)致了以家族為中心的中國式集體主義,所謂集體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圈子”。我們常說,華人社會是關(guān)系社會、人情社會,其關(guān)系取向、講人情的對象僅限于“圈內(nèi)”,對于“圈外”的人,華人可以像其他文化中的人一樣遵循公平法則。如果他認(rèn)為某項(xiàng)交易關(guān)系的結(jié)果對自己不利,他可能提出條件和對方討價還價;對于對方不合理的要求,他可能嚴(yán)詞拒絕;如果對方不接受自己的條件,他還可能終止這項(xiàng)交易而不以為意。正如一項(xiàng)研究所顯示的,當(dāng)情境中當(dāng)事人雙方感情程度淺時,個體則更傾向于不做出“人情行為”。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VFR旅游中,可以把旅游者的旅游目的理解為“純粹的旅游”,即使在旅游過程中去拜訪了東道主,其目的也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此行的“旅游目標(biāo)”。在Backer提出的VFR定義模型中,模型中的EVFRs旅游者與東道主的關(guān)系就屬典型的工具性關(guān)系。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下,VFR旅游者在旅游的過程中拜訪東道主,其目的可能只是為了從東道主那里了解從別的渠道不容易獲得的旅游信息、求得一處免費(fèi)的住所或者是請東道主當(dāng)自己的免費(fèi)導(dǎo)游。面對VFR旅游者如此明顯的工具性目的,東道主的做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報之規(guī)范”的“公平法則”去面對來訪的旅游者。東道主以公平法則與VFR旅游者交往時,其間不摻雜太多的情感成分,能以較為客觀的標(biāo)準(zhǔn)與東道主交往,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策。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下,東道主對VFR旅游者的禮待,相對于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下是“消極”的。雖然對方的VFR旅游行為已經(jīng)發(fā)生,但是他們并不是真心地歡迎VFR旅游者的到訪,更不愿以打亂自己日常生活秩序或付出額外的花銷為成本去招待“不速之客”;如果對方來訪期間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他們可以選擇溫和地或嚴(yán)詞地拒絕,只因來訪客人是“圈外人”。
3.混合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社會互動
“在中國社會中,混合性關(guān)系是個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來影響他人的人際關(guān)系范疇。這類人際關(guān)系的特色是,交往雙方彼此認(rèn)識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關(guān)系,但其情感關(guān)系又不像主要社會團(tuán)體那樣深厚到可以隨意表現(xiàn)出真誠的行為”。一般而言,這類關(guān)系可能包含親戚、鄰居、師生、同學(xué)、同事、同鄉(xiāng)等不同的角色關(guān)系。
借用“工具性關(guān)系情景下的社會互動”部分提到的“圈子”,此處所說的圈子是以當(dāng)事者為中心的。圈子中的其他人都與當(dāng)事者有關(guān)系,并且其他人又各自有自己的圈子,這些圈子互相交叉就形成了華人復(fù)雜的、獨(dú)特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文化心理學(xué)主張“一種心靈、多種心態(tài)”,認(rèn)為人類由生理遺傳所決定的心理功能都是一樣的,但他們在其獨(dú)特文化影響下所培養(yǎng)出來的心靈內(nèi)涵卻是不同的。華人社會中的混合性關(guān)系就是華人人際關(guān)系區(qū)別于其他文化社會人際關(guān)系最顯著的特征。混合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VFR旅游者和東道主雙方就被包含在這張復(fù)雜的關(guān)系網(wǎng)中。
黃光國的“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式雖然采用了“社會交易論”的基本概念,其思路卻是“符號互動論”的。符號互動論的大師Mead認(rèn)為:社會互動的另一個先決條件是行動者必須能夠把自己當(dāng)作客體,來觀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他將“自我”分為“主我(I)”和“客我(Me)”:“主我”不僅能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和他人互動,而且能夠?qū)ⅰ白晕摇碑?dāng)作社會客體來加以界定,這就是所謂的“客我”。在互動過程中,“客我”就像其他客體一樣受到“主我”的界定并不斷地被重新界定。這種“扮演他人角色”和“從他人角度看自我”的能力正是行動者和他人順利進(jìn)行社會互動的先決條件。混合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互動雙方不像情感性關(guān)系中的當(dāng)事者有很深厚的情感,亦不能像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下那樣“鐵面無私”。面對來訪的VFR旅游者,東道主若能預(yù)見自己將來會與來訪客人有情感性的交往,或者很在乎圈內(nèi)其他人對自己接待行為的評判,那么面對VFR旅游者,東道主就必須做一個依照 “人情法則”辦事的“客我”。假如東道主堅(jiān)持公平原則,拒絕給予VFR旅游者特殊的幫助,后果可能是不僅影響二者的關(guān)系,還會影響到東道主在二者共處的關(guān)系網(wǎng)中的名譽(yù)和聲望。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尤其是來訪的VFR旅游者擁有較高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時,東道主不得不遵循“人情法則”給予VFR旅游者幫助。按照“報之規(guī)范”的“人情法則”,混合性關(guān)系情境下,東道主既不會像情感性關(guān)系那樣對VFR旅游者提供“無私”的幫助,又不能像工具性關(guān)系那樣不顧人情而得罪VFR旅游者。東道主考慮到VFR旅游者可能做的各種回報,考慮到自己的接待行為會為雙方都關(guān)系到的第三個人知曉,他們在VFR旅游者提出要求或自愿的情況下,不敢怠慢對VFR旅游者的接待,而是根據(jù)情況考慮到底如何接待才是“妥善”的。
結(jié)論
本文從社會關(guān)系視角對VFR旅游基礎(chǔ)理論進(jìn)行了初步探索,強(qiáng)調(diào)了VFR旅游者與其東道主在旅游目的地存在親朋關(guān)系節(jié)點(diǎn),這是VFR旅游與其他旅游類型有所區(qū)別的關(guān)鍵所在。本文嘗試重新界定了VFR旅游及VFR旅游東道主的概念。為了更貼切地回應(yīng)VFR旅游的本質(zhì),本文借助關(guān)系情境理論對VFR旅游進(jìn)行了類型劃分,認(rèn)為VFR旅游存在3種基本類型,即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VFR旅游、混合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VFR旅游和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下的VFR旅游。為了更深入說明該情境下的VFR旅游本質(zhì),本文選取華人社會為例,探索了VFR旅游主體互動機(jī)制,提出:在情感性關(guān)系情境中的VFR旅游,東道主依照“需求法則”,積極禮待VFR旅游者;在混合性關(guān)系情境中的VFR旅游,東道主依照“人情法則”,妥善禮待VFR旅游者;在工具性關(guān)系情境中的VFR旅游,東道主依照“公平法則”,消極禮待VFR旅游者。回顧以往的VFR旅游研究,雖都曾關(guān)注了VFR旅游者和東道主,但這些研究關(guān)注都是側(cè)重某一方,即所謂的單向一元關(guān)注,而另一方只是作為服務(wù)于研究目的的研究輔助。為此,有必要在未來的研究中將VFR旅游的兩個主體整合對待,以整體論的視角切入,以過程論的視角分析,以目的論的視角加以總結(jié),該研究思路或許對推進(jìn)VFR旅游向縱深化方向發(fā)展有一定的幫助。
[1]Seaton A V, Tagg S.Disaggrega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VFR tourism research:the Northern Ireland evidence 1991-1993[J].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 1995,6(1):6~18.[2]Seaton A V, Palmer C.Understanding VFR tourism behaviour: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urism survey[J].Tourism Management
,1997,18(6):345~355.[3]Morrison A, Woods B, Pearce P, et al.Marketing to the visi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 segment: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J].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 2000,6(2):102~118.[4]Pearece D.Domestic tourist travel patterns in New Zealand [J].GeoJournal
, 1993,29(3):225~232.[5]King B.What is ethnic tourism?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J].Tourism Management
,1994, 15(3):173~176.[6]TsaoFang Y, Fridgen J D, Hsieh S, et al.Visi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 travel market:the Dutch case[J].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 1995, 6(1): 19~26.[7]Bischoff E E, Koenig-Lewis N.VFR tourism :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s hos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 2007,9(6): 465~484.[8]Young C A, Corsun D L, Baloglu S.A taxonomy of hosts visi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 2007, 34(2): 497~516.[9]Shani A, Uriely N.VFR tourism : the host experienc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 2012, 39(1): 421~440.[10]McKercher B.An Examination of Host Involvement in VFR Travel
[C].CAUTHE 1995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Conference.[11]Boyne S, Carswell F, Hall D.Reconceptualising VFR Tourism
[M].Berlin:Springer Netherlands, 2002 : 241~256.[12]Kotler P,Bowen J T, et al.Marketing 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London:Pearson Education India, 2006.[13]Backer E.VFR travel: an examination of the expenditures of VFR travellers and their hosts[J].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 2007, 10(4): 366~377.[14]Jackson R T.VFR tourism : is it underestimated[J].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
,1990, 1(2):10~17.[15]Cohen E.Contemporary Tourism Diversity and Change
:Collected Articles
[M].Amsterdam : Elsevier BV, 2004.[16]Bellman R E, Zadeh L A.Decision-making in a fuzzy environment[J].ManagementScience
, 1970, 17(4): 141~164.[17]Moscardo G, Pearce P, Morrison A, et al.Developing a typology for understanding visi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 markets[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 2000, 38(3):251~259.[18]Backer E.The VFR trilogy[A].Refereed paper in J.Carlsen, M.Hughes, K.Holmes & R.Jones.Se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CAUTHE Conference
[C].2009.[19]邊燕杰.關(guān)系社會學(xué)及其學(xué)科地位[J].西安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0(3):1~6,48.
[20]Hwuang K G.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87(92): 944~974.[21]黃光國.也談“人情”與“關(guān)系”的構(gòu)念化[J].本土心理學(xué)研究(中國臺灣),1999 (12): 215~248.
[22]黃光國.儒家關(guān)系主義的理論建構(gòu)及其方法論基礎(chǔ)[J].教育與社會研究(中國臺灣), 2001(2): 1~34.
[23]Backer E.VFR Travel
:An Assessment of VFR versus non-VFR Travelers
[M].USA : VDM Verlag, 2010.[24]Jang S C, Yu L, Pearson T.Chinese travell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ison of business travel and visi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J].Tourism Geographies
, 2003,5(1):87~108.[25]McKercher B.Host involvement in VFR travel[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23(3): 701~703.[26]鄭杭生.社會學(xué)概論新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3.
[27]Bales R F.A set of categories for the analysis of small group interac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1950,15(2): 257~263.[28]楊國樞.中國人的心理[M].臺北: 桂冠圖書公司, 1989.
[29]白凱,符國群.“家”的觀念: 概念,視角與分析維度[J].思想戰(zhàn)線, 2013 (1):46~51.
[30]張俊麗, 李冬梅.中西方家庭觀念的對比[J].語文學(xué)刊 (高等教育版), 2008 (3):171~173.
[31]陳程.中西方“朋友”觀的比較研究[J].太原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1, 10(3): 29~32.
[32]Levi-Strauss C.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J].Sociological Theory
, 1965:371.[33]Lien-Sheng Y.The Concept of Pao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M].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34]Ho D Y F.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llectivism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case and Maoist dialectics [J].Cross-cultural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1979 : 143~150.[35]Adams J S.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1965(2):267~299.[36]李雅斯.影響中國人人情行為傾向三因素的實(shí)證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xué), 2008.
[37]Fried M H.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a Chinese County Seat
[M].Lodon: Atlantic Press, 1956.[38]Shweder R A, Mahapatra M, Miller J G.Culture and moral development [J].The Emergence of Morality in Young Children
, 1987 : 1~83.[39]Mead G H.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M].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40]黃光國.互動論與社會交易: 社會心理學(xué)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J].本土心理學(xué)研究 (中國臺灣), 1993(2):94.
- 文景的其它文章
- 現(xiàn)階段我國旅游業(yè)發(fā)展中的新問題與新任務(wù)(一)
- 國內(nèi)外飯店業(yè)員工工作滿意度測量方法與工具述評
——基于國內(nèi)外2000—2012年實(shí)證研究的分析 - 原真性與標(biāo)準(zhǔn)化悖論:飲食文化的消費(fèi)情境與生產(chǎn)者響應(yīng)
- 會獎旅游與創(chuàng)新營銷
- 我國旅游公共服務(wù)體系的構(gòu)建及優(yōu)化研究
——基于新加坡與中國香港經(jīng)驗(yàn)及上海案例分析 - 創(chuàng)建中國旅游業(yè)新常態(tài):從政策調(diào)整到實(shí)踐轉(zhuǎ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