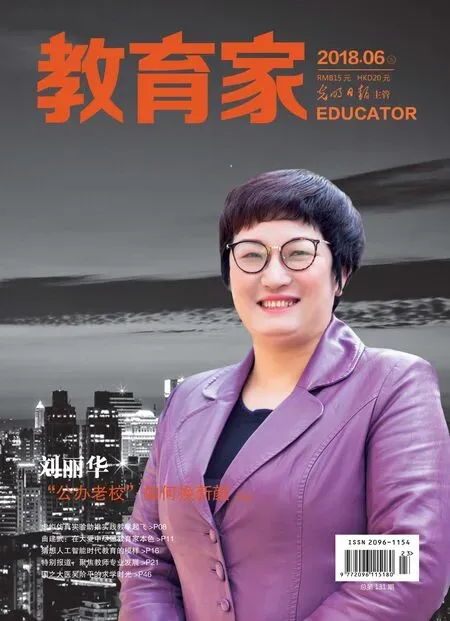高考那點事
恢復高考比改革開放早一年,說點高考的事,以此紀念改革開放這一偉大還在繼續的事業,也為我們的歷史坐標作一點形象記錄。
父與子
1977冬季,關閉11年的高考閘門打開了,累積11年的570萬無緣高考的學子懷著興奮、輕松與懷疑的心情如潮水般地涌進了考場。我清楚地記得那年高考預選考試,一個考場60人,左胳膊靠著別人的右胳膊,自己的考卷挨著別人的考卷,有時忍不住偷看別人,別人也幾乎大部分和我在相同位置留下空白,誰也抄不了誰。大家嘻嘻哈哈地考完了,又嘻嘻哈哈地回家種地或進工廠了,誰也沒有當真。但那一年,真真實實地有27.8萬人激動無比歡欣鼓舞地走進了大學。然后,所有人都認真了——這是真的!
我大學時的78級化學系的一位學兄和他的兒子一起考上大學且是同校。此事轟動不小,整個江蘇省鹽城專區人人皆知。父親上大學前是一位民辦教師,兒子17歲是應屆畢業生,數學系學生。父子雖在同一所學校,但不住一個宿舍,也不一同去食堂吃飯。只是星期天兒子會把衣服拿給父親洗,有時父子一起洗。兒子的媽媽和一個妹妹在農村老家,父子讀書家庭經濟有點緊張。那時,師范生國家補助伙食費每人每月16元,糧票27斤,助學金4元,看病不花錢,父親在學校勤工儉學,父子倆還能省點錢貼家用。生活雖不寬裕,但上大學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更不用說父子同上大學了。那時大家都懷揣夢想,心里都美滋滋的。
同學與老師
我1979年在公社的一個“戴帽高中”(那時生源多,初中辦成高中,小學辦成初中,教師還是原來的,所以加“戴帽”兩個字,意為實際辦學水平沒有那么高)學習過兩個月,老師幾乎都是沒有上過大學的,用自編的油印的講義幫我們復習,也不一定對路,全靠我們自己悟。班上有一個女同學和我一起參加高考。我考上了,她沒有考上,仍舊復習。畢業后我在一所高中教語文,她父親是學校后勤工人(后從公社中學調進來的),她也一直在這所學校繼續復習,我們也常遇到,交流不多。我1989年任教高三文科班語文兼班主任,她在我的班聽課,改稱我老師,雙方都有點尷尬。如果從1977年算起,她應該考了13年,這一年她終于考上了。我驚嘆于她無比堅強的毅力與勇氣,居然執著了13年。一個水花白凈的姑娘考成了疲憊憔悴的模樣,但上大學后幾年面貌又變得有紅似白的了。
四年級與大學生
我大學同班的一位和我同歲的孫同學,他是以小學四年級的學歷考進大學的。他家庭成分不好,是富農。一般來說,富農子弟就沒有機會讀初中了。見升學無望,孫同學四年級就輟學了。夏秋,背著草簍,拿著鐮刀,在古黃河邊為生產隊割草喂牛,掙工分。古黃河水是清的,他前途是混沌的,或者說像古黃河水一樣清亮:與承載著苦難歷史與燦爛文化的古黃河作伴,娶妻生子。恢復高考時,同村同齡人有的參加高考了,孫同學不敢想,但又想,偷偷地看了看同村人的復習試卷,感覺文科的也不太難,又偷偷地問招生辦。人家說:“你也可以考,現在不問年齡學歷!”孫同學大振,悄悄地找來幾本中學課本,白天上工,晚上啃書本。1979年,孫同學以數學、外語0分,總分309的成績考上大學。這得益于他平時自學,讀讀家里面一些殘書雜書,不懂,就翻《新華字典》,他甚至能背《新華字典》,我就和他賭過,他居然背上了。他現在已經是當地頗有名氣的書法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