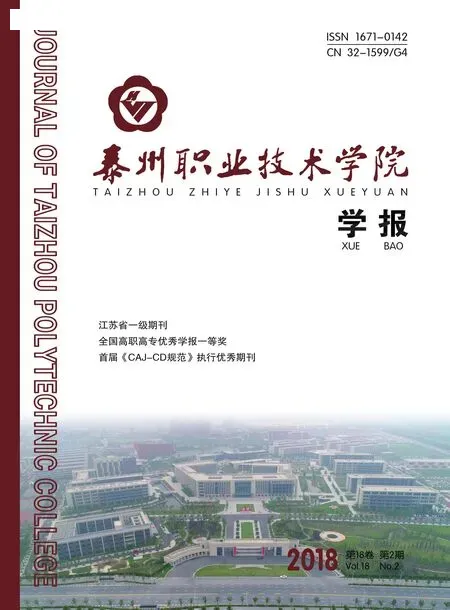論北京方言的形成、特點及保護
曹 然
(中國傳媒大學 傳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許多在北京生活過的外地人都有這樣一個認識:北京話和普通話是不同的。普通話說得再好的人,都很可能聽不懂北京話,甚至連學習播音的人到了北京都聽不懂北京話。這個“不可思議”的發現,讓筆者開始注意普通話和北京話之間的差別。《辭海》中對“普通話”的釋義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那么,普通話是北京話嗎?普通話和北京話是什么關系呢?本研究通過比較北京話、普通話的內涵,發現兩者之間的聯系和區別,進而在“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引導下,理解保護北京話的重要意義。
1 北京話的定義及北京話的歷時演變
1.1 什么是北京話
按主流學術觀點,北京話是一種主要分布在北京城區及郊區的漢語方言,屬于七大方言之一——北方方言的次方言,也有人稱它是北方方言的一個點。它主要分布于北京市、河北省承德市、廊坊市、涿州市,內蒙古赤峰市等地區,使用人口1500多萬,三聲四調,古入聲派入平、上、去且相對均勻[1,2]。
1.2 北京話的歷時演變
北京話的發展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大概從唐代末年起,由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936),幽州地區(今北京等地)從此脫離中原漢族的統治,成為遼金兩代少數民族政權的南方重鎮。后北京成為遼代的五京之一。公元1153年,金代把國都遷到燕京(今北京),在北京的漢族人被迫或自愿和北方少數民族雜居在一起,時間長達300年之久,北京成了各族人民交流的重鎮,北京方言體系初步成形。這一時期,由于漢族人文化高,以所掌握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影響當地少數民族,漢語在東北各族語言中也就逐漸占了優勢[3]。
元代滅遼金后,北京仍然掌握在少數民族手中。因而其語音逐漸喪失了中原語音的一些特色。加上元代把都城從元上都遷至北京,時稱“大都”,北京話中又摻雜進了蒙古族的一些語音,形成了“大都話”。比如“驛站”(古時傳遞軍政文書的人中途換馬、食宿或轉遞之所)的“站”,就源自蒙古語,如元代稱“驛站”為“站赤”。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話再次發展,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較多,故北京民間方言以河北口音為主;這一時期,受移入人口的影響,江淮方言也對北京當地的方言產生了影響。特別是朱棣篡位遷都北京后,頒布了《洪武正韻》代替蒙元所編訂的《蒙古字韻》,接續了漢唐以來中原音韻。滿族入主中原后,滿語對北京話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咋呼”(zhà hu)一詞源于滿語/cahu/,意為“潑婦”,現在意為不沉穩,喜歡大呼小叫。“磨蹭”(mò ceng)源于滿語/moco/,原意為“遲鈍”,今意為“做事不麻利,動作遲緩”;“掰持”(bai chi),源于滿語/baicam?bi/,本意為查看、詳查,原意為“爭論”[4]。
因此,如今的北京話,是近千年以來逐漸形成的以漢語為主、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主要是阿爾泰語系的語言)為輔的語音系統。一般認為,真正的北京話僅有400多年的歷史[3]。著名學者胡明揚先生也在其著作中梳理了北京話發展歷程:明末的吳語—清朝入關后的滿語—滿式漢語—內城北京話—官話—國語—內城北京話消失[5]。
2 北京話的特點
北京話尖團音不分,兒化音多,還有一些獨有詞匯。普通話雖然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但是北京語音和北京話不是一回事。
“酒糟鼻子赤紅臉兒,光著膀子大褲衩兒。腳下一雙趿拉板兒,茉莉花茶來一碗兒。燈下殘局還有緩兒,動動腦筋不偷懶兒。黑白對弈真出彩兒,贏了半盒兒小煙卷兒。你問神仙都住哪兒,胡同兒里邊兒四合院兒。雖然只剩鋪蓋卷兒,不愿費心鉆錢眼兒。南腔北調幾個膽兒,幾個老外幾個色兒。北京方言北京范兒,不卷舌頭不露臉兒。”[3]這是一個北京市民編的順口溜兒,從中不難看出北京話的特點。
在北京,尤其是南城有著濃濃胡同味兒的京腔、京片兒。因此,有的北京人戲稱自己說的是“胡同話兒”話、“痞”話。它的“吞音”、“兒化音”特點讓人印象深刻。2016年8月中旬,一張題為《學說北京話》的圖片在社交媒體上流傳開來,這張圖片列舉了8個北京話發音的詞語,包括“胸是炒雞蛋”(西紅柿炒雞蛋)、“王五井兒”(王府井)、“西日門”(西直門)、“公乳墳兒”(公主墳)、“石影山兒”(石景山)、“馬丫鋪”(馬家堡)、“燈兒口兒”(燈市口)和“裝墊兒臺”(中央電視臺)。在轉發、分享的過程中,很多網友似乎是突然意識到“原來北京話這么有意思”;對于從小在胡同兒里長大的人來說,這些老北京的文化元素更是勾起了他們的“鄉愁”和“童年記憶”。
那么“吞音”“兒化音”就是北京話嗎?一些人會給出肯定的回答,但也有一些人斥之為“市井文化”,認為它并不值得被效仿、推廣,并不能代表北京“寬容、開放的城市精神”。這些意見各有道理,但并不是在同一層面上的探討,間接造成了人們認知上的混亂。為獲得全面的認識,須以歷史的眼光加以認識,不妨先參考一下學者們的研究。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語言、方言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必然是在社會歷史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從原始語言一步步進化成長而來,并將始終保持變化發展的動態過程,北京話自然也不能例外。
3 “京音”在普通話中地位的奠定及其方言屬性的逐漸流失
3.1 民國初年的“京國之爭”及“京音”的勝出
民國初年,全國缺乏統一的語言標準,給百姓的溝通帶來了巨大麻煩。國會召開,南腔北調,如雞同鴨講,鬧了不少笑話。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總長的教育部成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由吳敬恒(稚暉)任主任,并制定讀音統一會章程八條。規定讀音統一會的職責是為審定每一個字的標準讀音,稱為“國音”(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此舉招致來自北方直隸省的著名語言學家王照(主張以純“京音”為主)的激烈反對。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長董鴻煒的推動下,通過了由許壽裳、周樹人(魯迅)提議的“注音符號”方案,語音以純北京語音為標準[6]。民國確定新國音以后,北京官話正式成為中國官方的標準語。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這就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層次上構建了新中國普通話的標準概念,并一直沿用至今。需要注意的是,在普通話標準的實際制定過程中,主要選取了河北省灤平縣作為語音采集地,對北京官話進行修正。灤平話以其直接、清晰、明確,尤其是沒有兒化、省字、尾音等發音習慣,更易于學習推廣。
3.2 北京話方言屬性的逐漸喪失
正如其他漢語方言一樣,北京話既受到普通話的推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受到其他外來方言的“入侵”,其自身相對穩定的狀態被迅速打破,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北京話中有著豐富的方言詞,但這些方言詞并非標準普通話中的慣用詞匯。比如“打這兒”(從這里起)、“放話”(公布消息)、“末了兒”(最后);又比如“白齋”(白吃白喝)、“跌份”(丟面子)、“解這兒”(從現在開始)和“棒槌”(門外漢)。隨著北京市外來人口的增加,包括東北話在內的外來詞(如趙本山的“忽悠”等)以其更加生動的表現力,顯示出越發強勁的“侵略性”,大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以至于有網友調侃說,真正的北京方言詞就只剩下“牛逼”和“二逼”了。
其次,前文提到北京話中存在的吞音現象,或稱語流音變現象(音節聚變),也是和普通話的區別之一,但有時被社會上層貶斥為“市井氣”和“侉氣”。例如:“不知道” /pu5155 tao51/0-2/在北京話中變為“不兒道”/pu?55 tao51/,“車公莊站”變為“撐莊站”,“西紅柿炒雞蛋”為“胸是炒雞蛋”。一些韻母的實際發音(尤其是在快速的語流中)與普通話有差別。鑒于這些詞匯大都涉及地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公交車售票員報站時散漫、隨意的腔調,并給予比較負面的評價。但也有學者認為,“吞音”的形成從根本上受到語言“經濟性”原則的制約,因此不能一概而論。
還有,北京話的語速比普通話更快,說北京話時比說普通話時的音域更高,北京話中還存在一些不被普通話承認的字音異讀。這些特點使得不少外地人往往在初來乍到時聽不清楚或者是聽不明白。
然而正是這些讓人“聽不清楚”“聽不明白”的內容,成為北京話區別于普通話的特殊性所在,成為承載著北京特色文化生活的依憑所在。不妨大膽設想,在普通話成為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的標準用語的同時,北京話在一定程度上也勢必擺脫普通話基準音來源的身份,解除附著其上的意識形態的屬性。它作為一門方言其既特殊的又貌似尋常的特質,將被日益凸顯出來。
4 如何保護北京話
盡管北京話自有其特殊性、重要性,但就目前來看,北京話正面臨著生存危機。2016年5月31日,教育部發布了我國第一部地方和城市版語言狀況調查報告——《北京市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報告顯示,北京市中學生對北京話認知程度日漸式微,而這事實上只是北京話整體受損現狀的冰山一角。其實不僅是中學生,如今大部分年輕人對北京話的認知都十分有限,日常生活中也多以普通話、而非北京話交流。教師谷斌不無憂慮地說:如今北京學生說的話,僅僅是普通話中帶點北京味兒,一兩百個學生中才有幾個學生能說地道的北京話。“老北京”賈大媽也說,小輩們說話,“您”字都沒有了[7]。2011年,筆者作了一個初步的調查,某中學一個班級中學生認為自己“會說”北京話的達34%,“不太會說”的達44%,“不會說”的為22%;而到了2017年,同一年級的學生中,認為自己“會說”北京話的下降到26%,“不太會說”的上升到38%,“不會說”的上升到36%。這一數據與媒體、學者的觀點基本一致。
除了普通話的推廣和外來方言的滲透之外,有學者認為,“人口流動”和“環境變化”是北京話面臨危機的重要原因:“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人口流動的頻繁,對北京話起到了很強的稀釋作用。隨著北京城墻的倒塌,胡同、大雜院的拆遷,城區中心地帶的老北京人被分散到了城內外各個地方。環境的變化對北京話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北京話正在失去長期存在的土壤,很多特征逐漸淹沒在大北京、新北京之中。”[7]
為了挽救日漸式微的北京話,相關部門已經采取行動。自2012年起,北京市語委啟動了北京話有聲資源數據庫建設項目。同年,北京市還舉辦了“尋找最地道老北京發音人”的海選活動,通過紙筆記錄、錄音、攝像等方式,全面調查采集并整理老北京話原始數據。此外,開設校本課程、開展有方言特色的校園文化活動也列入保護計劃之中。這方面國內有不少值得借鑒的成功案例。如江、浙、滬一帶的部分小學甚至幼兒園早就開設了方言課程,編寫了相關教材,以便于學生學習本地方言。又如:《十三五巴適得板》(四川話)、《喝餛飩》《擠公交》(南京話)等糅合了大量方言特色的說唱歌曲,在經過網絡傳播之后,受到當地年輕人的歡迎和追捧,不失為在新時期保護和傳承方言特色的有效途徑。
作為一種方言的北京話,一旦消失就難以再恢復了。所以,保護包括北京話在內的方言,對于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來說,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每一個有良知的語言文化學者,都應該行動起來,投入到這場方言的搶救性保護中去。即使作為一個普通的會講北京話的市民,也可以用手機將老一輩在日常生活中的“絮絮叨叨”錄下音來。那些八九十歲大鼓藝人的唱詞、評書,如果記錄下來,將會是明天的“二泉映月”般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庫中的語料。
[1] 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王飄笛,李海燕.功能對等理論下北京方言的翻譯——以電影《老炮兒》為例[J].林區教學,2016(4):39-41.
[3] 張卉妍.老北京的趣聞傳說[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
[4] 愛新覺羅·瀛生.北京土話中的滿語[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5] 胡明揚.北京話初探[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6] 張遠東,熊澤文.廖平先生年譜長編[M].上海:上海書店,2016.
[7] 謝丹.地道北京話日漸式微方言保護勢在必行——留住皇城根下的京腔京韻[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6-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