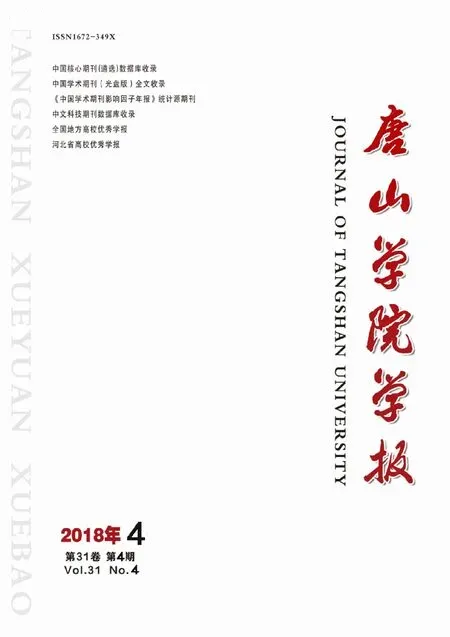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律儒家化
褚天舒
(華北理工大學 文法學院,河北 唐山 063210)
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戰(zhàn)亂頻發(fā),尤其是晉朝初期,司馬家族以“堯舜禪讓”的名義奪取曹魏政權。但有奪天下之能、卻無治天下之才的司馬家族,無心平定外族侵擾,卻對內大肆鏟除異己,打著“名教”旗幟殺掉了孔融和嵇康等諸多名士。這讓士大夫們逐漸痛恨起當世虛偽的禮教,寧愿放浪形骸不問政事,也不愿為其效忠。他們從對儒家經學的崇尚轉為對道家玄學的熱愛。由此,玄學開始興盛,儒學逐漸式微。
一、魏晉名士對儒學的抗拒
魏晉名士最大的特點是愛清談、好玄學,追求自然與真我,無視儒家禮教,并且抗拒用儒學中的治世之道來效忠當時的朝堂。在《晉書》《世說新語》等書中有諸多這樣的記載,下面將以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為例說明他們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來反抗當時社會與儒家思想的。
(一)無視禮教
中國古代受傳統(tǒng)儒家禮教影響,男女七歲以后不得同席,男女大防嚴格。但在《世說新語·任誕》中有這樣的記載:一次阮籍的嫂子準備回娘家,阮籍在大門口送別嫂子,被旁人看到,旁人嘲諷他不顧禮數。阮籍回答說:“禮教難道是為我們這些人設定的么?”
古時禮法要求父母去世后,兒子要守喪三年,不得同房、不得食葷,但就在阮籍的母親出殯當天,他先吃了一只肥豬肘,喝了兩壇子酒,然后到母親身邊做遺體告別。在靈堂前他大喊一聲“完了”,然后悲傷過度口吐鮮血,失魂落魄。
(二)不尊君王、無心仕途
儒家禮教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上下級的關系上也是有明確的嚴格要求的。《世說新語·簡傲》中記載:晉文王司馬昭功德盛大,坐在位子上嚴肅莊重,氣勢可以與皇帝相比,但是阮籍卻在自己的席位上盤腿而坐,或吟詩、或長嘯、或唱歌,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在封建社會中君主擁有絕對權威,阮籍面對君王而不守禮教尊卑,不在乎上級領導對自己的評價。
魏晉時期政治黑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司馬氏欣賞才名遠播的阮籍,要求其入仕,阮籍為求自保踏入仕途,但是極力避開政治中心。他不認真上班,不重視自己的前途,雖積極工作也是為了能夠喝上工作單位食堂所釀的美酒。
名士都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他們是魏晉時期的精英,是上層統(tǒng)治階級中最先進文化的代表,但是他們特立獨行、無拘無束、抗拒儒學、避談政治。然而在這名士們處于叛逆期的魏晉南北朝,儒家思想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它仍然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最具代表性的就屬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了。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儒家化的表現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禮,法律儒家化主要表現就是在立法方面和司法方面以儒家思想為價值取向和衡量標準。依據道德倫理標準判定犯罪是否成立、依據等級制度定罪量刑等都是儒家思想在當時法律中的體現。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律具有歷史性的進步,并為隋唐法律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一)“八議”入律
“八議”源自于周朝的“八辟”,辟是法的意思,即八種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犯罪采取與普通人不同的處罰措施。凡“八議”者犯罪,只要不是危害皇權和封建統(tǒng)治秩序、不孝尊長等重罪的,可用議、請、減、贖、當的方式減免刑罰。雖然周朝就有“八辟”之說,但是正式入律是在曹魏時期。秦朝時期主張刑無等級的法家思想,廢除了“八辟”制度。漢朝時期儒家學說成為指導思想,但是只有上請制度,即對觸犯法律的特權階級如何判罰,需要上請皇帝定奪。直至曹魏時期《曹魏律》正式將“八議”入律,并應用十分普遍。北魏時期“八議”制度范圍更為寬泛,擴大到了“八議”之人的子孫。到北齊時“八議”制度進一步完善并成為了歷代朝廷的重要法律制度。直至清代末年沈家本主持修律,“八議”制度才退出歷史的舞臺。
“八議”入律使統(tǒng)治階級特權合法化,即官僚地主在違反一般法時,受到了特別法的保護。《隋書·刑法志》記載:東晉成帝時期,廬陵太守羊聃,有一次錯判枉殺了將近兩百人,但是因為太守羊聃屬于可以議親之人最后免于死刑。南朝梁武帝時期,皇室子弟目無法紀,光天化日之下在集市上殺人,之后藏匿于王府之中無人敢逮。“八議”制度是儒家主張同罪異罰、等級嚴苛的制度體現。“八議”制度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可謂“縱封豕于境內,放長蛇于左右” 。
(二)準五服以治罪
“準五服以治罪”是法律思維儒家化的一個重要體現。“五服”制是“中國古代以五種喪服確定親屬關系親疏遠近的制度”[1],即在為親人服喪時依據血緣的親疏遠近來穿不同等級的喪服。五服由親至疏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關系最親近的為斬衰,要求穿著沒有任何修飾的生麻布制成的喪服守喪三年,之后按照血緣等級依次減輕守喪和服制的規(guī)格。“準五服以治罪”就是將血緣的親疏遠近用服飾來表現,并且作為決定罪行的等級標準。在嚴格區(qū)分尊卑、上下、貴賤、親疏的等級秩序中,親屬之間有加害行為的,定罪量刑標準是:以下犯上者服制越遠的處罰越輕;以上犯下者則是服制越遠處罰越重。例如當時法律規(guī)定:祖父母、父母等用兇器殺害兒子或孫子的,處以五年刑期;毆打致死的處以四年刑期,如果是懷恨在心故意殺人的,則罪加一等。但是如果子女殺害、傷害或者毆打父母的則要被判處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公公婆婆的也要棄市。
《晉律》規(guī)定的“準五服以治罪”是引禮入律的重要標志之一,是法律制度儒家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它將禮制規(guī)格刑法化,用血緣上的親疏遠近判斷社會危害性與社會不良影響,用法律來維護禮教,用禮教來輔助法律。
(三)重罪十條
儒家主張“尊尊君為首、親親父為首”,《北齊律》以此為根據制定了十條罪名用以維護君主制和家長制。這十條罪名是: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這些罪名屬于最嚴重的犯罪,不在“八議”“上請”“官當”的范圍內,不得從輕處罰。這些罪名從犯罪客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危害中央集權和損害封建君主專政的犯罪,如反逆、大逆、叛降、不敬等;另一種是違反封建禮教和破壞倫理綱常的犯罪,如惡逆、不孝、不義、內亂等。
在封建制度與家庭倫理的雙重約束下,從朝堂到家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尊卑明確、等級森嚴的制度。《北齊律》總結了各個朝代的立法經驗,制定了重罪十條,并將其置于律首,隋唐以后更是以此為基礎繼續(xù)發(fā)展,對我國法制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魏晉南北朝法律儒家化并沒有停住發(fā)展的腳步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之一,百姓食不果腹、顛沛流離。當權者無視百姓疾苦,打著儒家禮教的旗號鏟除異己,讓儒家思想在當時看起來十分的虛偽,這給予了玄學發(fā)展的機會。許多的有識之士放棄了自己一生的理想抱負,扔掉了在自己生命中根深蒂固的治世經學,轉而開始熱愛清談、玄學,至此儒家思想在表面看起來逐漸喪失了主導地位。在魏晉時期,玄學之風盛行,尤其是在才子名士的聚會中不善清談、不會玄學是被人看不起的。在西晉時期玄學與儒學的對抗中,玄學一直處于上峰,儒家學說處于劣勢。東晉時期,佛教開始興起,愿修來世、忍耐今生的佛教理念被當權者用來作為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思想武器,在這一時期佛教處于主導地位,儒家思想仍舊敗下陣來。但是儒家思想在這個名人志士都不得推崇的時代,在政治、法律上始終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開端和發(fā)展,對我國法制史有深遠的影響。究竟為什么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封建法律會有如此輝煌的發(fā)展成果?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儒家思想根深蒂固
儒家思想與周禮一脈相承,從西周開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便深入人心,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宗族制度也對后世影響深遠。西漢開始從黃老思想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家思想成為統(tǒng)治者設定的意識形態(tài),一直延續(xù)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如果五代人能夠培養(yǎng)出一個紳士,那么幾十代甚至上百代的時間足以讓儒家思想深入到人們的骨子里。
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名士消極抵抗、不愿效忠朝堂的理由歸根到底是皇權的正統(tǒng)性,即政權的合法性。魏朝時期追求漢朝的正統(tǒng)、晉朝時期追求魏朝的正統(tǒng)、南北朝時期又在拼命維護晉朝的正統(tǒng)。實際上,名士反抗的只是儒學禮教的外在形式,其實他們從根本上也一直是儒家思想的捍衛(wèi)者。
當權者積極設立太學、發(fā)展經學的熱情與腳步也始終沒有中斷。佛教只是統(tǒng)治者麻痹百姓的手段,真正能夠建立國家政權、維護政權穩(wěn)定、維持統(tǒng)治秩序的還是需要依靠儒家,所以無論是玄學、道教還是佛教都沒能撼動儒家的根本地位。因此以儒學理論為基礎的封建正統(tǒng)法律思想在立法與司法實踐中,仍產生著主要的影響與作用。
(二)儒學大家的推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有許多精英人士避談政治,但是朝堂之上仍有許多當時大儒參與朝政。魏武帝曹操是一位有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曹操尚法,但是不同于先秦的嚴刑峻法,他認為應當引禮入刑,堅持儒家傳統(tǒng)的禮法并用。由于曹操對立法活動的重視,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由陳群、劉劭等人參照漢法制定魏律,并且明確要求只用鄭玄的儒家觀點注釋,此法稱為《新律》,共十八篇。《三國志》記載,陳群在朝堂上發(fā)言時多引用經文,是當時儒家學說的忠誠擁護者;劉劭曾經接受皇帝布置的任務,匯集、整理五類群書,最終編纂成為《皇覽》,并制定當時的禮樂制度,著有《樂論》十四篇。
《晉律》是司馬炎令賈充、杜預、裴楷、鄭沖、荀覬、羊祜等人制定,杜預、張斐以禮的原則和精神加以注釋而成。他們“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2]“博涉群書,特精義理”[3],都是當時的大儒。他們以儒家思想為根基,修剪出一部部儒家化法律巨著。
(三)經濟的發(fā)展與少數民族統(tǒng)治者的學習與借鑒
西晉時期,統(tǒng)治者下令廢除曹魏的屯田制,實行占田制和課田制,對軍隊進行整編,讓士兵解甲歸田,大力發(fā)展農業(yè),促進了當時生產的發(fā)展。這使得當時經濟復蘇,在一些大的城市出現了繁榮景象。統(tǒng)治階級將這些歸功于儒家學說的引導與貢獻,從而更大程度上的推崇儒學,儒學出現了復興的勢頭,借此機會來抨擊玄學一派,這也是當時統(tǒng)治者愿意看到的景象。
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政權更替頻繁,少數民族紛紛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他們認真學習漢族語言和學說,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不斷進行改革,努力將自己由以狩獵為主的游牧民族向以農耕為主的農業(yè)民族轉變。他們將儒學作為指導思想,例如前秦皇帝苻堅精通儒學,積極設立學校,并每天都到太學查看學生們經義的學習情況。同時少數民族也十分重視法律的修訂,東魏制定的《麟趾格》、西魏制定的《大統(tǒng)式》、北齊制定的《北齊律》首創(chuàng)重罪十條、北魏孝文帝四次親自參與法律的編纂,等等,既有對秦漢以來法律制度的繼承,又有自己獨特創(chuàng)新。
四、結語
魏晉時期的學術之爭可以稱之為思想解放,人們希望擺脫儒家經學的束縛,尋求自然、真實的自我。但是魏晉的思想潮流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到儒家的地位,曹操偏愛漢朝時期的明德慎刑,司馬家族也以名教自居,并且人們千年來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方方面面都有儒家禮教的影子,這同時對南北朝時期的法律產生了影響。儒家思想作為魏晉南北朝立法的主要指導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上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魏晉南北朝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開端和全面發(fā)展時期,影響了以后的整個中國封建法制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