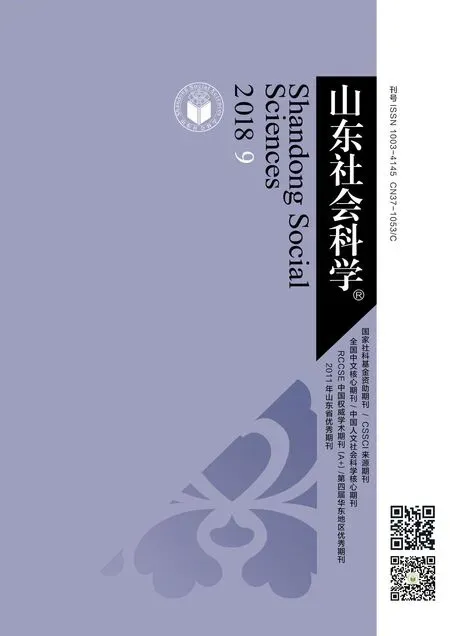明代社會輿論的歷史意蘊及啟示
展 龍
(河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輿論是社會中一種“普遍的、隱蔽的和強制的力量”②馬克思、恩克斯:《馬克思恩克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7頁。,具有強大的引導力和號召力,并“對社會權力、官府政策形成某種約束和制衡”③匡顯楨、蘭東:《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求是》2005年第6期。。明代是傳統與創新雜陳、保守與開放并存,具有明顯轉型趨勢的特殊歷史時期。處此境域,明代輿論呈現出極具時代特色的復雜態勢,不僅影響著時人的思想、觀念、情緒和行為,而且對國家權力、政治秩序產生了重要影響。緣此,明廷重視引導社會輿論,利用社會輿論,以期迎合民意,化解民怨,緩和矛盾,革新政治,維護統治,但囿于時代,明代社會輿論尚存在環境保守、策略專斷、渠道單調等局限。
一、明代社會輿論的歷史意涵
“輿論是一種社會精神現象, 是社會控制機制的反映”④程世壽:《公共輿論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頁。,其本質屬性決定于其基本構成要素,即大眾見解和意見、集合意識和信念、公共話語和意識等。這些富有時代特性的構成要素所蘊含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指向,決定了社會輿論的本質屬性。基于此,明代社會輿論亦因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別樣的構成要素而具有獨特的歷史意蘊。
(一)明代社會輿論是國家意志與道德說教的集中體現。明廷對社會輿論采取了迎合利用、壓制懲處的雙重策略,這種表面矛盾的輿論策略實際既利用了輿論生成中聚焦民眾意見、反映社會實情的功能,又發揮了輿論引導社會事件走向和公眾態度的功能,其根本都是出于維護朱明專制統治的考量。明代國家治理,除了嚴刑酷法“硬政策”之外,社會輿論發揮出了其作為“軟政策”在國家治理中的獨特作用。輿論控制策略不僅是懲處壓制,更多是出于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而利用輿論的一切方式,而這些方式之間是否矛盾,是否違反社會發展的規律則并不重要,這種輿論控制的意義在專制社會更為明顯。同時,明代社會輿論打上了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的烙印,其核心價值取向是統治者意志的集中體現;換言之,明代社會輿論是民間或官方從儒家倫理道德出發,就某一政治、經濟、社會事件產生的群體性的看法或意見,反映階級或群體訴求。諸如晚明東林黨人的批判精神就是借助儒家的道德范疇,在尊君、匡君、循道的多元意識中,以坦蕩的人格精神踐履了“以身殉道”的輿論自覺。因此而說,明代輿論控制策略是明廷“依法治國”的策略之外,實行的一種文教倫理策略。
(二)明代社會輿論是民眾意志與集體利益的別樣表達。公共意志取決于集體利益,明代廣大民眾無言論自由,其感性化、情緒化、零碎化和欲望化的輿論表達無法充分表現自我精神的集體取向。除大規模民變外,時代很難形成取向一致、訴求共鳴的社會共同意志;且限于傳播媒介和渠道,輿論傳播僅限于自然屬地的狹小空間。明代輿論引導者是權力頂端的皇帝、閣臣或黨社,或具有影響力的黨派和組織,而廣大民眾并不能有目的地引導社會輿論,更無法真正決定輿論的主流趨勢和發展結果。但縱然如此,以士人為先導的民間輿論,依然可以在某些時候、某些場景代表民眾的集體利益和意志,在發出輿論呼聲之時,引領民間社會輿論的生成發展,這種“輿論是一種很常見但又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簡而言之,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社會公眾的議論活動”*程世壽:《公共輿論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同樣的,在多數情況下,明代輿論也是人數較多的社會群體催生的,是廣大民眾關注某一事件或問題而產生的一種集體意識或共鳴,形成具有一定的利益目標、價值取向和社會認同的公眾議論活動,成為影響社會發展變革的重要話語力量。
(三)明代社會輿論是國家政治與民間話語的互動表征。輿論是官民對其關切的人物、事件、現象、問題的信念、態度和意見的總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持續性,并對政治秩序的發展態勢產生影響。*匡顯楨、蘭東:《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求是》2005年第6期。明代空前活躍的社會輿論,一定程度上成為國家政治與民間力量溝通互動的重要橋梁。一方面,官方利用輿論的正能量,壓制輿論的負能量;另一方面,民間社會利用輿論的話語力量表達意愿,申述訴求,并對國家政治產生一定的影響;但與此同時,民間輿論也因受制于國家政治及其主導的社會輿論而顯得較為蒼白。如東林黨人壯志凌云,氣吞山河,清議時勢,但一旦轉入現世,他們輿論呼喚便淪為政治附庸,難以擺脫國家權力的強力束縛,他們追求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信念必然扭曲變形,陷入窘境。因此,在君權至上的明代,民間社會輿論縱然可以形成一場場風波,并在特定歷史時期可以與國家政治形成某種互動,但在多數情況下,國家權力始終宰制著社會輿論的理性訴求和激情批判。
二、明代社會輿論的歷史特點
明代輿論生態取決于特定的歷史境域,專制統治的強化,社會經濟的轉型,市民階層的崛起,思想文化的多元,人口流動的頻繁等,特定的時代背景賦予明代社會輿論特殊的歷史意蘊。尤其是新市民階層的崛起和輿論訴求的高漲,輿論主體和客體的日趨多樣,將明代輿論推至空前活躍,使此期的社會輿論呈現出獨特的歷史態勢。
(一)輿論主體呈多樣性。輿論是社會中一定數量的人或團體對于某個特定話題所表現出來的一定的意見或態度。明代輿論主體主要指言官、生員、士人以及黨社等。其中,言官是官方輿論的主體,有監察百官、封駁奏章之責,是關注時政的主力,“凡政令施于四方,四方有所奏請者,必歸于給事中,然后五府六部受而行之,事有是非可否,與夫稽遲缺謬者,小則駁正,大則廷論之,而人無敢不服”*(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49頁。。有明一代,士大夫與士始終是社會的主導群體。*商傳:《走近晚明》,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36頁。他們在講習之余,結為黨社,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范,遙相應和,蔚為清流。*(清)夏燮:《明通鑒》卷八一“崇禎元年五月庚午”條,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3184頁。明中晚期,商人經濟地位不斷提高,與士人的界限日漸模糊,這使商人可以借助士人的話語力量來申述訴求,“由于商業在中國社會上的比重日益增加,有才智的人便漸漸被商業界吸引了過去,又由于商人擁有財富,許多有關社會公益的事業也逐步從士大夫手中轉移到商人的身上”*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頁。。農民是明代輿論主體的末端,他們大多不能閱讀撰文,只得以民謠、民諺等形式傳播輿情,表達意愿,抒發情懷,發泄憤懣。
(二)輿論演變呈階段性。明初,鑒于元亡,建立通政司、都察院、六科等輿論監察系統,并鼓勵臣民大膽進言,言失無罪,“凡有四方陳情建言,伸訴冤枉民間疾苦善惡等事,知必隨即奏聞”*(明)申時行等:萬歷《明會典》卷二一二《通政使司·通達下情》,《續修四庫全書》本,第519頁。。但重典之下,世風丕變,士林緘默,輿論陷入沉寂。成宣諸帝繼往開來,勤于國事,鞏固基業,永樂時御史分巡,成為定制,同時“革拾遺、補闕,仍置左、右給事中,亦從七品”*(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七四《職官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07頁。等。明中期以后,時勢艱危,內外交困,正嘉荒政,神宗不朝,以奏疏直諫、謠言諷喻為主的輿論日漸勃興,“晚明時代尤其是萬歷中葉以來,社會輿論對于時政的批評,已經從官場至民間,從少數而至普遍”*商傳:《走近晚明》,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29頁。。期間,市民成為輿論主體,輿論傳播方式也趨多樣,書院、青樓、茶社、劇院等成為傳播的重要場域;同時,官方輿論管控愈加粗暴,輿論反映的問題懸而不解,反而多行詔獄或留中。天啟以降,魏黨亂政,輿論淪為懲善揚惡、政治斗爭的工具,地方謠言四起,民變不斷,國之凋敝,每況愈下。處此情勢,官方輿論管控難以適應時勢變化,輿論策略也實難奏效。
(三)輿論系統呈獨立性。明代輿論監察是由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構成的獨立系統,其主要職責是監督行政機構,是明代法定的輿論監督系統。其中,都察院“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七三《職官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68頁。;監察御史“主查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七三《職官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68頁。;六科給事中直接受命于皇帝,執掌監察、彈劾之職,并借邸報傳布訊息。如此,都察院等構成明代較為獨立的言官輿論系統,“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七九《鄒智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756頁。。除官方輿論,明代民間輿論形式多樣,異彩紛呈,廣大士民對于有違國家治理、民眾利益以及倫理道德的現象,時常借助民歌謠諺、時事小說、說書戲劇等予以廣泛關注,乃至群起而攻之,通過集體性輿論力量對社會進行規范,進而對當局造成一定影響,形成一定壓力。
(四)輿論監督呈制衡性。明初,鑒于丞相權重,輿情難達御前,遂設立通政司,掌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赍狀奏聞。凡天下臣民實封入遞,即于公廳啟視,節寫副本,然后奏聞”*(清)張廷玉等:《明史》卷六《成祖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3頁。。明代加強輿論監督,但也造成皇權與輿論的分離,如言官不僅可對違法、瀆職、貪墨的官員進行彈劾,且當皇帝言行有違禮制時,也直言勸諫,如武宗“南巡”、世宗“議禮”等,皆遭致輿論反對。明代言官是官方輿論的操控者,由其行使的輿論監督是制約皇帝,抗衡宦官的重要路徑。晚明時,國勢日衰,皇權不振,輿論的導向作用使天下士人更具凝聚力,明初唯諾士風轉為黨結之風,社會輿論空前高漲。此外,明代按察司官與巡按御史互相抗衡,二者共同巡歷郡縣,察劾有司,受理民訟;二者又互相監督,頡頏行事,“御史糾彈,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清)龍文彬:《明會要》卷三三《職官五·都察院》,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564頁。。若按察官不法,巡按可隨事舉劾,若巡按違憲,按察官也可指實劾奏。
(五)輿論載體呈多元性。明代輿論包括以言官為主的官方輿論和以士民為主的民間輿論。官方輿論的傳播載體主要是邸報,它將奏疏印成小報,供士人與官員閱讀,是連接朝廷與士人的紐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信息性和真實性。除邸報外,揭帖也是傳播輿論的重要載體,其中私揭是公開散發的文書,匿名揭則是匿名散發的信息,但揭帖也有其弊端,“近起人情險惡,動以私揭害人,報復私怨”,因此明廷規定:“若挾私忌害,顛倒是非,輕重者,即便參奏拿問,比誣告律坐反。”*(明)申時行等:萬歷《明會典》卷一六九《《律例十·刑律二》,《續修四庫全書》本,第80頁。較之官方輿論,明代民間輿論的傳播載體較為多樣,如士人可以通過著書立說申述意見,表達論說,明末東林黨撰《萬歷疏鈔》等記述時政,而閹黨撰《東林同志錄》等詆毀東林。民間庶人囿于知識水平,多通過諺謠等方式發表意愿。明代印刷業的發展加速了出版物的刊布,也便于輿情的廣泛傳播。如明末涌現的一些時事小說,記述了《樵史通俗演義》等重大時事之始末。
三、明代社會輿論的現代啟示
社會輿論是人們對社會發展或社會現象的共同意見和集體態度*張學濤:《淺議社會輿論與社會穩定》,《理論導刊》2008年第10期。,它所蘊含的思想意蘊反映的是人們的生活訴求和現實問題,從中可以觸及時代的脈搏,傾聽社會的呼聲。因此,即使在封建社會后期的明代,社會輿論的發展態勢也會引起官方深切而廣泛的關注,這些都為新時期應對社會輿論提供了若干可資借鑒的啟示。
(一)重視輿論效應。社會輿論的演生往往會對輿論主體形成一定壓力,導致民眾社會心理的趨同傾向,并成為人們認識、解決現實問題的準則,進而影響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明代社會輿論是影響政治社會的重要力量,其中先進士人領導的民間輿論以公共批評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對準時代的主題”*林語堂:《中國新聞輿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形成比官方輿論更具影響力、傳播力的輿論力量。因此,明代統治者大多重視社會輿論,尤其是某些社會問題或事件引發的社會輿論,明代官方時常會乘勢觀民風、察民政,使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上達朝廷,并順應輿論訴求,化解矛盾,出臺政策,革新政治;否則,輿論關注的問題、矛盾或危機便會日益加劇,使社會處于混亂狀態。如神宗怠于朝政,留中奏疏,致使很多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問題未能及時解決,以致諸種問題層出不群,政治事件此起彼伏,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最終將明王朝推向覆亡邊緣。
(二)開展輿論調查。輿論調查作為社會運行的重要“警器”,能對社會走向進行預測,以了解輿論動態,洞察社會矛盾,傾聽民意民聲,反映輿情時勢。因此,官方在進行社會輿論調查、重視民眾呼聲時,要注意了解引起輿論生成發展的前因后果,引導輿論向正常的方向發展,惟其如此,輿論調查既可提升官方的公信力和執政能力,又可傳達輿情,凝聚人心,激發活力,進而增強社會治理,維護社會秩序。明代官方重視社會輿論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重視輿論調查,如明初鼓勵民眾狀告貪官、詣闕上訴;派遣巡按巡察地方,體察民瘼;指使廠衛等緝捕貪墨,刺探民聲;設登聞鼓,許人鳴冤,赴闕直訴;許民乞留清官,薦舉廉吏;搜集民間清議、黨議、謠諺等。凡此,皆是明代開展輿論調查的基本路徑,一定程度上成為官方及時發現社會問題,洞察民意動向,把握輿論態勢,制定政治決策的重要依據。
(三)引導輿論方向。輿論引導“是一種運用輿論操縱人們的意識,引導人們的意向,從而控制人們的行為”*周宇豪:《輿論傳播學教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頁。。較之以往,明代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明前期,在政治變革、政治專制的背景下,明廷通過一些列文化專制政策,強化思想控制,維系文化一元,引導輿論方向,如洪武一統學術,一述程朱;永樂官修《大典》,頒行“大全”。至明后期,明廷進一步強化對輿論方向的調控和引導,如禁毀書院,禁止講學,催抑“異端”,壓制清議等。同時,一旦輿論導向發生異化,輿論就成為引發政局混亂的根源。如明廷借助言官鉗制朝臣,致使二者常相水火,爭論不休;晚明黨爭日熾,“居言者各有所主”,“言愈多,而國是愈淆亂也”*(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二一五《劉奮庸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690頁。。正因如此,歷來官方重視引導輿論方向,歷史表明:只有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指引信仰追求、示范道德典范、促成價值認同,才能形成有利于增進社會和諧、鞏固執政地位的輿論導向和輿論環境。
(四)加強輿論監督。輿論監督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正確的輿論監督可以化解社會沖突,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明代重視輿論監督體系的構建,但輿論監督仍存在不足:一是社會輿論很難監督、制約皇權,雖然某些輿論訴求改變了皇帝旨意,但未能全然將皇權納入輿論監督的框架內;二是明代的輿論監督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人們很難憑借輿論充分獲悉政治事務和涉及公共利益的社會事務;三是明代輿論監督的媒體和渠道極其有限,僅限于奏疏、邸報等官方媒體,輿論監督渠道也僅仰賴于言官等政治群體的監督職責。因此,政府應加強對傳媒輿論的調控和引導,使輿論監督步入法治化、規范化軌道,以保障媒體與公民的知情權,充分熟悉社會輿論在公共事務中的重要作用,惟其如此,輿論監督才“利于社會問題的逐步解決,有利于黨和政府改進工作,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劉云山:《輿論監督要有利于問題的解決和社會穩定》,《黨建》2005年第1期。。
(五)營造輿論環境。“輿論環境是指人們面對的公眾意見的指向以及多種意見交叉的意識氛圍,包括若干公眾意見的和諧、對立或沖突”*劉建明等:《輿論學概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輿論環境是社會意識環境的表征,是在大致相對集中的時空內,不同群體的具體輿論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有機整體,反映了社會思潮和民眾思想狀況,并對社會民眾產生一定的影響。明代輿論環境總體表現出保守又壓抑,單一又專制的歷史特點。當時,在重典治吏、廠衛泛濫、固守程朱的專制情勢下,廣大官民正當、合理的輿論訴求、政治呼聲難得伸張,輿論生態長期沉寂而了無生機,即使在復雜多變的晚明時期,日益活躍的輿論風潮中依然充斥著漠視輿論、壓制輿論等極具專制色彩的輿論政策。鑒于此,輿論媒體應從政治生態、民眾生活的實際出發,充分反映民眾的呼聲和意愿,主動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及時疏導社會輿論,化解社會沖突,緩和社會矛盾,理順民眾情緒,平衡社會心理,以促成社會輿論的良性互動,進而營造出穩定、協調、和諧的輿論秩序和輿論環境。
總之,明代特定的輿論生態表明:社會輿論是審視現實社會的一把標尺,政治昌明,則言路暢通,政治專斷,則言路壅蔽。在任何時期,社會輿論都代表著一種公共權力,揭示著民眾的思想指向,包含著一定的民主色彩,一定程度上契合于民心可向、人言可畏、諍言可貴的定律。循此,在任何歷史時期,良好的輿論環境、先進的輿論主體、有效的輿論監控、科學的輿論預測及其構成的輿論體系,始終是化解社會危機、矯正執政理念、淳化思想觀念、健全意識形態、維護社會聲譽、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