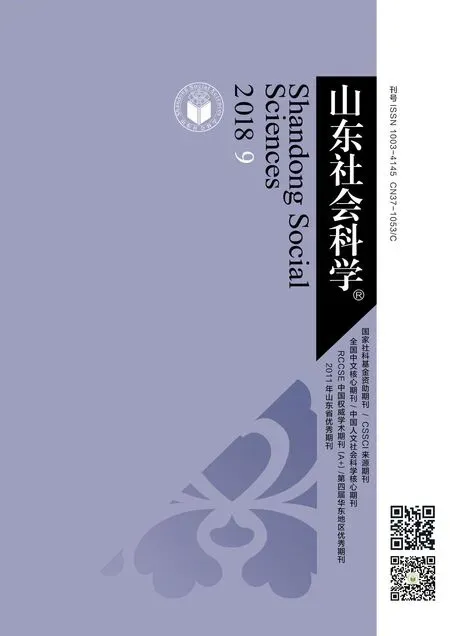道德的轉型:邁向現代公德社會
王小章 孫慧慧
(杭州師范大學 政治與社會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浙江大學 社會學系,浙江 杭州 310058)
一、“道德滑坡”、“道德爬坡”還是“道德轉型”?
作為在一定的價值理念下非直接強制性地①“非直接強制性”主要是與法律相對而言,同時,也是表明,真正體現行為者之德性品行的行為是出自行為者自由意志的行為,強制不可能產生這種意義上的道德行為,而只能產生“非道德”(不是“不道德”)的順從行為。但是,在行為者之德性的培育養成過程中,在道德規范所規定的道德義務范圍內,必要的外在壓力,包括對背離道德義務的行為實施制裁,則是任何一個社會進行道德規馴的必要手段。調節人們各類社會關系的倫理規范和準則,道德一頭連著人類一些基本的價值訴求,一頭則連著具體的特定的社會,最終則體現為人們的道德觀念(意識)、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由此,道德一方面具有跨越特定時代、超越具體社會的普遍恒常的特性,這一點,從古今中外許多道德楷模為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人們所共同景仰這一事實,就可得到證明——這實際上體現出,作為馬克思所說的“類存在物”,人類始終存在某些共同的普遍的價值追求(當然,這些普遍性的價值如何轉化落實為能夠有效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的規范,則也要隨社會和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另一方面,道德同樣也呈現出顯而易見的變異性:今天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在過去可能是離經背道,在這個社會被認為極其正當的行為在另一個社會則可能是不可饒恕的罪過。這是因為,無論作為價值還是作為直接調節規范人們行為的準則,道德都既反映著特定社會形態下的社會關系,也必須在特定社會形態下的社會關系中對置身于這種關系之下的行為主體發揮作用,因而,也就必然隨社會形態、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
改革開放四十年過去了,中國社會發生了舉世矚目的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既體現在外部世界的制度(體制)層面、結構層面,也體現在內部世界的精神層面,包括道德層面。對于自改革開放以來發生在國人身上的道德觀念、道德情感、道德行為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到今天,已經銷蝕了不少學者的大量筆墨。而縱觀這些學者對于國人道德變化之性質的基本認識和判斷,則其中的絕大多數基本上都可以歸入兩種對立的觀點,即“道德滑坡論”和“道德爬坡論”。前者主要以“道德滑坡”乃至“道德淪落”來認識看待改革開放以來發生在國人身上的道德變化,將這種變化認定為中國社會道德狀況的惡化,乃至前所未有的惡化,只是不同的學者對于造成這種惡化的原因在認識上有所不同或各有側重。比如,有人主要從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對人們的生活觀念和社會行為所產生的影響來探求“道德滑坡”的原因,認為“道德滑坡”是由于經濟主導的社會生活使得功利化和消費主義等觀念盛行,社會對道德的關注則大大減少,個體對自身的道德要求大大下降。有人從我國現有的某些制度來分析“道德滑坡”的原因:如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客觀上使得遵從道德的成本過高而違反道德的代價很小;不健全的法制無法對公民行為進行最低程度的強制性限制,從而使得道德在發揮社會整合作用時顯得無力。也有人把這種“道德滑坡”歸咎于現代多元化社會中各種不同價值之間缺乏整合以及西方價值觀念的負面影響。更有人從所謂經濟與道德的“二律背反”來說明我國當前面臨的道德困境。總的來說,持“道德滑坡論”的學者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發生在國人身上的道德變化,對于我國社會的道德現狀,都懷有一種深切的焦慮或者說悲觀的心情。與此相反,“道德爬坡論”者則對我國社會的道德現狀和前景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說,“道德滑坡論”主要是基于幾十年來發生在國人身上之實際的道德變化的一種思慮,是對我國社會之道德現實的一種回應,那么,“道德爬坡論”則更多的是對“道德滑坡論”這種觀點的一種回應。這一點,從持“道德爬坡論”觀點的一些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看出,如:《經濟與倫理之間是否存在著“二律背反”》(李雨村,1990)、《應走出歷史與倫理“二律背反”的誤區》(林劍、宋能文,1990)、《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進步與道德關系的思考》(劉鋒,1991)、《不存在商品經濟與道德的“二律背反”》(孔潤年,1992)、《不存在經濟與倫理的“二律背反”》(毛三元,1993)、《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定要以“道德滑坡”為代價嗎》(吳倬,1994)、《經濟與道德“二律背反”嗎》(唐凱麟,2005)、《聳人聽聞的“道德崩潰論”》(孫春晨,2012),等。也就是說,“道德爬坡論”主要是在比較一般、比較抽象的理論層面上對“道德滑坡論”的一種反駁,與此想聯系,其“道德爬坡”的觀點,主要也不是對于我國當下之道德境況的一種事實判斷,而是基于其自身的理論邏輯而得出的對于未來之道德前景的預期。
相比于“爬坡論”,“滑坡論”無疑更加符合當今多數中國人對于我國社會道德變化和現狀的感受,因而也引起更多人的共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滑坡論”和“爬坡論”對于中國社會道德變化的看法可謂針鋒相對,但事實上,它們卻隱含著一個共同的預設或視角,那就是都自覺、不自覺地把社會成員的道德素質作為關注的焦點和討論的出發點,并且,與此相應,都潛在地預設了道德之基本內涵的恒常性,因為,只有當它們所說的“道德”之所指是同一個對象時,才能就它究竟是在“滑坡”還是在“爬坡”進行真正具有實質意義的對話。換言之,它們都沒有,至少沒有充分地認識到,要從道德本身需要隨著外部社會結構形態的轉型而轉型的角度來審視發生在當今國人身上的道德變化,來分析認識今日中國社會所面臨的道德問題。當然,并非所有的學者都是如此,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道德轉型”的問題。早在1994年就有學者指出:要區分道德“轉軌”和“滑坡”,道德是具體的歷史的,要隨著整個社會、特別是它的生產方式的發展而發展;我國目前進行的改革, 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 是一個社會運行方式的轉軌過程,與此相應,道德模式和道德觀念也必然要轉軌,而“從傳統道德到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現代道德”, 則是這一轉軌的主要內容。盡管該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又從“道德的社會歷史標準”出發認為:“從歷史發展趨勢和社會轉型期的整體高度看,向前看,應該強調我們當前面對的道德形勢,本質上是要‘爬坡’”,不過,根本上,其“道德轉軌論”實際上就是“道德轉型論”。此外,也有學者注意到:今天的道德話語大都源于傳統社會,人們在做負面道德評判時依然訴諸傳統道德情感,而傳統道德并不能應對高度分化的復雜社會中的問題;所謂“道德滑坡”的實質,是傳統的道德范式在現代喪失了有效性,而以自由、平等為信念基礎的現代道德范式還沒有建立起來。也就是說,在這些學者看來,當今中國之道德問題的實質,是“道德轉型”的問題,而所謂“道德滑坡”或“道德淪落”,實際上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道德自身需要相應轉型以及這種轉型沒有按歷史發展所要求的那樣走上軌道的一種癥候,而不是,至少不單純地是社會成員的道德素質問題。
如本文開頭所述,作為在一定價值理念之下以非直接強制性的方式調節人們各類社會關系、并最終要體現為人們的道德觀念(意識)、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的倫理規范和準則,道德的內涵既有恒常普遍的一面,也有隨社會和時代的變遷而變遷的一面。因此,相比于“滑坡論”“爬坡論”,筆者認為,“道德轉型論”無疑更切合處于急劇轉型中的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境況。實際上,早在一個世紀以前,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就指出,一種道德必須與特定的社會結構形態相匹配、相適應才能有效地發揮其作用,社會成員對一種特定的道德規范的接受認同與否受制于社會成員本身所處的社會結構形態,社會結構形態的變化必然帶動社會成員思想意識的變化,從而使得原來社會結構中的道德的作用發生變化,即原有的道德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下降而失去有效性,此時,一味譴責社會成員道德素質下降,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是于事無補的,真正的出路在于因應社會結構的轉型而重塑與新的社會結構形態相適應、相匹配的道德。而要重塑與新的社會結構形態相適應的道德,則單是籠統地說這種轉型是要“從傳統道德到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現代道德”顯然是不夠的,甚至,只是指出這種新的道德的價值基礎是自由、平等也是不夠的。道德價值還必須要轉化為能夠直接引導、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調節、維系社會關系的行為準則,方不至凌空蹈虛。而問題是,即使是同一種價值,也可以有不同的行為。比如,仁慈是一種價值,但這同一種價值,既可以表現為針對具體受助目標的直接的助人,也可以通過捐款、納稅而通過中介組織、政府等來間接地助人。直接調節、約束人們行為的道德規范、準則把人們的行為引向哪一種方式更為有效,也即,什么樣的道德規范更容易為人們所認同接受,更容易真正扎根于世道人心,則除了取決于這種道德規范所體現的價值是否具有正當性之外,還與人們之間那受特定社會結構形態制約的社會關系、社會意識、社會情感密切相關。因此,為了道德的有效轉型,為了切實的道德重塑,必須科學地認識社會轉型的性質,認清這種轉型給人們的社會關系、人際情感等帶來了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為何使某些傳統的道德失效,在此基礎上,進而把握新的、能夠切合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生長起來的新型社會結構的新型道德的基本特性。
二、陌生人之間的人際期待和人際容忍:對X社區的經驗調查
那么,該如何認識看待當今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的社會轉型呢?許多人,包括上面提到的不少“滑坡論”者在分析道德何以“滑坡”的原因以及“爬坡論”者在反駁“滑坡論”的觀點時都十分看重當今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更有持“道德轉型”觀點的學者明確認為“從傳統道德到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現代道德”乃今日中國要實現的“道德轉型”的主要內容。不能說這種看法完全錯誤,但是,僅僅從市場化的角度來認識當今我國的社會轉型畢竟太狹隘了,而且,僅僅從“與市場經濟相聯系”的角度來認識“現代道德”也把“現代道德”的內涵看得太狹隘了:任何時代的道德所要調節的都不會僅僅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經濟行為,而是作為社會存在物的、外延遠為寬泛的社會行為。今天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轉型,固然首先是由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制轉軌引發的,但絕不僅僅限于市場化轉軌,而是由市場化轉軌帶動的整體社會結構形態的變遷,也即從傳統鄉土性的、封閉的、靜態的、同質性的共同體式社會,轉變為現代以城市為中心的、開放的、流動的、異質性的個體化社會。這一整體結構的轉型必然地帶動了受制于結構的社會成員之間關系的變化。而對于引導和約束人們的行為、調節和維系人們之間關系的道德來說,這種變化中最值得關注、最具根本意義的,就是“陌生人關系”日益取代“熟人關系”而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時刻要面對的基本關系,換言之,社會結構的轉型把我們帶入了一個不同于傳統熟人社會的陌生人社會。
需要說明的是,所謂“陌生人關系”,固然包含著彼此生疏、不了解、不相知的含義,但更主要的是指在雙方之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中,一方對于另一方來說不是作為具體的、活生生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而存在的,而是作為抽象的、符號化的、概念化或單一功能性的對象而存在(就此而言,兩個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也是一種陌生人關系)。美國法學家勞倫斯·弗里德曼這樣刻畫現代“陌生人社會”:“我們打開包裝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遙遠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們不知道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們的任何情況。我們搬進陌生人的——我們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我們生活中的很多時間是被‘鎖’在危險的飛快運轉的機器里面,如小汽車、公交車、火車、電梯、飛機等里面度過……因此我們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制造和運轉機器的陌生人手中。”換言之,所謂“陌生人關系”,絕不是通常容易誤解的那樣彼此之間沒有關系,而是一種不同于熟人之間關系但彼此之間依舊存在相互影響的陌生人之間的關系。當這樣一種關系取代熟人關系而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基本關系后,也就需要一種新的、與維系熟人關系的道德有所不同的特定道德來調節。那么,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特定道德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在W市的X社區做了一個調查。
X社區是W市近年建成的幾個最大的生活住宅區之一,位于該市L區東部。住宅區于2006年正式投入使用,2012年成立社區。社區下轄8個花園小區,即8個組團,包括安置房組團、經適房組團、人才房組團、商品房組團等。作為本次調查點的L組團,是X社區中一個典型的中檔商品房小區,目前已有約1100戶居民入住,呈現出典型的陌生人社區的特點。據筆者從物業和業主委員會了解,L組團中的大部分居民是從城市中各個地區購買房產而共同居住在這里的,在這之前彼此互不相識,也談不上血緣、親緣或業緣關系。盡管L組團自建成投入使用已有10多年,但其中居住8年以上的僅30.2%,24.5%的居民居住時間在3年以下,其中不少是通過購買早先住戶的二手房而搬來的;另有約10%的居民是租賃居住或借住在別人家的房子,這些居民的流動性就更高了。所有這些都使得L組團居民之間的關系大大不同于傳統上那些由生于斯、長于斯、終老于斯的熟人所構成的社區。
圍繞上面所提出的問題,即陌生人之間的人情之常與熟人之間的人情之常有什么不同,進而,從道德要順乎基本人情的角度,需要一種什么樣的道德才能更加有效地調節陌生人之間的關系,我們在X社區的調查主要關注了兩個方面:第一,陌生人之間的人際期待;第二,陌生之間的人際容忍。調查采取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通過網上問卷以及實地問卷調查兩種方式進行,網上問卷調查收集問卷44份,實地問卷調查收集有效問卷62份,共收集到有效問卷106份;訪談主要在實地問卷調查的對象中隨機進行。
(一)陌生人之間的人際期待
所謂人際期待,是指在一種既定的關系下,彼此對對方行為的期待。比如父母會期待子女常來看看自己,孩子會期待父母關愛自己;朋友會期待對方在自己有困難時能幫助自己,等等。這種人際期待有時是對等的(如朋友之間),有時是不對等的(如父母子女之間),但無論對等還是不對等,只要這種相互間的期待在雙方看來都是合情合理、可以接受的,那么,當它們轉化為一種倫理規則時,也就比較容易獲得認可,從而也就能夠對他們的行為產生內在的約束力。那么,陌生人之間的人際期待是怎樣的呢?從表1的數據,我們即可大體了解其基本特征。
前面指出,X社區L組團屬于典型的陌生人社區,鄰里之間的關系也是典型的陌生人關系。而從表1的數據可以看出,在陌生人之間,哪怕彼此是鄰居,對對方的期待也主要表現為一種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期待,也即,主要是希望對方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希望對方做什么。他們并不多么地期待對方幫助自己,更不介意對方拒絕幫助自己。他們更多地只是希望對方不要影響、干擾、妨礙自己。實際上,這種傾向不僅僅體現在主觀期待中,也體現在社區居民的實際行為中。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有64.2%的問卷調查對象表示從來沒有找過鄰居幫忙,僅26.4%的居民表示曾經找過鄰居幫忙。而如果進一步問那些曾經找過鄰居幫忙的調查對象,具體為了什么而打擾鄰居,得到的回答則要么是偶爾有點小事或者有關社區生活的問題需要問一下鄰居,要么是諸如“曬在窗外的衣服掉人家陽臺上了,要到他們家取”、“修理下水道時,曾得到鄰居的配合幫助”之類,也即是在極少遇見的沒有其他辦法的情況下而不得不打擾鄰居。這種情形在傳統的農村熟人社區中是不可想象的。在傳統熟人社區中,大到接濟困難鄰居,中到婚喪嫁娶、蓋房架屋時的大家共同出力,小到借個炒菜的蔥姜蒜、鄰居出門時幫忙照看一下房子,幾乎每個居民都有互助的意識,每個居民也都這樣實踐,所謂出入相守、守望相助,鄰里互助乃是常態。而在X社區L組團,居民所習以為常的,或者說首先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互幫互助,而是互不干擾。
確實,無論是在問卷調查中,還是在訪談中,都有受調查者表示,希望有事時可以找鄰居幫忙,特別是在一些比較緊急的特殊情況下鄰里之間能夠施以援手、提供幫助。有好幾位訪談對象都提到:要是能認識些鄰居也挺好,萬一遇到什么事也好有個照應。應該說,對于這種心理,從情理上講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對于本文所探討的問題而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這些人,也都表示,如果他們向鄰居求助而遭到拒絕,也會坦然接受,而不會心存芥蒂。一位受訪的Z先生說得明白:“有時遇到請人家幫忙但人家不樂意,那也沒什么。人家與你非親非故的,白天各自上班,晚上把門一關,總共都沒幾個照面。幫,是情,不幫,是份。”
(二)陌生人之間的人際容忍
這里說的“人際容忍”,指的是對于別人的某種與己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行為表現在內心情感上的接受或不接受,它既包括對別人實際做了什么的容忍與否,也包括對別人沒有做什么的容忍與否。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同,人際容忍也就不同。從道德應該順乎人之常情的角度,一種道德規范若能夠限制杜絕那些那些人們普遍容忍度低的行為,則比較容易獲得人們的認可接受。
除用于新一代電池組的液態密封、熱界面材料、粘合劑外,漢高還利用當下新產品和新技術,將電動機、電子電氣設備和變速箱集成到同一電動軸裝置中,以迎合電力驅動模塊的新興趨勢。此外,公司還為客戶提供適當的設計指南和工藝要求建議,包括可實現大批量自動化生產的設備。
人際容忍和人際期待顯然是相關的。對于本來就沒有期待的事情,人們不會介意它的沒有發生,更不會為它的沒有發生而氣惱憤怒;但是,如果期待中的事情沒有發生,或者,發生了你不希望發生的事情,那么,你為此而心生不滿、怨恨、甚至惱怒就不令人奇怪,反而是順理成章的。前面指出,在X社區L組團這樣的陌生人關系下,人們對于獲得別人的幫助并沒有太多的期待,相反,對于別人不要影響自己、干擾自己、妨礙自己則有著較高的期待。假如因為前者,人們對于別人不幫助自己有較高的容忍度,那么,反過來是否意味著,因為對于別人不要影響自己、干擾自己、妨礙自己有著較高的期待,因而,在陌生人之間,對于別人無端影響、干擾、妨礙自己的行為,容忍度就會比較低呢?從表2的數據來看,情形確實如此。

表2 居民公共道德行為容忍度(N=106)
從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在所列“在公共場所沒有及時處理寵物的糞便”等8項違反公共道德的行為(這些行為的共同特征就是有可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干擾、妨礙他人的正常生活)中,除了“把車停在人行道上”這一項,調查對象對于其他各項表示不能接受的(包括完全不能接受、不太能接受)均在70%以上。這表明人們對于這些行為的容忍度是比較低的。進一步訪談也發現,盡管在總體上,受訪者對于X社區L組團的生活是滿意的,認為這個小區整體生活氛圍不錯,居民之間雖然說不上親密,但還是比較和諧,至少是和和氣氣的;不過,大多受訪者也都表示,還是時不時的會遇到一些讓人鬧心甚至惱怒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基本上都與發生表2中所列的行為有關。當然,受訪者也還提到其他一些讓人難以接受的行為:
“總有人在電梯里吸煙,很討厭。有時我遇到了,就用手扇扇,把鼻子捂上。有的吸煙的這時會表現出不好意思,但也有的根本當你不存在似的。”(對L女士的訪談)
“我女兒怕狗,可有些人在遛狗時就是不牽狗繩。還有人從來不清理狗的糞便。大家都知道,沒人說他,說了也沒用。有次還將狗屎拉在了電梯里,真缺德。……這種人就是‘厚臉皮’。……養狗的問題好像不光是我們小區的問題,是個比較普遍的問題,電視里都講了好多次了,但沒用。” (對S女士的訪談)
“孩子喜歡玩,這可以理解。但有幾個孩子常在公共草坪上踢球,把草坪弄得像癩痢頭似的。我跟物業反映過,但好像沒用。父母是不是應該管一下?”(對F先生的訪談)
在表2所列的8種行為中,相對而言,“把車停在人行道上”雖然也是妨礙他人的行為,但調查對象對此的容忍度、接受度相對較高。進一步的訪談表明,這一定程度上與小區停車位不足這一客觀條件的限制有關——而這實際上也表明,盡管同樣是影響、妨礙他人的行為,但是如果這種行為是不得已的,人們對它的容忍度就會提高,這也說明多數人基本上是通情達理的,也正因此,許多事情可以訴諸于人情之常。
當然,像表2中所列的行為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行為,即使發生在熟人之間,也不會是令人愉快的。也就是說,對于影響、干擾自己的行為,即使來自熟人,也同樣是令人不悅或厭煩的。但是,熟人之間的情況與陌生人之間的情況還是有所不同。這不僅僅表現在對于什么樣的行為會被認為是干擾、妨礙自己的行為的體認會有所不同(比如在一個熟人社區中,鄰居家在辦什么事情時弄出通宵的噪聲一般不會有人有意見,但這如果發生在現代城市的陌生人社區中就有可能遭到投訴),更主要的是表現在當人們覺得別人的行為影響、干擾了自己時的行為反應上。在熟人之間,當你感到別人的行為影響、干擾了你時,通常的反應是選擇忍,或者說,忍受力會比較強,這是因為,熟人關系意味著你無可回避地要經常與對方為各種不可預知的事情而重復互動,因而你會努力在雙方之間維持一種比較和諧潤滑的關系。當然,有時,你也可能感到對方的行為讓你受不了,在這種情況下,你通常會選擇直接跟對方說。熟人關系中最罕見的,是在對方的行為干擾了你時向作為某個正式機構或部門的第三方反映,求助于第三方的介入和干預,因為這通常意味著同對方徹底“撕破臉皮”,以后再要打交道就困難了。但是,從我們在X社區L組團的調查看,在陌生人關系下,情形與此頗為不同,可以說正好相反。問卷調查顯示,當遇到諸如表3中所列的以及其他直接間接地影響干擾到自己的不文明行為時,只有極少數調查對象(7.7%)表示會當面直接進行規勸制止;但是,不進行當面直接的干預,并不意味著對于這種行為不加干預。進一步的訪談調查發現,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當遇到這種情況時,他們會選擇向有關部門,特別是物業和業委會反映,要求它們出面干預;有的受訪者還表示,當實在解決不了時,不惜訴諸法律途徑。*L組團還真曾出現一起兩戶鄰居產生矛盾訴諸法院的事件。當時樓下住戶在自家窗外搭建了雨棚,樓上住戶認為雨棚對小區安全有影響,小偷容易爬進小區樓層,而且雨棚在下雨天會產生很大的噪音,因此主張雨棚應該拆掉,然而樓下住戶堅決不肯拆,認為噪音、小偷都是子虛烏有,在自己家建雨棚是自己的權利。業委會、物業曾介入對雙方做過一定思想工作,但都無法協調這一矛盾,因此兩戶人家訴諸法院,最終經過法院一審、二審后要求樓下住戶拆掉雨棚,這件事才算真正得到解決。這一點,在我們對物業的調查中也得到了印證。而這,在崇尚“無訟”的中國傳統熟人社會中是難以想象的。
三、討論:邁向現代公德社會
簡單概括一下,從上述對于X社區的調查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基本結論:第一,在陌生人關系中,人們對別人的期待主要表現為一種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期待,即主要期待別人不要做什么以免影響、干擾、妨礙自己,而不是期待別人幫助自己;第二,與第一點相聯系,在陌生人關系中,人們一般能容忍、接受、理解別人不幫助或拒絕幫助自己,但是對于別人直接、間接地影響、干擾、妨礙自己的行為,則通常不太容忍;第三,在陌生人關系中,人們對于那些直接間接影響、干擾別人(包括自己)的行為,具有較強的干預傾向,但這種傾向一般不直接表現為對于這種行為的直接制止,而是求助于有關部門的介入。
這三點結論,對于我們前面所提出的問題,即在今天這個陌生人社會中,需要一種什么樣的特定道德來調節和規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系,可以提供什么啟示呢?
第一,盡管在道德上稱得上高尚的行為通常是超越義務的行為,但道德規范本身總是對道德義務的一種規定。而義務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積極的義務”,即作為一個特定社會的成員必須要做哪些事;一類是“消極的義務”,即作為特定社會的成員一定不能做哪些事。從一種道德若要有效地規范、約束人們的欲望和行為,其本身必須順乎人們基本的“人之常情”而不能背離“人之常情”的角度來說,那么,聯系上面第一、第二點結論,則調節、規范陌生人社會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就其內涵而言,應該首先并主要突出“消極的義務”。
誠然,規范熟人之間關系的道德和規范陌生人之間關系的道德在形式上也是有區別的。前者的表現形式是特殊主義的,就像費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樣“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來”;而這種特殊主義在陌生人之間的關系中是無法施行的,因此后者在表現形式上只能是普遍主義的,即無論對誰,都一視同仁,其標準是對所有人普遍適用的。不過,比這種形式上的區別更重要的,應該是道德規范具體內涵上的區別。從總體上看,規范和維系熟人之間關系的道德所要求于行為者的,既包括消極的義務,如不能做對不起父母、配偶、朋友的事等,也包括,并且相對而言更突出積極的義務,即要求行為者針對特定的對象積極地去“做”點什么,“奉獻”一點什么,以幫助對方,成就對方,愉悅對方,無論這個特定的“對方”是父母、兄弟、配偶、朋友還是其他什么熟人。而從熟人之間既有的情感基礎,以及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重復互動所導致的雙方對于長期“互惠”的預期而言,強調突出彼此之間的積極義務也是合乎情理的、具有現實可行性的。*熟人社會中的道德強調積極義務的另一個因素是,熟人社會通常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社會,很內從外界獲得所需的服務,因而只能更多地依賴于內部的相互幫助。但是,主旨在調節、規范陌生人社會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與此不同。它應該主要強調和突出的是消極的義務,而不能、也不必像規范維系熟人之間關系的道德那樣突出和強調積極的義務。這是因為,一方面,對于行為主體一方而言,要求他一定要去幫助一個跟他沒有任何直接關系的陌生人是不合情理的,至少是缺乏情感基礎的;另一方面,就行為接受方而言,他所期待于陌生人的,也不是對方來幫助自己,而是對方不要來干擾自己,他所感到難以容忍的,主要也不是那個陌生人拒絕幫助自己,而是他們直接間接地影響、干擾、妨礙自己的行為。
當然,說調節規范陌生人社會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應強調和突出消極的義務,主要是著眼于為維持一種平和的現代社會生活基本秩序確立一條“道德底線”,而并不意味著這種道德否定、貶抑積極幫助他人的行為。對“消極義務”的強調和突出只是意味著,不應將幫助別人當作一種對于個人來說沒有選擇余地的“義務”來年要求于他,而應將它理解為他可以自主選擇的“權利”。任何社會都應該鼓勵那些幫助別人的行為,鼓勵慈善、公益行為,對于完全無私的、甚至犧牲自己以成就別人的利他行為,更應該尊崇和景仰。但這種行為之所以值得尊崇和景仰,恰恰是因為它超越了常人之常情,也超越了“義務”。同樣,說調節規范陌生人社會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主要強調消極義務,也不意味著在陌生人社會中人們對他人就沒有積極的義務,只是,這種積極的義務在陌生人之間主要是以納稅等方式通過第三方如政府來間接地履行的,而不是在陌生人之間直接兌現的*關于陌生人之間的積極義務不相互直接履行而是通過第三方來間接履行,這兩者之間孰為因孰為果,是一個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很可能是在社會陌生化的過程中互為因果的。。在個人的直接行為方面,剩下的義務主要是消極義務,而積極的助人、利他,則表現為個人的“權利”。如果誰將別人的這種將“權利”當作“義務”來要求,實際上就是“道德綁架”,其本身恰恰是不道德的。
第二,如上所述,調節規范陌生人社會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主要強調消極義務,與此相聯系,培育形成這種道德,促使社會成員恪守這種道德義務的方式手段,與規范熟人之間關系的道德相比,也必然、并必須有所不同。規范熟人間關系的道德強調積極義務,突出從正面、積極的角度要求行為者為特定的對象去“做”點什么,“奉獻”一點什么,因而,它更多地需要、也可以通過正面示范、通過樹立正面的榜樣來教化培育;但是,調節規范陌生人社會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主要強調消極義務,主要從反面、消極的角度要求社會成員不能夠做什么,以免影響別人,妨礙別人,因而,也就無法通過正面示范、通過樹立正面的榜樣來培養(你怎么從正面來“示范”那“不能做”的事情呢?),而只能更多地依賴于通過懲罰那些做了不該做的事情的行為者,通過樹立“反面教材”,從反面來教會社會成員如何恪守自己的消極義務。換言之,你也許能夠通過樹立、宣揚一個孝子的典范而使孩子們懂得如何孝順父母,但你很難通過把一個尊章守法、誠信經營的商戶樹立為“最美誠信經營戶”而來改變那些制假售假并獲得暴利的經營者的行為,改變后者行為并進而警示其他社會成員以促使其履行消極義務的唯一有效辦法,只有制裁。而制裁就必然涉及到由誰來實施制裁的問題。作為個體的社會成員自然不是合適的實施主體,而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中,公眾輿論對于具體個體的影響作用也日益削弱(因為陌生人社會也是一個匿名社會),因此,作為相對比較正式的組織的有關機構(對整體社會而言,特別是政府相關部門)就成了實施這種制裁以規范人們行為的主要主體。換言之,在陌生人社會,那些正式的組織,特別是政府相關部門,在型塑社會道德方面,可以并且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承擔更多的責任。這一點,顯然也是前面第三點結論可以給我們的啟示。
調節、規范陌生人社會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首重消極的義務,這種道德的形成在手段上只能更多地依靠制裁、依靠樹立“反面教材”,作為制裁實施者之首選主體的正式組織、特別是相關政府部門在型塑這種道德方面可以而且應該發揮更大作用。這是一種在形態性質上相當不同于傳統熟人社會之道德的道德。在熟人社會中,任何兩個人之間的關系都是與眾不同的特定熟人之間的關系,因此,作為規范人的社會行為以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觀念,所要協調的也主要是一個特定的人和另一個特定的人之間的特定私人關系,是一種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維系著私人的道德”,不妨簡單稱之為“私德”。在道德形態上,傳統中國社會上一個私德型社會。當然,傳統社會中也有“陌生人”,但那是“熟人社會”中的“陌生人”,對于作為主流的“熟人社會”而言,“陌生人”是外來的“他者”,他與“熟人社會”的關系即“陌生人-熟人社群”的關系,相對于普遍性、基礎性的熟人關系而言只是一種例外。面對熟人社會,作為“他者”的陌生人要么努力成為后者中的一員,這意味者他接受并恪守熟人社會的道德,要么離開熟人社會或始終作為“他者”停留在熟人社會的邊緣。而無論哪種情形,都意味著不需要一種特定形態的道德來規范、調節作為例外而存在的“陌生人-熟人社群”關系。但現代社會不同,“陌生人”不再是社會中的“他者”或異類,而已成為社會生活舞臺上的基本角色,不是熟人關系,更不是“陌生人-熟人社群 ”的關系,而是“陌生人-陌生人”的關系,成了社會生活中的最為基本的關系。熟人關系當然依然存在,但那是覆蓋、隱沒在更為一般、普遍的陌生人關系之下的熟人關系。在此情形下,那種維系熟人關系的“維系著私人的道德”無論如何不能適應維護現代社會生活秩序的要求了。換言之,一個在“維系著私人的道德”上表現再好的人,也未必能夠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中穩妥地適應與應對同陌生人的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由此引起的問題,在我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碰撞接觸而進入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曾帶來過不少公共秩序、社會生活中的尷尬、窘困、矛盾、沖突,甚至由此招來外人的白眼和欺辱(如,據說曾出現在上海外灘公園門口的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事實上就與此有關)。調節規范現代陌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需要一種新型的道德,那就是上面所揭示的那種道德。與“私德”相對,不妨簡單稱之為“公德”。換言之,隨著我國社會結構從傳統熟人社會向現代陌生人社會的轉型,在道德形態上,也要相應地從傳統私德型社會邁向現代公德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