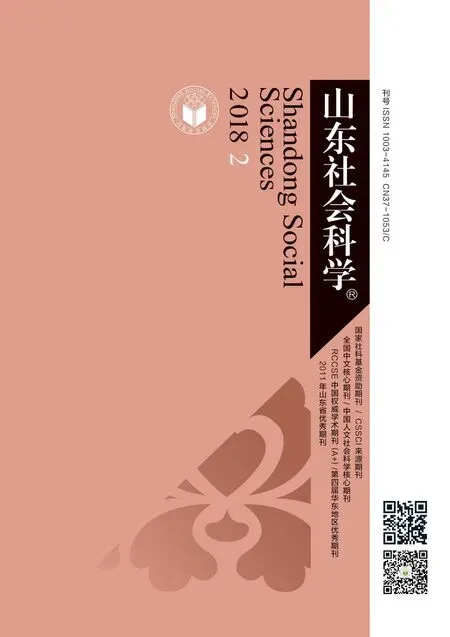馬克思的“自由三部曲”
白 剛
(吉林大學 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歐洲的自傳始于對自由的愛”(赫勒語)。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為人之自由而奮斗的“自由之子”,馬克思的自傳也始于“對自由的愛”。馬克思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戰和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斗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在此,筆者嘗試總結出馬克思自由思想發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論文》時期: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馬克思是一個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18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一直影響和鼓舞著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從一切對超驗對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哲學)宣言”:“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里跳動著,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瀆神的并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于眾神的人。”并強調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的神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反抗一切形式的限制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權威,不管它是來自宗教教義還是希臘神話。尤其是在伊壁鳩魯這里,青年馬克思還找到了最明顯、最關鍵的反抗宗教神權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現實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在這里,馬克思還是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為了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反對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開戰*在當時的德國,在宗教領域開戰要比政治領域相對安全,并且此時的馬克思對哲學的興趣和積極性遠遠大于對政治的興趣和積極性(參見[蘇]尼·拉賓:《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南京大學外文系譯,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38頁)。是當時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主流。
馬克思之所以選擇把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和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與斯多葛派、懷疑主義都是古代自我意識哲學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鳩魯代表的是“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馬克思此時正熱心于自我意識哲學和精神自由的張揚。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只關注原子的“直線運動”,注重的是原子的物質存在,而伊壁鳩魯則還說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質料和形式:“伊壁鳩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④⑤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5、28、24頁。原子不僅是現象世界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抽象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形式原則。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否認原子的“偏斜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并不僅是一種物理現象,而是意味著一種擺脫必然性控制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作為德謨克利特直線運動的“反題”,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識對物質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類思想超越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最終勝利。*[美]麥卡錫:《馬克思與古人》,王文揚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頁。馬克思之所以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持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仍然受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必然性的束縛,而否認偶然性的意義。而馬克思認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觀點,認為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④正是在承認原子偏斜運動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運的束縛”而追求個性和自由的意義上,馬克思稱伊壁鳩魯是“古代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說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先聲,他的哲學給人類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裝”(馬克思語)。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選擇,雖然還沒有完全超出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但也預示了未來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列寧語)之路。
在馬克思這里,宗教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喪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喪失,他反對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類精神變成單一的黑色。在《博士論文》中,為擺脫宗教束縛而獲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馬克思訴諸的已不再是對神的順從和屈服,而是作為哲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馬克思主張自我意識哲學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識哲學能使人從“阿門塞斯王國”的陰影中脫離出來,投入塵世的“茜林絲”的懷抱。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能夠進行獨立哲學思考的人就擺脫了宗教命運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通過確立自我意識哲學來通達精神自由的。因此,馬克思此時與伊壁鳩魯有著共同的哲學理想,也即哲學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于對自然的認識本身”⑤。在這里,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心靈的寧靜,比自然本身更有利于精神自由的獲得。所以,馬克思也認同和主張到哲學即人的自我意識中去尋找和實現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鳩魯的說法就是:“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志地獻身于哲學的人,用不著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于哲學本身就是自由。”⑥正是在“服務于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意義上,馬克思把哲學與自由等同了起來,其實質就是自我意識擺脫神的統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指認的反對宗教的“哲學(自由)狂歡”,以致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甚至說“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由此可見,此時的馬克思是徹底站在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立場上來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他作為黑格爾的最優秀的學生頒給自己的“畢業證書”。
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此時的馬克思還帶有青年黑格爾派的強烈的反對宗教色彩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思辨意味,還意識不到唯心主義哲學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歡幽靜孤僻、自我直觀的實質。雖然他批評康德和費希特只是在天空飛翔,也不太喜歡黑格爾的古怪調子,并強調自己只關心地上的事情,但這時馬克思所追求的作為擺脫宗教束縛也即神權統治的自我意識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的“哲學自由”,還缺乏穩固的現實基礎做支撐。而這正是馬克思后來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接觸,并最后在《資本論》時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萊茵報》時期: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個性和自我意識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擺脫了“宗教神權”的統治,那么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新聞出版自由”則是為了擺脫“封建王權”的統治。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強烈反對的就是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王權”。但這也同時表明,馬克思開始從關注一般哲學問題轉向分析具體的政治現象,也即從“哲學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對此,馬克思的傳記作家梅林有著明確的指認: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以后,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斗爭”的道路,現在他在《萊茵報》上繼續進行這個斗爭,而不再是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德]梅林:《馬克思傳》,樊集譯,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頁。。特別是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于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更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斗爭”和新的自由追求。馬克思此時最為關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謂精神自由——哲學自由,而是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從書齋走向社會,面向和解決具體現實生活問題的開始。
在《關于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對“自由”馬克思有一個明確的說法:“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活,不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這些事。不然,建筑師同海貍的區別就只在于海貍是披著獸皮的建筑師,而建筑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貍。”*③④⑤⑥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67、202、166、179、189頁。在這里,馬克思通過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而深刻認識到:“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③由此可見,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已不再是被當作人類本性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就是人類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貴的“裝飾品”。馬克思對作為人類本性的自由的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回應了盧梭的觀點: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所以,馬克思在該文的最后借斯巴達人之口號召人們奮起、甚至用“斧頭”去“為自由而斗爭”:“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卻從來也沒有嘗過。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斗了。”④但此時,通過報紙與現實親密接觸之后,馬克思已不再認為“服務于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強調“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⑤。在這里,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和保障,自由報刊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為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斗爭的有效手段和直接體現。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制度是不自由的體現,而新聞出版自由卻是自由的體現,自由報刊的本質就是自由的本質,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質,自由報刊就是現實的自由。如果人們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體的現實自由:“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斗爭升華為精神斗爭,并且把斗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涌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⑥可以說,在《關于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把自由的本質及其獲得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了,而不再單純依靠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演繹。為此,德國那些脫離現實、喜歡幽靜孤僻而空談自由的所謂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于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狂熱者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因此“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愿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⑦由此可見,在走出書齋開始接觸現實之后,馬克思已不滿足于抽象的、空洞的、單純說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來越關注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應該享有的各種真實的政治權利的自由。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穩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當然,馬克思此時還只是看到和反對封建王權對人的政治自由的限制,還不能深入王權背后深刻認識到和挖掘出真正制約和束縛人的自由背后的強大“物質力量”——經濟利益根源。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里還不能具體確定是何種社會關系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系。所以,馬克思此時反對的還只是作為普魯士政府王權的外在體現的書報檢查制度,并意識到“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制度”*②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153、176、186頁。。正是書報檢查制度阻礙了人們追求和獲得現實的自由,并引發了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張通過關于新聞出版的“立法”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②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獲得和實現,寄希望的還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權統治的“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立法”,認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同時,針對封建統治者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擔心,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新聞出版自由不會造成‘變動的局勢’,正如天文學家的望遠鏡不會引起宇宙系統的不斷運動一樣。”③與之相反,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而決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里,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實的自由,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民主文明的體現。
與《博士論文》時期相比,馬克思此時對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實現的理解和追求,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他已經從宗教批判前進到了批判政治與社會制度,這也是馬克思離開書齋開始走向社會的真實反映。但總體上看,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還是處于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善良愿望和理想主義階段,幻想著通過和平的“立法”來實現和解決問題,仍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在《萊茵報》的實際工作,卻使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埋下和獲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的“種子”和“原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后來為什么特別強調對“自由”(市民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資本論》時期:全面的人的“個性自由”
如果說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到“哲學”和“法律”中去尋找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那么到了《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逐步認識到對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馬克思語)。對此,恩格斯后來也有著深刻的認同:對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頁。。到“經濟”中去尋找,實際上意味著人的自由的獲得,不僅需要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更要擺脫“經濟權力”——“資本”的統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認識到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后來又在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里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而在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集大成的《資本論》中,資本更是搖身變成了具有“幽靈般現實性”的統治一切的“自動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獲得和實現真實的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資本這一“神權”和“王權”附體的“經濟權力”的支配。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實現自由背后所必須擺脫和克服的巨大物質力量。而馬克思此時已經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擺脫資本這一“經濟權力”的支配,僅僅“獻身哲學”和“出版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行最徹底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和批判。
自馬克思開始真正接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后,就逐漸認識到商品、貨幣和資本等這些“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作為支配力量的物與物背后所隱藏著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性和革命性,就在于揭示和強調資本的本質并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可感覺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超感覺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但這一關系又是以資本與人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顛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現出來的。這一關系,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天網,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納入其中,完全受其控制。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里“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的現實。這一“抽象統治人”的實質,是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的,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馬克思語)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在資本作為“經濟權力”的這一強大抽象力量的統治和壓榨之下,工人確實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④⑤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874、683頁。。所以,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工人對資本都是一種“絕對從屬”和“被統治”關系。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時期通過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和實現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學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人之自由”,也即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走向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性,還在于使政治經濟學由關于“物”——資本增殖的理論,轉變成了關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論。所以說,《資本論》的“中心思想”就是:“把人和人類從壓迫他們的種種勢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思想,對自身命運和全人類命運負責的個性的形成的思想。”*[蘇]羅森塔爾主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史》,湯俠聲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頁。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在資本邏輯的全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突破資本牢籠的無形統治,形成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仍然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特別是《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中心主題。
在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辯護士們看來,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自由的源泉,而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規律”,在進行“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同時,就已經在實現著所謂的自由。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通過“私有制”和“價值規律”完全實現了自由,歷史在資本主義這里“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在這里殊途同歸了。但馬克思卻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制正是異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謂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也只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由的錯覺”,而決不是真實的自由。為此,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同義語”的妄斷:“斷言自由競爭等于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們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頁。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規律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最大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為什么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反而走向了不等價交換的剩余價值規律。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批判”和“哥達綱領批判”。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們要想擺脫資本的權力統治,獲得真實的個性自由,就必須通過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④。正是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制”,才能徹底取代私有制而消除雇傭勞動和異化,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⑤這實際上就是用“自由勞動”來代替“雇傭勞動”,用“合作化生產”來代替“私人化生產”,用“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的個人”,從而真正使人從“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走向共同生產的“自由個性”,最終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馬克思語)。在馬克思這里,“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徹底的、絕對的和全面的:人應當從一切類型的非人的統治關系——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疏離和異化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真正還給人自己,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所有制革命”,才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在馬克思這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徹底擺脫外在“必然性”——資本、必然勞動和自然的盲目控制,獲得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強調:“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聯合生產”的基礎上,也即“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頁。。在馬克思這里,“自由王國”的建立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都是人擺脫資本的統治而獲得獨立性和個性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即人的個性擺脫勞動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覺的自主勞動中展開和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頁。。在此意義上,《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的廢除雇傭勞動的“勞動解放”,的確是“最高級自由革命”(塔克語)。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實質,就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⑥正是在“勞動解放”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我們說體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勞動自由”才是《資本論》的靈魂,這一靈魂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也同是在“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勞動才不僅僅是人單純“謀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馬克思這里,作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勞動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的證明,更是人的“個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義實現。
馬克思“傾其一生”并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寫的三大卷《資本論》,決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賺錢作合法性論證,更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上是為了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自由而斗爭”。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法]雅克·阿塔利:《卡爾·馬克思》,劉成富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頁。。為自由而斗爭,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諦,他的一生都是在迎著“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飛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