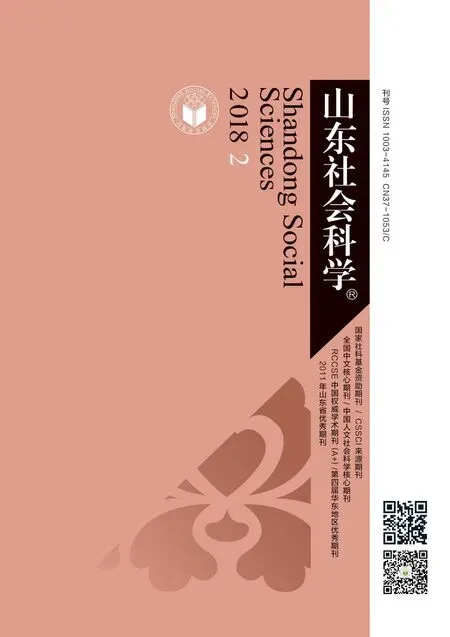轉型期的文化多元、文化沖突對社會焦慮的影響
王麗萍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3)
在中國轉型時期,受現代化、全球化和國內社會變遷的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文化發展呈現出多元化趨勢,文化沖突、文化失范、文化風險等現象增加。當今中國,隨著經濟社會的急劇轉型,一種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的價值觀迅速成為大多數人群的“集體無意識”。社會變遷中,伴隨著多元文化的沖擊,民眾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價值理念、精神信仰甚至行為方式。主導性精神價值的缺失、文化秩序的混亂,引起了整個社會的文化焦慮、價值焦慮,導致廣大民眾缺少自我價值感,找不到存在的意義,出現普遍的精神迷茫和社會焦慮。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人們的價值觀念極具現實性和理性化,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滿足”的價值目標中,容易產生社會心理失衡,難以形成社會共識,容易產生社會矛盾、社會焦慮,降低人們的幸福感。因此,轉型期的社會發展對文化轉型提出要求,整個社會呼喚文化價值重構,呼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積極培育和有效踐行,需要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來引導文化的健康發展。
一、轉型期的文化多元與文化沖突
中國的社會轉型時期恰逢世界的全球化,在文化層面上表現為全球一體化過程中的文化多元。這種世界范圍內的文化多元化,一方面促使多種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相互融合,呈現消解差異和地域性文化認同的趨勢,這種具有普遍性的、超越個體以及不同文化價值取向的規范性原則,成為社會團結和社會生活的理性基礎;另一方面全球化又催生了不同文化價值雜生的文化生態多樣性,各種思潮、理論相互碰撞,形成前所未有的文化復雜性。在現代性發展過程中,全球出現普遍的認同危機與道德焦慮,蘊含著文明沖突的風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和后進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面臨著西方主導文化價值的強烈沖擊,如何保持民族文化與傳統價值的自主性、延續性和獨特性,在多元文化中進行有效價值排序和文化選擇,在道德共識和文化認同方面進行符合本地發展的重構與定位,是所有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
社會轉型時期,巨大的社會變遷帶來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的極大豐富及多樣性發展,反映在社會行為主體的精神生活形式上就是文化的多元化,并構成社會發展的組成要素。文化覆蓋價值觀、思維方式、習俗、信仰、制度與規范體系等多個方面,其中價值體系處于文化的核心。文化的內在價值正是通過其折射出的價值觀來自我標識并體現其異質性。多元化邏輯既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現代性的內在邏輯。在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多元化所反映出的文化轉型和文化價值裂變,不僅體現了思想樣態上的差異,更折射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這是對文化多元化進行價值認知與價值評價的基本前提。然而,由工具理性引發的價值危機剝奪了人們對精神世界的追求,技術理性對人與自然和人類社會形成了全面統治,致使人們將外在存在物作為追求目標,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中,由于適應于新社會體系的價值體系尚未完全建立,沒能形成對純粹工具理性的功利性的糾正機制,限制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在多元文化模式下,文化體系內不同性質、特征、功能的亞文化之間互相沖撞、對抗、排斥的狀態即為文化沖突。當多元文化所體現的多元價值缺乏規范性原則、不能有效融合時,也就造成了價值內在沖突。轉型時期不同的相互沖突的信仰、價值和思維方式進入社會生活。社會主體以不確定的方式、態度對待文化沖突,做出各種選擇,采取不同的行為方式,導致轉型時期的社會行為缺乏社會規則約束,具有不確定性和非一致性。
(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
中國的社會轉型本質上是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脫胎于傳統文化價值體系、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以及計劃經濟思維,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包含了內嵌的傳統社會機制與思想觀念,傳統的和現代的文化價值觀念面臨劇烈的沖突,例如,傳統“正誼明道”的超功利主義與當代拜金主義、功利主義的沖突;傳統的勤儉節約美德與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沖突;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意識形態的沖突;啟蒙理性與技術批判理性的沖突等。中華傳統文化是植根于民族精神骨髓、集地域性與民族性于一身的文化傳統。當與現代思潮相碰撞時,文化差異導致的情緒發泄、習慣差異、規避不確定性等在達到新的文化互動與融合之前表現為劇烈的沖突。同時,中華文化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因而,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轉型時期的沖突的化解與消融需要價值重建和文化轉型。
(二)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沖突
精英文化是社會主流文化的承擔者,也是主流價值觀念的承擔者,體現了歷史文化的傳承和民族精神文化內涵。而大眾文化作為集體性文化行為,是在工業化、網絡化和消費社會的發展下,通過大眾傳媒廣泛傳播的,具有消費性、娛樂性、通俗性、復制性等特點。*肖鷹:《中國文化的問題在精英文化取向的下滑——兼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互動》,《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5期。當代社會文化轉型的一個標志就是大眾文化的興起。精英文化的衰落和大眾文化的興起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價值取向導致的普遍現象。*陳鋼:《精英文化的衰落與大眾文化的興起》,《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在現代文化生態中,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體現不同的價值取向,是具有不同特質的文化形態,因而,在文化活動的生產和傳播接受過程中存在沖突,精英文化無法完全控制和影響大眾文化。在大眾文化的沖擊下,精英文化作為主流文化載體和傳統文化的傳承者逐漸失去社會主導地位,沒有掌握中心話語權,出現邊緣化的趨勢。因而,在進行文化創新之際,對多元文化的存在形式和內在結構進行反思,擴大精英文化的影響范圍,突出其主導地位,促進多元文化的融合發展,保持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平衡與張力,這將是轉型時期文化領域面臨的新挑戰。
(三)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
任何文化的根本屬性首先是本土的、民族的文化。伴隨著現代性的發展,西方文化在全球性傳播,并在全球文化價值系統中掌握著主導權和話語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開放與交流,西方文化和價值不斷地輸入到我國。面對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傳統文化、民族文化和原有價值觀念的沖擊,我國在社會轉型中曾一度出現本土文化特殊價值趨于模糊的現象,國人在文化心理上受到巨大沖擊。在呼喚文化重構的過程中,文化全球化也同時喚起了本土文化的民族主義情結。經濟、政治和社會建設過程中客觀地需要文化的價值支撐,強化文化的本土性成為必然。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的競爭同時也給民眾的文化心理構成了壓力。
二、轉型期的文化失范與價值缺失
轉型期的文化失范是指在轉型期間社會發展缺乏價值文化的支撐,主導性文化價值缺失,社會基本價值觀念難以維護及文化秩序混亂無序的狀態。文化多元化一方面可能蘊含文化沖突;另一方面,可能導致文化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文化相對主義認為,任何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一面,具備其特殊價值,不能用一種文化標準去衡量和評判另一種文化。這種認知會導致文化處于價值的虛無主義,即各種思想不能對話,社會無法形成基本共識。*周德清:《社會轉型時期文化失范的效應分析——以馬克思的道德尺度和歷史尺度相結合的原則為評價標準》,《云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在文化平衡的狀態下,社會文化能夠提供明確的文化秩序,構建人的精神價值世界,并以文化的方式規定價值目標和價值標準。文化平衡狀態能夠為社會成員提供通過合法手段實現其特定價值目標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導向,此時,社會表現為穩定狀態。當社會文化分化、價值斷裂,文化的對立和沖突就會導致文化失范和嚴重的文化失衡,文化模式雖在精神生活中占主導地位,卻不能再有效地約束和規范個體行為和社會運行,導致自我存在與社會存在分離,人們開始從思想觀念上懷疑、批判甚至在行動上背離社會運行軌道,進而造成整個文化秩序的混亂。社會成員因而產生身份認同的焦慮,無法辨識達到預設文化價值目標的合法手段,人們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選擇不同的方式來擺脫這種失范造成的困境,導致整個社會生活的無序。文化平衡本身是動態的過程,與“失范”相對的“規范”也具有流動性,文化價值體系的動態調整、文化生態的平衡取決于社會文化結構是否合理。
在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傳統文化的規范作用逐漸被消解,新的主導性文化價值規范尚未完全建立,社會價值體系建設處于無序狀態。在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利益取向的沖擊使得社會文化結構紊亂,缺乏普遍認同的道德標準。文化本身具有重要的社會整合作用,在社會秩序調整中起到維護秩序、調節和約束控制手段的作用。當文化規范對社會生活、人的行為、價值體系失去引導力,就會引致社會無序行為的增長,導致在社會轉型中,出現扭曲、沒落和陳腐的價值觀念,侵蝕公共利益,腐化社會風氣,欺詐失信以及越軌行為泛濫。在轉型時期,文化失范的典型癥狀集中表現為:終極價值理想的失落、主導性文化價值缺失、道德滑坡等。*周德清:《價值斷裂與精神亂象:社會轉型期文化失范的癥候分析》,《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一)終極價值理想的失落
終極價值是具有信仰屬性的最高和最根本的內涵。在社會轉型期,終極價值缺失,功利主義和世俗化思潮盛行,從根本上摧毀了作為文化精神內核的終極價值和信仰體系。例如,伴隨著工業化而興起的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文化,追求享樂和消費至上的價值觀念,導致對個人成功的價值判斷以物質財富為標準,以炫耀式消費體現身份地位,瓦解了人的精神生活。信仰體系作為帶有終極關懷性質的價值理念是一個民族文化精神的內核,轉型時期,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實用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個體本位主義導致終極價值理想的失落,人們的社會生活失去深刻的規范約束,產生了信仰危機,從而深刻影響了國人的焦慮、恐懼、荒謬、孤獨等社會心理。
(二) 主導性文化價值缺失
主導性文化價值是指在社會得到廣泛認同的基本價值和信仰系統。在文化沖突的過程中,各種文化之間無法對話、不協調,導致難以形成統一的價值共識,無法形成約束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的普遍規則。轉型時期,伴隨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轉型,一旦出現文化失范,社會成員如果不能在內心深處認同核心價值,也就更無法將之轉化為自覺行為,其結果是,變相地消解了文化的權威性,主導性文化價值自身的合理性受到嚴峻挑戰,影響了社會成員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交往中的行為選擇上缺乏標準和價值參考。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統一奉行的主導價值,社會成員的行為將難以整體協調,從而影響社會、經濟、政治的和諧構建。
(三)道德滑坡
道德本身具有社會屬性。中國社會轉型以來,大量的假冒偽劣、不講誠信、社會冷漠、見利忘義、缺乏榮辱觀等毫無道德底線的事件層出不窮。如果社會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標準和道德目標,那么社會安全感和信任感就會喪失。人們在面臨行為選擇和價值評判時,缺乏明確的道德價值目標,道德評價標準混亂,導致道德追求上失去方向感。社會轉型過程中,原有的道德體系受到沖擊,新的道德價值目標尚未建立,從而出現道德滑坡的現象,使得公眾在人們思想上不知所措,行動上無所適從。
轉型期由于社會思想多元化,容易引發文化沖突與失范,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能力隨之下降,就無法從整體上調整文化秩序。當文化的發展遭遇逆向的否定、限制、消耗,文化生態喪失多樣性、趨向單一化,文化傳播過程中出現信息缺失時,就會存在系統性的文化風險。文化風險是一個多面體,包含多個層面、維度和層級。轉型時期,文化風險激發了知識分子在精神危機爆發時對各種文化問題的反思與檢討,因而重拾人文精神成為轉型過程中的時代責任。在新的時期,文化領域中凸顯出新的危機,提出了諸多新的挑戰,呼喚文化創新與文化創造以適應新的形勢。
三、社會焦慮的文化價值根源
社會焦慮既是當代中國轉型期典型的社會心理狀態,又是無法回避的社會心理問題。*于建嶸:《社會焦慮:當代中國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黨政視野》2016年第8期。當前,社會焦慮現象以各種形態表現出來,彌漫并散發著一種比較普遍的焦慮情緒,幾乎覆蓋了中國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類群體,某種程度上講,現今我們已經邁進了“全民焦慮”時代。
關于社會焦慮的影響因素,學界一致認為,當前社會焦慮的彌漫與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有密切關系*周曉虹:《焦慮:迅疾變遷背景下的時代癥候》,《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在急劇轉型的過程中,社會經濟整體利益結構發生了全方位、大幅度的調整,原來的社會結構重新調整并建立新的秩序和規則。*吳忠民:《中國為何彌漫著社會焦慮》,《學習時報》2011年6月13日。不同的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結構失衡,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社會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社會風險增大,致使社會成員普遍產生了“被剝奪感”、不公正感、缺乏安全感等社會心理特征,這均是社會焦慮的根源。然而,除了物質因素,伴隨社會的急劇轉型,人們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觀念等非物質因素的變化、沖突也是產生社會焦慮的重要根源。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沖突與文化失衡致使公眾心理普遍存在焦慮情緒。由于價值多元化,新的價值觀念與傳統價值觀念的沖突碰撞導致的價值焦慮,使主流的價值觀受到嚴重沖擊,失去了人的存在價值之根本,從而因其存在之價值受到威脅而產生焦慮。*倪稼民:《靈魂棲息何處——中國式社會焦慮之文化根源》,《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7期。
本研究采用課題組自編問卷,通過“問卷星”平臺,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問卷調查,系統研究當今中國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焦慮狀況,以及文化價值因素對社會焦慮產生的影響,進而提出有效緩解中國轉型期社會焦慮的有效措施。問卷調查共收回問卷4326份,剔除無效問卷,得到有效問卷4293份。數據采用SPSS20.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一)當前我國居民社會焦慮的基本狀況
課題組首先對全民社會焦慮程度進行了分析。統計結果顯示,認為社會焦慮程度嚴重和非常嚴重的居民分別占所有調查人數的36.3%和12.6%,認為社會焦慮不嚴重和一點不嚴重的居民僅占9.9%。這表明,總體上,我國居民社會焦慮嚴重程度處于“一般”到“嚴重焦慮”之間,屬于比較嚴重的狀態。這一研究結果與以往研究成果得出相似的結論。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34.0%的受訪者經常產生焦慮情緒,62.9%的人偶爾焦慮,只有0.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焦慮過。*謝小亮:《相比五年前47.8%的人“更焦慮了”》,《中國青年報》2006年12月4日。人民論壇社會調查中心對社會焦慮程度進行調研,調查顯示, 65.5%的受調查者選擇“4—5分”,自認焦慮程度較深;25.6%的受訪者選擇“3分”,認為自己比較焦慮;7.2%的人認為自己“不太焦慮”;僅有1.7%的人認為自己“不焦慮”。*張瀟爽、徐艷紅:《當前中國人為何焦慮,焦慮程度幾何?》,《人民論壇》2013 年第9期。眾多的研究數據表明,多數人處于深度焦慮之中。
另外,課題組還調查了居民對當前社會中焦慮情緒的感受和認知。當問及是否贊同當前社會是“人人存在焦慮情緒的社會”時,有51.25%居民贊同這一觀點。這就表明當前我國民眾能夠切身感受到社會焦慮情緒的存在和困擾,對社會焦慮情緒有比較強烈的感知,平時,大家也經常用“壓力大”“心里煩”“很糾結”表達自己的心情。
(二) 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焦慮水平
對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焦慮水平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發現,不同性別、不同年齡段、不同地域和城市、不同收入水平的社會群體之間的社會焦慮水平未達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水平,即不存在顯著差異。這一研究結果充分證實了以往學者的研究結論,即當前我國的社會焦慮不是個體現象,也不是某一類群體的獨特表現,而是廣泛彌漫于大多數社會成員之間。這充分表明,我國轉型期社會焦慮彌漫性、普遍性的特點。然而,具有顯著社會文化背景特征的居民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以及從事職業等因素,對焦慮水平卻存在顯著影響。
1.不同受教育水平居民的社會焦慮水平
對不同受教育水平居民的社會焦慮狀況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受教育水平居民的社會焦慮均值之間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F=6.251,P<0.01)。進一步事后檢驗發現,初中以下組的社會焦慮均值最高,明顯高于其他三組的平均值,其他三組兩兩之間不存在差異。這就表明,初中以下組居民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焦慮非常嚴重的人數比例要比其他組高很多。這也許與他們的工作環境和生活閱歷有很大的關系。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對勞動者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的要求就越來越高。文化水平較低的勞動者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就業環境相對較差,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因此,他們的生活壓力就會更大,感受到的社會焦慮更加強烈。
2.不同婚姻狀況居民的社會焦慮水平
對不同婚姻狀況居民的社會焦慮狀況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結果顯示,未婚組和已婚組的社會焦慮平均值均顯著大于其他組(F=9.173,P<.001),其他組包括婚姻狀態是離異或喪偶的群體。這個結果似乎出乎通常思維,按照社會學大多數研究的思維慣性,認為出現過婚姻變故的人,比離婚或者喪偶的人更加體味到人生的坎坷經歷,會更加焦慮。然而,本次研究的結果更是耐人尋味。從五個組的平均數來看,無論未婚,還是結婚,包括再婚人群,其社會焦慮平均分均顯著高于離婚或喪偶未再婚的人群,進一步事后檢驗也驗證了這一點。似乎說明從未步入婚姻殿堂的人有很大的社會焦慮感受,在婚姻中的人也被社會焦慮情緒困擾很多,反而那些經歷過婚姻又回到單身狀態的人更加灑脫和釋懷。雖然這個結論有點有違常理,但也許這就是當前社會階段中國民眾的婚姻狀態的真實反映。婚姻帶給人們幸福和歸屬感的同時,帶給人們的壓力和困擾并不比單身時少。這個研究結論應該引起家庭婚姻方面研究者的關注。
3. 不同職業居民的社會焦慮水平
對不同職業群體的社會焦慮程度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顯示,從事不同職業的民眾之間在社會焦慮程度方面存在非常顯著的差異(F=2.392,P<0.01)。具體來看,失業下崗人群的社會焦慮程度最嚴重,而黨政機關處級以上干部(含處級)這一群體的社會焦慮程度平均分最低。這就表明黨政機關尤其是級別比較高的干部人群較少受到社會焦慮情緒的困擾。進一步多重比較結果顯示,非常顯著的差異性檢驗出現在黨政機關處級以上干部(含處級)群體與幾乎所有職業類別之間(PS<.05);下崗失業群體與其他所有職業群體之間的差異均具有顯著作用;除此之外,其他職業群體之間均沒有顯著差異。這個結果充分表明,各級政府必須關注下崗失業人群的生存和生活狀況,守住底線,把弱勢群體、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做到萬無一失,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環節。
(三)社會焦慮的文化根源
調研發現,影響當前我國居民普遍焦慮的社會因素主要體現在事關人們的生存生活的物質利益和基本社會保障方面。物質利益是人的生存之本,沒有物質利益的滿足,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人們會陷于焦慮之中。社會轉型時期,各利益結構之間出現了不平衡,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個人發展機會不平衡以及權力濫用現象,從而使人們心理上產生“相對剝奪感”*吳忠民:《社會焦慮的成因與緩解之策》,《河北學刊》2012年第1期。,由“相對剝奪”問題引發的社會焦慮非常普遍。
社會文化因素也是這個時期引發社會焦慮的一個重要來源。社會文化因素主要是指精神層面上的,如理想信念、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民族心理以及宗教信仰等等。焦慮是人的生存之本受到威脅的一種精神狀態,生存之本不僅包括生命生存的物質需求,也包括價值需求。當人們的價值需求得不到滿足或者受到嚴重威脅時同樣也會產生焦慮。在現代社會,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多元價值觀的沖擊,世俗化成為一種時代印記,鐫刻在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導致文化藝術世俗化、價值觀念世俗化、道德信仰世俗化,等等。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變得越來越趨向于現實性、理性化,逐利心理嚴重,“活在當下,享受現在”的心態非常普遍,導致現代社會信仰缺失和道德滑坡現象頻頻出現。道德與信仰的普遍缺失嚴重威脅到了人們的生存之本、價值之本,導致社會焦慮。
四、舒緩當前社會文化焦慮的有效措施
普遍的社會焦慮是中國轉型時期重要的社會心理特征。社會焦慮是一種負面情緒,且極具傳染性和蔓延性,對轉型時期的社會矛盾具有催化作用*吳忠民:《社會焦慮的負面效應及其應對》,《傳承》2012年第1期。,容易激化原本不嚴重的社會矛盾。對近幾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進行剖析發現,焦慮情緒的傳染在事件演化過程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另外,社會焦慮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情緒,其負面效應還體現在降低了人們的幸福感,不利于社會成員的心理健康。*邢占軍:《焦慮之下的幸福指數》,《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7期。一個長期處在焦慮狀態的個體,在自我認同上會出現問題,很難體驗到幸福感。如果一個社會長期彌漫著焦慮心態,這個社會的幸福指數也只能停留在較低的水平。近年來一些實證研究發現,一些國家和地區現代化水平和其民眾幸福指數水平不完全同步,社會精英的焦慮水平并不比一般社會成員低,這足以證明社會焦慮的復雜性。
轉型時期,人們的公民意識、政府和國家觀念都發生了改變,既不推崇原有傳統的價值觀念,又沒有形成新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價值體系,價值出現多元化、個體化的趨勢。并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民眾的權利意識增強,平等意識增強。*王俊秀:《社會心態:轉型社會的社會心理研究》,《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1期。價值觀多元,從而缺乏基本的、大家共同堅守的核心價值觀念,社會互信出現阻礙,社會共識難以達成。*王麗萍:《中國轉型期社會焦慮問題的研究現狀及展望》,《理論學刊》2011年第10期。一個社會如果在基本問題上缺乏共識,就會有普遍持續的焦慮,就會面臨出現極端主義思潮的危險。當前,防范極端思潮、增加社會共識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增強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文化能洗滌人的心靈,能使人褪去煩躁,歸于平靜。
第一,要形成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圍。建立以中華民族創造的優秀傳統文化為核心的多元包容文化,以革命文化和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為供給養分,全體社會成員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形成因包容“不同”而和,因和而達到“大同”的文化氛圍。當然,在構建多元包容的文化之時,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多元之上有一元的靈魂,堅持辯證的觀點,防止陷入片面的“文化寬容精神”,不同之上追求的是大同理想,這是中國先進文化的本質要求。
第二,要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堅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加強心理疏導和人文關懷,引導社會成員正確對待困難、挫折和榮譽,正確看待自己、他人和社會,注重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健康向上、豁達從容的健康心理。
第三,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要注意如何有效地培育和踐行,不要讓核心價值觀“飄在天上,停留在紙上”,注重把它融入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日常行為中,從兒童抓起,從教育中灌輸。從基本公德的遵守開始,在民眾中逐漸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實現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
在轉型期的時代背景下,社會焦慮不僅僅是一個心理學概念,我們更應關注社會焦慮現象背后隱藏的社會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等。社會的變遷必然帶來社會心理環境的變化,社會結構調整更是形成了巨大心理沖擊。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環境等各個領域均取得了巨大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顯著改善和提高。特別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更是取得了歷史性的發展和進步。然而,社會心理建設嚴重滯后,隨著社會的轉型,人們的社會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多元化的價值觀沖擊著人們的心理,人們的內心產生強烈的心理沖突,各種情緒的糾結、焦慮涌入心底,降低了人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人們在享受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時,總覺得沒那么快樂、幸福、充實。因此,要正確認識轉型期社會焦慮的特點及其焦慮原因,把緩解社會焦慮的對策措施與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結合起來,共同努力,營造良好的心態環境,緩解當前的社會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