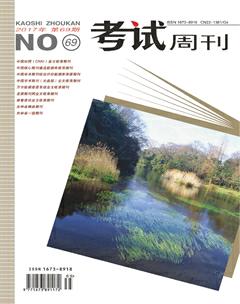赫爾巴特教育思想在中國
劉衡??
摘要:我認為赫爾巴特的思想對于當代教育仍有其重要的現實價值。隨著現代的素質教育觀念深入人心,使多數教育者忽視了赫爾巴特所代表的所謂“傳統教育”思想。究其根本原因,是受到了時代歷史背景不同、傳播途徑受限和學習不足的影響,阻礙了對赫爾巴特思想更有效的利用和更科學的評價。
關鍵詞:赫爾巴特;中國;歷史背景
作為“教育科學之父”,科學教育心理學的奠基者,是第一個明確提出“教育性教學”的思想的人。赫爾巴特的道德教育思想十分豐富,在全球的近代教育史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將從歷史背景的角度分析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想,把其傳入中國作為切入口,來表明其教育思想在今日仍然有很大的借鑒和參考價值,對如今的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的發展仍有非常巨大、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
赫爾巴特教育思想進入中國的背景源于洋務運動的興起。那時中國的舊教育體系正在向外求學,急需現代教育思想鮮血的注入。連續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使中國的近代新教育在外部多種因素的沖擊下產生了萌芽。如洋務運動下的新式學堂、教會學校等含有歐美教育內容和方法的新式教育機構被大量引入,中國教育近代化開始由此起步。但是由于不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學術界都僅僅是抱著“拿來主義,實用價值至上”的態度來運用,并沒有真正從深層次的理論是去理解其精神內涵和思想精要,就導致全民對赫爾巴特的“淺理解”,成為后來大眾誤解其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拋開赫爾巴特思想不談,從理論層面是分析知識在舊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傳統。
當時在亞洲作為變革先行者的日本正在迅速地進行現代化和歐美化,接受了許多近代化的教育思潮,在保留自我民族性的同時,大力學習新式教育思想,赫爾巴特的教育理論被視若珍寶,大量轉譯進行實踐運用。很多中國人都把鄰居日本成功的現代化部分歸因于接受并成功運用了西式思想教育,況且一直相愛相殺的中國和日本無論是在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還是社會人文等諸多方面均有相似之處,因此,在中國開始涌起一股向日本學習的思潮。在此時代背景下,通過日本向引進學習,以赫爾巴特思想為代表的各種著作開始快速大量的進入渴望變革教育的近代中國。但當時赫爾巴特的各種著作多數都是經過日本的和式改造,赫爾巴特那原本濃重的“個人教育學”風格已經無影無蹤了。這極大地阻礙了中國對赫爾巴特教育理論本身的分析和研究,使我們無法清晰認知其思想全貌,甚至會導致和真理的擦身而過。
由于開始引進赫爾巴特思想的時候,我國抱著拿來主義的實用目的,這也為后來杜威思想在中國的流行開來打下了思想基礎。相對于赫爾巴特的“科學教育”杜威流派更偏重于教育的實用價值,他嚴厲批判了以赫爾巴特為代表的傳統的學校教育,并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和“學校即社會”的教育本質論。比起赫爾巴特,信奉實用主義至上的中國更愿意相信杜威學說的真實性和實用性。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描述了對赫爾巴特思想的定位:認為赫爾巴特思想是為傳統教育思想的代表,其“以教學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的思想充滿弊端,忽視了學生主體。杜威主張教學應該以學生為主,圍繞學生,把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作為首要任務,而不是重點關注教師的教學方法。于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學在中國順理成章地迅速發展,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漸次地取代了赫爾巴特學派的主流地位,風靡于中國教育界,赫爾巴特的思想則漸漸地被忽視。
時至今日,在許多人眼中,赫爾巴特的學術流派代表了傳統教育學派,而杜威的思想則被劃歸為現代教育學派,但是事實真如此嗎?兩者真的不可兼容,站在了矛盾的對立面嗎?事實上,諸多研究資料都已經表明,赫爾巴特與杜威對應的時代背景不同,接觸到教育實際情況不同,因此他們必然擁有很多不同的教育思想,要從不同的思維層面考慮同一問題。也許乍一看,兩者的思想有很多不同之處。但是教育作為一門思想哲學,本身是具有歷史性和繼承性的,因此我們也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發現兩者的教育思想也有諸多相同之處。比如,他們都重視教育的目的性、服務性和社會性,看中培養人的道德素養,對教學的內容、過程、方法都進行了深入探究。總而言之,兩者都同樣重視教師與學生、系統知識與個人經驗、課堂與活動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針尖對麥芒,不可調和,兩者仍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共性。
如今縱觀我國教育學界,許多人對于赫爾巴特的思想認識仍然只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在往往對其知之甚少的前提下,單純地將赫爾巴特思想視為“老古董”和“舊派”,并且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我國教育界,很少有針對赫爾巴特思想的深入研究資料和文獻,我們僅能從一些泛泛介紹的書上對其思想進行學習和感知,這就導致了信息不對稱,只能讓我們被動的接收主觀的信息,對大眾正確評價其思想產生了極大的阻礙,這也成為導致其思想不受到重視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隨著進步主義教育思潮在全世界各地興起,赫爾巴特代表的教育思潮及赫爾巴特學派的影響也許逐漸衰落,慢慢被忽視,但是赫爾巴特本人曾說過,“任何時代都有它的時代局限。在這個時代中,教育學家都和其他的任何人一樣,同這個時代的思想、發現、嘗試和從中得到的經驗是分不開的”。同樣,我們應該認識到在現代教育的摸索中,其思想本身的局限性是難以避免的,但這并不影響其思想的光輝照亮繼續前行者的路,感知經典,總能幫助后來者成就更多。
參考文獻:
[1][德]弗·鮑爾生,滕大春,滕大生譯.德國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田正平.中國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3]侯懷銀,祁東方.赫爾巴特《普通教育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J].教育實踐與研究,2007(10).
[4]李其龍.赫爾巴特文集·教育學卷第1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王有亮.赫爾巴特并未忽視學生的主體作用[J].教育理論與實踐,1992(2).
[6]馮夢云.一盎司經驗,勝過一噸的理論[J].2012.
[7]賀國慶,劉向榮.赫爾巴特教育心理學化的理性分析[J]教育學報,2006-10-25.
[8]約翰·杜威.互動百科.
作者簡介:
劉衡,山東省青島市,山東科技大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