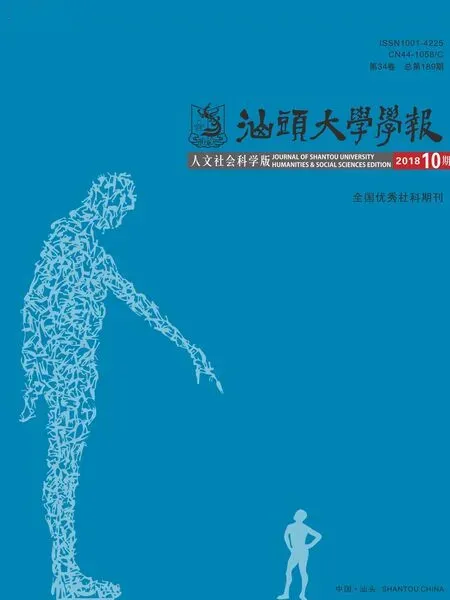個人在場的信仰與充滿荒原意識的救贖
——論徐則臣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兼及一種代際意識寫作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875)
一、作為遠景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主人公初平陽是一位專欄作家,他在《京華晚報》開設了名為“我們這一代”的專欄,主要討論70后一代人的成長。整部小說的副文本就是由初平陽的十篇專欄文章構成。其中第一篇文章《到世界去》,也是徐則臣的一部散文集的名字。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初平陽講述了一個具有寓言意味的故事。即在一個通有火車卻不停靠的小村莊里,人們為了坐上火車,到外面的世界,采取了各種極端的方法。其中一位年輕人在火車開來時悶頭往前沖,以求火車能夠停下來,載他到外面的世界。結果火車停下來了,年輕人死了,其他人繼續想著“到世界去”的問題[5]32-33。這個看似荒誕的故事,其實仍然是一個有關現代的寓言。在這個寓言里,火車作為最為關鍵的物象和載體,連接著小村莊和外面的世界,承載著村民對現代的想象。而外面的世界寄寓著村民超越此在空間,想象現代的渴望。于是,“到世界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到有別于自己所處的當下世界的另一個世界去。在到外面世界的過程中,作為行動主體的人完成了超越此在空間的移動。與空間移動相隨而生的是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即內心世界也將得以重塑。對這一層面的“到世界去”,徐則臣曾有過這樣的表述:“所謂到世界去,指的正是,眼睛盯著故鄉人卻越走越遠。在這漸行漸遠的一路上,腿腳不停,大腦和心思也不停,空間和內心的雙重變遷構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6]2然而,如果考慮到這一故事本身的荒誕性,并且結合小說中傻子銅錢到世界的沖動。那么,“到世界去”可能將會有另一番解釋。小說中,初平陽和銅錢有一次關于“世界”的對話。初平陽問銅錢:“你想到世界的哪個地方去?”銅錢說:“到世界的世界去”,“就像你一樣,遠得幾年不回來一趟家。”[5]23從銅錢的這一回答中,很容易發現在銅錢的意識里,世界是模糊的,無法確認的,更是無法命名的。這就如有的論者指出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具體所指的帶有寓言性、形象性和虛擬性的無法真切感知和現實確認的空間。”[4]因此,由傻子銅錢的意識里所傳達的“世界”一詞,便不再具有一種“現代”意味。而“到世界去”,也不再是一種追求現代的主體實踐。它毋寧是一種不由自主的沖動,一種個人無法控制的歷史進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初平陽說的“‘世界’從一個名詞和形容詞變成了一個動詞”[5]27這句話才具有說服力。
當“到世界去”不僅是一種超越此在空間,想象現代,追求現代的主體實踐,更是一種個人無法控制的歷史進程時。這就意味著,所有人都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受到這一歷史進程的影響。自然,徐則臣京漂小說中的人物也參與到了這一“到世界中”的歷史進程中。只不過,對于京漂人物而言,他們的“世界”是一個可以現實確認的空間——北京。但是,在《耶路撒冷》中,北京對于初平陽、易長安和楊杰這些從故鄉花街出走的主人公來說,已經是他們生活的當下世界。并且,北京已經失去能夠激發他們重新想象世界的能力,他們在北京也沒有獲得“心安”。考察他們“心不安”的原因,當然可以沿用解讀京漂小說人物的方法,在小說人物面對生活創傷和精神困境時,以物質生存的角度作為進入其內在世界的路徑。但是,應該注意的是,徐則臣在《耶路撒冷》中已經超越了底層敘述,力爭從整體上來把握70后一代人的成長史。小說塑造了多個不同階層的人物,初平陽是專欄作家,秦福小是電梯工人,易長安是偽證制造者,楊杰則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如果說初平陽和秦福小還能納入到京漂小說中的底層青年的人物譜系里面,那么易長安和楊杰則很難再說是從故鄉小鎮到北京的都市底層知識青年了。因為他們已經掙脫了底層,成為可以掌握和支配一定社會資源的成功人士。所以,徐則臣在《耶路撒冷》中超越底層敘述的方式無疑為我們理解這些花街少年“心不安”的原因增加了難度。
然而,隨著小說故事的逐漸展開,我們會發現景天賜之死是他們所有人內心無法跨越的一道坎。由于少年玩伴景天賜的死多多少少和他們都有著某種關系,這使得他們在內心深處對景天賜懷有一種負罪感。這種負罪感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發生的當下時間距離景天賜死已經19年)和空間的變遷(他們大多早已離開花街,在北京闖蕩多年)產生弱化的趨向。相反,它像一部無聲電影反復地在他們的回憶中出現,加重了他們各自內心的罪感。正如小說中所說:“在這個細節越發瑣碎和詳盡的下午,天賜死了。他的死經過無數夢境的增補和修復,已經超越了現場真實,因為福小站在他十五米之外的地方,但在夢里卻如同在眼前一般,最微小的死亡細節都不曾被忽略。”[5]132他們遭遇的這種情況就像有的論者所說,景天賜之死使得他們進入到一個閉合的倫理時間中。盡管物理時間一直在往前走,他們從花街少年成長為漂在北京的異鄉人。但是,倫理時間卻是一個閉合的圓圈,他們找不到出路。[7]34因此,可以說,從景天賜死之日開始,初平陽們就遇到了一個倫理性的困境。因為始終無法解決這一倫理性的困境,才使得他們即便身在北京,有的已經是成功人士,內心依然常懷不安。不過,19年來,他們一直都在試圖解決這一倫理困境。對于初平陽而言,他的方式便是到世界去。只不過,這次“世界”的現實確認空間不是北京,而是耶路撒冷。值得玩味的是,盡管耶路撒冷是讓初平陽感到心安的地方。但是,在整部小說中,耶路撒冷始終是作為當下世界的遠景而存在著。到耶路撒冷去,這一行為的行動主體初平陽到小說結尾也沒有走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于是,“耶路撒冷”在小說文本中是以一種將來時態呈現出來的。“耶路撒冷”這一獨特的呈現方式,在有的學者看來頗有意味,它使得“其承擔的是對當下的批判功能”。[8]這種看法無疑是有道理的,因為有了“耶路撒冷”這一遠景的存在,也就等于有了一個可以衡量、質疑、反思,甚至批判當下世界的參照物。而對于任何一個嚴肅生活的人,重要的不是逃離當下世界,而是反思自我的歷史。只有在充分地認識自我的基礎上再次出發,才會顯得更為堅實有力。徐則臣顯然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他會說:“我愿意從最樸素的立場上去理解人,希望為他們找出來路。對我來說,來路比去路更重要,‘不知生,焉知死’,不知來路也就很難找到恰切的去路。”[9]
具體到《耶路撒冷》這本小說,徐則臣運用了五四以來的“歸鄉模式”,按照“出走-返鄉-再出走”的敘述邏輯展開初平陽們尋找來路與去路的主體探索,敘述重點則放在初平陽們對故鄉的認識和體驗上。而自魯迅在《故鄉》中開創這一模式以來,無論是作為“需要被改造和放逐的空間”,還是作為“精神家園”或者“內在家園”,故鄉都不再是“原初”意義上的故鄉,它作為一種“故鄉”想象,被賦予了諸多的意識形態色彩[10]。因此,在“歸鄉模式”的敘述中,所有的“返鄉”往往都是為再次“離鄉”做準備的。初平陽的“返鄉”同樣如此,并且他對“返鄉”也有著自己獨特的認識。在專欄文章《夜歸》中,初平陽寫有一段歸鄉人的心理獨白:“他在想著自己與這個時間、這個地方產生的古怪關系:故鄉,老家,父親,母親,走出來又回來,彈指三十七年。他想著因為這些,他把一個陌生的女人和一個陌生的孩子帶到這里,被迫停在半路上成了有家難歸者。本來扯不上關系的人和事,此時此刻相互建立了嚴格的邏輯。這就是一個人的出處,你從哪里來,終歸要回到那里去,所以你才是你”。[5]147-148在這段心里獨白中,歸鄉人對故鄉的情感認同經歷了一個由模糊(“古怪關系”)到清晰(“嚴格的邏輯”)的過程。對故鄉的情感認同過程,也是一個人的自我確認過程,確認自己生命的來路(“你從哪里來”)和歸途(“回到哪里去”)。如此,歸鄉人在返鄉的過程中尋找到一條與故鄉、歷史、時代、自我進行對話的途徑。從歸鄉人的返鄉結果來看,初平陽認同通過返鄉找到確認自我,以及和故鄉、歷史、時代進行對話的途徑的有效性。只不過,對于初平陽和他的花街少年們來說,這種對話是通過回憶完成的。當初平陽們一個個從北京回到花街,就意味著他們已經開始回憶了。在回憶中,花街的歷史、父輩的歷史、自我的歷史重新浮出日常化生活的地表,提供他們反思與確認自我成長的機會。因此,對于初平陽們來說,回憶就不是一種虛構,而是對自我的一種正視,更是對生命意義的重新想象和建構。從這個意義上講,故鄉就是一把打開記憶之門的鑰匙,返鄉之旅就是一次天路歷程,它召喚起初平陽們對人與歷史、人與時代關系的思考,同時指向存在意義的探尋。
問題是,經由返鄉而激發起來的回憶最終是需要落實在具體的文化地理空間上的。對于初平陽們來說,承載著他們回憶的文化地理空間就是淮河、花街、大和堂。然而,正如費孝通所言:“事實上完全靜止的社會是不存在的,鄉土社會不過比現代社會變得慢而已。”[11]95在《耶路撒冷》中,花街經過30年的改革和發展,已經不再是《憶秦娥》《鴨子是怎樣飛上天》《花街》中的花街,它早已不是鄉村,它是淮海市的城區;它更不再是一幅江南水鄉圖,而是經濟發展主導下的“眾聲喧嘩”。生活在花街上的人也不再是《花街》中的老默,《傘兵與賣油郎》中的范小兵,《水邊書》中的陳小多,代替他們的是文化局魯局長和房地產商周至誠。正是在他們的主導下,可以為了一個莫須有的歌姬翠寶寶建立紀念館而拆除民居,甚至產生毀掉有百年歷史的斜教堂的計劃。也是在他們的策劃下,淮海市一座有著五百多年歷史的廟宇慈云寺被改造成為燈紅酒綠的會所,成為商界名流的樂園。這種為了經濟發展,不惜毀掉烙有一個城市記憶的文化地理空間的做法,讓初平陽感到“悲哀”“清寒”和“悲苦”。[5]442-443因為,隨著這些文化地理空間面目模糊的加劇,初平陽們對于故鄉的記憶將再也無法得到物象的印證。這使得他們感到自己雖然返鄉,卻并沒有覺得自己是身在故鄉,“這些天在街巷里走”,“我經常覺得這地方跟我沒有關系;她不是我的故鄉。”[5]486也就是說,他們成為了故鄉的“異鄉人”。在學者江飛看來:“‘異鄉人’(‘城市異鄉人’與‘故鄉異鄉人’)不僅是初平陽或徐則臣等‘70后’一代人的身份標簽,更是新舊價值更迭的‘過渡時代’中的大眾不得不承受的精神認同與身份認同。”[12]當“異鄉人”成為初平陽們“不得不承受的精神認同和身份認同”,一個隨之而來問題便是,既然承載著自己記憶和歷史的文化地理空間變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既然自己無論是在精神認同和身份認同上,都處在一個懸浮的狀態。那么,初平陽們依靠什么回到自己的歷史?畢竟對于他們來說,只有先回到自己的歷史中,認清自己的來路,才能重新出發,到世界去。顯然,在敘述故鄉文化地理空間被一種非健康的發展方式改寫后,徐則臣凸顯了初平陽們回到自我的歷史和到世界去的雙重困難。而此時,應該考慮的是,對于70后來說,何為歷史,何為他們的歷史!
二、個人在場的信仰
學者洪治綱先生曾這樣描述7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成長歷史:
他們的童年啟蒙都處在新時期,政治批判運動和革命理想主義已遠離了他們的精神視野,代之而起的是不斷規范化和科學化的知識譜系。因此,在他們的作品里幾乎沒有歷史記憶,更看不到歷史與個人的內在沖突,因為在他們的童年心理結構中,根本就沒有歷史的重負。當他們步入少年之后,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和日趨多遠的文化格局,使他們完全擺脫了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規約,并逐漸形成以‘個人’為中心、注重個人感受的生存理念。尤其是隨著九十年代之后社會轉型期的到來,物欲化、利益化的生存現實不斷加劇,某些后現代的消解策略也隨之興起,這又使得正處于人生定型期的他們越來越親近欲望化、時尚化、市場化的現實景象,而對形而上的理性思考更趨淡漠,對社會整體進程的宏觀體察也更加疏遠。[13]18
按照洪治綱的這一描述,70年代出生作家群與歷史的關系可以概括為“歷史”的“缺席”和“歷史”的“在場”。所謂“歷史”的“缺席”,指的是70年代生人沒有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大歷史產生交集。因此,現代中國革命以及在此革命中形成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和理想主義情懷也就失去參與70年代生人身心建設的機會。正是在此意義上,徐則臣認為“‘70后’是缺少‘歷史’和‘故事’的一代人”。[14]而所謂“歷史”的“在場”,則是指70年代生人完整地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這30多年的中國大轉型、大變革的過程。他們的身心建設受到這一轉型期歷史的深刻影響,“人們的心理和情感,人們理解世界和處理自身命運的方式完全改變了”。[15]從這一角度上講,徐則臣指出了70后“這代人從出生到成長的時間所發生的歷史的拐點”“無限的密集”,并且“每一個拐點都很重要。”[7]29
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軍方宣布 “自3 月 9 日 24 時起實施軍隊巡邏。 凡破壞公共秩序和妨礙市內正常生活者,一律扣留,并送民警局追究責任。”[6](P212)3 月10 —11 日,軍隊在市內加強了巡邏;各級黨組織紛紛召開維穩大會;各工廠企業安排了夜間值班;部分破壞者和挑唆者陸續被克格勃抓捕。這些“組合拳”式的措施采取之后,市內秩序逐漸趨于穩定。[6](P210)
徐則臣對70年代生人與歷史的關系的辯證認識,必然會影響到他對70后一代人成長經驗的書寫。在《耶路撒冷》中,徐則臣首先肯定了70后與歷史的在場關系,寫了很多中國大轉型期的歷史事件,包括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等等。70后一代人是這些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與見證者,不管個人與這些歷史事件處于什么樣的關系場域之內,它們多多少少都曾經切實地影響著70后這一代的現實處境。但是,徐則臣并不滿足于對大歷史的羅列與鋪陳,他還要追問這些宏大的歷史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如何產生細節上的聯系。在徐則臣看來,如果這些宏大歷史無法和日常生活產生細節上的聯系,它們也就不是一種“本色的,真實的東西”。[7]22也就是說,在徐則臣這里,對于個人而言,真實存在的客觀“歷史”只有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細節的關聯,它才是“真實”的“歷史”。否則,它對于個人是沒有意義的。這就如同阿蘭·巴迪歐在論述“存在”與“事件”的關系時指出的,“事件”最核心的特征是“創傷”[16],缺乏“創傷”的“事件”只能是事實。顯然,在《耶路撒冷》中,構成初平陽們自我歷史的“歷史事件”不是70后在場的中國大轉型期間的歷史事實,而是景天賜之死。因為景天賜之死是初平陽們所有人的“創傷”,它構成了他們“心靈史”最核心的部分。比如,初平陽因為“無法抹掉”“隱瞞的十分鐘”而陷入自責的恐懼之中,以至于“天賜的自殺很快就和影視、小說里的場景混為一談,以致很多年里,直到現在,都見不得文字和影像里的自殺場面”,最后不得不承認自己“繞不開的中心位置肯定是天賜。”[5]246-247同樣,由于認為景天賜用以自殺的小刀是自己送的,楊杰一直為此自責:“他一直喜歡的關羽和他的青龍偃月刀。這些年我都覺得是我殺死了天賜。”[5]298由此可以看出,景天賜之死對于少年初平陽們構成了一個倫理性的困境,它成為他們內心世界的一個幽靈,使得他們的成長時刻面臨著來自天賜之死的倫理挑戰和危機。為了躲避幽靈,克服危機,初平陽們選擇逃離花街。然而,對這一倫理性困境解決的延宕,并沒有消除他們內心的“不安”。為了消除內心的“不安”,初平陽們紛紛踏上返鄉之旅。從景天賜之死對初平陽們離鄉與返鄉的影響來看,它堪稱是初平陽們“心靈史”的最核心的“歷史事件”。在這一“事件”的推動下,形成了初平陽們“心靈史”的基本軌跡。并且,直到小說講述的當下時間,由它所推動的這一關于解決倫理困境的故事仍在進行中。這次,初平陽選擇解決困境的方式是去“耶路撒冷”。
為什么是耶路撒冷,初平陽去耶路撒冷“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哪兒。”[5]238這是賽謬爾教授的疑問。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共同的發源地,它的屬性無疑是宗教的。然而,對于初平陽來說,耶路撒冷并不是一座宗教之城,而是“精神的圣地”:“我知道這個以色列最貧困的大城市事實上并不太平。但對我來說:她更是一個抽象的、有著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這個城市里沒有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爭斗;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教徒,以及世俗猶太人、正宗猶太人和超級正宗猶太人,還有東方猶太人和歐洲猶太人,他們對我來說沒有區別;甚至沒有宗教和派別;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5]502-503在初平陽的這段表述里,“耶路撒冷”從宗教圣地變成了一個單純的信仰之所。于是,在初平陽看來,到“耶路撒冷”作為自己的主體實踐行動,便不是一次事關宗教朝圣的象征性行為,而是對“精神需要突圍和漫游”這一問題的回答,對“尋找一種讓自己心安的生活方式”[5]238-239的探索。因此,它是一個個人的、自由的、日常的行為。而初平陽之所以把去“耶路撒冷”看做自己個人的日常行為,又是出于自己對宗教和信仰的理解:“信仰制度化以后才成為宗教。信仰可以是私人的選擇,而宗教具有集體性和公共性。我只相信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的那部分。”[5]502“也許宗教的儀式需要莊嚴正大,安寧清凈得隨時聆聽到神意,但我以為更需要將信仰給日常化,像水溶于水,進入到最平常的悲歡與哀樂中。不管你心情如何,你都知道,這宗教和信仰最終要成就于我們的,是一個歡欣的世界。”[5]191在這里,初平陽將信仰給日常化了。而初平陽之所以持有將信仰日常化的觀點,又是與他對“耶路撒冷”這一宗教性詞匯的接受即是一個日常化的過程有關。
《耶路撒冷》中,初平陽最初知道“耶路撒冷”來自于對秦環在斜教堂里的“宗教活動”的偷窺:
你們繼續偷窺秦環在斜教堂。在那個暑假,這種偷窺幾乎是常態。秦環陡然放大了聲音:耶路撒冷……
你的耳朵動了動,一個奇怪而又悅耳的音節。“秦奶奶說什么?最響的那幾個字。”
“一路撒凍?”楊杰說。
“是野豬瞎蹦?”易長安糾正。
“要不,是一路瞎蹦?”楊杰也不確定了。
你覺得都不對。憑你的直覺,“野豬”和“瞎蹦”不足以讓你的耳朵動起來。你們蹲下來,在窗戶底下爭論那四個字最可能是什么。爭論半天,楊杰說:
“神經病!就是太上老君又跟咱們有屁關系?爭得一頭子勁兒!”[5]217-218
在對秦環奶奶宗教活動的偷窺中,初平陽無法確認“耶路撒冷”的正確發音,也不能理解“耶路撒冷”的含義,當然更不會知道花街上的老妓女秦環為什么每天要去斜教堂朗誦《圣經》。然而,這一系列的不知道并沒有妨礙初平陽對“耶路撒冷”這一詞匯的喜愛。正如小說中所說:“在你還不懂外語時,在你還不知道它是一個音譯外來詞、代表了什么意思時,在你還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漢字之美時,你已經在驚嘆這四個漢字組合之后所呈現的韻味和美感。美在哪里,你說不清楚,至今也理不出頭緒,但你確信它就是最美的漢字之一。”[5]219因此,對于初平陽來說,“耶路撒冷”對他的吸引力首先不是來自宗教的召喚、歷史的吸引,而是來自這一詞匯的聲韻之美。這種對一個詞匯出于感官的喜愛,無疑是切膚的,也是個人的。即便是后來,初平陽真正發現“耶路撒冷”對自己產生強烈的感召力時,也是基于對秦環一個人的宗教活動的歷史考察來確認“耶路撒冷”之于自我的意義。在《耶路撒冷》中,秦環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物。她在年輕時曾經做過妓女,因為一場瘧疾差點死去,后來沙教士救了她。她為了感恩,就跟著沙教士信了基督教。就是沙教士去世以后,她也會經常到教堂去看看,因為她覺得“沙教士一個人蠻孤寂的,過來看看他”。[5]215所以,秦環最初的信仰基督更準確地說是對沙教士的感恩。她真正開始信仰基督是在“文革”結束以后。在“文革”期間,秦環因為自己曾當過花街的妓女,經常去斜教堂,被認為有傷風化,搞迷信活動而被批斗。為此,秦環遭受了無盡的屈辱。為了擺脫“文革”帶給她的創傷,秦環重新走進了斜教堂,開始了十年如一日的宗教活動。對她而言,信仰基督是她自我拯救的方式,她以此來追求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平靜和篤定。對秦環一個人的宗教活動,作者說:“她一個人的宗教在花街人看來,也許就是一個人與整個世界的戰爭,但她毫無喧囂和敵意,只有沉默和虔誠。她侍奉自己的主。她的所有信仰僅僅源于一種忠誠和淡出生活的信念,歸于平常,歸于平靜。她戴著老花鏡,從目不識丁開始,到死之前無所障礙地通讀了殘存的《圣經》數十次。她也許甚至都沒有想過要把這本書徹底弄懂,她只要安妥和篤定。”[5]227
正是秦環這種將宗教轉化為一種日常信念的信仰方式影響著初平陽對“耶路撒冷”一詞和到“耶路撒冷”一行為的理解。當然,它也影響著初平陽的花街少年們成年后在遭遇精神困境時尋求解脫的方式,比如楊杰。當他對商場上的爾虞我詐感到厭倦時,他開始吃素,生產佛像掛件,希望能夠給紅塵男女帶來平安好運。有意味的是,雖然楊杰和佛教頗有緣分,但他卻從來沒有皈依的打算。他對于佛“只是好,心向往之,沒信,沒剃度的打算,也沒想過做居士。他就是覺得與佛有關的東西讓他內心篤定,身心都清新爽朗。”[5]166因此,楊杰信仰佛的方式與秦環信仰基督的方式一樣,都是將信仰給日常化。這與中國古人所說的“道在日常人倫中”頗有幾分相似。在這個層面講,《耶路撒冷》中初平陽們的信仰方式都是個人在場的信仰。所謂人體在場的信仰,用徐則臣在一篇訪談中的話來說,就是:“信仰是一個泛化的、日常的、個人化的東西。小說里的幾個主人公都沒有去過耶路撒冷,但不妨礙他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座耶路撒冷。它可能是一個地方,也可能是一個想法或者面對世界的方式,或者是實現某種目標的一個途徑。總之它讓你心懷篤定,獲得了生活于世的平衡。”[17]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在《耶路撒冷》中,徐則臣為什么花費很大篇幅來寫塞謬爾教授的上海之旅和初平陽導師顧念章的“文革”經歷。因為,對于賽爾謬教授而言,能夠尋訪父母在“二戰”期間在中國的足跡,可以讓他心安。至于顧念章,作為一個經歷“文革”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只有認識和理解“文革”,才能減輕“文革”帶給他的創傷,獲得生活于當下世界的安寧。由于引進了塞繆爾和顧念章的故事,“耶路撒冷”的含義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它不再僅僅是一個以色列的一個宗教圣城,也不僅僅是一座精神寓所,它更是塞繆爾所言的“一種讓自己心安的方式”。[5]238
三、充滿荒原意識的救贖
在與游迎亞對談中,徐則臣談到“回故鄉之路”與“到世界去”的關系,他說:“‘回故鄉之路’同樣也是‘到世界去’的一部分,乃至更高層面上的‘到世界去’。我們總認為世界在故鄉之外,但當我們心智成熟到一定程度,當我們的閱歷和見解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對故鄉尤其是心靈之故鄉有了全新的認識之后,世界為什么就不能在故鄉之中呢?于堅守故鄉者而言,世界在故鄉之外;對身居世界的游子,故鄉可能就成為真正的世界。”[18]徐則臣的這段話意在說明,對于早已遠離故鄉的游子來說,故鄉內在于世界之中,返鄉之旅屬于“到世界去”這一主體活動的一部分。因為,無論是最初的離鄉還是如今的返鄉,故鄉都是“到世界去”這一行程的原點。只不過,最初的離鄉存在一種將故鄉作為世界他者的傾向。因此,故鄉作為風景在游子的觀看視野里是一處“被放逐的空間”。然而,故鄉作為自己誕生和成長的地方,承載著自己生命的記憶。這使得故鄉不但無法離開自己,反而成為自身需要直面的對象。只有直面故鄉,才能召喚起關于自身的歷史,認識自己生命的來路。在此基礎上,在“到世界去”的路程上才能更加篤定和從容。從這個意義上講,返鄉之旅也就是一次特殊的“到世界去”。而對于《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陽們來說,他們一個個從北京返回到故鄉花街,在對故鄉的重新認識與理解的過程中,他們也對自己個人的成長歷史做了一番梳理,從而發現自己精神困境的原因,并盡各自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自己的精神問題,獲得了在日常生活中的穩妥和心安。但是,當個人獲得了篤定和心安,是否就意味了一代人的問題得以清理和解決。因此,問題應該回到小說中對70后這一代人的書寫上來。
《耶路撒冷》對于70后一代人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初平陽“我們這一代”的專欄文章里。那么,在這一專欄中,作家初平陽都關注著70后這代人的哪些問題呢?從專欄文章的題目來看,主要有以下這些問題:“70后之于神話、權威和偶像崇拜;70后之于歐風美雨;70后之于信仰;70后之于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70后之于物質生活;70后之于新左派和自由主義;70后之于思想資源;70后之于歷史的反思;70后之于城市化的進程;70后之于大事小事;70后之于民族性與全球化;70后之于消費文化等等。”[5]449從列舉的這些問題可以看出,初平陽顯然是把70后這代人作為“問題”來進行研究的。并且,在具體的研究中,初平陽時刻不忘70后這代人與大歷史的關系。因此,認識和理解70后,必須在與歷史的對話中去理解和認識。否則,很難切實地把握這代人的成長特點。正如梁鴻所言:“‘個人生活’,身體、欲望、情感從來都是在與歷史傳統、時代偏見的博弈中顯示出其存在的意義,身體的政治學也不只是欲望的覺醒或自我張揚,而是在自我的文化約束、道德成規與個人要求的掙扎中展示其力量。”[19]15具體到初平陽對70后這代人的認識和理解,主要體現在《這么早就開始回憶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講述了初平陽在一次以70后為主體組成的“回憶者俱樂部”的常規活動上的見聞。這次活動,由西哥的講述,引發了來自各個階層,各個行業的70后的討論。在初平陽看來,這些談論浮出了眾多的關鍵詞:“過去;歷史;童年;鄉村;鄉土;民生;生命;城市化;生存壓力;政治;改革;理想主義;我們這一代。”[5]108值得注意的是,在具體談論到這些關鍵詞時,它們指向的是70后整整一代人。比如理想主義,就是在與50后、60后和80后、90后的比較中,指出70后理想主義的特殊性。初平陽認為70后錯過了“可供無數次反芻的大歷史”和“波瀾壯闊的時光”,但是他們又聽到了“歷史結束的裊裊余音”,這聲音參與了70后的身心建設。這使得他們與50后、60后具有一種精神同構性,“傳承了理想主義”。在這個意義上,70后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義者”。[5]109
在這里,應該關注的不是初平陽對70后理想主義的認識和理解,而是他的話語方式和話語立場。也就是說,作為一個70后的專欄作家,他是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來發言的?顯然,初平陽是站在70后這一代人的立場上發言的。因此,他在談到關于70后的諸多話題中,總是以代際比較的方式來理解和認識70后的獨特性。小說主人公初平陽對70后的代際認同,以及他在言說70后時采取的立場和方式與徐則臣本人基本相同。可以說,小說中的初平陽就是徐則臣自己,在《耶路撒冷》中徐則臣再次運用了自敘轉的模式[19]139-148。而為了證明初平陽“我們這一代”專欄在闡釋和理解70后一代人的有效性,徐則臣在《耶路撒冷》中安排了這樣的情節,即秦福小、易長安、楊杰這些同代人都在一直關注著初平陽的書寫。由此,“營造了一個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存在的意識共同體,讓破碎的、分層化的社會在傳媒文化上實現了想象中的彌合。”“文學書寫擴展了一個無限擴大的共同體,最終的目的才是讓這些四分五裂的人生獲得一個可以共享的精神資源,同時也是在激勵一種被迫的自我反思和尋找。”[20]顯然,這一文學書寫目的也是徐則臣寫作《耶路撒冷》的目的。在《耶路撒冷》中,徐則臣集中書寫了初平陽、秦福小、易長安、楊杰4位身份與階層不同的70后的生命困惑,即如何在生活中獲得“心安”的問題。這個問題顯然不是特屬于70后的某一個人或者某一階層,它指向了是70后這一代人,它是70后這代人需要直面的精神與信仰難題。而徐則臣也正是透過敘述初平陽們在解決自身精神與信仰難題時的實踐行動,為70后這代人的理想主義做出了界定。在徐則臣看來,70后這代人的理想主義的實質是堅守一種個人在場的信仰,是在日常生活中持有一種樸素的生活觀念。從小說中初平陽、楊杰與秦福小的人生經歷來看,這種理想主義精神對于他們自身的心靈困惑確實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由此,初平陽們也就可以作為方法為整個70后這代人解決精神問題指明方向。這一方向就是,70后這代人只要在日常生活堅守著樸素的生活信仰,其內心便會篤定與平安。這便是徐則臣以代際意識來認識70后一代人的心靈困惑之后所給出了解決困惑的方法。顯然,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積極的作用。
但是,這里存在的問題是,或者說應該質疑的是:由代際認同而形成的意識共同體是否能夠回應70后整整一代人在場的社會學問題?固然,在一定范圍內,一些70后以代際認同形成了意識共同體。但是,很多問題未必就能得到解決。比如,作為70后的底層青年的生存問題,就不能得到已經擺脫生存壓力的初平陽們的理解。困擾初平陽們的精神問題也無法回應70后底層青年的生存問題。因此,徐則臣在《耶路撒冷》中以代際的視角來書寫作為整體的70后這一代人,固然通過一個贖罪故事寫出了這代人成長的獨特性。但是,也恰恰因為把70后作為“整體”來書寫,從而沒有寫出置身于30多年的中國改革的70后這代人的復雜性來。因為70后作為一個“整體”,如果從階級和性別的視角觀看,其內部的“景觀”是大相徑庭的。如果僅僅強調70后這代人的同一性,而不考慮他們內在的差異性。那么,對70后這代人任何的“心靈史”的書寫都有可能走向單一。因此,這種“心靈史”的書寫指向的救贖方向與一代人的困境便可能產生錯位感。另外,立足在當下,隱于日常人倫的生活信仰很容易使個人沉浸到自己的狹小生活之中,對有關集體的重大問題失去關注興趣。而如果個人無法超越自己生活的世界,與他人共建一個命運的共同體,那么集體的事物便很難得以解決。從這一角度上講,徐則臣在《耶路撒冷》中關于重建精神信仰的思考,雖然回應了70年代這一代人的成長史,但是卻無法回應都市底層青年的命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