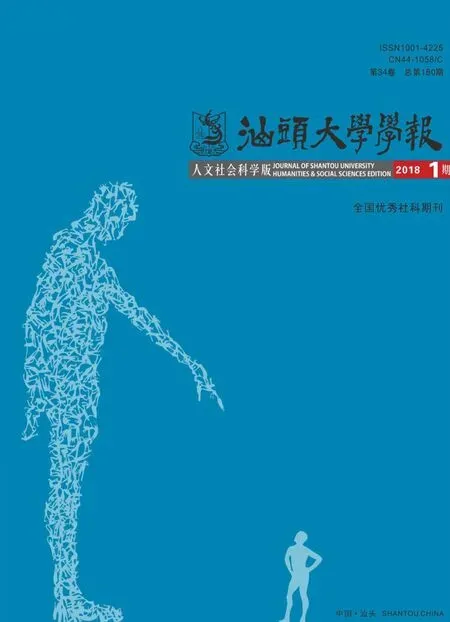著眼于文藝學生態建設的文藝學批評實踐
——讀鄭惠生先生《文藝學批評實踐》有感
易崇輝
(汕頭大學文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一
鄭惠生先生的《文藝學批評實踐》是一本頗為特別的書,也是一項頗為特別的“批評實驗”。其特別之處在于,作者批評實踐的對象,與一般的文藝批評的對象明顯不同,甚至可以感覺到,作者在刻意與傳統的文藝批評的對象保持距離。一般的文藝批評對象,是作家、作品抑或文藝思潮等,而鄭惠生先生著作的聚焦點,卻是作家、作品、文藝思潮以外的方方面面——盡管也與文藝學相關。具體而言,《文藝學批評實踐》的第一章“文藝批評的批評”、第二章“文藝理論的批評”、第三章“文學史的批評”,都可算作是“廣義上的文藝批評”的批評,這跟貫常的文藝批評的對象隔著一層;第四章“文藝學課題、標準和期刊的批評”及第五章“文藝學學術事件的批評”當是對文藝批評的條件、環境的批評,這跟我們理解的文藝批評的對象隔著二層;而第六章“高校文藝學的批評”,則跟傳統的文藝批評的對象隔得更遠些。掩卷沉思,一個強烈的感覺是:《文藝學批評實踐》一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對文藝學學科的“巡視”——對文藝批評的巡視,對文藝批評環境、條件的巡視,對文藝學學科從業人員素質及其培養的巡視,一言以蔽之,是對當下文藝學生態的一種巡視。
著眼于文藝學及其生態的批評,與傳統的文藝批評當然是很不一樣的:傳統的文藝批評對象——作家、作品、思潮等,感性而單一;著眼于文藝學學科巡視或生態建設的批評——對象為整個文藝學學科的諸方面、諸問題,即文藝批評的批評、文藝批評的條件、環境、隊伍素質與培養等等,則繁復得多。鄭惠生先生將前者稱之為“文藝批評”,后者,也是作者倡導并傾力而為的,則稱之為“文藝學批評”。《文藝學批評實踐》一書中踐行的不是“文藝批評”,而是“文藝學批評”,怪不得全書給人一種全新而特別的感覺。
“文藝學批評”,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論倡導,還是作為一種批評實踐,都是全新的。然而,任何新的理論的提出和倡導,都是為了應對和解決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至少也是為了應對和解決新問題的努力。“文藝學批評”理論的提出和批評實踐,不是作者一時心血來潮,異想天開,也不是作者趨時趕潮,花樣翻新;理論的提出和批評的背后,隱含著作者對文藝學生態環境的隱憂和責任。
二
在柏拉圖的《斐德諾篇》中有這樣一個神話故事:奧林匹斯的諸神每天駕著馬車駛向蒼穹的頂端,而人的靈魂尾隨其后。諸天之外是存在的居所,只有到那里,人的靈魂才能觀照到具有永恒秩序的存在之物。可惜,尾隨諸神之后的人的靈魂對永恒存在的觀照只有那么短暫的一瞬,此后他們就墜落在大地上而同真理分離,僅只保留著對這分離的真理的模糊的記憶。人的靈魂中曾與真實的存在有過照面,但只是片刻擁有這些事物的景象,時間短暫,記憶模糊;有些靈魂在落到地面上以后還沾染了塵世的罪惡,忘掉了上界的輝煌景象;更有人每逢見到上界事物在人界的摹本,就驚喜若狂而不能自制,將摹本視作天上的正本,于是,人世間大量堆陳的,自然是錯誤、悖謬、偏執、愚昧。
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討論的是兩千多年前的希臘的情形,倘若他們活到現在,他一定會驚異地發現,人的靈魂在從天上墜落在大地上后,在距他們二千多年后再一次發生了墜落——又從地上墜落到欲望的世界,一個了無理性燭照的黑暗領地。對于蘇格拉底而言,或者說對于柏拉圖的蘇格拉底而言,靈魂是不朽的;而經再次墜落而墮入欲望世界的人卻認為,人無須再回憶上天的永恒,永恒天庭中的“存在”并不存在,甚至人的靈魂也是虛幻的。墜入感性欲望世界的蕓蕓眾生認為,人即人的肉身,人生的意義即是肉身的充實。在肉身枯朽之前,盡可能使它充實、滿足、膨脹,才是人生最大的意義與目標。而能使人欲望不斷得到滿足的,是金錢。于是,欲望與金錢攜手,恣意狂奔。社會拼經濟,個人為賺錢。跟著感覺走,玩的就是心跳,我是流氓我怕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不再是目的,一切都是獲取金錢的手段——不是有一種資源稱之為“人力資源”嗎?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金錢是目的,其它一切都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學界也未能幸免,不僅學術環境、學術條件如課題、期刊等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弄潮,學術批評在日漸浮躁的學術氛圍者中也免不了在隨波逐流了,文藝學界亂象叢生,到處裸露出金黃色。
文藝學的學術生態猶如同時期的自然生態一樣,迅速惡化。文藝學生態失衡之深之廣,甚至更甚于同時期的自然生態。一個沒有靈魂的文藝學,一個視靈魂為虛幻的文藝學,或者用流行的話語說,只有眼前的茍且,不要詩和遠方的文藝學,文藝學何以成為文藝學?像很多學者一樣,鄭惠生先生知覺到文藝學生態失衡的嚴重;與很多批評者不同的是,鄭惠生先生積極開始了他的巡視、批評和批判,以期用他的理性反省和反思,整治、改善、建設文藝學的生態環境。正因為是以建設、整治和改善為目的,所以二十多年來作者秉持的始終是一種嚴肅而冷靜的態度,《文藝學批評實踐》始終也是一種純學術式的批評與反省——一種自覺嚴謹的慎思明辨,一種冷靜深沉的理性思考。至于辯駁文字極難避免的一些現象,如吹毛求疵地挑錯,上綱上線地指責他人,戴帽子、打棍子——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非學術式”的批評——“籠統式、自顧式、偏執式、臆想式、吹捧式、推銷式、捏造式、上綱式、打壓式、謗毀式、謾罵式”,則與《文藝學批評實踐》一書無緣。
再說一點題外話:我一直認為人性不是單數而是復數,感性欲望如飲食男女自然是人性的一部分,理性也理所當然地是人性的一部分,神性也應該是人性的一部分——我們不是都關心“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類問題嗎?不是一直都在追問死后的世界嗎?在人類歷史上,人類先是用神性壓制理性與感性,后來是用理性來排斥神性與感性,現如今,感性欲望又假人性之名而君臨神性與理性了。神性、理性、感性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論用人性的哪一部分壓制人性的另外兩個組成部分,不僅僅是將人性簡單化、單數化,更是對人性的割裂和摧殘,也都會導致學術生態或文藝學生態的失衡。在感性欲望君臨天下的今天,金錢與欲望致使文藝學生態失衡。《文藝學批評實踐》秉持理性的立場與態度,不隨波逐流,這不僅是在維護文藝學的生態與尊嚴,更是在維護人性的尊嚴與完整。
三
《文藝學批評實踐》都是辯駁、批評的文字,但就整個“文藝學批評”理論而言,其學術建構,也即是說,“立”,也是應有的題旨。
經常聽聞這樣的感慨: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學界非常熱鬧,西方數百年的各種思潮、理論走馬燈地在中國上演了一遍。然潮起潮落之后,沙灘上似乎什么也沒留下。確實,僅就文藝學而言,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尼采、弗羅伊德、薩特、海德格爾、阿多諾、弗羅姆、維特根斯擔、福柯、哈貝馬斯、利奧塔、德里達、德勒茲、杰姆遜、羅蒂、伊格爾頓等等都被引進到了中國,各式主義如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都依次登場,各種文學流派如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小說、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新小說派、黑色幽默小說、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垮掉的一代都被推崇和摹仿,各種文藝批評方法如精神分析、直覺主義、符號論、俄國形式主義、語義學和新批評、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接受美學、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都被中國文藝學界所關注。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們的文藝學界顯得異常繁榮、熱鬧。然而,在這熱鬧、繁榮的背后,學界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冷靜的思考:西方的理論、思想、思潮是在西方的社會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他們意欲描述、解決的是西方的社會和西方的社會問題。我們跟在西方的后面,自愿被西方牽著鼻子走,接觸和學習的也是西方的思潮和理論,思考和研究的也是西方的問題。我們緣于中國自己的社會歷史文化的現代理論在哪里?我們解決中國現當社會歷史問題的思想在哪里?當代中國我們自己的文藝理論、文藝批評方法在哪里?簡言之,當代中國自己的學術建構在哪里?我們對于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我們對于我們自己的社會現實,始終缺乏足夠的關注,也沒有足夠的學術信心,更沒有建立起自己有效的學術生長機制。誠然,僅就文藝學而論,近四十年來我們的文藝批評與研究有相當的實績,也有一些原創性的理論思想,但我們缺乏疏理,沒有沉淀,因而也就沒有了真正的學術積累和生長,至于一些可供學術累積和增長的思想,卻幾乎都淹沒在了大量對西學的追逐之中。倘若在文藝學批評中,我們在分析、反省、批判的同時,也分學科進行整理,披沙煉金,找出原創性的思考和思想,疏理出學術譜系和理路,分析其出現的問題及可能的解決方向,則在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的背景下,建立當代中國自己的思想與學術,建構當下中國自己的文藝學體系,則可期可盼。
當然,學術成果浩于煙海,這種基于學術建構和開拓的文藝學批評非短時間可以完成,即便在長時間里,靠一個人或一群人也難以完成。但是,如果有這么一個“文藝學批評”學科建立起來了,結果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應該有理由期待。
鄭惠生先生的《文藝學批評實踐》,致力于打造一個全新的學科,整治和維護文藝學領域的學術生態,我贊賞他的努力。郭德茂教授說他讀過鄭惠生先生的著作后的印象是:無邊的荒原上,遠方有一束光,一個學者從青年到中年,一直踉蹌而執著地朝那束光走去……。我眼前出現的畫面已然是:這位孤寂的學者踽踽獨行中將灑漏在他身上的光亮采擷、聚集起來,然后回過頭來,悉心撒播在他所摯愛的文藝學這片園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