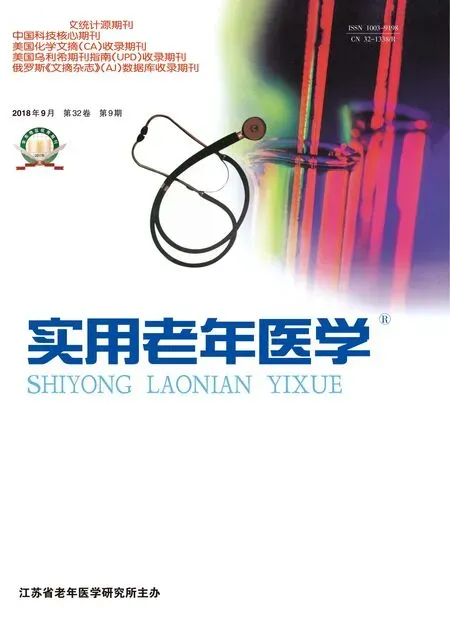住院老年病人衰弱早期識別與評估的研究進展
衰弱在老年人中比較普遍,其發生率隨著年齡增加逐漸升高。有研究表明通過早期識別衰弱老年人并積極給予預防干預措施,可以有效地避免或延緩不良結局的發生[1]。
1 老年衰弱的概念及其研究必要性
2001年美國Fried等[2]首次提出,衰弱是一種重要的臨床綜合征,以生理儲備功能減弱、多系統失調,機體對應激和保持內環境穩定的能力下降為特點,對應激事件的易感性增加。2013年有專家提出,衰弱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臨床綜合征,以力量和耐力減少、生理儲備功能下降、對抗外界應激能力下降為特點,較小的刺激均可引起不良健康結局的發生[3-4]。由此可見,衰弱是由于老年人生理儲備功能及抗應激能力的下降,使其較易發生不良健康結局的一種易感狀態。
衰弱在我國老年住院病人的發生率很高,且隨著年齡增長發生率升高。大量研究顯示,衰弱增加了老年人發生多種不良結局的風險,進而嚴重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降低其獨立性,縮短了其預期壽命,從而增加了社會和家庭的照護負擔[5-7]。
隨著健康老齡化的提出,衰弱漸漸成為了老年醫學研究的熱點,衰弱前期的老年人在18個月內進一步發展為衰弱的風險是正常老年人的5倍。 但醫護人員、老年人及家屬都沒有足夠的重視,仍是過多地關注疾病而忽視衰弱,錯過了干預的最佳時機。因此,衰弱的早期識別和評估對于促進老年人的健康非常重要。
2 老年衰弱的早期識別
早期識別衰弱并給予針對性干預,可以更好地幫助老年人面對衰弱及其相關問題,維持功能狀態和提升生活質量,同時可以延緩甚至逆轉衰弱。一篇納入22篇文獻的系統評價指出,針對衰弱尚未有統一的識別工具,最常用的識別指標包括軀體功能、步速和認知功能,其次是體質量下降、日常生活能力和營養狀況[8]。
2.1 軀體功能 軀體疾病是衰弱的重要危險因素之一,是衰弱綜合征的核心問題,一些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亞臨床問題與衰弱的發生呈顯著相關。軀體功能的準確評估有助于識別衰弱,評估包括:5次起坐時間、3 m起立-行走時間、握力、步速、簡易軀體能力評定(SPPB)。姜珊等[9]發現,衰弱組握力、步速、SPPB評分均低于非衰弱組,衰弱組5次起坐時間,3 m起立-行走時間長于非衰弱組。
2.2 步速 康琳等[10]對153例老年病人,進行老年綜合評估及臨床衰弱量表(CFS)評估,發現步速是衡量衰弱與否的獨立測量指標,步速減慢是衰弱和不良后果的最佳預測指標。6 m步速和6 min步行試驗可用來測量步速,中國人群中尚無明確的衰弱診斷界值,但0.8 m/s的步速界值預示著受試者達到了平均預期壽命,步速每增加0.1 m/s,生存率可改善10%[10]。
2.3 認知功能 認知功能評估采用簡易智力狀態檢查量表(MMSE)。國外已經證實,衰弱與認知功能下降呈正相關,2013年國際營養和老齡學會與國際老年學和老年醫學協會達成“認知衰弱”的共識,即具有身體衰弱和認知障礙兩個特征[11]。認知功能障礙的衰弱老年人功能性殘疾和再入院的風險均增加。
2.4 其他識別指標 1年內出現不明原因的體質量下降>5%,應注意評估是否有衰弱的發生。對于≥75歲老年住院病人,日常生活能力得分與衰弱指數呈負相關[9]。若病人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有部分依賴即進入衰弱期。因此臨床工作中可以借助Barthel指數評分作為識別衰弱的指標。陳凌燕等[12]選取244例老年住院病人,排除干擾因素,發現營養不良及營養不良風險的病人衰弱發生率高。 營養不良是影響老年住院病人臨床轉歸的重要因素,營養不良者更容易出現衰弱狀態。
3 老年衰弱危險因素的識別
衰弱受多因素影響,臨床工作中加強衰弱危險因素的識別,有助于預防及延緩衰弱的發生。
3.1 多病共存 多病共存是老年人普遍存在的現象,≥75歲老年人5種常見慢性病共病率已高達80%[13],是導致老年人衰弱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危險因素。衰弱、共病、失能相互影響,促進發生。
3.2 年齡 隨著年齡增長,衰弱的發生率逐漸增加。姜珊等[9]分析發現,65~74歲老年人中衰弱者占23.1%;75~84歲中占38.4%;≥85歲中占79.3%。因此對于高齡老年病人應加強衰弱的識別。
3.3 炎癥因子 有研究發現炎癥因子如白細胞介素6(IL-6)、C-反應蛋白等與衰弱獨立相關[14-15]。Li等[16]對社區老年女性進行了3.5年的隨訪觀察,發現IL-6較高的基線水平是失能和肌力快速衰退的高危因素。衰弱老年人IL-6的含量顯著高于非衰弱老年人,IL-6水平被認為是衰弱的獨立危險因素[17]。
3.4 其他 運動下降是衰弱的主要特征,生活方式如久坐、少運動亦會導致衰弱的發生。肌少癥是衰弱的主要病理改變,老年男性睪酮水平降低及更年期后女性雌激素的下降亦可導致肌少癥[16],從而導致衰弱的發生。
4 老年衰弱病人的評估工具
老年住院病人是衰弱的高發人群,對住院病人進行衰弱評估,對準確判斷其不良預后及治療策略的選擇非常重要。有專家總結目前衰弱的評估量表大致可以分為四類:自我報告式問卷、準則定義為基礎的測量、累積指數類評估工具、生物學標記物評估法[1]。國內外尚沒有統一的評估工具,比較常用的是美國學者Fried的衰弱診斷標準和加拿大學者Rockwood的衰弱指數(FI)。
4.1 Fried衰弱表型(FP) 包含以下5個條目:(1)不明原因體質量下降:近1年內體質量下降>5%;(2)自我感覺疲乏;(3)握力下降;(4)行走速度下降;(5)軀體活動降低。具有1~2條為衰弱前期,3條以上為衰弱期。Fried衰弱評估還可獨立預測3年內跌倒、日常生活能力受損情況、行走能力下降、住院及死亡率等。但其研究排除了帕金森綜合征、卒中等病人,且其包含的變量不夠全面,有些變量在臨床工作中不易測量。
4.2 FI FI主要包括生理、心理、功能狀態,從認知、情緒、自理能力、營養狀況等方面評估。通過對衰弱的高危因素存在與否進行綜合評價,以健康缺陷累積為基礎衡量衰弱,FI=存在健康缺陷的數目/視為健康缺陷項目的總數目,取值為0~1,且數值越大表明個體越衰弱。 通常認為FI≥0.25提示該老年人衰弱;0.12 綜合評估衰弱指數模型(FI-CGA)是基于老年綜合評估(CGA)量表,并據Rockwood等提出FI構建的,主要包括疾病和體征、視聽力、老年綜合征、營養及認知功能等64項健康缺陷變量,從每個變量賦值為0~1,健康項目為0,不健康項目為1,健康缺陷越嚴重其數值越大[18]。FI-CGA可準確評估中國老年病人病情,在老年醫學臨床中值得推廣。 4.3 其他 步速、起立-行走試驗和PRISMA(Program of Research in Integration of Servic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Autonomy)簡單、快速、靈敏,適合與老年人接觸時的任何情境下篩查衰弱[19]。此測試敏感度較高,但特異度一般,適用于篩查。無法進行起立和行走的病人,可以用握力篩查[20]。 愛特蒙特衰弱量表(EFS)[21]是由愛特蒙特開發的簡易篩查量表,包括認知、總體健康狀況、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量表(IADL)完成能力、社會支持、用藥、營養、情緒、尿失禁和功能。總分17分,0~4分為健壯,5~6分為明顯脆弱,7~8分為輕度衰弱,9~10分為中度衰弱,11~17分為嚴重衰弱。此量表有很好的信效度,且簡單易評,可供門診和病房的篩查[22]。 衰弱量表簡單易行,信效度高,適用于臨床老年衰弱的快速評估,用于術前衰弱的評估,可防止術后并發癥[1]。基于FP和FI形成5個條目:疲憊感、阻力增加/耐力減退、自由活動下降、最近1年內體質量下降>5%、患有5種以上疾病,每條1分,總分0~5分,1~2分為衰弱前期,3~5分為衰弱。 CFS由臨床醫生在全面評估病人的基礎上根據老年人ADL和疾病程度分為1~7級,級別越高衰弱越重。該量表反映的是醫生對老年病人長時間的縱向觀察和多次印象的綜合,能夠有效預測預后。 目前,尚沒有針對我國老年衰弱病人的識別和篩查工具,建議對有衰弱指標和危險因素的老年住院病人進行衰弱的初步篩查,對篩查結果為陽性的老年人進一步評估。 住院老年病人衰弱的發生率高,早期識別和評估可以預測不良結局,促進老年人健康老齡化,降低再住院率及死亡率,指導臨床診療策略及護理干預。 但未來還需要查找和確定老年人衰弱相關因素,明確適合中國老年人的衰弱指標的診斷界值,同時也需要對衰弱的生物標志物、新的治療方法進行更多的臨床研究,以便科學診斷,早期治療,降低殘疾、再入院和死亡的風險。5 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