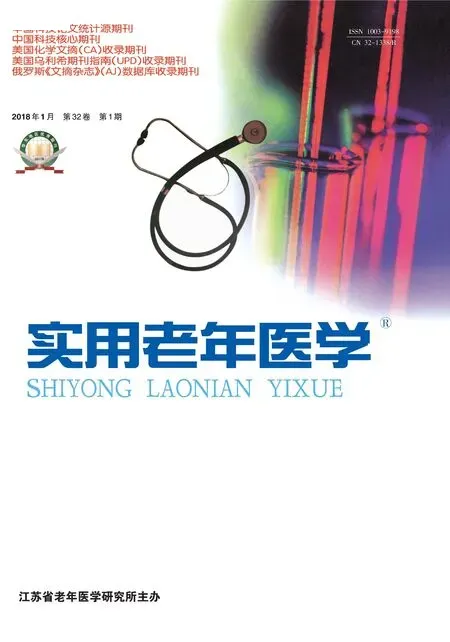臺灣緩和醫療研究現狀
現代安寧緩和醫療始于1967年,而臺灣緩和醫療的理念則萌芽于1983年天主教康態醫療教育基金會首創癌癥末期病患的居家照護服務[1],至今有三十余年的歷史。在臺灣緩和醫療的催生與茁壯的過程中,善終善生的“四全照護”一直是發展核心。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將緩和醫療照顧(palliative care)定義為:“對于不可治愈的疾病,所采取的一種積極的、全人的照顧”[2]。廣義而言,緩和醫療照顧是一個整合性的全方位照顧,它的目標就是增進重病病人和家屬的生活品質(包含身、心、靈三方面),并減輕他們的負擔。專業的癥狀控制,社會心理層次的支持、咨詢,良好的溝通,以及協助家屬和病人處理復雜的醫療問題和決定,這些都是組成緩和醫療照顧不可或缺的部分。
1992年臺灣緩和醫療專業人員的課程開始標準化,使得緩和醫學與護理齊頭并進,成為一項經訓練考核的臨床專業。2000年5月,臺灣立法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末期病人自此有權利自我決策,可選擇不接受心肺復蘇術,也使得醫護人員第一次依法有據,同年將癌癥病人的安寧住院、安寧居家納入給付試辦計劃。2009年健保給付亦從癌癥及漸凍人延伸至其他八類慢性末期疾病(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性精神病態、其他大腦變質、心臟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其他疾病、慢性肝病及肝硬化、急性腎衰竭、慢性腎衰竭),涵蓋五大器官:腦、心、肺、肝、腎,使緩和醫療服務的面向更跨出了一大步。[3]
1 臺灣緩和醫療終末期照護的機構
臺灣正進入老齡化社會,是全世界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地區之一。基于此,臺灣政府積極規劃長期照護。推動在“在地老化”、“在家往生”的理念,故生命末期的照護應脫離機械式的照護,從醫院延伸至社區,安寧緩和的四全照顧,轉變成五全照顧(全人、全家、全程、全隊、全社區)。終末期照護類似于長期照護,雖然與年齡相關,但不是老年人獨有,任何人都會因疾病或傷害進入生命的末期。
由于醫藥與公共衛生的進步,早在1988年馬偕醫院就已成立安寧照顧小組,并在2年后(1990年)成立臺灣第一家安寧病房,而后,1994年耕莘醫院設立了臺灣第二家安寧病房。1995年臺大醫院成立了安寧緩和病房,帶動了臺灣安寧緩和醫療的發展。安寧緩和醫療在政府機構的主導之下,從政策及保險給付方面促進緩和醫療的日益發展。根據臺灣安寧照顧協會統計的資料,截至2016年1月31日,臺灣共有62家安寧住院照顧醫院,101家提供安寧居家照顧的機構,142家醫院提供安寧共同照顧的服務,此數據約為2010年同期數據的2倍。基于2010年7月公布的全球首次臨終品質調查結果(臺灣末期照護的基礎環境、照護品質及照護費用三個方面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僅臨終照護可得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臺灣積極推動社區善終照護,截至2016年,共有200家社區安寧居家照顧醫院(乙類),擔負著社區照護人員的培訓及社區資源的連結,使病人能無后顧之憂,回到家中渡過生命最后的時光。
2 臺灣緩和醫療終末期照護的理念
到目前為止,沒有對生命終末期的精確定義,但一般情況下指個體因疾病或失能逐步走向自然死亡的一段時間。因此,在終末期需要面對兩個方面的問題:晚期疾病的急性期以及增齡相關的衰弱。由于醫療科技的進步,疾病型已由以急性治愈為主的傳染病、事故傷害,轉型為長期照護為主的慢性疾病,如慢性心力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退化性神經系統疾病以及腫瘤等。臺灣近10年來死因前五名都是慢性疾病。尤其是老年病人死亡前明顯有較長一段時間處于身體癥狀未被正確或適當診治的病程,陡然增加了病人往生前所受的痛苦。基于此,以醫院為本的共同照護理念應運而生。
共同照護就是將緩和醫療整合于所有重癥和末期疾病的傳統治療服務中,以使更多的重癥和末期病人可受惠于緩和醫療照護。而以醫院為本的緩和醫療照護團隊就是實際執行共同照護的單位,是一個多方整合的團隊。一般而言,受過緩和醫療訓練的護理人員往往是最基本的成員,稍大一些的組織會有醫師和社工的加入。除了這些核心成員外,經常性照護或是常規的設置心理師、社工、藥師、營養師、宗教人員、哀傷輔導小組、志愿者等都是一個好的共同照護所需具備的[4- 5]。
共同照護團隊在功能上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只提供院內照護的服務,這種形式的照護主責是在病患原本醫療團隊上。這樣的方式比較有彈性,較易連到全醫院,而對原本的醫療團隊、病人以及家屬來說,漸進式的導入緩和醫療是它們比較能接受的方式。另一種形式則由緩和團隊對照護的病人負起全責,他們可能擁有一個專門的安寧病房,也可能是利用院內其他單位的病床,來提供緩和醫療。這種方式需要較多的人力和資源,相對的影響力也較大。許多醫院的共同照護則同時包含這兩種形式。從客觀條件來看,一家醫院的規模、病人數、床數、醫療的特性、以及受過緩和醫療訓練的人員數都應該列入考慮,從而提供更好的照護服務。
3 臺灣緩和醫療終末期照護的內容
3.1 疼痛與癥狀控制 緩和醫療照護至少包括:(1)電解質不平衡;(2)急性疼痛;(3)嚴重呼吸困難;(4)惡性腸梗阻;(5)嚴重嘔吐;(6)發燒,疑似感染;(7)癲癇發作;(8)急性譫妄;(9)瀕死狀態等癥狀控制,處理原則與傳統醫療無異。
3.2 靈性照護 許多終末期病人面對靈性危機,引發其對于自身存在意義以及原有價值體系的質疑,但是在臨床醫療人員對于靈性照護卻常被忽略。具體沒有一個通用的定義來界定靈性。有學者透過概念分析介紹四個靈性的特征,即主觀認為具有幸福感、肯定自我存在價值、以接納態度面對所有關系和擁有內在資源能量,護理人員可依照以上四個特征深入評估病人的靈性需求,以提供個體化,且適合個案靈性需求的護理[6]。除了靈性安適的概念分析,靈性亦可能存于其他概念中,以次概念的方式呈現。運用Walker及Avant的分析步驟,進行舒適概念的探討,發現心理靈性層面亦屬舒適概念的一部份,屬性定義為內在自我覺察,包括自尊、生命意義、滿足感、安全感、與更高存有的關系等;其次,與靈性相關的社會文化層面,包含人際、家庭、社會關系、文化傳統、儀式與宗教[6- 8]。
靈性照護就是促進健康照顧、尊重并且支持病人的信念、提供面對痛苦時的情緒支持、促進或提供“超越性品質”、分享自我、促進關系、提供特別的活動來滿足宗教上的需求,并且與病人有言語上的互動。靈性照護在臺灣被應用于各個領域:(1)癌癥領域中,有學者介紹癌癥末期病人靈性照護的關系重建與修復模式[9],包含個體與天、人、我、物等關系,訂立了解、同理、指引及成長等四個階段操作步驟,并運用此操作步驟于一位平滑肌瘤癌癥末期病人身上,以達成重建與修復其與天、人、我、物等關系的靈性護理目標。(2)精神領域方面,靈性護理對于精神科具有重要性,東西文化對靈性的定義存在差異性,而靈性需求受文化、生活經驗、和個人主觀感受影響[10]。(3)老人領域方面,可提升病人心靈和諧與平靜,并將隔離、孤獨、寂寞、沮喪、和無望等負向情緒與思維,轉化成有歸屬感和希望[11]。
在靈性的問卷和量表方面,屬靈性的分類,包括職場靈性、工作意義和目標問卷、中文版spirituality and spiritual care rating scale (SSCRS- C)和靈性健康量表;與靈性相關的問卷和量表,如Herth希望指標和幸福感;因靈性狀態而受影響的指標方面的問卷和量表,包括Mishel疾病不確定感量表、正向心情/正向心情量表、情緒耗竭/情緒耗竭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和離職意圖/護理人員的離職意圖衡量。
3.3 預立醫療自主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 ACP起源于英國“醫療服務體系”中生命末期照護計劃,屬于優先次序照護的一部分。預立醫療計劃書強調以病人為中心,通過不間斷的溝通,了解病人對末期照護的優先考量、協助病人找到希望與心靈安適,緩解家屬做決定的負擔及強化病人與所愛的人的關系,由此可見,ACP 的執行并非強調完成預立指示文件的簽署,而是注重持續的溝通討論,讓家屬了解并尊重病人心愿,最終提升病人與家屬的生命品質與照護滿意度。
臺灣參考歐美正積極地推動此立意良好的ACP觀念,ACP是基于尊重自主、行善、不傷害、正義的倫理原則下,賦予個人為自身所期望的醫療選擇預先作出規劃的過程[12],而預立醫囑的書面文件為確保病人的意愿得到充分的尊重。但在臺灣的傳統文化下,談論死亡是個忌諱的話題,是否對病人告知病情以及告知的程度經常是由家屬主導[13]。無法確認病人真正的意愿為何,影響病人的自主與自決的權利。在簽署拒絕心肺復蘇(DNR)后,仍有病人于臨終前接受急救處置。為維護病人的自主與自決的權利,應及早透過ACP的過程,協助病人與家屬討論預立醫囑,經由溝通與會談來澄清彼此的經驗、價值信念、自主意愿與期望等,達成病人、家屬和醫護人員之間的共識,完成預立醫囑,提升照護品質。
3.4 哀傷輔導 哀傷輔導目標是協助喪親者調適喪親后的新生活[13- 14],以營造一個安全、接納和受支持的環境,協助個案在合理時間內,完成悲傷任務,以增進重新開始正常生活的能力[14]。哀傷輔導四個階段性介入為:(1)接受失落的事實:喪親者常處在徘徊狀態,相信逝者已離開,又幻想再重聚,透過對失落事件敘述回顧,有助于強化喪親者現實感。(2)經歷悲傷的痛苦:逃避及壓抑悲傷的人,只會延長痛苦及陷入憂郁,藉情緒表達整合對客體正負兩極感受,將有助于關系的重整。(3)重新適應沒有逝者的新環境:在喪親之后不能認知到環境改變,會導致喪親者適應困難,應協助個案坦然面對及承擔自己的新角色,必要時轉介資源進入,有助提升其適應能力。(4)將情緒活力重新投注在其他關系上:不再將希望與回憶依附在逝者身上,而是在情感生命中,為逝者找到一個適宜的地方,同時也為他人保留空間,以便能在世上繼續有效地生活[15]。
[1] 鍾昌宏.安寧院之介紹[J].臺灣醫界, 1983,26(4):37- 38.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ancer pain relief and palliative care. Geneva: WHO, 1990.
[3] 陳榮基.我國安寧緩和照護之相關政策的過去發展與未來展望[J].護理雜志,2015,62(2),13- 17.
[4] Dunlop KJ, Hockley JM. Hospital- based palliative careteams- the hospital- hospice interface[M]. Second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5] Fischberg D, Meier DE. Palliative care in hospitals[J]. Clin Geriatr Med, 2004, 20:735- 751.
[6] 楊均典,顏效禹,陳瑞娥.縵性安適之概驏分析[J].護理雜志, 2010,57(3):99- 104.
[7] 蔡佳玲,李雅玲,胡文郁.舒適之概驏分析[J].護理雜志, 2012,59(1):76- 81.
[8] Walker LO, Avant KC. Strategies for theory construction in nursing[M].4th ed. NJ: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5.
[9] 鄭如芬,林雅卿,黃百后,等.癌癥末期病人縵性照護模式[J].護理雜志, 2014,61(6):93- 97.
[10] 楊均典.精神科護理的縵性照護[J].若瑟醫護雜志, 2010,4(1):7- 14.
[11] 林燕如,周桂如,張佳琪.音硯治棹于臺灣儀人之應用[J].新臺北護理期刊,2011,13(1):53- 62.
[12] 蔡甫昌,潘恒嘉,吳澤玫,等.預立醫療計畫之倫理與法律議題[J].臺灣醫學,2006,10(4):517- 536.
[13] 許禮安.病情世界初探——由病情告知談起[J].安寧療護雜志,2002,7(3):239- 251.
[14] 曾秀玲,金淑華,蔡玉梅,等.一位中年車禍病人同時面對喪偶之護理經驗[J].馬偕護理雜志,2016,10(1):58- 68.
[15] Worden JW.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M].3rd ed.New York, NY: Springer. 2001.
[16] 丁秀蓉,齊美婷,周植強.運用悲傷輔道于憂郁癥患者喪女之護理經驗[J].榮總護理,2011,28(1):82-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