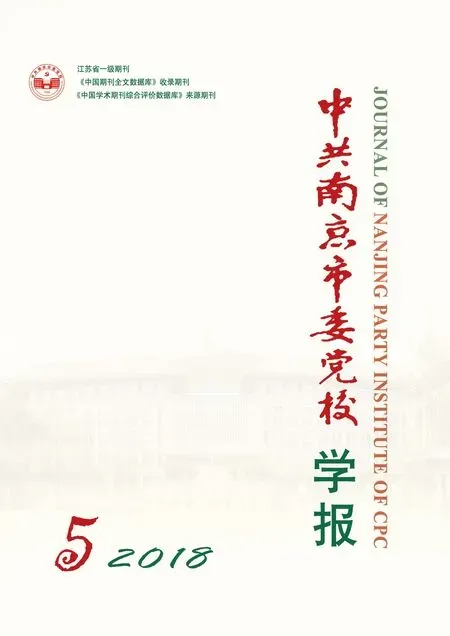水陸交通網絡與蒙元時期的“絲綢之路”*
時 磊
(揚州大學商學院 江蘇 揚州 225127)
一、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以兩個重大倡議為核心,2015年3月28日,中國政府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了符合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倡議: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合稱“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是新時期中國領導層統籌國內發展和國際合作的主要政策框架。它代表了中國欲以不斷壯大的經濟實力、逐漸增多的政策工具、日漸豐盈的知識經驗與周邊地區協同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抓手是交通網絡為核心的基礎設施建設。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倡議初期就指出,“將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在此基礎上,我們愿同各方積極探討完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為各國經濟發展和人員往來提供便利”。
絲綢之路是指從中國長安出發,橫貫亞洲,到達非洲、歐洲的古代陸路通道的總稱;因為中國的絲綢是這條通道上最重要的商品,故名“絲綢之路”;它不僅是一條商業要道,也是東西方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這一通道的開辟可追溯到西漢時代,但是其貿易規模和文化交流一直較為稀少,并未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元時代來臨。巴爾托德(2007)寫道,“蒙古帝國把遠東和近東的文明國家置于一個民族、一個王朝的統治之下,這就不能不促進貿易和文化珍品的交流。中亞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得到了空前繼后的發展”[1]。《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1985)也寫到,“穿過中亞的陸上貿易在蒙古人統治下復興”[2]。固然,蒙元時期歐亞大陸的政治一統為貿易興盛奠定了基礎,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蒙古人建立的交通運輸體系。蒙古帝國瓦解之后,中華文明進入明清時代,“絲綢之路”沒有重現昔日的榮光。回顧中國古代歷史,蒙元時期可能是“絲綢之路”輝煌的頂點。
更為有趣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復興也是在蒙元時代。“海上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其開創可能也要追溯到秦漢時期。但由于海洋船舶技術與海洋型政府缺失,這一通道一直并未獲得足夠發展,直到南宋時代,南宋恐怕是世界史上最早的疆域頗具規模且保有“常備”大艦隊的政權。蒙古帝國在忽必烈時期接收江南水上軍力和貿易船隊后,轉眼之間就成為一個擁有巨大海上艦隊的國家。南宋150年間,處于萌芽狀態的造船能力與航海技術,在忽必烈帝國這個具有罕見凝聚力的國家主導型政權影響下,一鼓作氣以人類史上最大的航海艦隊登場。內陸型的軍事政權與海洋志向型“生產社會”相連接的結果,催生了這個過去未嘗有的新形式(杉山正明,2015)[3]。遺憾的是,蒙元之后的明清政府都實施了較為嚴厲的、長期的海禁政策,中華文明錯失了轉向海洋的重大時機,直到晚清末期被西方海洋文明的堅船利炮打開大門,蒙元時期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極點。蒙元復興“海上絲綢之路”的細節是什么,可以為這個時代提供什么借鑒和啟發呢?
蒙元時期的兩個“絲綢之路”復興是一個重大經濟史命題,是“一帶一路”倡議歷史經驗研究的核心部分,可能需要從不同視角進行探索,交通網絡也許是蒙元時代兩個“絲綢之路”復興的重要原因。檢索文獻發現,近幾年“一帶一路”研究數量迅速增加,以“中國知網”為例,2014年前沒有題目中含有“一帶一路”的研究論文,2014年172篇,2015年3446篇,2016年4382篇,截止2017年4月3日已有731篇。但是,如果加入全文搜索“蒙古時代/蒙古時期”,結果就變為0篇,全文搜索“蒙元時代/蒙元時期”也只有7篇。使用題目中搜索“絲綢之路”,全文搜索“蒙古時代/蒙古時期”,2014年以來則有5篇,如果改為“蒙元時代/蒙元時期”也只有36篇,而且這些大多并非經濟史研究,沒有太多的參考價值。總而言之,現有文獻從經濟史視角研究“一帶一路”仍然非常有限,尤其是蒙元時期,本文可視作一種嘗試性探索。結構將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主要介紹蒙元時代陸路交通網絡與商業擴展;第三部分重點梳理蒙元時期水路交通體系和網絡的建立;最后是結論和啟示。
二、陸路交通網絡:驛站、道路與商業擴展
蒙元時期通過陸路交通網絡,歐亞文明圈之間實現了空前未有的大交流、大交換,這使世界歷史出現了重大轉向,杉山正明(2015)的題目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4]。威澤弗德(2006)的《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形成》也寫到,“如果沒有全球性的商業擴張恐怕也就沒有今天的世界體系,在促進全球商業方面沒有哪個民族能與蒙古人相比。”“近代的世界體系是在資本主義的沖擊之下形成的,而在13世紀已經出現過由蒙元帝國維持了一世紀之久的‘世界體系’。在歐洲,自蒙古人入侵50年以來,眾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小圈子里的文明融為了一體,有了統一的洲際交通、商業、技術和政治體系;在亞洲,中國傳統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徹底打破,中國的工場增加全新的品種,出口歐洲。”[5]商業革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絲綢之路”復興,蒙古人“從亞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開辟了一條寬闊的道路,在軍隊過去后,他們把這條大道開放給商人和傳教士,使東方和西方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進行交流成為可能”(道森,1983)。[6]
(一)驛站系統
蒙元時期陸路交通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是驛站系統。驛站系統本來是中國古代供傳遞官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可以追溯的歷史有3000年之久。但蒙元時代之前,首先,歷代王朝建立的驛站數量非常少。例如,廣州與高雷地區唐宋時期并沒有路上官方驛站,直至元代才新開一條直接到達的驛道(顏廣文,1996)[7];不少研究發現,蒙元時代第一次設置了通往西藏的驛站系統(祝啟源、陳慶英,1985)[8],甚至通往緬甸等中南半島的(方鐵,1987)[9]。其次,歷代王朝驛站系統主要是官方和官員使用,并未開放給商旅和普通居民。再次,歷代王朝的驛站系統的維護不如蒙元時代。蒙元時期驛站系統規模巨大,由于疆域遼闊,為軍事、經濟考慮,持續強化驛站制度。這時驛站也叫“站赤”,“站赤”是蒙古語驛站的音譯。蒙古的驛站、運輸、交通網“站赤”的范圍遠至俄羅斯。這個交通網不只是連接起歐洲與亞洲的陸上交通,也為通往波羅的海、里海、黑海、地中海、紅海、波斯灣的海上交通帶來便利。但《元史》對海外部分一帶而過,資料和研究缺乏,波斯文《史集》(1986)有不少記載[10]。
蒙元時期驛站系統建立起始自成吉思汗時代,第二代大汗窩闊臺即位,就下令在全境遍建驛站。關于中國本土的驛站系統,《元史》有非常細致的記錄和統計,如中書省管理的驛站有陸站175處,水站21處,牛站2處。各省驛站分布是,河南省陸站106處,水站90處;遼陽省陸站105處;江浙省馬站134處,轎站35處,步站11處,水站82處;江西省馬站85處,水站69處;湖廣省陸站100處,水站73處;陜西省陸站80處,水站1處;四川省陸站48處,水站84處;云南省馬站74處,水站4處;甘肅省馬站6處。總計全國總站數約1400處,加上嶺北、土蕃等處,應在1500處以上。史料極其缺乏的是,蒙古三次西征建立的四大汗國——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兒汗國,資料顯示,這些汗國與早期首都哈拉和林建立了驛站系統(黨寶海,2004)[11],這些驛站系統又通過三條干道和后期首都元大都緊密相連,這一系列可能是“絲綢之路”主體,由于這一部分隱藏在俄文、波斯文和拉丁文文獻中,關注較少。
(二)道路建設
史料顯示,成吉思汗西征時期,連接中亞和西方的“絲綢之路”,很多已經廢弛。成吉思汗為征服中亞,在新疆的天山、天池和金山附近都修筑道路,重新打通亞歐大陸并建立了驛站系統(張來儀,1991)[12]。這一道路重建和修復后,每一代蒙古大汗都非常重視對驛站系統的維護,蒙古人不僅重建并維護“絲綢之路”通道,還擴大了“絲綢之路”的范圍,例如通往蒙古高原的“草原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的頂點是哈拉和林,哈拉和林與元大都之間,以三條干線與一條旁道又作聯結。然后,從大都開始,往東亞區域,又整備著放射狀的道路網。根據當時從東西世界來造訪的旅行者記載,忽必烈的“王道”在寬廣的公共道路兩側挖掘有水流通過的溝渠,在彼處種植白楊或柳樹等樹木,從兩側打造了覆蓋公共道路的涼爽綠蔭(杉山正明,2015)[13]。這種規模遍及中國全境的公共道路系統,至少是自唐代以來首次。更何況,北起黑龍江及西伯利亞,南至越南、緬甸、西藏等東亞全境道路系統的整備,又和橫貫草原與綠洲世界的驛站系統作聯結,以陸上交通體系與歐亞全境相連,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全球交通網。
(三)商業保護
如果說驛站系統和道路建設屬于陸路交通體系的硬件建設的話,商業保護、系統維護可能屬于陸路交通體系的軟件。商業保護政策,第一條是優待商旅,這和傳統中華王朝的“重農抑商”有重大差異。蒙古國家由于出身于游牧經濟,資源較為缺乏,非常注重商業和貿易。成吉思汗時期就在大道上設置守衛并頒布一條敕令:凡進入國土內的商人,應一律發給憑照。而值得汗受納的貨物,應連同物主一起移送給汗(志費尼,1980)[14]。成吉思汗的這種商業保護政策,被窩闊臺及繼承者繼續執行,商人們經常騎著驛站的驛馬往來于蒙古各地,直到蒙哥時期才廢除這項優待。第二條是廢除過路稅,實施一次性的、很低的銷售稅,只有三十分之一。由于傳統征稅技術缺陷,歷代中國王朝往往采取過路稅方法征收商業稅收,這對商業貿易具有非常不利影響,例如晚清和民國時著名的“惡政”——厘金(趙留彥、趙巖和竇志強,2011)[15]。第三條是保證商旅安全。裴哥羅梯《通商指南》中說,“據商人曾至契丹者言,由塔那至契丹,全途皆平安無危險,日間與夜間相同”。志費尼寫道:“成吉思汗統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環境,實現繁榮富強;道路安全,騷亂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圖之地,哪怕遠在西極和東鄙,商人都向那里進發……”①
蒙古政府重商主義的商業保護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東西方的文明圈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物資和人員交流。物資交流方面,中國史籍常常是官方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商旅和商業活動較少被記錄下來,尤其是“重農抑商”的封建王朝,編撰《元史》的士大夫階層有意無意中忽略了商業活動的描述。盡管如此,許多文獻還是證實了蒙元時期異乎尋常的商業繁榮,例如劉政(2010)就從前代的文集、筆記中整理出許多寶貴的歷史證據[16]。傳統時代跨國貿易的一種重要類型是“朝貢體系”(波蘭尼,2007)[17],杉山正明(2015)記載了,旭烈兀汗國使節團,帶來被稱作“答納”的大珍珠、名產“大馬士革劍”、優良的“阿拉伯馬”、中東的優質織金,包括香料在內的種種藥材,還有作為寶石的青金石[18]。蒙元時期中央政府在元上都和元大都之間構筑大量手工業(汪興和,2004)[19],以奢侈品生產和貿易獲取收入,這是由中國輸出中亞和西方的物資來源之一。東西方物資交流的一個更重要的證據是青花瓷,一種白瓷質地上涂上鈷藍色彩的器物。做紺青染色是伊朗一帶的習慣和偏好,作為上繪顏料的鈷也如此。不過,伊朗主要為陶器,瓷器則是中華特產。蒙元時代,官窯景德鎮生產的這種東西,經印度洋大量運送至中東地區,甚至歐洲。這是蒙元時代“歐亞通商圈”最大的暢銷商品,深藍和白色相間的調和效果成為“時代的品味”(杉山正明,2016)[20]。但源于中東的顏料鈷如何進入中國卻沒有記載。
蒙元時期、蒙元帝國的商業保護政策,讓它與歷代的中華王朝格格不入,傳統中國的農耕文明盛行的是“重農抑商”。更值得記錄的是,蒙元時期中央政府收入并不是來自于田賦、丁稅,核心組成部分竟然是商業運營利潤。陳高華、史為民(2000)記錄,中央政府收入8成以上是透過鹽的專賣所得利潤,還有1成到1成5的商稅收入,將二者合并,總計90%-95%的中央政府收入來自商業活動[21]。這與之后明代政府收入中商業稅收僅有1.1%(張宇燕、高程,2005)[22]相比,真是天壤之別。蒙古人所組成的政府,精神上類似于“商人的政府,商人組成的政府,為商人服務的政府”,這也是在西方存在“蒙古自由主義”說法的原因,甚至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思想可能也和蒙古有非常緊密的關系,是蒙古人催熟了現代世界體系(王紀潮,2007)[23]。
蒙元時代兩個“絲綢之路”復興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歐亞文明圈之間的人員交流。以蒙元政府為例,雖然中央行政機構是根據中原模式創設的,但其成員不僅有蒙古人、畏兀兒人,也有漢人,女真人、契丹人、波斯人,甚至還有歐洲人。這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可能是穆斯林商業集團,例如,忽必烈時期成立了以穆斯林企業家阿合馬為首的特別中央機關,而海洋經濟活動幾乎都是以另一個穆斯林蒲壽庚為核心。蒙古軍事遠征中的情報站、補給站也主要依賴穆斯林,在之后的管理上穆斯林的能力得到更大發揮,例如征稅,主要采取包稅制的方法。人員交流的其他證據也非常多,許多旅行家留下大量的筆記,時至今日,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某種程度上說,蒙元政府充分吸收世界各國的文明成果和聰明才智,構架起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綜上所述,蒙元時期通過建立一整套驛站制度,重新修建和完善陸路交通網絡,加上商業保護等軟件維護,使得蒙元時代來臨之前已被廢弛的“絲綢之路”再度煥發活力。“絲綢之路”的復興,使得東西方的物產交流和人員交流規模空前,光耀古今。
三、水路交通網絡:運河、海洋與遠洋貿易
如前文述,蒙元時代海洋實力主要來自于南宋的遺產,宋代的海外貿易已有不少研究(如黃純艷,2016)[24]。蒙古統一南宋的襄陽戰役,曠日持久,為了應對南宋強大的水上戰斗力,蒙古政權也開始聚集水船、建造艦艇,根據《元史》記載,蒙古水師竟然有五千艘船,七萬人的兵員之多。南宋中央政府無血獻城之后,所培養的海上艦艇除崖山沉沒的,都歸入了蒙古政府。由于對海上戰斗力的熱衷,忽必烈還熱烈地招諭擁有海上艦艇的“海盜們”(杉山正明,2015)[25]。被接收的除了南宋直屬艦隊之外,還有東南沿海以泉州為中心的貿易船隊,尤其是以穆斯林商人蒲壽庚為核心的遠洋船隊,這樣蒙古政府就具備了海洋商業基礎。傳統時代,遠洋貿易無外乎有兩大困難:一是船舶制造技術,要制造出可抗擊海洋風浪的大型船舶;二是海洋型政府,要肅清影響海路的“海盜”實力。忽必烈接收了南宋的通商勢力,籠絡蒲壽庚,蒙古政府開始在泉州建造大型船艦,同時由于龐大的水上戰斗力,可以使得天威遠播,海路暢通。
(一)疏浚運河
蒙元時期的水路交通建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京杭大運河的疏通和改造。唐末之后,中國本土長達數百年的戰亂與南北對峙,使得京杭大運河這一南北運輸的動脈被徹底廢棄。甚至在南宋時代,長江和黃河之間,以淮河為中心形成了接近三四百公里遼闊的帶狀“空白”(王海冬,2016)[26]。蒙古人接收南宋之后,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對縱貫中國的京杭大運河再行開鑿,大運河的重新復活是蒙元時代水路體系建設的第一步。蒙古人水路運輸體系建設的第二步是將運河延伸到北京市市區的“積水潭”,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首次,傳統封建王朝往往只是將運河修到北京郊外的通州碼頭。第三步則是構建和疏通了通州到出海口直沽(天津)的運河和自然河流,這樣大都就成為一個與海洋相連接的首都。北京與其外港天津的這種形式,創始于蒙元時代。蒙元時期水路交通體系的構建,是一個十分宏大的體系,將首都與海路、水路緊密相連,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在那個水運成本最低的時代將中央政府所在地置于核心交通樞紐之中,這與那些出于安全考慮甚至不肯修路的政府表現出巨大的不同(馮維江,2009)[27]。十分完善的水路交通體系、網絡,使得中國南方的豐富物資,以米谷為主,以及滿載著伊斯蘭世界或西方物品的船,通過印度洋來到東方,也在此排列舳艫。
(二)開辟海路
蒙元時代水路交通建設,雖然大運河疏浚是極其重要的一環,但是其運輸體系中更重要的可能是海洋運輸(潘清,2014)[28]。蒙元時代海洋運輸的起點漕糧海運,忽必烈初期的南糧北運,古運河尚且沒有完全疏通,由揚州北上輸送糧食需要多次裝卸,成本極其高昂。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兩個前“海盜”奉旨創建漕糧海運于劉家港(今江蘇太倉)。首航成功后,忽必烈下旨在今天的江蘇太倉建立市舶司,并允許通過海路進行“通番貿易”(王海冬,2016)[29]。海上漕運的新海路從長江口直至天津,這條海路將傳統的南方遠洋海路連接起來,成為溝通中國南北方并蔓延至海外的海上交通網絡。更有意思的是,海上漕運的發展為上海的建立和發展提供巨大的機遇,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正式建城,但在此之后上海陷入了長達5個多世紀左右的隱沒不聞,直到現代海洋文明的曙光來臨。海上漕運通道的建立,打通了世界遠洋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中國海洋發展史的輝煌篇章。這種蒙元時代的海路系統直到晚清時代經歷外部沖擊才重新繁榮。雖然蒙元時代的海上通道很大一部分繼承自南宋時代,但構建通往中國北方的新海路的角色應該充分肯定,這是中國本土海路全線貫通的第一次。
(三)海路系統維護:降低交易成本
如果說蒙元時代的海上通道的硬件繼承自南宋,那么蒙古政府對海上通道的維護這一軟件系統則有重要的改善。蒙元政府的海洋貿易管理是獨樹一幟的,許多舉措時至今日看來也非常先進。第一是通商口岸數量眾多、分布廣泛,據文獻記載,蒙元政府先后設置的市舶司至少有7個之多,分別是泉州、慶元、上海、澉浦、廣州、溫州和杭州等(陳賢春,1993)[30],這與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的多口通商類似。第二是海洋貿易的關稅非常低,絕大部分關稅是三十分之一,依據船商的種類偶爾也有5%或7%的關稅。這即使放在WTO的框架內,也是非常低的關稅,遠低于當代世界平均關稅。第三是政府參與并主導海洋貿易。雖然蒙古政府管理貿易事務和進出口的官署名稱與南宋一樣,也是“市舶司”,但蒙古政府更多獎勵、推動遠洋貿易。政府機關在泉州等地建造船只,附上資金出借給海洋商人,力圖促進貿易,并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這與被動管理的歷代王朝有本質區別。第四是蒙元政府對海路進行系統化的管理。文獻記載,東南亞沿岸的要沖,甚至印度沿岸中繼點,都有政府的派駐機關的存在(杉山正明,2015)[31]。因此不難理解,蒙元時代遠洋貿易國家由南宋時的51個,增加到140多個,商品種類也大大增加。
蒙元時期遠洋貿易發展管理策略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人員的開放性。遠洋貿易人員的主體是穆斯林商業集團,也稱為“回回海商集團”。自唐宋以降就有眾多穆斯林商人東來,在東南沿海定居,推動了東南沿海的崇商氛圍。蒙元時代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讓更多的穆斯林商人東來,聚居于沿海重要城市如泉州,這逐漸成為推動遠洋貿易的核心動力之一。這一時期,穆斯林商人開始廣泛聚居于東南亞,印度洋沿岸,東南亞、南亞開始了“伊斯蘭化”浪潮。穆斯林文化的共通之處,降低了“蒙古體系”遠洋貿易的交易成本。甚至明代初期,下西洋的鄭和也被證明是穆斯林身份,這樣就不難理解永樂皇帝任命他為艦隊首腦,并且七下西洋獲得成功的原因,穆斯林文化降低了交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據現有文獻考證,泉州、揚州、鎮江都有大量的穆斯林存在和活動的證據,甚至蒙元時代某些時期的最高長官都由穆斯林充任。大量的清真寺,阿拉伯文、波斯文墓志銘、墓碑、石刻均證實這一點。穆斯林參與海洋貿易、市舶司管理在史料中廣泛記載,例如蒲壽庚父子、馬合謀、沙的、贍思丁、木八剌沙等(楊志娟,2013)[32]。
總而言之,蒙元時代的水路交通網絡,首先是疏通國脈“京杭大運河”,和首都相連,其次是構建本土水系和海路的連接,最后是將“海上絲綢之路”打通。遠洋貿易體系的有效運轉需要較為低下的交易成本,蒙古政府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廣開口岸,降低關稅,政府投資降低風險,甚至在海路沿線設置派駐機構。這些行為在新制度經濟學框架內,都可以視作“優秀政府行為”。蒙元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繁榮,與其開放的人才使用也有很大關系,穆斯林商業集團使用和東南亞“伊斯蘭化”的歷史機遇結合,進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已提出交通改善、市場擴大可以促使生產資源的重新配置,引起分工產生和生產力提高,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前現代時期,要想克服自然的障礙,建立完善的交通體系其中的困難遠超今日想象,但蒙元時代這種巨大的努力確實有著豐碩的回報。遺憾的是隨著蒙古帝國的分崩離析,這種交通體系和網絡也瓦解了。
四、結論和啟示
歷史風煙,俱已往矣,中華文明又迎來一個偉大時代,具有遠見卓識的政府提出了復興“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新時期中國領導層統籌國內發展和國際合作的主要政策框架,這個倡議需要一個重要的抓手,如果從政治、能源甚至經濟視角可能會引起周邊國家反感,反而可能不利于“一帶一路”推進和實施。以交通網絡為基礎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很好的起點。現實需要背景下,對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絲綢之路”復興和發展進行研究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史命題,本文可視作一個探索性嘗試。我們對經濟史資料的搜集、整理發現,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元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兩個“絲綢之路”復興時代,這一時期的核心經驗可能是構建交通網絡。蒙元時代交通網絡構建分為:陸路交通網絡和水路交通網絡,陸路交通網絡的核心措施是:驛站制度、重建道路和商業保護,這些推動歐亞文明圈物資和人員交流,實現了“絲綢之路”的復興;水路交通網絡的核心措施是:疏浚運河、開辟海路,和降低交易成本,這些繁榮了遠洋商業貿易,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復興。
毫無疑問,蒙元時期兩個“絲綢之路”復興的核心舉措具有很好的啟發意義,但由于歷史久遠,技術時代差異巨大,生搬硬套蒙元時期可能是削足適履。這種中國經濟史一個時代的精神內涵提煉可能需要很多的專業技能,我們不揣冒昧,姑且言之,權做一種嘗試和探索,以供人批評和反思。我們認為,當代的“一帶一路”建設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借鑒和吸收蒙元時期經驗:第一,不僅僅是協助各國建立和修筑陸路基礎設施,更要強化這些基礎設施的管理和維護,中國豐富的交通管理經驗值得進一步總結、推廣,尤其是結合現代科學技術實現軟件化、程序化;第二,“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僅是修筑基礎設施,更重要的可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貿易成本,中國政府要當仁不讓地牽頭加強多邊磋商、多邊合作,甚至合適的時機提出構建“絲綢之路”自由貿易區,“海上絲綢之路”自由貿易區,并削減各國之間的非關稅壁壘和其他貿易壁壘;第三,構建開放性的“一帶一路”管理機構,這一機構要充分吸收沿線各個國家的人員,一方面豐富知識經驗、降低交流成本、緩解文化沖突,另一方面展現中國政府的世界格局、戰略眼光。整體而言,“一帶一路”倡議是世界視角的宏大戰略,是中國政府為推動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所做的有意義的嘗試,但其中的構建細節需要學術界和其他機構群策群力!
注釋:
①轉引自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中華書局,1977年7月版,第314頁和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