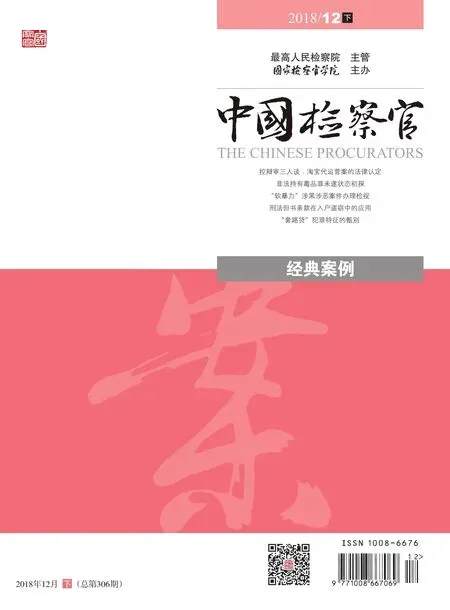搶劫手機后又轉走支付寶內余額的行為定性
文◎高蘊嶙
*重慶市南岸區人民檢察院[401336]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27日22時許,犯罪嫌疑人譚某預謀搶劫后,便守候在重慶市南岸區的某偏僻路口。后譚某見王某孤身一人路過此地,便用預先準備好的水果刀指著王某,讓其交出身上值錢的東西。王某見狀便交出身上唯一值錢的手機,譚某拿過手機后便立即逃離了現場。次日,因王某設置的手機解鎖手勢簡單,譚某又意外試出了該手機的解鎖手勢,并發現手機內的支付寶軟件上有余額4500元,于是又將支付寶軟件上的余額4500元錢轉至自己的賬號。犯罪嫌疑人譚某被抓獲歸案后如實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實。經重慶市南岸區價格認證中心認證,王某被搶的手機價值3100元。
二、分歧意見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犯罪嫌疑人譚某意外試出手機的解鎖手勢后,又轉走王某手機上支付寶軟件內余額4500元錢的行為該如何定性,主要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譚某意外試出手機的解鎖手勢后,又轉走王某手機上支付寶軟件內余額4500元錢的行為單獨成立盜竊罪,本案應以搶劫罪(數額3100元)和盜竊罪(數額4500元)對譚某進行數罪并罰。理由是:譚某以搶劫故意搶走王某手機應成立搶劫罪;在搶劫行為完成后的次日,譚某意外試出王某手機的解鎖手勢,并發現王某手機上支付寶軟件內有余額4500元錢,于是又另起犯意,秘密轉走支付寶軟件內的余額4500元錢,應認定為盜竊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譚某意外試出手機的解鎖手勢后,又轉走王某手機上支付寶軟件內余額4500元錢的行為系搶劫行為的延伸,不能單獨成立盜竊罪,本案應以搶劫罪(數額7600元)一罪論處。理由是:譚某搶走并占有手機的同時亦對支付寶軟件上的余額具有概括占有的故意,因此,轉走王某手機上支付寶軟件內余額4500元錢的行為系搶劫故意的進一步實現,決不能將前面搶劫手機的行為與后面秘密轉走手機支付寶軟件上余額的行為割裂開來評價,應當將兩個行為進行整體評價,本案只能以搶劫罪一罪論處。
三、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他山之石:信用卡與其記載的資金具有一體性和分離性的雙重特性
《刑法》第196條關于信用卡詐騙犯罪的第3款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筆者注)的規定定罪處罰”。有觀點認為,刑法將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規定為盜竊罪,是一種法律擬制。所謂法律擬制,又叫法定擬制,是指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該規定處理。筆者認為,刑法將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認定為盜竊罪,并非是法律擬制,而是根據信用卡與其記載的資金具有一體性和相對分離性的雙重特性而得出的合理結論。所謂一體性是指,行為人一旦事實上占有了信用卡這一載體,就可以(不是必然)實現對卡上資金的占有;所謂分離性是指被害人即便沒有事實上占有信用卡這一載體,也可以通過掛失等方式實現對卡上資金的占有。
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兩搶意見》)第6條“關于搶劫犯罪數額的計算”規定:“搶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費的,其實際使用、消費的數額為搶劫數額;搶劫信用卡后未實際使用、消費的,不計數額,根據情節輕重量刑”。根據《兩搶意見》可以得出,搶劫信用卡后又使用、消費的僅以搶劫罪一罪論處,事后又利用信用卡進行使用、消費的行為不另外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可見,最高人民法院的《兩搶意見》沿用了刑法關于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立法精神。但是有觀點并不贊同 《兩搶意見》的規定,如劉明祥教授在《法學》2010年第11期上發表的《搶劫信用卡并使用行為之定性》一文(以下簡稱劉文)認為:一是搶劫信用卡并當場使用的,使用信用卡的行為不屬于信用卡詐騙行為,此種情形應當認定為搶劫罪一罪,使用信用卡的數額計入搶劫數額;二是搶劫信用卡并事后使用的,事后使用信用卡的行為應當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不應以搶劫罪論處;三是搶劫信用卡既當場使用又事后使用的,則應以搶劫罪和信用卡詐騙罪數罪并罰。筆者認為,劉文之所以得出這種結論,是因為沒有認識到信用卡與其記載的資金具有一體性和相對分離性的雙重特性。當行為人以搶劫的故意占有他人信用卡時,根據信用卡與其記載的資金之間具有相對分離性的特點,不能就此認為行為人已經搶得了信用卡上的資金,這一點學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識;但是又由于信用卡與其記載的資金之間具有一體性的特點,一旦行為人以搶劫故意占有了信用卡,那么對信用卡上的資金則具有概括占有的搶劫故意,而后續使用信用卡的行為只是搶劫故意的進一步實現,決不能將使用信用卡的行為理解為另起犯意和犯罪行為,從而就將使用信用卡的行為評價為信用卡詐騙罪,因為沒有搶劫信用卡的行為,就不可能有使用信用卡的行為,二者猶如皮與毛的關系,決不能將使用信用卡的行為進行單獨評價。
(二)用以攻玉:手機金融軟件具有與“信用卡”類似的雙重特性
隨著銀行業的繁榮、手機行業快速發展以及互聯網的普及,智能手機上裝載手機銀行、第三方支付平臺等具有金融功能的軟件已成為常態。人們攜帶智能手機外出消費逐漸取代攜帶信用卡進行消費已成為一種趨勢。手機支付寶軟件作為智能手機常備的一款金融軟件,具有與“信用卡”類似的雙重特性,即手機支付寶上的余額以手機及支付寶軟件為載體而存在,手機及支付寶與余額之間同樣具有一體性和相對分離性的雙重特性。其一體性表現在行為人以搶劫故意占有手機后,客觀上就可以(不是必然)實現對手機金融軟件上所記載資金的占有,主觀上行為人對手機金融軟件所記載的資金同樣具有概括占有的故意;其相對分離性表現在行為人雖然客觀上搶得了手機,但對手機金融軟件上所記載的資金并非必然占有,被害人亦可以通過修改金融軟件登錄密碼等方式實現對金融軟件上所記載資金的占有。如果說信用卡具有將卡片與資金二合一的功能,以搶劫故意占有信用卡的行為對信用卡上所記載的資金具有概括占有的搶劫故意,那么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智能手機則具有將手機、金融軟件、銀行卡片與資金等多合一的功能,以搶劫故意占有手機的行為,難以否認行為人對手機金融軟件上記載的資金不具有概括占有的搶劫故意。
(三)結論
本案中,譚某以搶劫故意占有王某手機時,其對王某手機支付寶軟件內的余額具有概括占有的故意,后續利用手機支付軟件進行轉款的行為只是譚某搶劫故意的進一步實現,而非另起犯意后進行的犯罪行為。因為如果沒有譚某搶劫手機的行為,就不可能發生利用手機支付寶軟件進行轉款的行為,搶劫手機行為與利用手機支付寶軟件進行轉款行為之間同樣猶如皮與毛的關系,故不能將利用手機支付寶軟件進行的轉款行為獨立于搶劫手機行為進行單獨評價。綜上,本案應以搶劫罪(數額7600元)一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