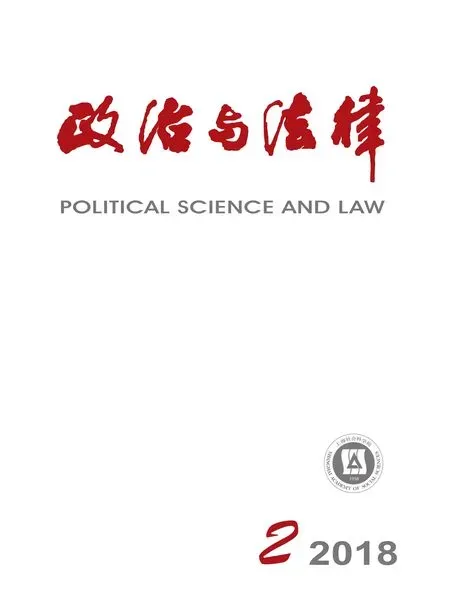中國憲法學言論自由觀的再闡釋
——與徐會平先生商榷
(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上海 200241)
2016年4月,《學術月刊》刊發了徐會平先生的論文《中國憲法學言論自由觀反思》(以下簡稱:徐文)。*參見徐會平:《中國憲法學言論自由觀反思》,《學術月刊》2016年第4期。該文對我國憲法第35條與第41條進行了富有創見性的解釋,認為憲法第35條在性質上屬于基于人權理論的個體自由條款,憲法第41條是一個以人民主權理論為基礎的政治自由條款。這一解釋方案頗具新意,讓人耳目一新。然而,仔細讀來,筆者在深深敬服作者學養的同時,也發現文章的觀點有過于極端甚至牽強之處。學者對憲法條款進行學理解釋,意在探求憲法條文的語義表達及其規范性意義,憲法解釋這一事業假定了有良知、負責任的解釋者在尋找憲法的真實含義或最佳解釋。*參見[美]索蒂里奧斯·巴伯、詹姆斯·弗萊明:《憲法解釋的基本問題》,徐爽、宦盛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頁。基于此理念,筆者不揣淺陋,試與徐先生商榷一番。
一、將我國憲法第35條解釋為個體自由條款難以成立
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徐文在區分個體自由與政治自由的基礎上,*徐文認為,個體自由是以個體利益的滿足和實現為指向的自由,政治自由是一種以政治生活參與為指向的自由。參見前注①,徐會平文。認為該條并非是源于人民主權理論的政治自由條款,而是以個體利益為指向和依歸的、源于人權理論的個體自由條款。其立論依據如下:其一,該條款采用了“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游行、示威的自由”的句式,這是一種以個體對權利和自由的擁有為重點的表達,旨在強調言論自由對個體的意義;其二,該條是個體自由條款可以從其受我國憲法第51條限制的事實中得到進一步證明,因為我國憲法第51條是對個體自由進行限制的條款。以下擬逐一分析上述兩個論據。
徐文第一個論據運用文義解釋方法,涉及對“公民有言論……自由”的理解,認為這是一個以個體對權利和自由的擁有為重點的表述,因此條文中的“自由”應當解釋為以個體利益滿足和實現為指向的個體自由。從字面含義的一般性理解角度分析,這一解釋具有合理性。然而,任何語言都不可能像符號語言那樣精確,僅通過語言用法本身不能獲得清晰的字義,而是會有或多或少的意義可能性即意義變化的可能性。*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01頁。條文規定無論多么詳盡,都無法窮盡現實生活所展示的無限多樣性,相對于條文的實際適用,條文本身總是呈現給其適用者一種“開放結構”。*參見張志銘:《歐洲人權法院判例法中的表達自由》,《環球法律評論》2000年第4期。根據不同的語境,當言及“公民有言論……自由”,人們可能是基于保護個體利益的意向,也可能是以政治生活參與為指向,還可能兼而有之。因此,僅通過分析憲法第35條的句式難以得出該條規定的言論自由是以個體利益為指向、源于人權理論的個體自由條款。
徐文第二個論據運用結構解釋方法,試圖通過分析憲法第35條與第51條之間的體系關系與意義脈絡推導憲法第35條的性質。徐文的論證可歸納為一個三段論推理,邏輯大前提為,憲法第51條是對個體自由進行限制的條款;邏輯小前提為,憲法第35條受第51條的限制;結論是,憲法第35條是個體自由條款。徐文從學界通說和制憲者原意兩個角度對小前提“憲法第35條受第51條的限制”加以論證,筆者不持異議,但對于邏輯大前提“憲法第51條是對個體自由進行限制的條款”,徐文并未明示推導過程。實際上,憲法第51條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的規定是對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概括限制條款,無論從文義解釋還是歷史解釋的角度,都難以推導出其限制的“權利和自由”僅指個體自由。從文義解釋角度分析,“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既可包括個體自由,也可包括政治自由;從制憲歷史的角度分析,憲法第51條制定過程的討論中并未區分該條限制的“權利和自由”屬于政治自由還是個體自由。憲法第51條是我國現行憲法修改過程中新增加的條款。1981年,我國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在憲法修改稿中增加了“公民在行使權利和自由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和集體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權利。任何濫用權利和自由的行為也要依照法律給予制裁”這一條款,*參見許崇德:《許崇德全集》(第七卷),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9頁。1982年的我國憲法修改草案第48條將其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草案中的此規定為現行憲法第51條所采用。我國憲法之所以增加上述規定,其意在確立自由和權利的憲法界限。1982年4月22日,彭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說明中指出:“世界上從來不存在什么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權利。國家保障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權利,不允許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犯,但也決不允許任何人利用這種自由和權利進行反革命活動和其他破壞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的犯罪活動。”*許崇德:《許崇德全集》(第七卷),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1頁。1982年11月,彭真向全國人大作憲法修改草案報告時再次強調:“世界上從來不存在什么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權利。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頁。可見,憲法第51條的制憲規范意圖在于確立“自由和權利”的憲法界限,并未對“自由和權利”的屬性加以區分。因此,將憲法第51條解釋為僅對個體自由進行限制的條款難以成立。在上述三段論推理中,“憲法第51條是對個體自由進行限制的條款”這一邏輯大前提不成立,那么“憲法第35條是個體自由條款”這一結論當然也不可靠。
綜上所述,對現行憲法第35條性質的認定,僅通過文義解釋和體系解釋難以得出確切結論。由此必須引入其他解釋方法。
二、我國憲法第35條應解釋為政治自由條款
在法律解釋的實踐中,我們很難說哪一種解釋方法總是處于獨立、主導的地位,而不具有輔助意義,哪一種方法則完全處于輔助地位,各種解釋方法總是相互為用的。*參見張志銘:《法律解釋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頁。由一般的語言用法獲得的字義,構成解釋的出發點和界限,若字義存在多種意義可能,可通過法律的意義脈絡確定規范的含義。假使依法律的字義及其意義脈絡仍然有作出不同解釋的空間,則應優先采納最能符合立法者規定意向及規范目的之解釋(即歷史的目的論的解釋)。*參見前注④,卡爾·拉倫茨書,第207-220頁。魏德士強調指出,任何解釋首先都是一個歷史的研究任務,只有對規范產生歷史和歷史的規范目的進行解釋,才能使客觀規定的要求內容具有可能的清晰性。*參見[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丁曉春、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331頁。對憲法第35條性質的解釋,*徐文在探討憲法第35條性質的過程中區分了條款本身的性質與條款內容的性質,指出“憲法第35條的性質和它所保護言論自由的性質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認為“條款的性質是由其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決定的。”這一論斷顯然與人們使用“條款”這一語詞的日常習慣相違背。因為當我們談及某條款時,往往所指的就是該條款規定的內容,而不是其他。即探討該條款到底屬于保護個體自由的條款還是保護政治自由的條款,其本質是在探求該條在當前我國憲法規范體系之中具有何種標準意義的問題。在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難以得出確定結論的情況下,回溯到該條款制定與變遷的歷史過程,無疑是探求憲法第35條性質的重要途徑。
我國憲法第35條源自1954年新中國制定的第一部《憲法》(以下簡稱:“五四憲法”)第87條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規定。而“五四憲法”第87條源自1954年3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的“五四憲法”初稿第80條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規定。為探究該條款的規范宗旨,需要詳細研究立憲資料中記載憲法起草工作者規范意圖的討論記錄。“五四憲法”初稿第80條的起草過程的討論記錄顯示,該規定被憲法起草委員會視為政治自由條款。1954年5月6日至22日,憲法起草座談會各組召集人聯席會議對“五四憲法”初稿進行了深入討論,針對第80條,田家英指出:“言論、出版等自由,恐怕要加以保證;宗教信仰自由,不好加保證。因此,準備分兩款寫,第1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公民在享受這些自由的時候的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第2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隨后,胡愈之提出:“宗教信仰自由,是否可另列一條,因為公民的意義搞清楚了,政治權利的意義也就搞清楚了。所謂政治權利,一是選舉權,一是言論、出版等等的自由。信仰宗教自由,不是政治權利,另列一條好。”周鯁生也提出:“宗教信仰自由還是單列一條好,言論、出版等自由是政治權利,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基于上述討論,田家英提出:“這一條就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公民在享受這些自由的時候的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宗教信仰自由另寫一條,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韓大元:《1954年憲法制定過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頁、第251頁、第252頁。憲法起草座談會各組召集人聯席會議的上述意見被《憲法草案座談會各組召集人聯席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的修改意見》所采納,最終形成“五四憲法”第87條。*“五四憲法”中言論自由條款的設置借鑒了蘇聯1936年憲法的經驗。蘇聯1936年憲法第125條規定:“為了適合勞動人民的利益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法律保障蘇聯公民享有下列各種自由:(一)言論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會自由;(四)游行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這些權利的保證是:印刷廠、紙廠、公共場所、街道、郵電和其他一切為實現這些權利所必要的物質條件,都供勞動者和勞動的組織和團體享用。”韓大元:《外國憲法對1954年憲法制定過程的影響》,《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4期。
針對“五四憲法”第87條,許崇德教授指出:“1954年憲法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都是公民表達意見或者發表政見的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人民除了派遣代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這種基本的形式外,人民應該有直接的自由權利對于國家事務發表意見、表明態度。否則的話,假如沒有表達意見的政治自由,不能對國家機關提出積極的批評和建議,那么,社會主義民主將無從談起。所以,憲法第87條的規定是我國的權力屬于人民的一種體現。”*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頁。韓大元教授指出:“憲法第87條的規定是國家權力屬于人民原則的具體體現。憲法規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指的是我國人民有權對國家和社會各種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提出各種合理化建議,討論各種問題,特別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權對國家機關活動提出批評。”*同前注,韓大元書,第412頁。可見,許崇德教授和韓大元教授都認為“五四憲法”第87條是源自人民主權理論的政治自由條款。這與制憲者的規范意圖相契合。
現行我國憲法第35條言論自由條款繼承了“五四憲法”第87條的政治自由屬性。針對憲法第35條言論自由條款的性質,許崇德教授指出:“憲法的哪些規定應屬于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的范圍,這個問題似乎是不容爭議的。因為人民法院往往要宣告剝奪某個已被判定為犯罪的公民的政治權利,這個政治權利的內容必定是確定的。不然的話,在執行的時候就會出現困難。政治權利的內容包括:憲法規定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這是普遍認可的觀念。”*同前注⑧,許崇德書,第493頁。許崇德教授的這一觀點極具說服力,一方面,許崇德教授作為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的成員深度參與了1982年憲法的制定過程;*1980年9月10,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名單;9月15日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設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胡喬木為秘書長;9月17日,秘書處吸收王叔文、肖蔚云、孫立、許崇德為秘書處成員。參見前注⑦,許崇德書,第2271-2272頁。另一方面,將憲法上的言論自由解釋為政治權利是出自全國人大的權威解讀,具有高度的民主正當性。早在1979年全國人大制定的《刑法》第54條中就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納入到可被剝奪的政治權利范圍之中,1982年我國憲法施行后,刑法繼續沿用這一條款,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
此外,將憲法第35條解釋為政治自由條款,也符合強化對國家公權力民主監督和制約的客觀目的。我國憲法將基本權利一章置于國家機構之前,其意在強調基本權利相對于國家權力的優位性。憲法第35條言論自由條款被置于基本權利章的前列,體現了制憲者對于言論自由之民主監督價值的高度重視。言論自由在促成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意見討論以及監督和制約國家公權力運行方面發揮著無可替代的功能。當前我國公權力監督方面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而避免“把質疑者和監督者關進籠子里”。在現實生活中,政治性言論的表達往往容易受到嚴格管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對憲法保護的“言論”的性質存在根本性誤解。*有學者將“言論”區分為“公共言論”與“私人言論”兩種類型,認為憲法意義上的言論是指以政治表達為核心的“公共言論”。同時,該學者認為我國當前批評公共事務或官員的言論容易受到嚴格管制,而貶損他人名譽、隱私等民事法益的言論卻被寬容以待,其根本的原因是對言論在不同法律關系中的性質、功能及其規范性含義存在某種根本性誤解。參見姜峰:《言論的兩種類型及其邊界》,《清華法學》2016年第1期。將憲法第35條解釋為政治自由條款,把憲法保護的“言論”嚴格限定于政治表達領域,進而為政治性言論的法律規制設定嚴格的憲法界限,有助于充分保障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強化對國家公權力的民主監督和制約,這也是“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題中之意。
因此,將現行憲法第35條解釋為源自人民主權理論的政治自由條款,既符合歷史上制憲者的規范意圖,也符合強化對國家公權力民主監督和制約的客觀目的,是更為妥當的解釋方案。
三、我國憲法第41條兼具個體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雙重屬性
徐文指出我國憲法第41條不但是言論自由條款,而且是一個以人民主權理論為基礎的政治自由條款。其立論依據如下:其一,許崇德教授對“五四憲法”第87條的說明中將“表達意見的政治自由”與“對國家機關提出積極的批評和建議”相提并論,政治表達的實質即在于對政府提出批評、建議,而批評、建議權規定于現行憲法第41條之中;其二,從該條款的句式表達看,它是一個以公共參與而不是個體利益滿足為指向的憲法條款,旨在強調批評建議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體現的是公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其三,該條款僅受自身但書條款的限制,*我國《憲法》第41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但書條款是一個隱含著絕對保護邏輯的限制條款。政治自由的享有以受到限制為例外。*參見前注①,徐會平文。以下逐一分析上述論據。
徐文第一個論據引用許崇德教授對“五四憲法”第87條的說明,意在說明對國家機關提出批評和建議屬于政治自由,進而推導出包含批評、建議權的憲法第41條屬于政治自由條款。僅就批評、建議權而言,筆者對徐文的論證不持異議。然而,徐文忽視了憲法第41條除規定了批評、建議權之外,還規定了申訴權、控告權、檢舉權和賠償請求權。考察憲法第41條中上述六項權利的入憲史可以發現,控告權和賠償請求權先入憲,之后依次為申訴權、批評權、建議權和檢舉權。公民的控告權和賠償請求權源自“五四憲法”第97條。*“五四憲法”第9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由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1956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主張,憲法第97條應考慮增加對控告人不許進行打擊報復的內容。*參見前注⑦,許崇德書,第268頁。1975年的我國憲法第27條吸納了毛澤東的這一建議,規定:“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1978年的我國憲法第55條進一步增加了申訴權,規定:“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有權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控告。公民在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有權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申訴。對這種控告和申訴,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1982年我國憲法第41條在此基礎上修改增加了批評、建議和檢舉權。針對我國憲法第41條對之前幾部憲法近似條文的修改,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成員肖蔚云教授指出:“新憲法規定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的權利,這是綜合了過去幾部憲法的規定,又增加了批評、建議、檢舉的權利,同時增寫了‘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肖蔚云:《論新憲法的新發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頁。因此,憲法第41條是一個綜合性條款。徐文若論證該條為政治自由條款,除應論證批評、建議權的政治自由屬性外,還需要論證另外四項權利也屬政治自由。此外,如前所述,許崇德教授對“五四憲法”第87條的說明,側重點在于表明這部憲法第87條規定的言論自由是基于人民主權的政治自由,并且這一政治自由包括“對國家機關提出積極的批評和建議”,意在強調第87條言論自由條款的政治自由屬性。
對于上述論據的不足,徐文的第二個論據從文義解釋的角度加以補充,認為憲法第41條是一個以公共參與而不是個體利益滿足為指向的憲法條款。從文義上分析,對國家機關及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和檢舉權確實體現公民的政治參與,但作為個體權利救濟權的申訴權、控告權和賠償請求權,其顯然屬于以個體利益保護為指向的權利,盡管這些權利的行使在客觀上具有強化民主監督的功能。正如有學者分析憲法第41條的六項權利時所指出的,真正屬于政治性權利的只有批評權、建議權、檢舉權,而控告權、申訴權、賠償請求權,則應該屬于獲得權利救濟的權利,這部分權利跟政治制度無關,相當于請愿權。*林來梵:《憲法學講義》(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頁。
徐文的第三個論據認為現行憲法第41條的政治自由條款性質,可以從其僅受自身但書條款的限制中得到進一步證明,因為但書條款是一個隱含著絕對保護邏輯的限制條款。這一論據至少面臨如下詰難。
其一,某個憲法條款是否屬于政治自由條款,與該條款是否僅受自身但書條款的限制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憲法中基本權利的但書條款是對基本權利的限制,憲法既然側重于對基本權利的保護而不是限制,憲法權利的但書的條款就不應該太多。*馬嶺:《憲法權利但書與憲法義務》,《當代法學》2009年第3期。在我國憲法文本上,基本權利的但書條款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概括性但書條款,比如憲法第51條對基本權利的概括限制;另一種為具體基本權利條款后面附著但書條款,比如憲法第36條第3款關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但書條款和本文所述憲法第41條第1款的但書條款。*我國《憲法》第36條第3款規定:“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某項基本權利條款后面附有但書條款,其說明對于此項權利而言這一但書條款特別重要,但并不能據此推導出該項基本權利的特殊性質。
其二,憲法第41條的但書條款并非蘊含著絕對保護的邏輯,相反,該條但書條款是對公民申訴、控告、檢舉權的特別限制,是制憲者基于文革教訓所作的特殊安排。許崇德教授回憶彭真參與1982年憲法修改工作時指出:“彭真根據‘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大字報的內容是假的,特別加上:‘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許崇德:《彭真與1982年憲法的修改工作》,http://www.zgdsw.org.cn/n/2015/0716/c244516-27316121-3.html,2017年6月10日訪問。憲法第41條的這一但書條款相對于憲法第51條更為具體,在涉及對公民申訴、控告、檢舉權的限制方面,具有優先適用性。
其三,從憲法第41條的句式語法上分析,該條的但書條款并不適用于對批評、建議權的限制。憲法第41條在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之后,用分號作區隔,隨后規定“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這意味著分號之前的批評、建議權并不在但書條款的限制范圍內。那么,這是否蘊含著我國憲法對批評、建議權絕對保障的邏輯,對此存在不同解釋。*參見侯健:《誹謗罪、批評權與憲法的民主之約》,《法制與社會發展》2011年第4期。
因此,憲法第41條并不完全是以人民主權理論為基礎的政治自由條款,而是一個兼具個體自由與政治自由雙重屬性的復合性條款。
四、憲法第35條與第41條共同構成言論自由憲法保障的規范基礎
徐文區分了兩種言論自由觀,即言論自由的個體自由觀和言論自由的政治自由觀,*根據徐文的論述,在言論自由的個體自由觀念之下,言論自由被視為一項以個體為指向和依歸的自由,對言論自由正當性的辯護以及理論和制度保護的探討都以個體為中心而展開;言論自由的政治自由觀是一種從人民主權角度來看待言論自由的觀念。在政治自由的觀念中,言論自由是一種以人民主權為指向和依歸的自由,其正當性辯護及其理論和制度保護的探討以人民主權為中心而展開。參見前注①,徐會平文。并在對探討兩種言論自由觀的歷史傳統和中國憲法學界有關言論自由問題的思考后得出如下結論:其一,個體自由一元觀支配著中國憲法學界有關言論自由問題的思考,具體體現就是當前憲法學界一致同意將言論自由憲法保護的探討建立在憲法第35條的基礎上;其二,當前中國憲法學界沒有能自覺意識到關系論政治自由和本質論政治自由的區別,*根據徐文的論述,人民主權與“言論自由是政治自由”之間存在本質聯系,而人權意義上的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之間僅僅具有經驗或者說或然意義上的關聯,但我們往往從經驗立場出發認可言論自由與民主的關系,從而認為言論自由是政治自由。前者為本質論政治自由,后者為關系論政治自由。參見前注①,徐會平文。給予政治自由觀念以適當理論表達,從而將憲法第41條保護的政治自由融入到了憲法第35條之中,把政治自由降低到了個體自由的地位。*參見前注①,徐會平文。
針對徐文上述第一個結論,存疑的是:個體自由一元觀完全支配著中國憲法學界有關言論自由問題的思考嗎?答案是否定的。中國憲法學界以許崇德教授為代表的諸多憲法學者都是從人民主權的角度分析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條款的,普遍將憲法第35條解釋為保障政治權利和自由的條款。*持這種觀點的較有代表性的學者及其見解主要: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206頁;林來梵:《憲法學講義》(第二版),第371-372頁;蔡定劍:《憲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頁;張千帆主編:《憲法》(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250頁;周葉中主編:《憲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頁;童之偉、殷嘯虎主編:《憲法學》(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頁;周偉:《憲法基本權利 原理·規范·應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頁;吳家麟:《憲法學》,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頁。并且,從文義解釋角度分析,“言論”的字義涵蓋了對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和“檢舉”,憲法學界將對言論自由憲法保護的探討建立在憲法第35條的基礎上,既符合制憲者的規范意圖,也符合憲法學研究從憲法文本“字義”出發的一般邏輯。
徐文上述第二個結論認為中國憲法學界并沒有能自覺意識到關系論政治自由和本質論政治自由的區別,因此將憲法第41條保護的政治自由融入到了憲法第35條之中。對于許崇德教授等將憲法第35條解讀為人民主權為基礎的政治自由的憲法學者來說,其本身是從本質論政治自由角度理解憲法第35條的言論自由的,因此排除了關系論政治自由的影響。
倘若將憲法第35條理解為保障政治權利和自由的條款,那么接下來面臨的問題便是如何在保障政治性言論方面妥當地處理憲法第35條與第41條的關系。對此,憲法學界是否會將憲法第41條保護的政治自由融入到憲法第35條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國憲法之所以將憲法第35條言論自由條款包含的“對國家機關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和檢舉權”明確規定于憲法第41條,其意在“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加強人民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監督,改進國家機關的工作,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肖蔚云:《論憲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頁。當涉及對國家機關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和“檢舉”,其會同時落入憲法第35條和第41條的規范領域,由此會出現憲法的法條競合。對于法條競合的處理,通常適用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的原則。因為憲法第35條言論自由的規范領域涵蓋了憲法第41條批評權、建議權和檢舉權的規范領域,對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建議權和檢舉權的保障優先適用憲法第41條。*杜強強:《基本權利的規范領域和保護程度——對我國憲法第35條和第41條的規范比較》,《法學研究》2011年第1期。憲法第35條作為政治言論保障的兜底條款,用以保障那些未能落入憲法第41條規范領域的政治言論。憲法第35條與憲法第41條之間的相互合作構成憲法上言論自由保障的規范基礎。
此外,徐文認為政治言論兼具個體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雙重屬性,當將政治言論視為一般性政治表達時,它受憲法第35條保護并受第51條限制,將政治言論視為批評建議時它就會受憲法第41條保護并受其自身但書條款限制。同一政治言論會因理解不同而受兩個不同憲法條款保護并因此而受到兩個截然不同憲法原則的限制。*參見前注①,徐會平文。由其引出的問題是:政治言論如何兼具個體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雙重屬性呢?按照徐文的觀點,個體自由是以個體利益為指向的,倘若是政治言論,其便是以政治生活參與為指向,而不可能同時以個體利益為指向。即使現行這一雙重屬性能夠成立,一般性政治表達受憲法第35條保護,批評權、建議權受第41條保護,也不一定能確定地得出同一政治言論會受兩個不同憲法原則限制的結論。正如上文分析所指出,批評權、建議權并不在憲法第41條但書條款的限制之列,那么其在憲法規范體系上便有受憲法第51條限制的可能性。
即使憲法第41條的批評、建議權和其他一般性政治性言論都受憲法第51條的限制,這也并不意味憲法對政治言論的保護強度一定會降低。憲法第51條只是一個基本權利的概括限制條款,我們可以對這一“概括限制條款”的適用范圍進行限縮,以此建構一個“基本權利限制的限制”的釋義學體系。這一體系可包括兩個層次:其一,法律保留原則的確立與類型化;其二,比例原則的引入。*張翔:《憲法釋義學 原理·技術·實踐》,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148頁。在涉及對政治性言論限制的司法審查過程中,可對憲法第51條的適用范圍加以嚴格限縮,比如在政治性言論審查中引入“實際惡意”原則等,*石畢凡:《誹謗、輿論監督權與憲法第41條的規范意旨》,《浙江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以強化對政治言論的憲法保護。
另外,可能有討論空間的問題便是非政治性言論的憲法保護問題。若從制憲歷史上分析,憲法第35條保護的言論屬于政治性言論,因此非政治性言論并不包含在這一條款的保障范圍內,但若從字義解釋的角度分析,非政治性言論在“言論”的字義射程范圍之內,將非政治性言論納入憲法第35條的保障范圍具有一定的解釋空間。*陳明輝:《言論自由條款僅保障政治言論自由嗎》,《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7期。只是,即使將非政治性言論納入憲法第35條保護范圍,其在受保護的強度上顯然要弱于處于規范核心領域的政治性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