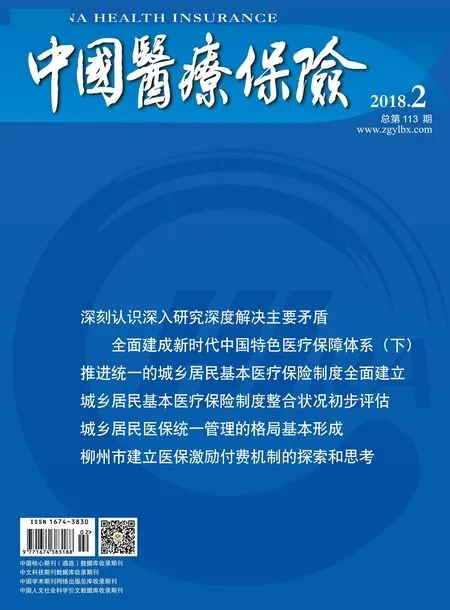職工上班時“串崗”受傷能否認定工傷
文/黃慶慶
案情回放
田某是某機械設備制造有限公司車間操作工。某天,田某在工作過程中,見同車間班組的其他崗位人手緊張,影響到自己崗位的操作和工作效率,于是前去幫忙。在幫忙過程中,因操作不當導致左手被機器碾壓,后送往醫院治療,診斷為左手碾壓傷、左手背皮膚逆行撕脫傷、左手掌皮膚裂傷。事后田某向當地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當地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受理后進行立案調查,于數日后作出工傷認定決定,認定田某屬于工傷。公司不服,向當地法院提起訴訟。法院經審理認定當地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法院維持了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定田某為工傷的決定。
爭議焦點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田某在非本人工作崗位受到的事故傷害是否應當認定為工傷。
田某認為,事故發生前,自己也多次幫助其他崗位工作,公司并沒有制止,應當屬于有利于公司利益的行為,因此受到的傷害應當認定為工傷。
公司認為,田某是公司的招用工人,在車間卷板機崗位工作,事發當天,田某未經公司和車間管理人員的指派和許可,擅自到型材彎曲機崗位開機操作導致受傷。因其受傷并非在本職崗位上,又未經公司臨時指派,故不符合工傷認定的條件。田某的行為屬于“串崗”,他所受到的傷害并非履行本職工作所致,不符合認定工傷條件。
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認為,事發當天,田某是在上班時間和工作場所,雖然不是在本崗位工作時受傷,但協助其他崗位仍然屬于工作原因,符合工傷認定的三個基本要素。而且,出事故前,田某曾和其他工人多次到其他崗位幫忙,公司并沒制止,他的工作應屬正常的工作范圍,應予以認定工傷。
案例評析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在本案中爭議的焦點在于對勞動者“串崗”行為的認識,“串崗”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脫離自己的工作崗位,從事與工作無關的行為,此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違反了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那么在工傷認定方面如何界定此種行為呢?
首先,從工傷認定的基本要素來看。工傷認定的三個基本要素: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和工作原因。“工作時間”,包括職工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或者用人單位規定的工作時間以及加班加點的工作時間。合法的加班期間以及單位違法延長工時的期間,都屬于工作時間。具體到本案來看,田某的“串崗”時間當然屬于其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包括職工日常工作所在的場所和領導臨時指派其所從事工作的場所,還包括職工在工作時間內往來于多個與其工作職責相關的工作場所之間的合理區域。田某“串崗”行為只是導致具體工作崗位及相關工作內容有所變動,并不能改變田某仍在工作場所內工作的事實。“工作原因”,是指職工受傷與從事工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認定工傷的核心要素。工作原因與本職工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勞動者雖不是在本職崗位上受傷,但其客觀上“串崗”從事的工作與其本職工作也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其行為的目的仍是為了用人單位的利益,并非為自己謀取私利,應當認為屬于工作原因。
其次,從工傷認定的歸責原則來看。工傷保險施行“無過失補償”的原則,職工違反單位規章制度不是影響確定工傷成立的因素。職工違反單位規章制度致傷,可以按違反勞動紀律對其進行處理,但不能據此作為不得認定為工傷的理由。《工傷保險條例》并未將是否在本職工作崗位上工作規定為認定工傷的法定條件,也未將職工離開本職崗位到其他崗位受傷作為認定工傷的法定排除條件。只要職工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因工作原因受到的傷害,就應當認定為工傷。
第三,從工傷認定的立法本意來看。我國對工傷認定的立法宗旨和原則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主觀無惡意的職工權益,使其因工作原因遭受傷害或者患職業病后能得到及時的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因此,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在適用《工傷保險條例》時,應當遵循這一立法本意,充分保護而不是限制受傷職工的合法權益。職工“串崗”主觀上并非故意,因此將“串崗”受傷認定為工傷,保障因工作造成傷害的勞動者能夠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是符合立法之本意的。
工傷認定是一項嚴格的行政行為,應當嚴格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本意來執行,而不能隨意擴大,這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任何人不應以一己之見釋立法本意,否則就會造成有法不依或執法不嚴的局面,有悖于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