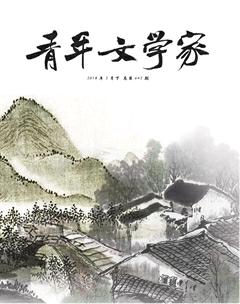熊式一的世界性
摘 要:熊式一早年因為教育部的沒有留洋背景而不能被聘為國立大學英文教授這一規定而憤然出英留學,從此開啟他的流散人生之旅。在海外,他結交國際友人,用雙語進行創作和翻譯的文學作品獲得巨大國際影響力,成為世界性的Shih-I Hsiung。
關鍵詞:熊式一;流散人生;世界性
作者簡介:陳蓉蓉(1983-),女,漢,江西萍鄉,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6-0-03
熊式一是世界的。從鮮有人知的熊式一到蜚聲國際的Shih-I Hsiung,印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墻內開花墻外紅”。熊式一的世界性,體現在他流散人生中,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和翻譯創作中,體現在他的作品的影響力中,也體現在他所結交的朋友中。
一、流散人生
熊式一一九0二年生于江西南昌。幼時從母習經史古文,自十一歲時起,便喜“附庸風雅”及“高攀當時當地的名士”[1]。在學習國學的同時,學習英文。后來進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英文科專習英文,于一九二三年畢業。
憑借著深厚的中文功底和不俗的英文水平,熊畢業后在北京、上海、南昌各地公私大專院校前后教過幾年書——不僅教英文,還教中文。可惜熊在國內教書的命運實在坎坷。“不管我教得多認真多好,多么受學生歡迎,每逢有一個好一點兒的職位空缺,如是屬國文科的,一定是他們國文系畢業生得去了。若是英文科的,留英留美回國的,哪怕只出過一次洋,鍍了一點金就回來,好位置一定會全給他們”[1]。有一次,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源先生聽聞徐志摩贊嘆熊對英文戲劇很有研究,于是專程拜訪熊式一,想聘請熊就任正教授。然而當陳聽聞熊未曾出洋留學,便凄然搖頭道歉,說根據教育部明文規定,熊的資格不能受聘于國內任何國立大學的正教授。
正是受此事的刺激,熊式一決定破釜沉舟,出洋留學。一九三二年,熊只身來到英倫,為了功讀一個英國文學博士學位。熊式一的流散人生自此開始。誰知這一出國,便是數十年!
來到英倫后,熊創作了四幕英文喜劇《王寶川》,翻譯了《西廂記》,創作了話劇《大學教授》和小說《天橋》,這些作品在國外都影響巨大。
二戰后期,熊式一在不了解國內政治局勢的情況下作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為蔣介石寫傳記。一九四八年,英文傳記Life of CHIANG KAI-SHEK(《蔣介石傳》)出版。雖然此書的出版增進了歐美等英語地區人士對中國的了解,但在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由國共聯合抗日轉向內戰的時期,此書的出版對熊式一及其家人來說無異于一場大災難。“熊式一當即遭到了國內作家群的集體排斥,他被冠之以右翼作家。新中國成立之后,熊式一繼續遭到口誅筆伐。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他被批為‘罪大惡極的反動作家——不光自己遭到排斥,就連子女和親戚也屢遭批斗……”[2]
如果說當初因為沒有留洋背景遭受歧視而不顧一切遠離家園,為了學業和事業而主動開啟自我的流散人生之旅的話,那么后來的《蔣介石傳》則把熊式一牽扯進國內的政治斗爭而無法返回家園,被迫繼續自己的流散人生。一九四九年,熊式一應來自捷克的郝壤(Gustav Haloun,兼通英德兩國文學)教授之約,到劍橋大學教授近代文學和元代戲曲兩門課程。后來新加坡的華僑要開辦南洋大學(現在的新加坡大學),熊應約去其時的劍橋文學院任職。一九五五年底,熊從南洋大學文學院院長卸任后來到香港,創辦清華學院。一九八二年熊從清華學院退休,一直在香港、臺灣等地居住。直到一九八八年,年近九十的熊式一終于回到大陸省親,看望在北京工作的幾個子女。一九九一年八月二日,病逝于北京,終究未能了卻生前回故土江西南昌之夙愿。逝世后卻安息在故土,終于葉落歸根,結束了聲譽響徹國際而又顛沛流離的一生。
20世紀初中國人在海外用英文創作并蜚聲國際的有三人:林語堂,蔣彝和熊式一。林蔣的作品在大陸出版很多,并且廣為人知,而熊式一在大陸卻鮮有人知,這大概和當年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作為文人,熊式一無意于政治,然而流散的一生卻始終與政治緊密相聯。第一次遠離國土是因為“中華民國教育部嚴擬的蠢規定”[1],使熊的抱負不得施展,不得不出洋鍍金;第二次身在異鄉不得回國是因為在國內內戰嚴峻,蔣介石逃亡臺灣之際作了《蔣介石傳》,從此熊在大陸便“臭名昭著”,不僅曾經的文學成就和國際聲譽無人提及,連回國探親的機會都不可得。王寧在《流散文學與文化身份認同》中寫出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呈現出的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們出于對自己祖國的某些不盡人意之處感到不滿甚至痛恨,希望在異國他鄉找到心靈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國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難以動搖,他們又很難與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國家的文化和社會習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召喚出來,使之游離于作品的字里行間。”[3]熊式一對國內的政治也表示過不滿,然而大陸對他不利的種種政治,并沒有打垮他,更沒有讓他懷恨祖國,反而刺激他在國外不斷努力,筆耕不輟地宣揚中國文化精髓,不僅為自己贏得了國際聲譽,更讓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為瓦解西方的東方主義作出了貢獻。
二、雙語創作,溝通中西文化
熊式一一生用中英雙語進行交流和創作。根據龔世芬(新西蘭)的《關于熊式一》,熊式一的創作生涯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學畢業起到一九三二年底出國之前,熊式一用中文翻譯了西方諸多名家的英文作品,比如巴蕾、蕭伯納的作品。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三年抵英起,至五十年代初。此段時間熊式一旅居英國,用英文創作了《王寶川》、《西廂記》、《大學教授》等劇,并創作了英文小說《天橋》。這幾部作品都是用英文寫就的關于中國的故事,或為宣傳中國文化精髓,或為表達愛國熱忱。第三階段自五十年代移居香港之后至一九九一年與世長辭,熊式一用中文自譯了在英期間創作的英文作品,并用中文創作了一系列反應現世的戲劇作品,如《女生外向》、《事過境遷》、《梁上佳人》等。[4]endprint
熊式一一生筆耕不輟,流利地運用中英雙語進行翻譯和創作,為中國譯介西方的名家名著,介紹西方文化和思想,同時為西方國家介紹中國文化、思想及社會現狀,打破西方人對中國人刻板而不良的印象,瓦解西方久存的東方主義,讓西方公眾了解真實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他的文學創作和翻譯創作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架橋鋪路的作用。
三、作品的國際影響力
出國前,熊式一雖翻譯了巴蕾、蕭伯納等名家的作品,得徐志摩賞識,但畢竟還未有大成就。然而自一九三二年出國以后,人生際遇大不相同。從第一部英文戲劇《王寶川》在國際上的巨大成功到英文小說《天橋》出版后在西方的洛陽紙貴,熊式一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生一躍而成為蜚聲國際的戲劇家,其文學作品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王寶川》最初的出版和演出雖頗費周折,但最終的成功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從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在倫敦的劇院演出,便反響巨大,此后兩年多,在倫敦前后上演九百多場,還搬了兩三次戲院。在有一千二百多個座位的薩和愛劇場,瑪麗皇后曾攜兒媳和孫女(后來的伊麗莎白女王二世)親臨觀看八次之多。倫敦演出的巨大成功讓該劇名聲大噪。之后《王寶川》飛越英吉利海峽,在瑞典、捷克、荷蘭、愛爾蘭、德國等歐洲大陸其它國家相繼上演。一九三五年《王寶川》來到美國紐約百老匯的布茲劇院演出——這是中國劇作家第一次把作品搬上百老匯舞臺,意義非凡。之后在芝加哥及東西中部和美國西岸各地演出,共計九百多場,在美引起不小的轟動,就連羅斯福總統夫人在觀劇之后贊嘆不已,親自接見了熊式一及演出的主要演員,并合影留念。
《王寶川》劇本出版時由倫敦大學英文文學教授亞伯康貝作序,出版后銷路甚廣,評論界對《王寶川》的反響很不錯。 “《西。克。切士忒頓》文學周刊說:‘這是一篇小型的杰構。《觀察者》文學周刊中名詩人愛德猛伯蘭敦說:‘這是優美文化的象征。《太陽神》期刊說它是‘一顆頭等水色的寶石,而鑲嵌得美麗奪目。《泰晤士星期日》周刊說作者‘是一個難逢難遇的迷幻人的魔術家。”[1]
此外,《王寶川》在世界其他各國都有譯本,而且在各國的大都市都有演出。但是有的譯本對原文纂改較大。比如,在荷蘭,劇名改為《繡球緣》,主角改名為 “珠川”,認為珍珠比金銀更寶貴;在捷克,王寶川改名為“王春泉”;在匈牙利,改名為“王鉆川”。各種譯本,雖有的改得面目全非,但從另一方面說明該劇影響力實在太廣,深受世界人民的喜愛。
《王寶川》的巨大成功并未讓熊式一得意忘形,他深知《王寶川》是一出通俗的商業劇,算不上文藝精品。為了讓世人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熊式一隨后花費十一個月的時間逐字逐句譯出了元曲精品《西廂記》。出版后,雖不如《王寶川》那般一紙風行,但是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稱贊,并且影響深遠。大詩人博萊(GORDON BOTTOMLEY)為之作序贊譽。蕭伯納讀完《西廂記》,寫信給熊式一道:“我非常之喜歡《西廂記》,比之喜歡《王寶川》多多了!《王寶川》不過是一出普普通通的傳奇劇,《西廂記》確是一篇可喜的戲劇詩!可以和我們中古時代戲劇并駕齊驅。卻只有中國十三世紀才能產生這種藝術,把它發揮出來。”[1]。熊式一所譯的《西廂記》出版三十年后,西方仍找不到一本可讀性超乎其上的英譯本。西方各大名校亦用《西廂記》作教材。熊在劍橋大學教元曲課時,用《西廂記》做課本。其它英美大學的中文系或亞洲研究系,也有許多用了熊式一譯的《西廂記》做教材的。
《大學教授》一劇雖生不逢時,影響流傳,卻依舊得到名戲作家及詩人唐山尼爵士(Lord Dunsany)恭維備至的序文,并在摩溫戲劇節同蕭伯納的戲劇一同上演。之后出版的英文小說《天橋》,再一次把作者推向文學創作的巔峰。 “《天橋》出版的當月就銷售一空,不得不在同月再加印,同年就重印了四五次,第二年又重印了四次,最終重印了十次之多,真可謂洛陽紙貴。”[5]之后馬上就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捷克文、荷蘭文等各種文的譯本,在各國問世。可見《天橋》如《王寶川》一般,已流入世界各地,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文藝界對《天橋》一直予以好評和贊許。而作者最引以為榮的,是這三個人的重視:一是當時英國桂冠詩人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為《天橋》作代序詩,二是大文豪威爾斯(H.G.Wells),在他的著作中對《天橋》的評論,他認為“《天橋》是一本比任何關于目前中國趨勢的論著式報告更啟發的小說……是一幅完整的、動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圖畫,描述一個大國家的革命過程”[6],三是歷史學家陳寅恪讀后贈詩三首(兩首絕句,一首七律)。
熊式一的文學作品在國際上流傳深遠、影響深廣,大大拓寬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為世界性的Shih-I Hsiung。可貴的是,在東方主義風行西方世界的時代,熊式一并不迎合此潮流,即通過丑化中國人而取悅西方人來讓自己成功,相反,他懷著滿腔的愛國熱忱,為了瓦解西方人眼中刻板丑陋的中國人形象,為了向西方世界重構形象生動而真實的中國人,為了宣揚中國文化精髓,為了讓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社會而進行創作的。因此,熊式一作品的國際影響力,對在西方世界重構真實的中國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國際知名友人
根據熊式一的回憶,他自小喜歡“高攀名士”,所以一生之中,知名友人和忘年交,中國的或國外的,非常之多。熊自身為有這些友人而引以為豪,反之,熊能取得如此之成就,在國際上名聲斐然,自然少不了這些友人的提攜和幫助。
出國之前,熊式一在北京上海南昌等地輾轉,以文會友,交往的人大都大他二三十歲,甚至于四十歲,“如林琴南(紓)、張菊生(元濟)、黃伯雨(霖)、沈信卿(恩孚)、江問漁(以字行)、黃任之(炎培)、曾農髯(熙)、陳師曾(衡恪)、樊樊山(增祥)、陳半丁(年)、王夢白(云)等”[1]。徐志摩對熊式一也是頗為賞識,當年讀完他譯的巴蕾戲劇,贊嘆不已,并四處宣揚,極力推薦。
出國之后所結交的國外朋友,大都地位頗高或成就斐然。出國到英倫后的第一個朋友是張菊生介紹的駱仕廷(Sir James Lockhart)(曾在香港做過輔政司,香港的洛克道是紀念他的)。后來熊英譯《西廂記》,便借用了駱仕廷家的藏書室,通過比較其中的十七種不同版本的《西廂記》,花了十一個月逐字逐句翻譯出來。在英倫期間,正值文藝當道時期,而倫敦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熊式一依舊憑借文字,結識了當時不少名家。如“蕭伯納(Berbard Shaw),巴蕾(J.M.Barrie),威爾士(H.G.Wells),平內羅(Sir Arthur Pinero),米恩(A.A.Milne),毛姆(Somerest Maugham)等”[1]。當然還有名校里的教授,如牛津大學的蘇提爾(Soothill)教授,霍克斯(David Hawkes)教授,劍橋大學的翟理士教授,倫敦大學的莊士敦(Sir Reginald Johnston)爵士等,這些教授都是名副其實的漢學家,為中西文化交流做了不小的貢獻,如莊士敦爵士曾任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外籍教師,著有《儒家與近代中國》、《佛教中國》等書。翟理士教授,翻譯了諸子史籍等,還編纂了漢英大字典。
熊式一最引以為豪的朋友應該是一九二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八十回憶》的四篇回憶錄中有一篇《談談蕭伯納》是專門講他眼中的蕭伯納以及他們之間的交情的。在一個蕭伯納名聲享譽世界的時代,每個文人都想攀附他籍他出名。而熊式一作為一名初出茅廬的劇作家,所作的劇作不僅能得到蕭的點評,還能和蕭的戲劇同臺演出(《大學教授》同蕭的《查理二世快樂的時代》在英國摩溫爾世界文藝戲劇節一同上演),這是多么榮幸的事情;況且私底下,二人雖年齡相距四十多歲,交情卻不淺,成為忘年之交,這又是多么難得的緣分。
熊式一一生喜交文人雅士,從幼時的“高攀”名士到出國之后的結交國際知名友人,他所結交的這些友人大都成為他的貴人,為他事業的成功、為他成為世界性的Shih-I Hsiung,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幫助,也是他人生當中不可忽略的一筆財富。
參考文獻:
[1]熊式一:《八十回憶》,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23、99、66、4、17頁。
[2]姜猛:《熊式一——沉浮海外的雙語作家》,《名人傳記》2015年第1期。
[3]王寧:《流散文學與文化身份認同》,《社會科學》2006年第11期。
[4]龔世芬:《關于熊式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2期。
[5]熊德輗:《為沒有經歷大革命時代的人而寫》,臺灣版序,熊式一《天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6]熊式一,香港版序,《天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