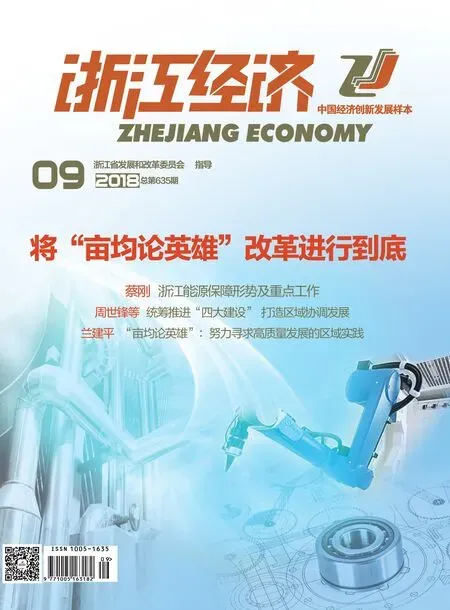政府數字化轉型下的信用監管
□王寧江
在政府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信用監管的意義在于提升政府監管效能。事前、事中和事后每個環節均可以做流程設計,但重點是事后
政府數字化轉型是趨勢,既是科技進步推動下的轉型,也是政府管理模式對科技進步的適應。各國和地區均面臨這樣的路徑選擇,回避不了,只有主動適應,才能有更好作為。
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難點是觀念的轉變,涉及職能設計部門、流程再造部門、業務執行部門、IT團隊等各個環節,每個環節的人員都要有大數據治理的理念,有實施數據記錄、分析和應用的思維習慣。只有切切實實地轉變了觀念,才可能提出符合數字化轉型趨勢的業務需求,由IT團隊幫助實現政府的大數據監管和治理。
政府數字化轉型和實施信用監管的基礎就是政府監管和治理數據的記錄,標準化的記錄!這既是生產信用產品的基礎,也是實施信用監管的基礎。否則,信用監管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將成為主線,貫穿于數字化轉型的始終。每一條記錄起碼應當有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或行業管理碼為唯一標識,以便做到主體識別。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統一信用代碼在應用環節的覆蓋率并不高。除了有記錄之外,還得保證記錄及時更新,只有動態的記錄才是有價值的。
在政府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信用監管的意義在于提升政府監管效能。事前、事中和事后每個環節均可以做流程設計,但重點是事后。
事前查詢信用產品。信用產品包括公共類信用產品,如省級信用條例規范的信用檔案和公共信用評價結果;市場類信用產品,如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生產的大數據產品、征信報告、評價報告等。查詢信用產品,主要是幫助解決監管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以便政府在組織實施監管前,全面了解監管和服務對象的主體信息,承諾制改革也可以在此環節展開。
事中開展信用評價。有了數據記錄,政府才可能組織評價畫像。有了評價,有了打分,才有可能實施分類監管、精準監管,這是一個遞進關系。做信用評價主要是解決政府監管的效率問題。如“雙隨機”抽查監管,完全可以依法對于信用評價優秀的主體,減低抽查頻次,對有多次被投訴舉報、異常名錄、失信行為、嚴重違法違規等評價結果較差的市場主體,增加抽查頻次,加大檢查力度。
這里所講信用評價是指公共信用評價,是基于政府監管所記錄的數據,依據一定的方法,對主體進行公共信用畫像,結果主要用于政府信用監管,也可以作為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開展市場化評價的參考。當然,政府也可以借助第三方服務機構,利用其數據和技術優勢,協助政府對主體進行評價畫像,作為有效支撐和補充。
事后實施信用聯合獎懲。我們講違法這個概念時,大家都會很清楚,就是指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講失德時,大家可能會停頓一下,提出自己的觀點,確實“德”有社會公德、職業道德等普遍性的標準,可能也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失德無非就是違反或違背這些標準和尺度的行為。那失信是什么,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答案。確實,信用帶有較為明顯的個體特征,評判守信和失信的標準往往是個體的契約或者承諾,因為相對人不同而有不同的評判結論。信用評判是個分散決策系統。另一個概念,誠信是公共的,主體的信用構成了全社會的誠信。
社會信用體系良好運行的核心機制是信用獎懲機制。守信者暢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難行。加強信用獎懲的一個有效制度設計是紅黑名單制度,抓兩頭、抓重點。科學制定紅黑名單認定標準、認定依據和認定程序,把信用檔案和公共信用評價結果信息作為認定紅黑名單的重要指標。同時,向社會公開紅黑名單結果,鼓勵推行社會性獎懲;向政府共享紅黑名單結果,依法實施行政性獎懲。信用聯合獎懲主要是解決政府監管的績效問題。
以上是一家之言,也可以理解為各行業領域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實施信用監管的“標準件”或“三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