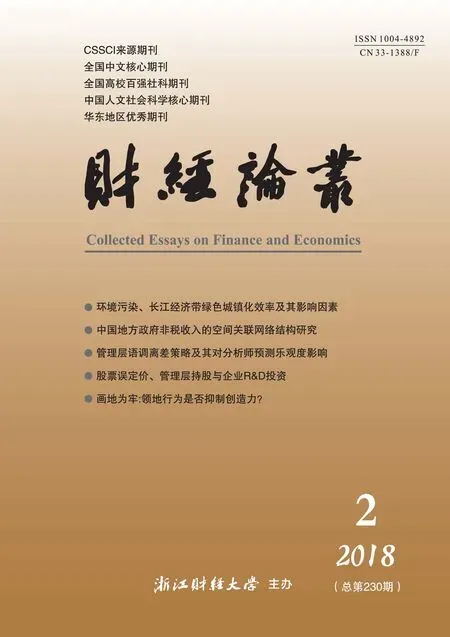職場中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的曲線關系
——自我效能感的情境機制
趙紅丹,江 葦
(1.上海大學管理學院,上海 200444;2.上海大學戰略管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一、引 言
組織公民行為是與組織中正式的獎勵制度沒有直接或外顯聯系,但能夠在整體上提高組織效能的一種個體行為[1]。由于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組織的運作成本不斷攀升,越來越多的組織開始要求員工更多地從事自身工作職責之外的組織公民行為,從而在不增加經營成本的同時盡可能的提高組織效能[2]。然而,這種特定的工作要求會耗費員工一定的額外工作資源,使得其在從事組織公民行為時會產生一種壓力感[3]。Bolino等(2010)將這種壓力描述為組織中的公民行為壓力(Citizenship Pressure,CP)[4],并將其定義為員工在從事職責外行為過程中所體驗到的壓力感[5]。雖然公民行為壓力已經得到研究者們的日益關注,但學界對于公民行為壓力究竟是好是壞仍闡釋不清。有害論的觀點強調公民行為壓力會導致工作-家庭沖突和工作-休閑沖突,并帶來較高的工作壓力和離職意愿[4];而持有益論的學者們則認為公民行為壓力不僅與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正相關,還有助于提高員工的工作投入和帶來工作-家庭增益[6]。從公民行為壓力研究的結果變量來看,多是聚焦于員工心理、情感等方面,較少關注員工創造力(Employee Creativity,EC)等結果變量。創造力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在當前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組織往往試圖通過鼓勵員工主動發揮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技能來刺激員工從事更多的創造性行為[7],以此促使員工創造力的提升并獲得競爭優勢。此外,根據以往公民行為壓力影響效果的兩面性,我們還期望檢驗這種雙面影響效應是否同樣適用于創造力領域。
同時,本文還將探究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二者之間的情境機制,即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SE)的調節作用。這是由于員工在過多地從事組織公民行為的過程中往往會造成資源緊張,而自我效能感則可能對緩解這種緊張起到一定作用。此外,工作要求-資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JD-R model)主要描述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二者之間的權衡關系[8],而連接公民行為壓力、自我效能感、員工創造力三者之間的關系紐帶主要就是工作要求和工作資源,故該理論能夠對調節作用進行有效解釋。具體而言,根據工作要求-資源模型,公民行為壓力作為一種特定的工作要求,會占用員工有限的工作資源,從而使員工更不容易感知到“挑戰”,同時還會影響員工創造力產生所需的資源[8]。而自我效能感作為一種認知資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資源缺乏的情況。
綜上,本文將根據工作要求-資源模型,同時把自我效能感作為調節變量,建立公民行為壓力、自我效能感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理論模型,進而深入探討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的作用機制,這無論是對于相關理論的完善與發展,還是指導管理實踐都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二、理論與假設
(一)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
公民行為壓力這一概念由Bolino等(2010)所提出[4],目的在于了解員工對從事超出自身工作要求范圍所感受到的壓力狀況。當今社會,越來越多的企業要求員工主動承擔更多的額外義務,然而這種特定的工作要求會使員工在自己本職范圍之外的任務上消耗較多資源,進而在從事公民行為時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公民行為壓力是指員工在從事組織公民行為(包括創造性行為、助人行為、建言行為等)過程中所體驗到的壓力感。公民行為壓力所強調的并非是組織公民行為在員工之間司空見慣的程度,而是聚焦于員工從事的那些本應自主決定的組織公民行為所感受到的壓力。作為一種特定的工作要求,公民行為壓力能夠為組織帶來一些積極的影響效果,如增加員工的工作投入、提高工作-家庭增益和組織公民行為等[4][6];但也有研究發現公民行為的壓力會降低員工幸福感、增加工作-家庭沖突和辭職意愿等[4][9]。
創造力(creativity)在心理學領域研究的較多,而在組織情境下對于員工的創造力展開研究則是一個較新的領域[10]。員工創造力是指員工在有關于服務、產品、方法或者流程上所產生的新穎并且有用的觀點或想法[7]。對于創造力而言,員工對其并非是遙不可及,更不是那些進行科技研發的人員所特有的,從事任何工作的員工都有可能表現出創造力[11]。富有創造力的員工,充滿了創意與激情以及敢于挑戰傳統的魄力,并且員工創造力作為組織進行創新和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之一[12],不但可以促使組織效能顯著提高,還可能影響到組織生存發展[13][14][15]。因此,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越來越多的企業希望通過要求員工從事更多的創造性行為來促進企業的成長,因為組織中的員工如果不具備創造力,就可能導致組織因欠缺進行持續創新的動力而停滯不前,最終被市場所淘汰[12]。
已有研究表明,公民行為壓力的作用結果存在兩面性[4][6],不難推斷不同情境下公民行為壓力對于員工創造力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兩面性。同時,公民行為壓力作為壓力的一種,其同樣具有壓力的一些特性,且關于壓力的一些研究結果對于公民行為壓力可能一樣適用。Van Dyne等(2002)認為當員工由于感到壓力而變得緊張、疲勞時,他們往往會忽略工作中極具挑戰性的方面,轉而采取常規行為模式,放棄自身的創造性行為[16]。與此相反,也有研究認為員工創造力的提升需要一定的外部刺激,要不然員工會固守原有的知識體系而停止創造,這時候需要一定的壓力來刺激員工,并激活員工進行創造的活力[17]。因此,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之間的關系可能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很有可能存在一種曲線關系。
具體而言,當公民行為壓力水平較高時,這種特定的工作要求會消耗員工自身所擁有的工作資源,導致資源不足。Eysenck(1995)研究發現,壓力可能會減少員工產生創新性想法所需要的認知資源,導致其產生更加平庸的觀點或創意,繼而降低創造力[18]。依據工作要求-資源模型,可以有效解釋不同水平(高、中、低)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當員工處于工作要求程度高、工作資源匱乏的情境時,會在一定程度上打擊員工的士氣,使其表現出消極的工作態度和行為,影響創造力的提升[8]。然而,當公民行為壓力水平較低(即低工作要求)時,雖然不會占用員工個人多少工作資源,但其可能因為幾乎感受不到任何創造性動力而處于一種過度的自我放松狀態,降低對于自身的要求,并且很有可能固守當前的知識或者忽視創造性工作中具有挑戰性的部分,阻礙個體創造性思維的產生,從而不利于創造力的提升[16]。在中等程度公民行為壓力水平下,相對于高水平的公民行為壓力而言,此時由于公民行為壓力而占用員工自身的工作資源相對較少,通常在其可控范圍內,從而不至于出現明顯的資源不足;而相對于低水平的公民行為壓力而言,中等程度的工作要求能給員工帶來適度的壓力感,讓其意識到創造性工作中挑戰性的方面,進而產生創造動力并提出更多的創造性想法[17]。故員工處于中等程度公民行為壓力水平的情境下,最能激發員工創造力的產生。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是一種倒U型曲線關系:公民行為壓力水平較高和較低時,員工創造力均較低,而在中等程度的公民行為壓力水平下,員工創造力最高。整體來看,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可能存在倒U型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即公民行為壓力較高和較低時,員工創造力都較低;在中等程度公民行為壓力水平下,員工創造力最高。
(二)自我效能感的調節作用
自我效能感是指“個體對影響自己生活的事情,以及對自己的活動水平施加控制能力的信念”[18]。Stajkovic和Luthans(1998)給出了更為廣泛且實用性更強的定義,他們認為自我效能感指的是“個體對自己能力的一種確切的信念(或自信心),這種能力使自己在某個背景下為了成功地完成某項特定任務,能夠調動起必須的動機、認知資源與一系列行動”[19]。作為個體一種重要、穩定的內在認知資源,自我效能感往往被認為是個體工作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20],并在壓力研究中被認為可以有效緩解壓力造成的負面影響[21][22][23]。類似地,本文推想員工自我效能感可能調節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
工作要求-資源模型能夠有效地解釋以上論斷。根據Demerouti等(2001)提出的工作要求-資源模型,工作特性分為兩類:工作要求(如公民行為壓力)和工作資源(如自我效能感)[24]。如果員工處于高工作要求、高工作資源的情境,則其會將此知覺為一種“挑戰”,并意愿付出更多的努力,展現出積極的工作態度與行為;而當員工處于高工作要求、低工作資源的情境時,其個人的士氣會受到一定的打擊,展現出消極的工作態度與行為[20][25]。因此,我們認為當員工面對不同水平的公民行為壓力時,既能將其感知為一種“挑戰”,也能感知為一種“障礙”。Bakker和Demerouti(2007)提出很有必要深入探究個體資源(如自我效能感)在工作要求-資源模型中的作用機理[24]。同時,不少實證研究也驗證了自我效能感的調節作用[26][27][28]。此外,個體特征(如自我效能感)作為一種內在認知資源,具有普遍意義[29]。故不難推斷,對于具有較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而言,他們擁有充足的內在認知資源,這會使其創新士氣極大提高,從而產生較高的員工創造力;相反,對于自我效能感較低的員工而言,他們的認知資源相對匱乏,當面臨相同的情境時,員工對自身產生創造性思維缺少信心,進而阻礙創造力的提升。所以,自我效能感高的員工不論是處在挑戰性工作情境還是阻礙性工作情境,自身的創造力水平都明顯高于自我效能感低的員工。
具體地,對于自我效能感較強的員工而言,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倒U型關系不明顯。一方面,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具有較高的自我認知,積極的工作態度與行為[25]。而擁有較低水平的公民行為壓力的員工處于一種低工作要求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會主動尋求工作中的“挑戰”,表現出積極的工作態度,從而更好的激發自身的創造性思維。另一方面,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擁有更多的認知資源,并努力尋求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之間的平衡[20]。而較高的公民行為壓力意味著較高工作要求,需要員工投入更多的資源。在這種情境下,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能夠有效彌補由于公民行為壓力而導致的資源不足,更好的平衡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進而更容易感知到“挑戰”,促進自身創造力的產生。
對于低自我效能感的員工來說,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倒U型關系則較為明顯。一方面,低自我效能感的員工缺乏自我認知,做事往往比較消極、被動。因此,在較低公民行為壓力的情境下,由于應對工作要求需要更多的工作資源投入,而低自我效能感的員工對此缺乏正確的認知,并且消極對待,最終導致較低的員工創造力。另一方面,由于低自我效能感的員工在認知資源上比較匱乏[29],因而對這類員工來說,較高的公民行為壓力所帶來的較高的工作要求會致使員工更易感知到“阻礙”,進而不利于創造性想法的提出。而在員工中等水平公民行為壓力的情況下,一方面,適度的公民行為壓力不至于讓員工過度的放松自我,進而忽視創造性工作中具有挑戰性的部分,還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激發低自我效能感員工的積極性與自我認知;另一方面,中等水平的公民行為壓力不會給員工帶來過高的工作要求,讓其可以通過自身的積極行為來有效平衡工作要求與工作資源,最終促進自身創造力的產生。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自我效能感對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倒U型關系有顯著調節作用。即自我效能感越強,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倒U型關系就越不明顯。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收集
本文采用中間人輔助調查的方式進行問卷的發放與回收,為了規避共同方法變異等數據偏差,本文選擇直接上司-目標員工的配對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在2016年8月的中旬至2017年1月上旬這段時間里,我們對我國上海、福建、浙江等不同地區,互聯網、制造、金融等不同行業的員工及其直接上司發放問卷。在目標員工問卷中由目標員工自我評價公民行為壓力、自我效能感,在直接上司問卷中由直接上司評價目標員工的創造力。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412份目標員工問卷和412份直接上司問卷,分別回收318份和301份,回收率分別為77.2%和73.1%。剔除填寫無效或配對失敗的問卷,得到有效配對問卷297份。
樣本描述性統計表明,被調查的目標員工中,男性占41.4%,女性占58.6%;年齡:25歲及以下占7.3%,26~30歲占25.5%,31~35歲占26.1%,36~40歲占24.7%,41歲以上占16.4%;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占5.1%,大專占8.4%,本科占76.8%,碩士及以上占9.7%;工作年限:1年以下占7.8%,1~3年占13.7%,3~5年占32.3%,5~10年占38.1%,10年以上占8.1%;所在單位性質:國有企業占21.2%,民營企業占31.4%,外資企業占16.4%,合資企業占14.1%,其他占16.9%。
(二)變量測量
公民行為壓力:公民行為壓力的測量使用的是Bolino等(2015)開發的公民行為壓力量表[30],該量表總共包含8題項。如:“在工作中,被視為具有運動員精神的人做的事情通常比組織要求他們做的要多得多”。按李克特5點計分法評定,即“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公民行為壓力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38。
自我效能感:對于自我效能感的測量采用Zhang和Schwarzer(1995)所開發的10題項量表[32]。如:“我能冷靜地面對困難,因為我信賴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按李克特5點計分法評定,即“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967。
員工創造力:對于員工創造力的測量采用Farmer等(2003)所開發的4題項量表[31]。如:“他/她能主動尋求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和新思路”。按李克特5點計分法評定,即“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員工創造力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73。
控制變量:以往研究發現[33][34],員工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工作年限、所在單位性質等人口統計學變量會對創造力產生一定的影響,為了避免這些變量對研究結果的可能影響,我們在模型中將其作為控制變量處理。其中,對性別進行虛擬變量處理,男性為“1”,女性為“0”;年齡分為5個等級:25歲及以下,26~30歲,31~35歲,36~40歲,41歲及以上;文化程度分為4個等級:高中及以下,大專,本科,碩士及以上;工作年限分為5個等級:1年以下,1~3年,3~5年,5~10年,10年以上;所在單位性質分為5個等級: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其他。
四、數據分析和結果
(一)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了確定本文所研究的潛在變量是互不相同的概念,需要對公民行為壓力、自我效能感、員工創造力3個變量做區分效度的驗證性因子分析,具體的數據分析結果如表1(該表只列出了所有二因子模型中的最優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三因子模型與其他模型相比,其數據擬合程度更為理想,假設模型的方差自由度之比小于3,RMSEA小于0.07,并且IFI、CFI、TLI均大于0.9,表明該模型與數據的擬合度較好,從而得知各個變量間具備較好的區分效度。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N=297)
注:CP代表公民行為壓力;SE代表自我效能感;IC代表員工創造力。

表2 各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相關系數(N=297)
注:*表示在0.05水平下顯著。
(二)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如表2所示。根據相關分析的結果可得: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r=0.112,n.s.)的相關關系不顯著,也暗示二者之間可能是一種曲線關系。
(三)假設檢驗
本文采用多層次回歸分析的方法,在回歸時逐次加入相對應的變量,進而對前面所提假設(H1和H2)進行檢驗。此外,由于要檢驗公民行為壓力與自我效能感之間的交互作用,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在運用SPSS進行回歸分析前,本文首先對所有相關變量進行了均值中心化處理,具體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1.倒U型關系檢驗
模型1是檢驗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的線性影響,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和所在單位性質等變量的情況下,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42,p< 0.05)。模型2則檢驗的是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的非線性影響,由表3可知,公民行為壓力的平方項與員工創造力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β=-0.908,p< 0.05),并且該模型顯著改進(△R2=0.032,p< 0.01)。綜合模型1和模型2的分析結果表明,雖然從整體趨勢來看,隨著公民行為壓力水平的提高,員工創造力也隨之增加,但當公民行為壓力的水平高于某一個臨界值后,員工創造力則會隨公民行為壓力水平的提高而減少,即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因此,H1成立。
2. 自我效能感調節作用檢驗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調節變量自我效能感。模型4在模型3的基礎上加入公民行為壓力與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項、公民行為壓力平方與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項。表3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加入交互項后該模型顯著改進(△R2=0.080,p< 0.001),并且公民行為壓力平方與自我效能感顯著正相關(β=1.052,p< 0.05),表明自我效能感顯著提高了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倒U型關系。

表3 多層次回歸分析結果(N=297)
注:*表示在0.05水平下顯著;** 表示在0.01水平下顯著;*** 表示在0.001水平下顯著。
此外,為了形象而清晰的展示自我效能感對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曲線關系的調節方向及調節效果,根據Aiken等(1991)提出的方法[35],本文使用回歸系數,描繪了在不同自我效能感水平下員工創造力值的變化情況。如圖1所示,當自我效能感較低時,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但當自我效能感較高時,從整體上看,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關系變化幅度并不大。同時,簡單斜率(simple slopes)分析的結果顯示,對于自我效能感水平較低的員工來說,其低水平公民行為壓力的簡單斜率為顯著的正值(β=0.608,t=2.298,p< 0.05),中等水平公民行為壓力的簡單斜率為顯著的正值(β=0.514,t=2.240,p< 0.05),高水平公民行為壓力的簡單斜率為不顯著的負值(β=-0.337,t=-0.620,p=0.579);對于自我效能感水平較高的員工來說,其低水平公民行為壓力(β=-0.153,t=-0.268,p= 0.806)、中等水平公民行為壓力(β=0.068,t=0.484,p= 0.630)、高水平公民行為壓力(β=-0.486,t=-0.786,p= 0.514)的簡單斜率與零均無顯著差異。因此,H2成立。

圖1 自我效能感在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間的調節作用
五、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探討了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的非線性關系,尤其是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調節作用,并且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得出了以下主要結論。首先,關于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非線性關系研究,本文發現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存在一定的轉折點,即公民行為壓力水平在較低和較高時,員工創造力都比較低,但當公民行為壓力處于中等水平時,員工創造力最高。其次,關于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情境機制研究,本文發現自我效能感顯著調節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倒U型關系。即在自我效能感越高的情況下,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倒U型關系不明顯。這說明公民行為壓力的作用需要在一定的情境條件下才會被激活,進而影響員工創造力,而自我效能感就充當了這種情境條件。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國外對于公民行為壓力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國內的創新研究則較少涉及到這一主題,對于公民行為壓力的影響效果更是知之甚少。本文根據工作要求-資源模型,揭示了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這說明壓力二元性的結論在公民行為壓力之上同樣適用,也就是說,公民行為壓力并不總是有損于個體創造力的,當組織賦予適度的公民行為壓力時會給予成員創新動力,進而推動創造力的提升。這一研究發現不僅有助于我們理解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復雜關系,也豐富了公民行為壓力和員工創造力的研究成果,有效且清晰的闡釋了學界關于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究竟“是好是壞”的困惑,適度的公民行為壓力能夠顯著促進員工創造力的產生。
不僅如此,本文還將自我效能感作為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關系的調節變量進行研究,從認知層面探討了影響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非線性關系的情境機制,有效揭示了公民行為壓力對員工創造力產生作用的邊界條件。這說明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倒U型關系會隨著外部因素尤其是個體的認知要素發生變化,也凸顯了個體認知要素在創造力提升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該研究結果為我們理解如何激發員工創造力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無法改變公民行為壓力的情境下,可以通過調節自我效能感水平的高低來激發員工創造力。
此外,雖然公民行為壓力的測量工具的有效性在西方得到了相關實證研究的支持[20],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使得它們在中國情境下的測量適用性仍有待進一步檢驗,而本文的實證研究對此進行了驗證,發現它們在中國情境下同樣適用。這一研究成果能夠為國內學者進行后續實證研究,尤其是測量工具選擇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管理啟示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的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研究所得結論揭示了公民行為壓力的“雙刃劍”性質,組織管理應充分認識到這一性質,在實際管理中不必對公民行為壓力談虎色變,而要懂得正確看待公民行為壓力,通過讓員工承擔適度的工作要求和工作職責等舉措,使其自身感知到適度的公民行為壓力,從而避免由于公民行為壓力水平過高或過低對員工創造力的產生造成不良影響。另一方面,自我效能感會對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關系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因此,組織在管理實踐中組織還應當為員工創造更多的機會,給予員工更多的獎勵和幫助,讓他們能夠更好的勝任自己的工作,從而提高員工的自我效能感,增加其認知資源,最終促進自身創造力的產生。
(三)局限及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需要改進。首先,本文橫截面的研究設計不能對變量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全面推斷,未來可以采用縱向的研究設計,即先測量前因變量(如公民行為壓力)和調節變量(如自我效能感),間隔一段時間后再對結果變量(如員工創造力)進行測量,進而使各相關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更具說服力。其次,本文所得樣本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部分企業,由于地區文化和組織情境的差異可能會對研究結論的普適性產生影響,后續研究可以拓展研究區域和組織類型,進而增加論證所得結果的有效性。最后,還可考慮加入其他調節變量,如公民行為厭倦、知覺上司地位、上下級關系等,對公民行為壓力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關系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究,并詳細闡述與論證它們之間的作用機制。
[1] Organ D. W.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Good Soldier Syndrome[M].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8.
[2] Zhao H., Peng Z., Chen H. K. Compulsory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erceived Interactional Justice[J].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4, 148(2): 177-196.
[3] Bolino M. C., Klotz A. C. The Paradox of the Unethical Organizational Citizen: The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Unethical Behavior at Work[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5, 6(8): 45-49.
[4] Bolino M. C., Turnley W. H., Gilstrap J. B., Suazo M. M. Citizenship Under Pressure: What’s a “Good Soldier” to Do?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0, 31(6): 835-855.
[5] 趙紅丹, 江葦. 職場中的公民壓力[J]. 心理科學進展, 2017, 25(2): 312-318.
[6] Cates D. A., Mathis C. J., Randle N. W. A Positive Perspective of Citizenship Pressure among Working Adults[J]. 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2010, 22(3): 330-344.
[7] Amabile T. M., Conti R., Coon H., Lazenby J., Herron M. 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5): 1154-1184.
[8] Demerouti E., Bakker A. B.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Challenges for Future Research[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2011, 37(2): 1-9.
[9] Bolino M. C., Klotz A. C., Turnley W. H., Harvey J. Exploring the Dark Side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3, 34(4): 542-559.
[10] Shalley C. E., Zhou J.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Research: An Historical Overview[A]. Shalley C.E., Zhou J.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C].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3-24.
[11] Zhou J., George J. M. Awakening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Role of Leader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3, 14(4): 545-568.
[12] Oldham G. R., Cummings A. Employee Creativity: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 at Wor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3): 607-634.
[13] Yang Y., Lee P. K. C., Cheng T. C. 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ompetence,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 Frontline Employee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6, 171: 275-288.
[14] Gong Y., Huang J. C., Farh J. L. Employee Learning Orienta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Creative Self-Effica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4): 765-778.
[15] Shalley C. E., Gilson L. L. What Leaders Need to Know: A Review of Soci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 that Can Foster or Hinder Creativity[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4, 15(1): 33-53.
[16] Van Dyne L., Jehn K. A., Cummings A.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Strain on Two Forms of Work Performance: Individual Employee Sales and Creativit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2, 23(1): 57-74.
[17] Ohly S., Fritz C. Work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 Appraisal, Creativity, and Proactive Behavior: A Multi-Level Stud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0, 31(4): 543-565.
[18]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215.
[19] Stajkovic A. D., Luthans F. Self-Efficacy and Work-Related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 124(2): 240-261.
[20] Bakker A. B., Demerouti E.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State of the Art [J].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07, 22(3): 309-328.
[21] Siu O., Lu C., Spector P. E. Employees’ Well-Being in Greater China: The Dir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eral Self-Efficacy[J].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56(2): 288-301.
[22] Lu C., Siu O., Cooper C. L. Managers’ Occupational Stress in China: The Role of Self-Efficacy[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5, 38(3): 569-578.
[23]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 New York: Freeman, 1997.
[24] Demerouti E., Bakker A. B., Nachreiner F., Schaufeli W. B.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of Burnou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86(3): 499-512.
[25] Bakker A. B., Demerouti E., Euwema M. C. Job Resources Buffer the Impact of Job Demands on Burnout[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5, 10(2): 170-180.
[26] 王寧, 趙西萍, 周密, 等. 領導風格、 自我效能感對個體反饋尋求的影響研究[J]. 軟科學, 2014, 28(5): 37-42.
[27] 周浩, 龍立榮. 基于自我效能感調節作用的工作不安全感對建言行為的影響研究[J]. 管理學報, 2013, 10(11): 1604-1610.
[28] 馮冬冬, 陸昌勤, 蕭愛鈴. 工作不安全感與幸福感、 績效的關系: 自我效能感的作用[J]. 心理學報, 2008, 40(4): 448-455.
[29] Hobfoll S. 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the Nested-Self in the Stress Process: Advancing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J].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50(3): 337-421.
[30] Bolino M. C., Hsiung H. H., Harvey J., LePine J. A. “Well, I’m Tired of Tryi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Citizenship Fatigu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5, 100(1): 56-74.
[31] Farmer S. M., Tierney. P., Kung-Mcintyre K.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aiwan: An Application of Role Identity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5): 618-630.
[32] Zhang J. X., Schwarzer R. Measuring Optimistic Self-Beliefs: A Chinese Adaptat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J]. Psychologi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the Orient, 1995, 38(3): 174-181.
[33] Jafri M. H., Dem C., Choden 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Moderating Rol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J]. Business Perspectives & Research, 2016, 4(1): 54-66.
[34] 張鵬程, 劉文興, 廖建橋. 魅力型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機制:僅有心理安全足夠嗎?[J]. 管理世界, 2011,(10): 94-107.
[35] Aiken L. S., West S. G., Reno R. R.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M]. California: Sage,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