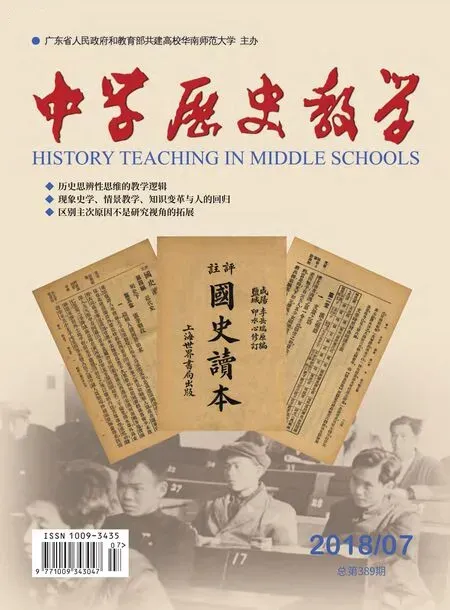從垂直到平行:近代中國外交體制與觀念的逐步確立
——從2018年全國高考文綜卷Ⅰ、Ⅱ卷第28題談起
◎ 華春勇 陜西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在2018年高考的三套全國卷近代史部分的考查中,有兩道題考查了近代轉型中的外交,分別如下:
(2018年高考全國Ⅱ卷·28)19世紀70年代,針對日本阻止琉球國向中國進貢,有地方督撫在上奏中強調:琉球向來是中國的藩屬,日本“不應阻貢”;中國使臣應邀請西方各國駐日公使,“按照萬國公法與評直曲”。這說明當時
A.日本借助西方列強侵害中國權益
B.傳統朝貢體系已經解體
C.地方督撫干預朝廷外交事務決策
D.近代外交觀念影響中國
(2018年高考全國Ⅰ卷·28)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制定輿論宣傳策略,把中國和日本分別“包裝”成野蠻與文明的代表,并運用公關手段讓許多歐美輿論倒向日方。一些西方媒體甚至宣稱,清政府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中得到解放”。對此,清政府卻無所作為。這反映了
A.歐美輿論宣傳左右了戰爭進程
B.日本力圖變更中國的君主政體
C.清朝政府昏庸不諳熟近代外交
D.西方媒體鼓動中國的民主革命
兩道題從選項來看,一個強調19世紀70年代,近代外交觀念影響中國;一個說,19世紀90年代甲午戰爭時,清朝政府昏庸不諳熟近代外交。按照一般理解,19世紀70年代近代外交觀念既然已經影響中國,那當時的清政府就應該受這種影響了解了近代外交并逐漸熟悉,何至于20年后甲午戰爭時,清朝政府還是昏庸不諳熟近代外交?這兩個結論不是矛盾的嗎?
為有效地解決這兩道高考選擇題,我們需要把近代中國外交體制建立和外交觀念成熟的過程做一初步的梳理。
一、近代外交體制的演變
美籍歷史學家徐中約認為“儒家意識的天下一統帝國,傳統上不維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關系;也不承認有任何對外事務,只認為有藩務、夷務或商務”[1]。這里將明清中國的對外交往分成二類:一稱為藩務,指的是與中國有藩屬關系的國家交往。這些國家政治上認可宗主國的地位,經濟上則是朝貢貿易。明清之際先后與朝鮮、琉球、越南、緬甸等建立了這樣的關系,隸禮部職掌。二是夷務。所謂的夷務和蕃務盡管在今天看來基本是一樣的含義,但在古代王朝有“內蕃外夷”的差別,蕃有“生”、“熟”而夷則無這樣的差別便可明了。夷務本質上是中央王朝體制外的事,被稱為夷范疇的國家,與中央王朝聯系疏松。夷務發展到后來就是近代的洋務、外務。蕃務和夷務在明清統治者眼里都帶有上下垂直關系的視角,因此,都不符合近現代外交的“平行”視角看待兩國關系的特點。在日本學者坂野正高看來,“外交是對等的獨立國家間關系的現實,它不是縱向關系,而是橫向關系”[2],因此,中國周朝以后(春秋戰國時期)的朝貢體制基本上是上下關系,因而不是外交。
改變這種秩序的是《南京條約》的簽訂,在中英以及隨后的中法、中美之間通過談判建立起了新的“條約關系”。從夷務到條約,這是一種巨大的轉變。相對于傳統的夷務,條約關系所涉及的交往內容更為廣泛,因此,可以說《南京條約》開啟了傳統帝國一種全新的對外關系。盡管當時朝野上下將條約視為權宜之計,并沒有意識到和之前的夷務有何差別。之后圍繞著公使進京、覲見禮儀等兩個核心問題進行了長期的爭論,清政府終于在被動挨打的逼迫中逐漸接受現代外交觀念,確立外交體制。條約體制的形成,公使駐京的實現、覲見問題的解決,都是中國近代外交體制形成的重要內容,也都為這一體制的到來創造著條件。
但這一時期的對外活動并不具有“主動性”,是一種被動的應激反應,因此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外交。一般認為,清政府對外交往自我意識的形成及近代外交模式的確立,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與對外事務的開展;第二,中國向外派使的嘗試。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皇上和太后逃往熱河,被迫留京的恭親王奕訢與英、法、俄分別簽訂《北京條約》。在這一過程中,奕訢一方面深感清廷“夷務”處理混亂不堪,“弊在體制”,一方面,對外國人改變了看法,認為其并非不講道理的野蠻人。加之增開通商口岸、列強公使駐京已成定局,于是萌生在京設一機構,統籌外交全局的想法。[3]1861年1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京設立,簡稱“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奕訢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等負責主持,下設英、法、俄、美及海防五股,專門辦理對西方各國的交涉及各項洋務。總理衙門的設立,改變了以往由禮部、理藩院等機構兼辦對外交涉、內政與外交界限不分的狀態,從而向近代外交體系跨出了建制的第一步。
1865年,赫德在給總理衙門寫的《局外旁觀論》中,就中國應派使駐外提出了強烈建議。他稱:“派委大臣駐扎外國,于中國有大益處。在京所住之大臣,若請辦有理之事,中國自應辦。若請辦無理之事,中國若無駐其本國,難以不照辦。”[4]總理衙門的設立、對外派使的實行,都是近代清廷對外交往新模式確立的標志。
以上事實表明:在鴉片戰爭后,在條約體制確立、外國公使駐京實現以及覲見問題最終解決的同時,清朝同西方和日本等非屬國之間的交往方式也已發生變化,而對外交往新模式的出現則標志了中國近代外交體制開始確立。
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外交近代化,經歷了從傳統的“華夷秩序”體系向近代西方“條約體系”逐步轉型的過程。這一過程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晚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是對處理日益增多的“洋務”的一種被動應對,也是對建立近代外交體制的初步探索;清末“外務部”的產生,既順應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需要,又為清王朝維持國家主權與獨立提供了重要工具;民國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從形式上改變了國家外交機構,滿足了中國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南京政府實現了國家統一的目標,進而對外交制度進行全面調整和改進,到1936年基本建成近代化的外交體制和制度機制,為全面實現近代化轉型創造了條件。[5]
綜上,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總理衙門的設立和駐外公使得派遣為標志,中國開始逐步建立起來了近代外交體制。這一過程也伴隨著對外觀念的更新。
二、近代外交觀念的形成
鴉片戰爭以后,林則徐和魏源雖然意識到西方國家在軍事上的強大,但“華夷之辨”的根本認識邏輯沒變,對于西方也有很多扭曲的認識。整體而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雖然清廷與西方各國勢力相較已顯衰落,但是在絕大多數時人的思想意識里,“天朝”仍是世間最強大、最富有的國家,“天朝”體制仍是優越于西洋的制度。
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爭是近代外交意識形成重要的分水嶺。戰爭中皇室倉皇北逃,“天朝”體制、“天朝”獨尊在西方“洋夷”的堅船利炮面前已被糟蹋得一文不值,關于公使進京和覲見禮儀的較量讓大清意識到,必須屈從西方“夷人”的交往規則。至此,晚清時人對時局及中西變化的認識也只能發生變化。
李鴻章于同治四年(1865年)就提出“變局”觀點。他是從現實的世界變化以及國家政治、軍事需要的角度,而非從新舊體制的堅守與否角度提出這一觀點。他稱:
“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鄙人一發狂言,為世詬病,所不能避。”[6]
經過道咸同時期中西之間的沖突與磨合,清代時人的思想意識尤其是傳統“華夷”觀已經發生變化。尤其是在第一批走出國門的外交使節中,西方文明對于他們的沖擊尤為震撼,他們不僅從空間上重新審視中國,更從文化上從新定義華夷。他們認識到中國雖為華夏,西方雖被稱為“夷狄”,但華夏并不一定比“洋夷”優越;相反,華夏倒有可能被西洋人看成半野蠻人。持此論者的代表人物是郭嵩燾。“西洋謂之無教化。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于中國而名日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7]這種審視當然不是直接的外交觀念,但為平等的外交觀念的形成撕開了華夷之辨的裂縫。
同治十年,李鴻章在駁斥日本剛行訂約又馬上悔約時,也借用萬國公法知識來批判日本這一做法,以維護清朝的“利權”。[8]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又因日本侵臺而用萬國公法來維護清方的“利權”。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清方大員正企圖利用近代外交法則去維護清方權利。
安樹彬先生曾稱: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隨著國際法傳入中國,迫于外交形勢的壓力,中國人開始接受并運用其核心內容——國家主權平等原則”[9]。
衛三畏于1868年(同治七年)致威廉斯牧師的信中所稱:“中國正試圖理解自己在世界上所擁有的權利,并試圖維護和擴大這些權利,同時給予別國它所必須給予的特權。”[10]
三、結論
通過粗淺的梳理可以看出,19世紀70年代,近代外交觀念影響中國,中國也初步建立了近代外交體制,這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必須指出,這種觀念并非普遍流行。在一個前現代化國家中這樣先進的觀念不僅不能上升為國家外交意識,反而往往由于其沖破了固有的“華夷之辨”而備受非議。郭嵩燾的悲劇既是其個人悲劇也代表著轉型時代知識精英的不幸。
回到本文開端的高考試題,看似矛盾的兩個觀點卻真實地反映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外交觀念和實務面臨的困局。就觀念而言,個別先進的士大夫甚至已經構成一個小群體,已經敏銳地感知到了世界的變化,并積極應對,利用規則因勢利導地順應這種變化。而另一方面,面對傳統的慣性思維和嚴酷的派系斗爭環境,任何過激言論都有可能喪失所有政治資本。因此,個人正確的意見,很難上升為政府決策和國家意志。就國家整體而言,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外交上又顯得拙嘴笨舌,自說自話。
一方面,個別地方封建官僚的個體認知日新月異地與世界同步,一方面國家整體卻懵懂無知,裹步不前。究其原因,除了士大夫明哲保身的政治策略以外,前現代化國家未能建立有效制度動員“智庫”,并使之上升為國家政策,怕是更重要的原因。
【注釋】
[1]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第39頁。
[2]坂野正高:《現代外交分析——情報、政策決定及外交交涉》,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第9-10頁。
[3]申曉云:《民國政體與外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頁
[4]寶鋆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20頁。轉自周海生:《清季遣使之爭與駐外使館的建立》,《歷史教學》2006年11期。
[5]王承慶:《中國外交體制的建立與近代化轉型》,《史學月刊》2015年第6期。
[6]《李鴻章全集》第6卷,朋僚函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復朱久香學使”,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37頁。
[7]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9頁。
[8]李細珠:《李鴻章對日本的認識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為中心》,《社會科學輯刊》2013年第1期。
[9]安樹彬:《從傳統天下觀到近代國家觀》,《華夏文化》2004年第1期 。
[10]衛斐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