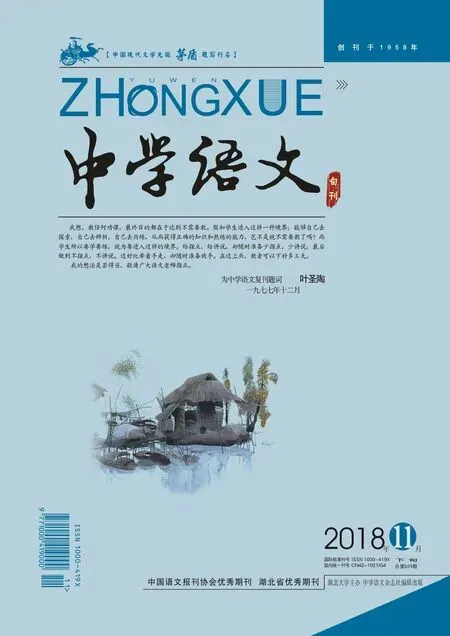2018年江蘇高考作文閱卷反芻
劉紅健
明朝胡應麟在他的《詩藪》中說“初學必從此入門;庶不落小家窠臼。”意為初寫文章必須要與眾不同,匠心獨具。但是高考作文又是有標準答案的,無論怎樣個性跳脫的文章,都需要閱卷老師用統一的等級標準去衡量。這個矛盾讓考場作文有了不一般的寫作要求。
一、考場作文:“戴著鐐銬跳舞”
這個“鐐銬”當然指作文審題。
2018年江蘇高考作文材料有三句話構成,“花解語,鳥自鳴,生活中處處有語言。不同的語言打開不同的世界,音樂、雕塑、程序、基因……莫不如此。語言豐富生活,語言演繹生命,語言傳承文明。”
這個作文材料的核心詞是“語言”,這一點,考生基本無人出錯,都能抓住核心詞語行文。
這個作文材料一如江蘇往年的高考作文命題,是命意作文,不僅規定了寫作核心詞,還規定了寫作的意向,考生要在命題者圈定的范圍內施展才華。如2017年考生在寫“車”時,一定要在“見證了時代的變遷、觀念的轉變、代表了社會的發展”這三個范圍內。
作文材料的命意提示啟發了考生的思維內涵,提高了考生的立意品質,降低了考生審題的難度,但是偏偏有不少考生對命題者的這一苦心視若無睹。
今年作文材料的這三句話分別從三個角度提示了考生的寫作方向,分別是景語、物語、人語。
從景語的角度行文,其實就是竺可楨在《大自然的語言》的寫的“杏花開了,就好像大自然在傳語要趕快耕地;桃花開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趕快種谷子。布谷鳥開始唱歌,勞動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麥插禾。’這樣看來,花香鳥語,草長鶯飛,都是大自然的語言。”也是我們平時課堂上講的“一切景語皆情語”。從這一角度行文,考生在審題層面上基本沒有偏差,只是普遍思維品質不高,大部分都是用華麗的語言漫無目的的描摹自然之景。
從物語角度行文,一定要寫出“不同的世界”的特征,要用基于該領域的專有語言展開評說或者記敘,例如寫音樂,那么旋律、節拍、和聲就是音樂作品的“語言”,音樂作品流露出來的激昂、悲傷、迷惘等情感是音樂家的“語言”。總之,考生的行文要能“打開不同的世界”,領域特征是暗含在題目中的命題意向。
從人語的角度行文,要點出人語的作用,“語言豐富生活,語言演繹生命,語言傳承文明。”考生順從命題者的三種意向之一,很多考生的記敘文通篇是對話,媽媽說、奶奶說……認為這就是寫語言,既不點題目,也無對主旨的提示,這其實是考生對作文材料的斷章取義,沒有很好體現命題者的命題意向。
考場作文當然不能是自由奔放的舞蹈,“戴著鐐銬跳舞”是考生的常識,只是這個鐐銬不是金屬的,而是紙做的,考生在翩翩起舞時,稍稍得意忘形,便會在不知不覺之間,掙脫斷裂,付出代價。
二、高考作文閱卷:高三語文老師的相親會
高考作文閱卷時間緊,任務重是盡人皆知的秘密,平均1分鐘一篇。這1分鐘內要閱盡考生十二年的語文素養,“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
高考作文閱卷就是高三語文老師的一場相親會,始于顏值,陷于眼界,敬于才華,分秒之間,便精準評價眼前的“對象”的等級。
卷面是最好的顏值,幾乎瞬間便是永恒。最好的字跡能明顯看出體式章法,一看便知臨碑多年,幾乎讓人一見傾心,如果字如其人,應該是金字塔頂的考生。其次是“衡水體”式的卷面,中規中矩,干凈利落,做不到卷面漂亮,可以退而求其次,做到卷面端正。但有近一半的卷面要讓閱卷老師耐下性子去閱讀,更有不少卷面會讓閱卷老師“眼殘”甚至“眼盲”。
眼界主要體現在考生的閱讀積累上。有考生取材于西斯萊油畫作品的獨到觀察和評價,有取材于約瑟夫·海頓的弦樂作品的描繪與頓悟。“虧他這個都知道!”這類考生的閱讀眼界直讓閱卷老師稱嘆,這些選材幾乎“秒殺”閱卷老師,這些讓閱卷老師一下子淪陷。
才華是考生拿到這個題目以后,匠心獨具的臨場發揮。筆者記得有一個考生把6月7日早上媽媽的嘮叨連綴成文,嘮叨我的衣著、嘮叨我的早飯、嘮叨我的文具準備、嘮叨爸爸的送行,看似凌亂無心的語言,寫出了特殊日的忙亂、家庭的囑望與關愛,生活氣息濃厚。考生對雷同生活的深入觀察和獨特思考,使得這篇文章活力十足、生機盎然。
三、高中生作文:語文老師操控,考生表演的木偶戲
相對百里挑一的匠心之作,高考作文充斥著大量泛泛而談的平庸文,記敘文流水賬式的平鋪直敘,波瀾不驚;議論文以材料的三句原話作為分論點,有的插入三個例子,有的甚至連例子都沒有,通篇“喃喃自語”,怎能不讓閱卷老師相看不厭?
高考作文絕對不能是考生的“獨舞”,在他的背后隱隱站著他們的語文老師,高考作文是由語文老師操控,考生在前臺表演的“木偶戲”,是考生用自己的手寫老師作文課堂的種種叮嚀,審題的注意點、立意的選擇、行文的技巧,可以說高考作文既是檢驗考生十二年的寫作成果,也是檢驗考生的語文老師十二年的作文課堂的教學成果。
那些庸作都是無思想、無技巧、無語言表現力的三無產品,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他們把十二年來語文老師的耕耘棄之腦后,猶如被剪掉線的木偶,怎么能翻身能跳躍?
考場作文是有標準答案的,這個標準答案就是“作文評分細則”,就是江蘇省近幾年都實行 “六類評分法”。無論是考生的寫,還是老師的教都要牢記這一準則,迎合這一準則,才能寫出“討巧”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