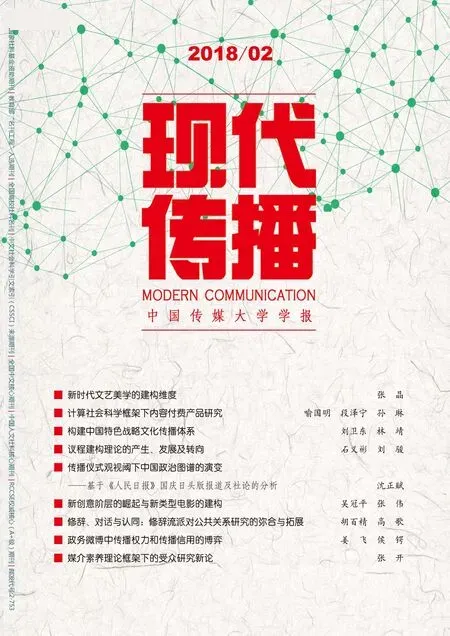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與“技術(shù)決定論”關(guān)聯(lián)的再思考
■ 謝清果 杜愷健
當(dāng)我們提及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時,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一詞始終是它揮之不去的陰影。不管是早期的麥克盧漢被斬釘截鐵地認(rèn)為是一個技術(shù)決定論者,學(xué)界為伊尼斯以及麥克盧漢為首的多倫多學(xué)派冠以的諢名“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①,還是各種教科書在論述麥克盧漢的理論時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以“麥克盧漢和他的技術(shù)決定論”為題。再到八十年代以降,萊文森等人不停地為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正名,認(rèn)為他們不完全是一個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者。“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一詞始終是學(xué)者們用來定義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所使用的最多的表述話語,不管對它是肯定也好,否定也罷。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關(guān)于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與“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關(guān)系的爭論,實質(zhì)上也是學(xué)界對于“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觀點的爭論,不同學(xué)者、不同時期對于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與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關(guān)系的解讀實際上恰恰反映了學(xué)界對于“技術(shù)”一詞在不同時期的理解,本文正是以此出發(fā),來探討“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與“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關(guān)系的觀念演進(jìn)史。
一、早期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具有“技術(shù)決定論”傾向
要討論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被稱為“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歷史,首先就要回到原點,去看看這一理論的發(fā)源者哈羅德·伊尼斯與麥克盧漢是如何討論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以確定在他們的理論之中是否存在一種“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傾向。
首先是哈羅德·伊尼斯,學(xué)界熟悉他的“傳播的偏向”理論,即“傳播的媒介的性質(zhì)往往在文明中產(chǎn)生一種偏向,這種偏向或有利于時間觀念,或有利于空間觀念。”其含義是從“媒介對各種文明的意義,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見自己文明的偏向。”②“傳播的偏向”理論實際上就是關(guān)于媒介對文明、對社會影響的理論。以往學(xué)界對于“傳播的偏向”的論述,往往側(cè)重于媒介對社會的影響這一層面上,正如何道寬所說“他(伊尼斯)認(rèn)為,媒介的形態(tài)對社會形態(tài)、社會心理都產(chǎn)生深重的影響。”③而伊尼斯自己也說“一種媒介經(jīng)過長期的使用之后,可能會在一定程度時決定它傳播的知識的特征。……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dǎo)致一種新文明的產(chǎn)生。”④
照著上述的觀點來看,似乎伊尼斯就是一個“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者。從他在《傳播的偏向》中的敘述來看,他也一直在強(qiáng)調(diào)媒介對于文明以及社會的影響,例如通過對埃及文明之中莎草紙對石頭以及象形文字媒介的挑戰(zhàn),他認(rèn)為媒介影響文字與思想的傳播,進(jìn)而導(dǎo)致了社會的變革。⑤之后對于兩河流域以及中國文明的分析也延續(xù)了這種媒介對社會影響的基調(diào),因此,后人認(rèn)為伊尼斯帶有著明顯的“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味道是有一定依據(jù)的。
然而,問題在于,伊尼斯的論述之中,并不完全只有“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論調(diào)。“決定”一詞在伊尼斯的眼中并不是那么關(guān)鍵,“平衡”恰恰才是那個最重要的一環(huán)。在論述“傳播的偏向”時,他就曾說過“穩(wěn)定的社會需要這樣一種知識: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維持相當(dāng)?shù)钠胶狻!雹廾浇橥鶗绊戇@種平衡,但媒介并不是單一的決定因素,通過其他因素的改變,人也是可以去維持這種平衡的。他曾說過“傳播的突然進(jìn)展,是文化動蕩的反映。”⑦并不僅僅是媒介會影響到社會進(jìn)程,社會進(jìn)程同樣也會影響媒介。在這一境況之下,他開始強(qiáng)調(diào)我們不應(yīng)太過關(guān)注技術(shù),關(guān)注媒介,而應(yīng)當(dāng)去注重社會各種因素之間的平衡。他引用希臘文明的“勿過”觀念來說明我們不應(yīng)太過關(guān)注技術(shù)的問題,“‘萬事勿過’是希臘人治理箴言,其暗示的意義是不信賴專門化的記憶,在一切文化生活領(lǐng)域都是如此。”⑧因此,對于伊尼斯來說,現(xiàn)代性的最大問題即在于專門化所導(dǎo)致的“過”(in excess)。現(xiàn)代的工業(yè)主義對伊尼斯來說就是關(guān)注技術(shù),這意味著媒介注重于時間的要求,人們評價空間的能力則被削弱,技術(shù)的長短變化,使我們難以認(rèn)識到時間和空間的平衡,而求得時間和空間的平衡就更難了。⑨也正因此,伊尼斯之所以如此關(guān)注媒介的問題即在于他希望尋求一種媒介與文明、社會之間的平衡,通過這種平衡來解決媒介所導(dǎo)致的偏向問題。在他后來的著作《帝國與傳播》之中,他就試圖去言明在帝國之中,傳播(媒介)與社會(文明)的關(guān)系。通過對美國報業(yè)和廣播的分析,他認(rèn)為美國主要的媒介報紙是一種偏向空間的媒介,它使得美國具有機(jī)械化的傳播體制和有組織的力量。在這一偏向的影響之下,美國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并將其強(qiáng)加于普通法,并用來擴(kuò)張帝國主義。⑩因此伊尼斯在文章結(jié)尾處就強(qiáng)烈呼吁要開發(fā)出一套強(qiáng)力的行政體制,去制衡這種傳播的偏向。而這恰恰也是伊尼斯另外一本書《變化中的時間觀念》未點明的主題,媒介雖然有一種偏向,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它可能是偏向技術(shù)的,但我們?nèi)詰?yīng)該去尋找獲得時間與空間平衡的方法來引導(dǎo)媒介,保證社會的穩(wěn)定。
另一方面,我們再來看看麥克盧漢關(guān)于媒介與社會的觀點,一般來說,各類文獻(xiàn)在論述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時都會認(rèn)為他是一個強(qiáng)烈的“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支持者,這里以切特羅姆為例來闡述,他認(rèn)為麥克盧漢的技術(shù)決定論,或可稱之為“科技天生論”,即人類正常使用科技時,生理上已經(jīng)被科技局限住,新媒介不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橋梁;它們根本就是自然。在這種論斷之下,媒介早已經(jīng)成為了環(huán)境本身,成為主宰人們思考世界的唯一起點。一切事物都變化為了媒介的延伸,這就是通常人們對于他的名言“媒介是人身體的延伸”的“科技決定論”式的解讀原由。
但關(guān)于麥克盧漢是一位“科技決定論”者的論斷,麥克盧漢自己就有著很明確的否定意見。他曾就自己是否是一個技術(shù)決定論者一事致電萊文森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在他后來的一系列著作之中,這種思想更加明顯。他認(rèn)為對于技術(shù),如果我們不加以批判的話,我們都將成為機(jī)器人。他引用艾德蒙·伯克對十九世紀(jì)人們對技術(shù)的觀念來說明自己的觀念即“每個人的首要權(quán)利是受到保護(hù)”,其目的無非是要說明技術(shù)始終不會是主宰人的唯一因素。在解釋新媒介是如何產(chǎn)生時,他的說法是社會依靠集體行動開發(fā)出了一種新媒介,而這種新媒介所傳遞的新訊息,才會威脅到舊訊息和舊媒介。也就是他所說的任何信息傳播過程中的變化必然要引起一切社會模式的調(diào)整。但在這之下,媒介本身不是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的,而是社會集體運(yùn)動才造就了新媒介的產(chǎn)生。要說麥克盧漢是一個“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者,倒不如說他是為了突出他對于媒介對社會的作用的看法才將“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這一觀點凸顯了起來。
綜上所述,在早期的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之中,不管是伊尼斯還是麥克盧漢,他們實際上都沒有很明確的、堅定的“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觀點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最多只能算得上一個溫和的“技術(shù)決定論”者。因為他們在強(qiáng)調(diào)媒介決定社會的同時,他們還強(qiáng)調(diào)了一種媒介批判的維度,強(qiáng)調(diào)了社會對于媒介所應(yīng)該采取的態(tài)度。因此,他們倆都算不上是一個絕對的“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者。他們作為一個“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者的出現(xiàn),應(yīng)該是被后來學(xué)者對于他們討論的而強(qiáng)化結(jié)果。
二、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被冠以“技術(shù)決定論”名號的生成路徑
既然我們已確定了在早期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理論之中,媒介并不完全處于一個決定社會的地位,那么我們只能認(rèn)為將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界定為“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論斷是在后來的討論之中逐步產(chǎn)生的。至于產(chǎn)生的過程正是此處討論的主題。
實際上造成這種技術(shù)決定論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其他人,恰是“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先鋒旗手米歇爾·麥克盧漢。在他為伊尼斯的《傳播的偏向》撰寫序言時,就認(rèn)為伊尼斯把注意力指向了技術(shù)的偏向和扭曲里,在確定了文化中占據(jù)支配地位的技術(shù)時,伊尼斯就可以斷定技術(shù)是當(dāng)前文化結(jié)構(gòu)的動因和塑造力量。并認(rèn)為這一力量(即媒介)必然會受到掩蓋。一旦認(rèn)準(zhǔn)了一種文化的主要技術(shù)的話,他就知道該文化的物質(zhì)模式和社會模式。可見,麥克盧漢所理解的哈羅德·伊尼斯就是個典型的“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者。后來他在參加俄亥俄州立大學(xué)一個名為“傳播革命”的小組討論時再一次重申“他(伊尼斯)的觀點是,任何信息傳播過程中的變化必然要引起一切社會模式的調(diào)整。”而在他所出席的演講之中,他不止一次強(qiáng)調(diào)了這種媒介對社會結(jié)構(gòu)的決定作用。在麥克盧漢的眼中,似乎社會對于媒介的影響顯而易見,而他需要更多闡述的是關(guān)于媒介如何影響社會的議題,同時又受限于他鑲嵌畫式、非線性的、跳躍式的文學(xué)風(fēng)格,“先知式”的敘述話語,麥克盧漢關(guān)于技術(shù)的論述尤其是“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式的論斷逐漸被凸顯了出來,他和伊尼斯自然也被當(dāng)作了“技術(shù)決定論”式者,而被后來的人所接受。
麥克盧漢的這一理解后來隨著麥克盧漢的成名而逐漸被學(xué)界所接受。按照沃爾夫的說法“麥克盧漢熱”應(yīng)是形成于20世紀(jì)的60年代。1966年這一年,介紹麥克盧漢的文章就多達(dá)120多篇。與此同時,Sloan注意到當(dāng)時麥克盧漢的思想對于媒介效果研究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非常強(qiáng)大的影響。他認(rèn)為只要是研究傳播或是演講的人都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麥克盧漢的觀點。Sloan這種注重媒介效果的觀點實際上與當(dāng)時的研究環(huán)境是完全重合的,參看當(dāng)時的社會語境,經(jīng)驗性的、定量的社會科學(xué)研究本就是當(dāng)時傳播學(xué)研究的主流,這種研究在當(dāng)時一直受到了“效果導(dǎo)向”的主導(dǎo),這種關(guān)注于大眾傳播單向傳播的研究模式無疑是當(dāng)時的主流。這種“效果”導(dǎo)向的經(jīng)驗研究在學(xué)者看來無疑是一種技術(shù)決定論式的研究,即相信技術(shù)是社會變化的原因之一,不同的僅在于其程度的多少的問題。在這種情境之下,注重于傳播效果的思維自然也被延伸到了麥克盧漢的思想之上,媒介對于社會的影響在這里被當(dāng)成一種媒介的“強(qiáng)效果”作用于社會的每個人。后來賽佛林在他的《傳播理論》一書之中就說曾有研究者試圖去測試麥克盧漢的研究觀點,但這并不能夠在短期就能夠取得效果,因而也認(rèn)為這是一種“長期效果”論。
同樣的情形在麥克盧漢的理論被譯介到華人地區(qū)時也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通過早期華人學(xué)者對麥克盧漢的研究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長期效果論”的影子。首位介紹麥克盧漢理論到華人地區(qū)的臺灣學(xué)者徐佳士在1968年介紹麥克盧漢的文章之中就首先認(rèn)定他是一個“技術(shù)決定論者”。在他的視角之中,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并不是像原先的“效果論”那樣關(guān)注于施教、態(tài)度改變、商品銷售的短期效果,媒介對于社會的影響實際上就是媒介的一種“長期效果”,麥克盧漢則是這個領(lǐng)域之中的第一人。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學(xué)界對于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的理解,實際上還是從原先經(jīng)驗研究的出發(fā)點出發(fā)的,后來邵培仁在其《傳播學(xué)》之中批判麥克盧漢的理論時也認(rèn)為這種“長期效果”是一種對短期效果內(nèi)容的豐富。
至此,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理論在麥克盧漢天馬行空的語言塑造之下,其關(guān)注媒介對于社會作用的部分逐漸顯現(xiàn)出來,甚至被當(dāng)作了一種“媒介科技決定論”的理論。這種理論恰與當(dāng)時美國注重效果研究的氛圍相互吸引,麥克盧漢本人就被當(dāng)成了一位研究媒介長期效果理論的研究者,也正因此,麥克盧漢關(guān)于媒介影響社會的理論就被當(dāng)作一種“長期效果論”而被顯現(xiàn)出來,他對于媒介的批判與反思則相對地被隱藏了起來,而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早期學(xué)者也就這樣被定義為一個“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者了。
三、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與“技術(shù)決定論”關(guān)系的拓展討論
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理論雖然對當(dāng)時的美國學(xué)界造成了不小的沖擊,但它依然被當(dāng)時注重“效果研究”的經(jīng)驗型研究范式所接納,并作為“長期效果論”的一種而被賦予了“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名號。但當(dāng)一個學(xué)科的范式出現(xiàn)轉(zhuǎn)移時,科學(xué)家會以一個不一樣的范式來看待世界。“技術(shù)決定論”一詞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可以被當(dāng)作是一面“魔鏡”,它所照射出來的是早期傳播學(xué)的研究者對于“技術(shù)”的態(tài)度。20世紀(jì)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各種新興范式的興起,經(jīng)驗型、定量型的“媒介效果”研究本身也受到了沖擊,在這種沖擊之下,對于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當(dāng)時并沒有這個說法)與技術(shù)決定論之間關(guān)系的看法也在發(fā)生著改變。又或者說,是當(dāng)時的學(xué)者對于“技術(shù)”一詞的態(tài)度也在發(fā)生著改變。1983年在《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醞釀了一場“領(lǐng)域的發(fā)酵”活動,不同研究范式的學(xué)者爭相討論著傳播領(lǐng)域的未來,這也標(biāo)志著傳播學(xué)的研究范式的多元化發(fā)展趨勢的到來。從這個時候起,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研究范式也就逐漸被重新闡述了。
首先一種情況是繼續(xù)承認(rèn)早期媒介技術(shù)環(huán)境學(xué)派的“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因素,但卻認(rèn)為他們的理論闡釋還可有所作為的。Em.Griffen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承認(rèn)麥克盧漢在學(xué)術(shù)上的洞察力,并通過舉證的方式說明他那些奇思妙想的論斷在他身后都得到了實現(xiàn)。但他依然指出麥克盧漢是一種科技決定論,并認(rèn)為他是在以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來談?wù)撁浇橐庾R,在這方面麥克盧漢沒人能出其左右。與其相似的是,李金銓在他的《大眾傳播理論》中也是認(rèn)為麥克盧漢的觀點是傳播科技決定著歷史發(fā)展的軌跡和特質(zhì),具有支配性力量的是傳播科技本身,而不是內(nèi)容。他承認(rèn)麥?zhǔn)现赋雒浇楸旧硭哂械耐?但是威力多少就不再多說了。相同的情況還有邵培仁的《傳播學(xué)》,這些書籍都是在承認(rèn)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本身具有變革力量的前提條件下,繼續(xù)給他們按上“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帽子,進(jìn)而批判這種單因素的決定論,質(zhì)疑其所存在的問題。
另一方面,此時也逐漸有學(xué)者開始為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翻案,認(rèn)為他們不是一種“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其中的典型就是麥克盧漢的高足——保羅·萊文森。早在20世紀(jì)70年代時,萊文森曾認(rèn)為麥克盧漢是一位“技術(shù)決定論”者,但在十年之后他在出版《數(shù)字麥克盧漢》的時候卻說道“1978年,事實本身似乎證明,麥克盧漢持媒介決定論。如今,用事后諸葛亮的眼光來看,我也可以清楚地看見,用‘媒介決定論’來描寫他未必是妥當(dāng)?shù)摹薄A治膭倓t采取了另外一種方式來摘除了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媒介決定論”的帽子,他首先認(rèn)為所謂的“決定論”是一個理論的連續(xù)體,在這兩端是兩種不同的解釋性觀點。他將萊文森歸入了“軟決定論”的范疇即認(rèn)為人可以扮演一種決定性的角色,而另一端則是一種強(qiáng)大的“硬決定論”。此外,還有一種處于兩者之間的“文化、技術(shù)共生論”。但不管是哪種論斷,林文剛認(rèn)為它們并非是僵死的、條塊分割、黑白分明的范疇。在這里,媒介的作用得到了承認(rèn),不同的僅僅是對于他們的解釋與看法的不同,此時“媒介決定論”一詞也就不那么時髦了。
值得注意的是,德布雷則通過分析麥克盧漢的“媒介”概念,進(jìn)而直接解構(gòu)了麥克盧漢的“媒介決定論”標(biāo)簽。在他看來,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一種技術(shù)與用途的混淆,這種混淆使得“媒介”變成了一種未經(jīng)區(qū)分的抽象力量,同時它以鏡像的方式生產(chǎn)出一種想象中的大眾群體,以為媒體就是一種能夠捕捉一切、具有傳染性的“超自然力”,并據(jù)此認(rèn)為麥克盧漢的理論經(jīng)不起推敲。安伯托·艾柯則指出麥克盧漢實際上已經(jīng)把三種東西混淆在了“媒介”之中,即“渠道”“代碼”“訊息”,而麥克盧漢派(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媒介就是一種“沒有訊息也沒有代碼”的媒介。雖然這種評論稍顯激烈,但卻也點出了實質(zhì),即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雖然一直在強(qiáng)調(diào)“媒介”的作用,但這個“媒介”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德布雷認(rèn)為從技術(shù)出發(fā)來思考媒介實際上比從文化出發(fā)來思考技術(shù)更有好處,同時把思想的傳播看作是具有慣性和中性的技術(shù)遷移,即技術(shù)確實在思想的傳播之中扮演著一定的作用。技術(shù)已經(jīng)實實在在地嵌入于我們的生活之中,正如唐伊德所說,這是一種“借助技術(shù)手段與環(huán)境相互作用方式”的開始,“作為身體的我”實際上已經(jīng)與技術(shù)密切相關(guān)了。在這種層面之上,所謂的“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既是事實,又沒有意義,因為它已經(jīng)確實存在了。
由此,隨著不同范式、不同研究取向的進(jìn)入,對于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與“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關(guān)系也在不停地發(fā)生著改變,對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定性不單單只是一個是不是“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問題。在此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不同學(xué)者對于“技術(shù)”的不同理解而導(dǎo)致了對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的不同理解,在此過程之中,“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本身的意義都開始逐漸瓦解了。
四、結(jié)語
隨著學(xué)科的發(fā)展,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實際上關(guān)于“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討論已不僅僅是針對于某個理論是否是“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的討論了,正如胡翼青所說,“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一詞也可以作為一種視角來重新理解和分析傳播學(xué)術(shù)史。對于媒介環(huán)境學(xué)派與“媒介技術(shù)決定論”歷史的探討,不僅僅是對媒介技術(shù)環(huán)境學(xué)派的探討,更是傳播學(xué)對于“技術(shù)”的深入思考,同時也顯示了傳播學(xué)對于“媒介”一詞觀念的不斷變換。林文剛的三種“技術(shù)決定論”視角實際上也代表著傳播學(xué)對于“媒介技術(shù)”觀念的三種轉(zhuǎn)變,從早期的“硬決定論”到中期的“軟決定論”再到現(xiàn)在的“文化、技術(shù)共生論”。關(guān)于討論誰決定誰的問題,不管學(xué)者采取的是哪種視角,可以確定的是技術(shù)本身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今生活世界之中不可逃避以及回避的問題。討論誰決定誰這一類問題的意義則在于凸顯出媒介與技術(shù)的關(guān)系是這一問題的重中之重,誠如德布雷所說:媒介應(yīng)該是一種媒介化的力量,通過這些媒介化,一個觀念成為物質(zhì)力量,而我們的媒體只是這些媒介化當(dāng)中一種特殊的、后來的和具有侵略性的延伸。
(本文系廈門大學(xué)人文社會科學(xué)“校長基金·創(chuàng)新團(tuán)隊”項目“海峽兩岸輿論:動力機(jī)制及其演化軌跡研究”〔項目編號:20720171005〕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②④⑤⑥⑦⑧⑨ [加拿大]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8、28-29、53、25、116、118-119頁。
(作者謝清果系廈門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兩岸關(guān)系和平發(fā)展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研究員;杜愷健系廈門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