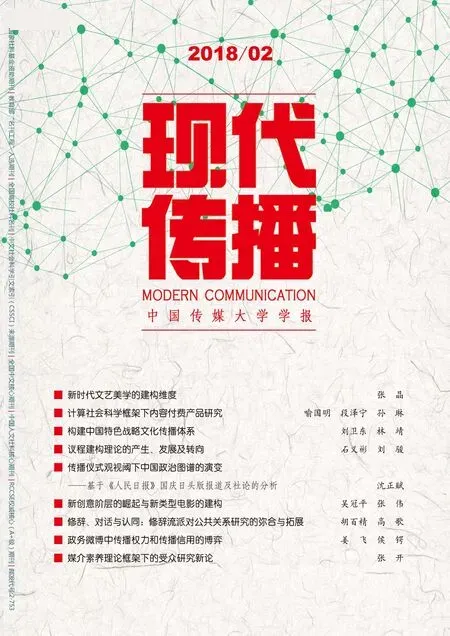手機拍照、社會參與及主體建構*
——基于一個城市中老年女性群體的觀察
■ 孫信茹 趙 潔
在攝影技術普及和個人攝影興盛的當下,肖像照作為個體自我形象展示的方式和手段,既可以記錄人們在某個特定瞬間的狀態,同時又凝聚了人們特殊的情感表達。如果說,過去,拍照大多在較為正式的場合展開,因而拍照也往往會成為一種儀式化的行為,而今天,手機攝影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時,當照片進入到社交媒體后,它不再是沉默不語的圖像和畫面,而成為了可以與他人溝通交流的“媒介”。蘇珊·桑塔格說,“人類無可救贖地留在柏拉圖的洞穴里,老習慣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實本身而僅是真實的影像中陶醉。”①手機媒體的時代,不僅未讓人們走出這種“陶醉”,似乎更加劇了人們的自我欣賞和沉浸。這種拍攝讓不同階層、年齡的人成為完全平等的攝影者。相較更容易被社會認為是攝影文化“活躍者”和“主導者”的年輕人,老年人則往往被視為這一文化行為的“落后者”。然而,手機的出現,使得中老年人的拍照變得輕而易舉,并成為他們生活的慣常表現。不僅如此,這部分人群也借助社交媒體的平臺,將這些照片“公之于眾”,一方面供他人評頭論足,一方面也實現自我的心理滿足和訴求。盡管這個時代人人都在隨時隨地拍照,然而,中老年女性的拍照卻呈現出自身獨特的拍攝和表達方式,而這些照片也和她們的生活境遇、情感表達緊密相關。
一、攝影和自拍的文化意義
在研究者看來,攝影最早的流行,是用來紀念被視為家族成員(以及其他團體的成員)的個人成就的。②在這點上,瓦爾特·本雅明也談到了人像攝影,他強調早期的攝影是以人像為中心的,膜拜價值在人像攝影中得到了較好地體現。③而之后,攝影開始與旅游這種典型的現代活動并肩發展。④旅游成就了攝影,讓攝影變成了一種大眾化的行為。布迪厄的攝影觀則為我們展示了攝影的社會功能,在《攝影:中等品味的藝術》中,布迪厄認為攝影既是家庭團聚所必須的一種儀式,還發揮了社會階層區隔的功能。與其他文化實踐不同,攝影的普及致使不同社會階級對攝影實踐的態度遵循階級優越感的邏輯規則,從而降低了攝影的價值。⑤另外,學者們也從視覺文化的角度來研究攝影或人體肖像。約翰·伯格認為人們的觀看方式受到信仰和知識的影響,他提出,“影像是一種重造或復制的景觀,它體現了一種觀看方法。”⑥國內也有學者指出視覺圖像技術影響著人們對于自己身體的態度,并最終凝聚到了人的肖像意識上。⑦
在網絡媒體的影響下,個人攝影得以完成的技術手段,照片保存、傳遞等方式發生了極大改變,一些學者也對網絡時代的攝影予以關注。比如,有研究者認為數字復制時代的攝影,特別是與互聯網技術、虛擬技術相關的攝影技術,將機械復制時代的視覺的“看”延伸成“體驗的、穿越的看”。⑧有學者提出個人攝影經歷了從“個人中心化”到“社交網絡中心化”的轉變,在這過程中民主性得到了突出。⑨還有研究者提出進入社交網絡時代后,個人攝影已經成為社會交往的媒介,從私人領域進入了公共空間。⑩相較這些研究者對網絡時代個人攝影的討論,還有學者將視角集中在自拍的領域。事實上,在傳統時代也不乏自拍,但是因為網絡技術的出現,自拍更多指人們運用智能手機或網絡攝像頭對準自己拍攝的行為。在新媒體技術的影響下,自拍逐漸得到了蓬勃發展。國內外一些學者多從社會學、心理學等角度來解讀自拍現象,如邁克爾·福斯曼通過對瑞典的四所學校進行觀察,認為自拍是一種社會話語,是性別的自我表現形式。美國學者戴娜·博伊德研究了網絡在青少年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自拍是一種印象管理。Jennifer L.Bevan將自拍視為一種中度甚至是高度的自戀行為。我國則有研究者認為隨著新媒體的出現,手機自拍圖像正建立起新的身份認同、文化主題和社會影響力。一些研究者將自拍的研究對準青年群體,認為自拍是青年亞文化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一種心理反應。
這些研究及討論,為我們進一步理解手機攝影提供了多種視角。然而,手機拍照對于不同年齡層和性別的使用者來說,是否具有不同的使用和呈現?手機拍照在不同的群體中所展現出來的意義和功能,是否具有差異性?我們發現,在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市中老年女性的手機拍照頗為頻繁且具有豐富的呈現與表達。為此,本文試圖對這個群體的手機拍照、上傳肖像照等現象展開解讀。
二、城市中老年女性拍照的觀察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一群生活在昆明的中老年女性,筆者在云南省老年大學中與她們相遇相識。所觀察的這個群體共有25人,其中20人常住昆明,另有5人在昆明和老家時常往返。她們的年齡集中在55至70歲之間,退休之后,她們在閑暇時間去老年大學上課,其余時間主要在幫子女照看孫兒。退休前,這群人的工作性質、生活經歷差異較大,但在退休之后,她們的生活狀態、興趣愛好有著較多的相似。比如,她們都喜歡文藝活動和外出旅行,當然,拍照更是她們的共同愛好。近年來,智能手機在這個群體中日漸普及,25個人都有自己的微信賬號。將生活場景和旅游景象拍照并上傳朋友圈,幾乎成了她們每天必做的事情。她們中甚至不乏微信使用的“重度依賴者”,按她們的說法,每天用微信都上癮了,欲罷不能。
通過對這25個人微信朋友圈中的照片進行統計和分析,我們發現她們的手機拍照呈現出較為鮮明的特征。首先,她們對自我想象和“美”的理解有著自己的呈現方式。照片中人大多衣著鮮艷,各種顏色的圍巾成為她們精心妝點自己的常見物品。雙手上舉,手指上翹;或拿傘,或叉腰,又或擺出某個舞蹈造型;或身姿婀娜,或微笑淡定。盡管照片沉默不語,但卻能感受到她們健康、自信和自得其樂的狀態。和年輕人熱衷美顏相機修圖不同,她們的照片較少修飾。其次,照片對生活與交往場景的呈現較為集中,尤以展示她們豐富的文藝活動為主。看得出,這是一群熱愛廣場舞的女性,照片中她們的起舞場景頗為常見。退休后的日常生活里,彈琴、寫書法、打太極、練劍,無一不被她們記錄到了照片里。呈現和家人、朋友團聚的時光也是她們的最愛。有時,有的人也會模仿年輕人的拍照方式,展現出俏皮可愛的形象。當照片發到朋友圈后,接受贊美或是評論,她們會認真地逐一回復。在對這個研究群體有了較為深入的觀察和交談后,我們將重點放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身上。盡管這些女性的個體仍然具有較大差異,但接下來呈現的這幾個女性形象,從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這個群體中女性的拍照方式和大致類型。
1.展現自我“另一面”的錢麗銘
錢麗銘是云南省老年大學攝影班的學生,今年62歲。上初中時就去當知青,回城后去了政府機關工作,退休后生活相對富足。由于出生在教師家庭,她對文藝有著極為濃厚的興致。在老年大學,除了學習攝影,她還學習詩詞文學。據她說,她每年花在微信上的時間不少于3個小時,她一共加入了15個微信群。群里的成員很多和她一樣,既喜歡在微信里聊天,也熱衷于上傳照片。2016年的一次經歷讓她很難忘:她在朋友圈里上傳了老年大學朋友們集體練習鋼琴的照片,并配上了自己思索已久的文字:“分別才三月,歡聚續琴緣。重議再返校,琴藝花永開。”九張照片配合這幾句精心寫作的文字,在朋友圈備受好評,收獲了上百個贊。她的一位朋友點評:“一群有才的女子在一起就是優雅。”錢麗銘對我們說:“這簡直是對我最大的鼓勵,我上傳照片后可以收獲這么多美好的贊。”而這次的經歷,也使得她極其珍惜每一次上傳照片的機會。她覺得,照片能夠將自己優雅知性的一面展現出來,更讓家人和朋友知道“另一個我”。
女兒長大后就很少和我交流,加之工作繁忙,見面也是很少的。退休前,需要我幫助時才會找到我,例如生活費不足時需要我資助。女兒成家后,她也很少需要我了,交流時間更少了。然而,微信朋友圈的相冊能讓女兒看到我的狀態,我感覺現在女兒對我還是很佩服的。
由于女兒工作忙,外孫幼兒園的作業均由錢麗銘負責,她自學圖像處理技術,完成了幼兒園的電子相冊和視頻制作。錢麗銘似乎也在這樣的圈子里獲得了自信與滿足,這也是她喜歡在朋友圈里上傳照片的原因。同時,讓她沒有想到的是,朋友圈里上傳照片,也讓她和別人有了心靈相通的渠道。她的微信好友有兩百多個,時常保持聯系的是老年大學里的人。一次,她在朋友圈里上傳了6張肖像照。照片中的錢麗銘穿著艷色旗袍,或手拿扇子,或執毛筆書寫,宛如鑲嵌在水墨畫之中。她寫下這樣的話:“做了幾張中式風格的照片,體會中國元素的唯美!”這幾張照片一如既往地收獲不少朋友的贊,還有人將她的照片再次分享。最讓她意外地是來自一位同學的評論:“美女+才女=精品+經典”。在錢麗銘看來,這位同學頗有知識分子的高傲,很少與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交流。同學的評論讓錢麗銘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后來兩人經常在錢麗銘的肖像照片下聊天,這讓錢麗銘覺得她們找到了一種心靈溝通的好方式。
2.不服老的“技術牛人”曹老師
曹老師是這個群體里年紀最大的一名女性,今年已滿71歲,退休前曾是一名中學教師,她被公認為這個群體里的“技術牛人”。退休后才開始學習攝影的她不僅攝影技術好,還精通Photoshop技術,經常教群里的其他女性修圖。盡管曹老師發自己的照片不太頻繁,但一旦在朋友圈發照片,基本都是她手拿單反相機拍照的模樣。最近,曹老師在為老年大學的團隊制作《夕陽紅》MV專輯,內容都是她自己拍攝的照片和視頻。在微信里,筆者注意到一段她們借用酒店通道“玩”時裝秀的照片和視頻。畫面中幾個女性身著旗袍等各式服裝,向鏡頭里微笑示意,盡顯年輕狀態。作為這段視頻的拍攝者和制作者,曹老師十分滿意這樣的“身份”。事實上,這樣的放松、玩樂在她們的生活中也較為常見。
視頻里的我們是不是很“瘋”?我們這群人很瘋狂,我感覺我們這個群體還是很有創造力的,我們哪里老呢。我們很年輕,對不對。
這種表達,展示出這群中老年女性的一種突出形象:不服老,富有創造力,對新鮮事物仍舊充滿了渴求與熱望。
3.追憶青春愛自拍的梁嫣
出生在昆明的梁嫣,父親曾是上海灘名角兒,早年舉家南下昆明。梁嫣15歲時就去到農村當知青,后來,她到了工廠工作,換過幾個崗位,目前還在哥哥的公司里當會計,所以一直未“退休”。梁嫣的哥哥是云南攝影家協會的成員,深受哥哥的影響,她也很喜歡攝影。梁嫣喜歡自拍,更喜歡展示旅游過程中美景和人交融的場景。她最滿意自己去昭通大山包拍攝的一組照片,照片中的她逆光戴著墨鏡,面對鏡頭展開微笑。或許,在他人看來這只是一張極為普通的自拍照,但對她的意義卻是非凡的。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你看陽光灑在我身上,我的身體輪廓都發光了啊。自拍照能看到我喜歡的自己。
另一張自拍照對于梁嫣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去年梁嫣生日那天,女兒帶著全家去爬山,中途,女兒給梁嫣喂了一個剝好的雞蛋,梁嫣很感動,拿手機迅速拍下了這個情景。這張自拍照很特別,雖然梁嫣吃著雞蛋的表情不美,甚至拍出來的臉部有些變形,但畫面卻讓人溫暖感動。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就拿起手機拍下這張照片。但我覺得這是張十分美好的自拍照,我會時常拿出來看,每看一次就覺得十分幸福。
遇到美好的景、美好的事,梁嫣都會“條件反射”般地舉起手機自拍。自拍對于她來說是一種情感表達的方式,更是一種記錄美好瞬間,甚至是幫她追憶過往青春年華的途徑。
4.堅強的李麗芬
李麗芬是一名退休女工,中專學歷,因為所在單位破產,很早就退休了,退休后李麗芬還堅持打工供養家庭。剛退休時,覺得很無聊去香港找同學玩,看到朋友的工作狀態后,她決定留在香港打工一段時間。幾個月的打工經歷讓她感覺自己像白領一般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體驗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生活,也感受到了自己的價值。這段經歷對她影響很大,回來后她并沒有像以前的同事那樣閑下來,而是不停地給自己找活干。后來,她做了一個公司的銷售,每月拿的工資遠高于她的退休工資。在參加公司組織的聚會和培訓中,她找到了歸屬感和自身價值,也是在這里,她跟著年輕人學會使用微信。自從有了微信后,她便成為了“低頭族”,經常被家人調侃去到哪都蹭wifi。而她自己將微信作為學習的渠道之一,認真看朋友圈里的帖子甚至記錄在筆記本上。
李麗芬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遭遇一些事故后成為了“啃老族”,因為要養家,年近七十歲的她仍堅持工作。李麗芬偶爾流露出悲觀情緒,但在外人面前卻表現得異常堅強,正如她在朋友圈照片下寫的話:“內心的強大,永遠勝過外表的浮華。”“一個人最大的失敗,不是貧窮,而是你不但給不了自己希望還消耗著別人的希望。”在朋友圈里,李麗芬十分喜歡上傳自拍照,并配上積極樂觀的話語。她的自拍照,常常展現眺望遠方的自己。有時,她會拉著丈夫一起拍攝,丈夫呆板的表情和她嫻熟的自拍表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也會模仿一些年輕人的表達方式,將當下流行的段子,或是一些營銷式的話語記錄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或許照片和文字并不完全吻合,但通過這種方式,她似乎找到了自我表達的另一種途徑。
三、社會參與及主體建構
本文關注的這群女性,正處于吉登斯所說的“第三年齡”,“這是一個展示終生成就的時期,同時允許個人成長、學習和探索”。退休使這群女性從教育孩子的責任和勞動力市場中解脫出來,進入自己可以支配時間的“自由”生活,比如旅行、接受繼續教育或學習新的技能。然而,面對新的生活,這群女性需要完成角色轉換和心理調適。她們中有的剛從工作崗位上退休,尚未完全適應退休生活;有的則要面對照看孫輩的繁重瑣事;有的漸漸面臨健康方面的威脅。筆者調查的這群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多數為初中、高中學歷,后來又經歷了下崗。訪談中,不少女性自嘲為“文盲”。這種頗有些無奈的表達,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她們對當下自我的理解:曾是國家和體制內被人們看重的一員,而今卻仿佛被時代甩下。與國家干部相比,知識和層次都不如他們,與年紀小的一代人相比,學習能力又遠遠不及,這使得她們心理產生明顯的落差感甚至自卑感。我們的調查對象還有5名是從外地到昆明跟隨子女一起生活的女性,相較生活在本地城市的女性來說,她們剝離了以往的社會關系,在相對陌生的環境中愈加需要重新定位自我身份并建立新的社會交往。然而,生活中的艱辛和大部分中老年女性的不善于表達,使她們更多時候將內心隱藏起來。在訪談中,她們不止一次和我們說起之前的工作和生活很開心、滿足,而現在更多了一些孤獨。
在研究對象中,生活的遭遇和境況各有不同,人生階段的轉型、身份角色的變化難免讓人失落,但由于手機和微信的普遍使用,讓這群女性找到了一個新的傾訴和交往空間。她們運用手機拍照,在社交媒體中對自我形象和生活世界進行展示,一定程度上幫助她們實現情感表達和心理調適。手機拍照,上傳社交媒體,和他人展開互動、對話和溝通,成為她們新的社會參與方式。
具體而言,這里的“社會參與”,主要指的是這群中老年女性通過手機拍照并上傳社交媒體,從而重新建立起她們的社會交往圈子,進而獲得新的交往關系。國外學者Mélanie Levasseur等人認為社會參與是一個人參與社會活動并為其提供社會互動關系的介入程度。按照Bath等人的說法,社會參與也是老人健康和生活質量的重要標準。社會參與反映了個人介入社會的程度,退休的女性從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和過往的很多社會關系割裂,甚至被社會遠離與拋棄,因此,建立新的交往關系對她們來說尤為重要,也是她們積極融入社會的重要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的社會交往關系的建立成為衡量她們與所處社會情境進行互動的重要指標。而微信,恰恰是新的社會關系得以搭建和形成的新平臺。在微信朋友圈里,這些女性上傳個人肖像照,照片在朋友的評論和關注之下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有時,這些評論和新的意義,又會反饋到人們的內心,一定程度上促成她們的自我調適,由此形成這群女性建立自己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方式。一位訪談對象曾在帶孩子的過程中與兒媳發生過一些沖突,她上傳自己的照片后,一些老朋友對她贊美,不僅勾起了她對年輕時的美好回憶,更增強了對當下生活的信心。除了和同齡人重新建立起關聯和社會關系,這群女性也渴望與年輕人有更多的交流。不同的出生年代和生活環境,在她們與年輕人之間形成了很難逾越的鴻溝,但這并不阻礙她們仍渴望像年輕人一樣生活和了解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與年輕人的交往和溝通,也在促成她們的社會參與。這群女性中不乏積極學習和擁抱新技術的人,還有不少人嘗試用最流行的網絡語言為照片做注解。同時,不少女性有過這樣的感受:自己的照片和微信得到子女和年輕人的鼓勵與認同,在她們看來是讓自己更興奮的事。卡斯特曾說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不同形態的社會空間和社會交往。德布雷卻認為,“技術能實現不同區域里不同文化的人之間連接”。一方面,媒介技術在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造成“區隔”,另一方面,它又讓人們得以產生新的連接和共享的意義。從這樣的角度講,與其說這群中老年女性是單純對新技術產生興趣,不如說她們試圖通過這種技術的使用達成與他人對話,尤其是與年輕人溝通的目的。在這里,照片成為中介,就是她們與社會對話交流的一種方式,也是她們展開社會參與的獨特表達。
在手機照片的拍攝和社交媒體的運用中,這群女性還常常通過照片展示個人成就和價值。退休生活讓她們在很多公共事務的參與中喪失了機會,人際交往的圈子和范圍也發生變化。她們在微信朋友圈里常常展示自己的多才多藝,呈現出的多是熱愛生活、參與各類活動、積極向上的生活狀態。照片既是對她們當下日常生活的還原,也折射出她們對個人價值的期許與理解。由此可以看出,這群女性用拍照這種方式能夠進行自我身份的彰顯和表達,繼而在網絡空間中展現主體性建構。
我們所研究的這群女性,她們所經歷的社會情境和目睹的社會變遷大致相似,其中一些人還有過“下鄉”的經歷。退休之后,她們從早已習慣的集體生活環境中脫離出來,慢慢進入到個體化的生活日常中。而今天社會各個層面廣泛凸顯的個人主義風潮,也時常讓她們自小就建立的價值認同遭到沖擊和挑戰。加之這些年城市急速發展和節奏的加快,“為自己而活”的新觀念也在這個群體中逐漸有了一定的影響。即便年老,獨立、不依附男性和一些頗具現代性新女性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感染著她們,建立自我主體性地位的意識形成她們新的追求。在這個過程中,網絡的興起,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運用,為她們在社交媒體中發言、自我展現提供了極為便利和廉價的方式。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中老年女性在參加社會活動,上傳照片凸顯個人成就的過程中,那些健康、自信、獨立、有成就的都市女性形象得到展示。在這個過程中,她們還顯露出刻意淡化年齡因素的心態,盡管身體不可避免地衰老,然而,內心依然保持對美和年輕的追求。追逐和效仿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與表達方式,在現實生活中或許有一定難度,然而在網絡這個獨特的文化情境中,她們卻能實現“移植”和“模仿”。當然,她們的手機拍照也并非全然是對年輕人的追逐和羨慕,她們也在照片中表達對往昔歲月的眷戀。她們拍照的姿態、手勢的比劃、舞蹈動作的呈現等,都留有她們所生活的那個年代深深的印跡,因此她們盡管是獨立個體,但照片展現出來的形象共同性極大。顯然,懷想過往,共同追憶,手機照片在這里成了構筑集體記憶的符號化表達。布迪厄在闡釋“習性”時,曾談到習性使得過去的,沉積在感知、思維和行動的每一種組織形式的經驗,成為鮮活的現實存在。對于這群女性而言,這些長久以來形成的“慣習”,使得這個年齡階段城市女性的照片呈現和形象在很多時候表現出極為相似的特點。加之對她們逐漸形成“壓制手段”的年齡,使她們常常被“放入到固定的、已成成規的角色中去”。然而,今天,我們也看到許多老年人正在“反抗強加于他們身上的這種對待,并探索新的活動和自我實現的方式”。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個人的手機拍照和對社交媒體的運用,正是她們與“受年齡束縛的社會”做斗爭的一種嘗試,同時,也是她們尋求自我身份和主體性建構的重要方式。
主體性身份的建構,常常在人們的社會交往、情感抒發和自我價值的認定等復雜和多重的關系之中建立起來,因而,人的主體性建構往往會和情感表達相連。在現實生活中,這群女性或許并不常常將個人情感輕易表露,然而,在朋友圈上傳的照片中,照片畫面本身就對她們的情感進行了傳達甚至渲染,再配合她們寫下的文字,讓觀者看到她們坦率和直白的表露。
四、結語
本文關注了一群生活在都市中,受過一定教育,退休前有著較為穩定的工作,退休后不必過多為生活、物質擔憂的一群中老年女性,呈現了手機拍照在她們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和功能。對于這部分女性來說,拍照,顯然是早已慣常的行為方式與活動,但在新媒體還未出現或是普及的過去,她們的拍照常常是略顯慎重的,她們會挑一些特定的時空完成拍照。很自然地,照相館、一些紀念性的空間是她們拍照最常選擇的地方。并且那時候的拍照,時間的指向也是較為明確的,拍照不可能隨時展開,特定的時間節點往往是引發她們拍照的好時機。這種情形之下形成的照片,需要她們精心收集或是束之高閣。然而,在今天的手機拍照里,盡管這群女性還是會受到過去生活和社會風潮的影響,一些舊有的方式仍舊留存,但是,我們看到更多的表現是,她們將拍照引入了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時空與情境之中,對照片的態度和理解,她們也有了和過去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說,過去的照片是當她們完成拍攝后,將之收藏在影集里,偶爾等候家人或朋友觀賞追憶,而今天,她們將照片上傳網絡,樂于自己在照片中發表感言,更歡迎他人參與到共同的點評和討論之中。這個照片生成和傳播的最后環節,指向的是拍照帶來的巨大改變:手機拍照,實則就是一種社會交往和參與社會的方式。
更進一步說,手機的照片上傳到微信朋友圈,成為這群女性一個新的“生活世界”,那里是她們文化活動和實踐展開的重要場所。“生活世界可以被視為文化資料的儲存庫,是生活在一起的社群所共享和共有的,其主要作用是促使人類相互間的溝通。”在這種新的共享和溝通之中,這群女性為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性建構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和空間。在這點上,我們當然也可以說,其他群體或許也是一樣的,但是對攝影文化這個領域來說,長久以來,似乎年輕人更具有主導權和發言權,而網絡這種新技術手段的使用和這個新空間的出現,使得那些在新技術面前較為“弱勢”的群體,也擁有了同樣創造文化、表達自我的權力與可能性。
注釋:
①②④ [美]蘇珊·桑塔格:《論攝影》,艾紅華、毛建熊譯,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5、15頁。
③ [德]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頁。
⑤ Pierre Bourdieu.Photography:AMiddle-browArt.Oxford:Polity Press.1990.p.46.
⑥ [英]約翰·伯格:《觀看之道》,戴行鉞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⑦ 李鴻祥:《視覺文化研究——當代視覺文化與中國傳統審美文化》,中國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237頁。
⑧ 韓叢耀、唐悅之:《數字時代的攝影觀》,《新聞界》,2017年第6期。
⑨ 楊莉莉:《從“攝影中心化”到“社交網絡中心化”——中西個人攝影史比較研究》,《中央美術學院2012年青年藝術批評獎獲獎論文集》,2013年第1期。
⑩ 任曉敏:《從個人攝影的轉變看社交網絡時代的人際交往》,《新聞大學》,2014年第5期。
(作者孫信茹系云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趙潔系云南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