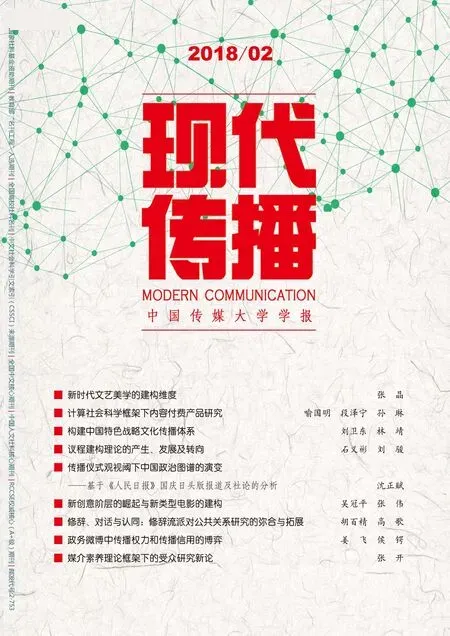從空間轉向到空間媒介化:媒介地理學在西方的興起與發展*
■ 謝沁露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空間理論研究思潮引發了一些學科圍繞著空間論題開展了交叉融合的跨學科研究,“西方文化思想界興起發動的空間理論轉向,對當代西方社會生活、文化政治和學術思想產生重大影響”①。在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思潮的文化影響下,文化研究與新文化地理學研究(文化地理學的分支)相互“文化轉向”,逐步將研究視野轉向了“空間”。上世紀末期,文化研究與新文化地理學研究進一步與媒體、傳播研究相結合,圍繞空間生產理論與大眾傳播、地方社會文化生產等新的研究題域產生的“媒體與傳播的地理學”(即媒介地理學,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或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逐漸成為媒體與傳播研究、地理學研究的新興焦點。該學術領域發展至今,以跨學科視角,在以歐美國家為主的西方學術界已經成為媒體與傳播學研究、地理學研究的一個新興學科分支。
媒介地理學是一個典型的媒體、傳播、地理與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交集下產生的跨學科交叉研究,既是一種研究思潮,也是一種現象;既是一個研究過程,也是一個研究結果,還是媒介作用下思考空間與地方問題的一種方法論。我國學術界對媒介地理學的關注研究多集中于近幾年,對國外媒介地理學發展研究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成果譯介較少,尚未激活媒介地理學研究興奮點。但媒介地理學研究的潛力是巨大的,也逐步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②。本文在文獻回顧基礎上對國外這一支學科分支的興起進行學術背景介紹,試圖通過對國外媒介地理學研究的背景和歷史階段、研究內容、研究特征的梳理及發展趨勢的探討,展現其從最早的空間轉向研究到當前空間媒介化的發展脈絡。
一、媒介地理學興起的背景
媒介地理學研究興起的時間較晚,概念緣起至今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歷史溯源。20世紀50年代,加拿大學者哈羅德·亞當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出版的《傳播的偏向》探討了空間時間與地域、政治、權力、文化、宗教之間的關系模式并“確定了媒介的屬性:媒介在時間和空間上對社會組織產生決定性的影響”③。1964年,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中也對時間的訴求和空間的問題進行了闡釋,認為“每一件物體或一套物體憑借它與其他物體之間的關系而產生自己獨特的空間”④。同一時期,法國著名社會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1967年做了一場題為“其他的空間”的演講中提出:“當前的時代或許應是空間的時代……我們在時間上經歷的經驗的世界遠不如空間網絡點的連接與交叉所形成的混亂的網絡中獲得的多”⑤。
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德國的地理學家開始關注大眾媒體(更明確的說是當時的報紙)的空間組織與分布問題”⑥。1965年,在美國傳播效果研究受到推崇的背景下,瑞典地理學家托斯滕·海格斯特蘭德(TorstenH?gerstrand)發表文章運用創新擴散理論對瑞典城市的使用時間與城市規模之間更精確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以闡明“社會傳播在創新擴散中的作用”⑦,同時他還通過農業社區的傳播研究發現農業社區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關系⑧。1974年,美籍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出版了著作《戀地情結: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觀研究》⑨,基于地方現象與人的感知經驗結合,以他獨特的“人文主義”視角提出了“戀地情結”(Topophilia)的理論概念,解釋因感情聯系而產生了人與地方之間的關系,人對地方的感知、態度、價值觀和世界觀等。其后的文章⑩中也認為地方感應包括對地方客觀特征的依戀與想象,因為“想象力是一種對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則是想象力的產物。人類歷史的發展離不開人的想象力”。加拿大地理學家愛德華·雷爾夫(Edward Relph)于1976年出版了《地方與無地方性》一書,他通過探討地方的地理現象與日常生活經驗之間的關系,重視個人第一手經驗對地方的決定性意義,得出“生活的世界充滿了第一手經驗,媒體提供的只有二手經驗。因此,媒體與時空扭曲”有關的結論。
從上可見,雖然有學者思考媒體與地理、空間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關系生產問題,多是基于研究者的興趣,離真正意義上的研究相去甚遠。“沒有一個學者、獨特的事件或具體的出版物可以被看作是媒介地理學的發起者或開始。相比之下,傳統研究運輸地理、交通地理,如擴散理論的研究和時空壓縮的工作,可以看作一個媒介地理學研究的先驅”。
伴隨著戴維·哈維(David Harvey)、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以及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愛德華·索杰(Edward W·Soja)對空間問題的理論分析與探討,地理學者在研究中不斷結合媒體的效力,關注文化地域的空間問題如何被不同的媒體以不同的角度表述與提出。80年代初期文化地理學家關注新聞報道如何對空間區域進行覆蓋,涌現出第一批對媒體與地理關系研究產生興趣的地理學家及相關研究。從內容上來看,主要討論內容包括:媒體地理的主要理論在環境背景下的影響、新聞報導的空間偏見以及大眾媒體和空間意識、媒介對空間領域進行區域的類別生產與認同的可能、新聞的空間信息內容等;從研究者地理位置分布來看,代表學者有瑞典地理學家海格斯特蘭德、加拿大地理學家拉爾夫、澳大利亞地理學家D.J.沃姆斯利(D.J.Walmsley)、德國地理學家漢斯·海因里希·布洛特福格爾(Hans Heinrich Blotevogel)以及英國杰奎琳·伯吉斯(Jacquelin Burgess)和約翰·戈爾德(John Gold)、芬蘭地理學家安西·帕西(Anssi Paasi)等。
到80年代中期,新文化地理學者率先展現出媒體與地理研究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1984年,德國地理學家布洛特福格爾通過日常報紙的空間組織對中心區域空間、日常報紙以及廣告市場三者關系的傳播功能區分,認為媒體是地理研究的一個課題,分析出區域報業市場的存在以及對結算系統的依賴是由報紙的出版場所和流通領域決定的。二是專門的媒體、地理與大眾文化研究文集的出現。1985年,英國地理學家伯吉斯和戈爾德編寫了《地理、媒體和流行文化》的文集作為第一部明確地指向這個主題的書籍出版,該書“主要的方法論靈感來源于英國文化研究,特別是關于媒體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受眾積極塑造媒體產品的意義問題,主要是當時在編碼和解碼方面展開的爭論。”文集的出版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升了研究的意義,明確了媒體、地理與大眾文化的關系及討論的重點,為媒介地理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思想及方法論的啟示。
“空間理論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是空間生產作為一種媒體和社會實踐的結果”。同一時期的社會學家也沒有忽視媒介與地理之間存在的關系問題。1985年,“社會心理學家喬舒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在傳播學者英尼斯和麥克盧漢媒介理論基礎上,結合戈夫曼(Goffman)的心理互動出版了對媒體研究空間轉折的重要貢獻。他斷言,電子媒體不僅改變了人們對空間的看法,而且還促進了社會角色和社會的改變。”而“以英國社會學家格雷戈·費羅(Greg Philo)為首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Glasgow Media Group)開展了關于主流電視新聞報道與礦工罷工、福克蘭群島沖突、權利、性別和空間相互關聯的創新研究,并成立了‘女性與地理研究小組1984’”。
文化研究學者戴維·莫利(David Morley)是較早關注空間與微觀地理關系的學者,在電視成為焦點的時代,發表了《全國的觀眾》和《家庭電視》。莫利以民族志方法關注電視與日常生活的空間地理(區域)關系,“延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編碼/解碼理論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的焦點小組訪談,了解不同社會群體解讀國家范圍時事電視節目,以及這些合成模式如何闡述社會經驗”,總結出電視對私人和家庭公共空間的關系和建構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而后在《家庭電視》的研究中莫利通過觀察家庭收視行為及情況,以家庭性別權力關系為主題,從觀看電視的行為復雜性中分析性別的權力動態與觀看電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密切關系,展示出在“家庭”這一微觀區域中存在性別權力與地位的問題。
就整個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研究情況來看,早期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媒體與傳播研究,文化研究學者以及地理學者對媒體與大眾文化產生“空間文化轉向”的研究興趣而出現。這些新的研究興趣雖然不是系統性研究,看上去也是薄弱的,媒介地理學也還遠不夠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分支出現,但對后來媒介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跨學科思想延伸和一個令人興奮而有趣的研究方向。
二、媒介地理學的確立與發展
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是媒介地理學確立的重要時期,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大眾媒體成為人類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改變并影響了人的生活與社會文化發展,也引起了學者對于大眾媒體與環境之間的關注。1984至1997年期間,延續了段義孚(1974、1977)人文主義景觀與環境感知的研究,以美國學者利奧·佐恩(Leo Zonn)、斯圖爾特·艾特肯(Stuart Aitken)、克里斯蒂娜·肯尼迪(Christina Kennedy)、克麗絲·盧金比爾(Chris Lukinbeal)為代表的美國地理學者關注電影文本敘事和結構與人、環境背景之間存在什么樣的相互影響,成果豐富。相互影響論成為了這一時期美國學者討論媒體與地理的主要理論。1987年,在文化研究思潮的時代背景下,英國地理學家伯吉斯在其《景觀客廳:電視和景觀研究》一文中建議語言學和符號學是用于分析風景的合適工具,提出索緒爾的語義學和皮爾斯的符號學思想對于圖像的意義生產和解釋具有一定的作用。她“以傳播學為研究對象,提出了地理研究議程……應用文化研究中的理論觀點,從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中得到證據來證明環境意義在不同形式的媒體文本中被編碼的方式,以及由不同群體組成的受眾的解碼方式”。與莫利和他的受眾研究一樣,伯吉斯“參考了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和斯圖亞特·霍爾的工作,試圖在地理學中建立媒體研究的環境氛圍。”她認為媒體的地理學應該考慮四個方面內容的研究,分別是:媒介文本背后的生產過程、文本本身、讀者對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讀、以及將這些意義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這篇文章,被稱為“媒介地理學研究的關鍵部分”,“不是作為地理學家研究媒體的一個‘秘方’,相反的是,伯吉斯從文化和媒體研究的視角提出更廣泛的地理研究”。
此后,芬蘭學者帕西對大眾媒體與地理關系的研究做了進一步探索。他的作品關注文本、自傳、人的故事、地理教材、符號、地圖、繪畫和照片的表征、符號和隱喻。1989年,帕西在他的《媒體作為地方和區域文化的創造者》一文中討論了大眾媒體如何創造地方及區域的文化以及區域文化的主題與身份塑造、維護身份問題。此文延續了他1986年對報紙如何影響芬蘭四省區域意識問題的研究,關注地方和地方廣播、電視、報紙等大眾媒體如何創造特定的區域身份構建,突出大眾文化的發展與區域地方存在的特定關系,也提出大眾傳媒積極生產和維護的刻板印象,不一定會促進形象建立反而有反作用。另一位英國的地理學家吉莉恩·羅絲(Gillian Rose)偏好通過視覺材料分析和追蹤圖像如何生產展現出一個特定的世界。羅絲通過調查研究視覺生產、媒體產品和受眾,“形成了她以分析討論羅伯特·杜瓦諾(Robert Doisneau)的照片為基礎,包括對圖像的生產情況問題,在圖像本身的動機和顏色選擇,以及不同的觀眾和他們對圖像的形象解讀問題……證明了受眾意義生產的多樣性文化研究”。
20世紀90年代,列斐伏爾引入了“社會空間”的概念,從社會與空間的本體性關系的關注進一步延伸到社會空間所生產出來的空間構成、空間實踐過程與空間表征。多琳·瑪茜(Doreen Massey)在這一時期也將研究視角轉向了空間、地方與社會關系產生的問題,她的作品《空間、地方與性別》(1994)從女性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批評的視角展開空間與地方的認識。1996年,受列斐伏爾和福柯的啟發,索杰提出“第三空間”(Third Space)概念,超越和取代二元知識,提出在地理范圍的想象中現實空間與想象空間的探索。從文化研究批判視角,“鼓勵你用不同的方式來思考空間的意義和意味,思考地點、方位、方位性、景觀、環境、家園、城市、地域、領土以及地理這些有關概念,它們組構成了人類生活與生俱來的空間性……以期打開并且擴展你先已確立的空間或地理想象的范域和鑒別情愫”。
空間論的進一步探討與展開很快引起了媒體和傳播學家對空間維度的興趣,研究焦點開始明確地轉向空間,開展了與地理學者相對應的研究。1995年,莫利和凱文·羅賓斯(Kevin Robins)論道:“我們看到,正在重新構建信息圖像空間并形成新的傳播地理……我們正在大大改變空間與地域的概念”。明確提出現代媒介對于我們想象時間和空間的方式具有構筑新地理的效應影響,并進一步思考媒介如何參與到日常現實地理與虛擬地理中“電子媒介構建虛擬時空和虛擬社會群體的新體驗”。在談到媒介新秩序下地方文化與政治、社會的關系時,他們認為全球化與認同感的危機帶來全球媒介的新景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術已經形成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過程,產生了媒介作用下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矛盾下空間及地方發生變化,即“解域化”“再地域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等現象功能。也就是在虛擬與現實中交錯進行的空間實踐產生了空間壓縮、空間折疊、空間拉伸和地方想象等新的空間問題。這些現象的形成與媒體技術和電子通訊技術的發展緊密相連,虛擬可移動、多層想象的空間結構是空間實踐過程中產生的空間屬性,是時間與空間在各種社會關系連接下形成的多重而復雜的空間幾何關系。
從研究內容來看,超越了早期主要通過“對地方的意義生產和如何促進改造,規模重新配置”的媒體文本分析研究,呈現“以媒體為焦點,研究文本與文本閱讀的意義,轉移到文本與媒體作為實踐的更廣泛的基礎上發展”。同時結合批判性思維探討不同社會空間下的社會階級、人文、政治、經濟、種族、性別、消費、女性主義、霸權等問題。20世紀末的媒介地理學研究呈現出以利奧·佐恩、斯圖爾特·艾特肯、克里斯蒂娜·肯尼迪、克麗絲·盧金比爾等學者為代表的美國電影地理學研究;以愛德華·雷爾夫、杰奎琳·伯吉斯、約翰·戈爾德、托斯滕·海格斯特蘭德、漢斯·海因里希·布洛特福格爾等學者為代表的地區媒體與地理空間意識問題研究;以吉莉恩·羅絲、安西·帕西等學者為代表的媒體對地方與區域文化創造的研究和以多琳·瑪茜、戴維·莫利、凱文·羅賓斯等學者為代表的特定區域與媒體關系研究的學科研究分布地圖。
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的前10年是媒介地理學研究最關鍵的發展期。首先是跨學科的領域交叉研究使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相關研究討論。在早期研究思潮發展關系的延續下,形成了以歐洲(瑞典、芬蘭、丹麥、英國、德國等)與北美地區(加拿大、美國)為代表的兩大媒介地理學研究陣地。研究內容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但整體研究趨勢相同。鑒于下面要討論研究的特點與趨勢,此處不再對派別的發展進行介紹。更重要的是,媒介與日常生活存在一種明顯或隱藏的空間關系,即空間作為媒介的體驗與實踐滲透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和想象中,空間的生產也成為了一種媒介,展現出空間奇妙而豐富的人文與社會內涵,呈現出空間媒介化的特征和作用。其次是新技術下地理信息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GPS)、數字遙感系統(RS)、計算機的技術協助了媒體報道對于地域、空間信息的數據采集、儲存、分析、顯示和描述,使多媒體融合更加順應全球數字信息化、移動全媒體可視化的發展而融入人類日常生活。也使空間壓縮、空間折疊、空間拉伸和地方想象、地方感知等新的空間思維關系與媒介傳播之間明與暗、虛與實的關系更進一步凸顯。
與此同時,進入21世紀的媒介地理學研究伴隨著新青年的崛起涌現出大量專門的媒介地理學綜合性研究論著。這些著作綜合了相關內容、理論、視角、實踐等多方面不同類型的研究,為媒介地理學成為一門學科分支及發展奠定了基礎。德國美因茨大學從2008年開始推出的媒介地理學研究系列著作“美因茨媒介地理學系列叢書”(Media Geography at Mainz)陸續出版,成為德國媒介地理學研究的代表陣地。在多方努力下,媒體、傳播與地理作為一門專業進入大學成為一門學位課程;專門的媒介地理學雜志《以太:媒體地理雜志》(Aether:The Journal of Media Geography)在美國誕生;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成立了“媒體與地理學專業組”。媒介地理學,正式以地理學科中的一個分支的身份,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子領域受到關注與認可,并逐步構建了較完善豐富的媒介地理學研究共同體,形成一支典型的跨學科結合的研究分支。呈現出以保羅· C·亞當斯、朱莉·庫普勒斯、克麗絲·盧金比爾、蘇珊· P·梅因斯、安德烈·約翰遜、杰斯珀·法爾克海默、肖恩·穆爾斯(Shaun Moores)、吉姆·克雷恩(Jim Craine)、賈森·迪特默(Jason Dittmer)、凱文·格林(Kevin Glynn)、印加·薩羅瓦拉-莫林(Inka Salovaara-Moring)等為代表的媒介地理學研究者和以美國北亞利桑那大學、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德國美因茨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英國鄧迪大學、瑞典馬爾默大學、瑞典隆德大學等為代表的媒介地理學研究重鎮,積極熱情地帶領著一批年輕的學者從事相關研究,深入研究的著作也仍在日益增多,他們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推動了媒介地理學研究學術地位的鞏固與研究的深入發展。
三、國外媒介地理學的主要特點與研究趨勢
從媒介地理學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媒介地理學經歷了復雜而豐富的理論與經驗分析,凝聚了許多國家地區幾代研究者的智慧。當下的媒介地理學研究在積累中逐步深入與系統化,呈現出其特點及研究發展趨勢。
(一)國外媒介地理學的主要特點
從上個世紀后半期至今,國外媒介地理學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媒體、傳播與新文化地理學研究的空間轉向
現有文獻的回顧展示了國外媒體與傳播研究者早期關注了“空間轉向”話題,但媒介地理學首先發起于西方新文化地理學的學者受文化研究的影響對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及空間關系的關注,最終結合媒體與傳播研究成為一個研究分支。盡管相關研究在早期延遲且薄弱,但在該領域的發展是積極而有潛力的,這種現象的一個解釋在比較晚的現在被認可為一種“文化轉向”的理解。媒體與傳播參與了社會發展與社會空間的生產,與流動的空間和地方空間之間存在著多樣且復雜的意義生產和交流互動,媒介的出現意味著空間和地方的出現,媒介研究的空間轉向是社會發展的自然轉向。同時,“地理和傳播之間的聯系在于,所有形式的傳播都發生在空間,所有空間都是通過傳播的表現形式產生的。換句話說,空間生產理論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為傳播和介導的理論。”尤其是20世紀末,“在列斐伏爾的影響下,曼紐爾·卡斯特爾、戴維·哈維、愛德華·索賈等將結構主義、社會批判理論與后現代主義相結合,進一步發展壯大了社會空間理論”。在媒介地理學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中,空間理論與媒體、傳播理論的結合一直與媒體、科技信息技術和時代社會的發展齊頭并進,使得媒介與地方、時空的關聯越來越緊密,媒體傳播與地理時空之間存在一種既相互影響又相互依存,既互相照應又互相生產的關系,相關的不同媒介產生了不同的空間、不同的生產過程和不同的理解。
2.明顯的文化研究的焦點
英國文化研究為媒介地理學研究的早期工作提供了“主要的方法論啟示”,而從文化地理學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新文化地理學“是與當時英國的文化研究運動、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論、法國的后結構主義背景以及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批評的興起聯系在一起的”。他們認為空間與地方本身就是社會重要的一部分,空間研究是社會研究的一部分,“將文化視為空間過程的媒介,認為文化是通過空間組成的,是日常的生活的實踐,不同的空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經驗、意義、進程;關注了地理學家們很少關注的社會生活領域,提出精英群體對空間和文化的權力、支配、控制等問題……”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使人類的空間與媒體、世界、傳播、信息、時間緊密關聯,構成并創造了更為豐富而復雜的日常生活實踐與經驗,擴展了經濟、政治、消費、文化、身份、行為等社會問題的空間性,這些關聯點的形成產生了媒體、傳播、空間、地方四個象限下的新的文化研究焦點,也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社會關系、價值與文化表征。使文化研究開啟了新的多領域而又有價值的交叉學科研究路徑。
3.媒介的空間生產與空間的媒介化解釋
經歷了從媒體對地方、空間的傳播生產研究到以媒體為焦點關注媒體創造建構了什么樣的現實與想象的空間、地方及社會,再到形成以空間、地方為介導的空間媒介化研究。媒介地理學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是:媒介的空間生產與空間的媒介化解釋。與早期關注大眾媒體影響下空間與地方的生產不同的是,空間與地方開始作為媒介,執行媒介的生產與傳播功能,體現出空間與地方的特質及關系。“空間媒介化”是空間再生產再建構的路徑,對于解釋空間的虛擬與現實,超現實與超空間,空間隱喻與想象的空間以及空間地方感知等現象,更符合網絡與融媒體時代的空間關系。“‘媒介化’概念鼓勵我們捕捉復雜的社會變化過程,……通過在日常實踐和(超)結構條件下的社會力量相互作用而發展起來的,而這種概念并不意味著改變只會影響某些個人或暫時的情況。媒介化指的是更大的圖景。這就是為什么這個概念引入到與現代社會平行發展的理論中去,尤其是個性化。”因此,空間與地方是媒介生產的結果,也是生產媒介的媒介。媒介傳播既是起因,又是過程,也是結果,是普遍的也是個性的,詮釋著空間生產力的強大與變化。
4.研究整體呈現出混合且高度零碎狀態
不限制于固有的科學話語,媒介地理學多學科跨域交叉研究的性質決定了它的研究必然是復雜而豐富的。從上個世紀至今,整體上來看,媒介地理學的研究是比較獨特而少量的。無論是研究對象、內容,還是研究者身份、研究歷史、研究方向和目的,媒介地理學研究是混合的、令人興奮的、高度零碎的,“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或單一奇異的重點”,讓人望而生畏又難以回顧。“這門學科的碎片化本質是一個弱點,也是一個更緊密合作的獨特機會”,展現出媒介地理學豐富而廣泛的勢態。也正是如此,每一個研究成果的問世,都不可能包括媒介地理學研究的所有領域。時代的變化發展,物理空間的現實生產、價值和改變,與文化研究相聯系,參與了社會文化的變化與發展。我們欣喜的看到空間、地方、時間的多元交叉點也逐步受到關注,在許多問題領域都出現了媒體、傳播與地理之間的重合。
(二)國外媒介地理學研究的主要趨勢
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媒介地理學經歷了媒體觀照下空間與地方的生產、空間轉向認識論的討論、空間介導理論與實踐生產分析再到空間與地方自身媒介化再生產研究的理論與經驗分析,以及對空間想象的介導等研究發展歷程,呈現出其獨有的研究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1.從分歧到融合的研究
從媒體與傳播、地理學的相關文化轉向研究以來,學者們各自均立足本學科視角方法進行研究,得出各自研究的認識與解釋,因此,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首先是概念定位分歧:北歐學者認為媒體研究的空間轉向產生了“傳播地理學”,通過地理學家和媒體研究者的合作在文化研究領域產生一個獨立的研究區域。而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學者認為媒介地理學研究始于新文化地理學,盡管主要研究方法的靈感受文化研究啟發,但媒介地理學關注的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問題始終是圍繞不同地理維度展開的,是地理學研究中一個新興而重要的研究分支,是“媒體與傳播的地理學”。其次是派別的分歧:《地理,媒體和大眾文化》的編輯指出“歐洲和美國的研究之間存在根本的分歧”“美國學者采用了一種基于傳輸者(多個)和接收者(多個)之間的傳輸模型,都是個人和重點轉移保真度的構思,以及對人們的觀念和行為的影響,有點刻板的特征;相比之下,歐洲人把框架傳播作為一種社會力量,采用主張社會模型,揭露和批判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和范式。”然而隨著當代學術研究高度關聯與學科交融的增加,歐洲與美國學者的合作研究越來越多,開展了多方面的合作,界限已經模糊,“這個鴻溝基本消失”。格林和庫普勒斯(2017)認為“我們對‘傳播地理’或‘媒體與傳播地理學’沒有根本的異議,因為它是一個松散的學術研究領域的名稱。在這方面,我們的方法主要是務實的。”媒介地理學研究總體呈現出研究的融合態勢。
2.從空間轉向到空間媒介化的研究
萬事萬物皆可為媒介。作為一種中介體,媒介介入的動作狀態,在社會與文化中扮演著介導的角色,引導了包括媒體在內的敏感介質的區域關系連接,產生了新的空間和地方。早期空間轉向的研究主要關注“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媒介”如何影響、改變、生產了空間。報紙、廣播、電視、雜志、電影等大眾媒體通過文字、圖像、音頻、同期聲、視頻新聞等符號,構建起信息涵蓋范圍內多元文化社會“中心—周邊”的空間、時間、地域關系,以媒體為中心產生的周邊相關內容對空間進行了分解,生產出新的空間及社會文化問題,凸顯了大眾媒體的象征性、建構性與權力。新媒體技術下以融媒體為主流代表,在空間分解和空間生產的基礎上生產出空間折疊、空間壓縮、空間拉伸、空間想象與感知等現象,進一步進行空間再生產,衍生出符合當代信息對人類社會、文化產生重大變革和影響的生活習慣及觀念,凸顯了信息時代空間媒介的虛擬性。時下,以環境、景觀、氣候、文化、地點、事件、美食、服飾、音樂、歷史背景、情感等為代表的“非媒體為中心的媒介”在人類日常生活實踐、互動和體驗感知的過程和結果中,各種不同的元素與符號疊加起認知的代碼,更加突出了媒介介導下虛與實的空間介導感知。在普遍中強調了地方空間維度的特別之處與獨有的“地方感覺”,形成了特定的空間想象、感知與流通,顯現出空間媒介化的特征。因此,空間媒介化作為一種虛實相間的交流形式,連接了事物之間可持續性發展的關系,成為媒體、傳播與地理之間多維界面的研究趨勢。
3.從虛擬到現實的研究
“大眾媒介給地理學家及其相關領域帶來了一個有趣的空間問題,這不僅是因為媒體代表的是世界、個人和社會概念的一部分,而且是因為媒體具有概念化和傳播政治思想、加強霸權秩序的力量”。而在迷戀移動媒體的時代,空間的媒介化下時空轉移帶來了白日夢的實現也帶來了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想象與不確定性。一方面是媒介、傳播與地理的關系是每一次虛擬與現實的連接,過分的強調并關注媒體與空間媒介化議程產生的新形式與問題,以及以非媒體為中心的媒介空間生產了種種假設與想象帶來新鮮感,而較少“嘗試連接空間與生活世界問題的媒介化概念”;另一方面,全球數字信息技術融合帶來媒體、視覺數字信息化與地理空間科學技術(如衛星定位系統、地理信息系統、遙感技術等)的空間結合。媒介化的數字地理知識與媒體傳播的數字化解釋,打破了傳統媒體平臺二維的空間理解,展示了空間媒介與媒介空間的網絡數據化形態。“媒體研究的分析框架需要對媒體進行‘中心解構’,以便更好地理解媒體的發展進程及其與日常生活的關系”。面對未來傳播科技發展建構起來的虛擬世界,“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去媒介中心化的媒體研究模式,從而理解新老媒體彼此的適應和共存共生的各種方式”。與生活更貼近,在日常感知、互動和體驗中關注生活具體化實踐的現實生產,使數字化信息空間更加體現出數字化生活空間,讓過程與結果更接地氣,更形象生動,更有說服力是媒介地理學未來的發展方向。使媒介地理學結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更真實地進入日常生活研究中,跨越虛擬環境,結合現實在媒介環境中的體驗與實踐。
4.空間的不平等與威脅
媒體、傳播與地理學的結合也帶來了空間的不平等與威脅問題。首先,“空間也充滿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再現的空間是‘被統治的空間’”。在介導的過程中,涉及權力分配和使用的空間生產及關系便會帶來空間分配的不平等與不平衡;其次,媒介空間的界限模糊使得移動、技術融合、互動下無空間界限的電子監控深入了日常生活當中,產生了私人生活如監獄般受到控制等隱私監控問題;再次,媒體的出現減少了人類面對面交流見面的機會,改變了群體活動、社區活動等共同活動空間的原有地位,尤其是“過分依賴虛擬電子連接破壞了我們與實際物理位置的聯系,威脅到我們的公共空間交流,在網絡空間漂流”。此外,在空間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空間和地方會經歷折疊、壓縮、延伸等空間形態的變化,帶來了空間形態的不平衡現象。空間被先進的通信技術所替代的同時,空間與地方的位置是媒體和通信技術控制下的地方感,形成了“超空間的移動空間控制”。還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大眾媒體、社會文化、集團企業、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等在內的介質,在介導過程中空間的時間表征與時間的空間再現會呈現不均衡的現象。直接或間接地呈現出“時空扭曲”,削弱了地方(或空間、景觀等)身份的代表性意義和定位再生產。因此,媒介對空間的影響也存在空間分裂,促進了空間發展也影響并約束了空間發展,這種對立又統一的空間辨證關系在虛擬與現實的空間環境中決定了我們需要思考空間生產如何有序地存在。
四、結語及局限性
本文從媒體與傳播的地理學研究發展的歷史線性實踐出發,分別從媒體與傳播研究、地理學研究兩個學科領域為切口進行分析,試圖在“媒體、地理與空間研究”的脈絡中尋找其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進程、特點與研究趨勢,呈現出從上個世紀學科之間空間文化轉向思潮下的研究發展到當今時代下產生空間媒介化為新特征及趨勢的研究。因媒介的快速變化發展帶動著媒介地理學研究的變化發展,媒介地理學也呈現出復雜分支態勢,在歷史溯源方面,本文只聚焦至21世紀前10年媒介地理學研究。同時作者自身文獻參考視野與文章篇幅有限,在本文歷史梳理中難免有遺漏局限,此文僅為我國發展中的國外媒介地理學的研究作以借鑒參考之意義。
注釋:
② 參見熊壯、方惠、劉海龍:《2016年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1期。作者以2016年中文新聞傳播期刊中傳播學方向的論文為基礎總結了2016年中國的傳播學的重要議題與主要成果。指出我國傳播學研究集中在包括“城市傳播與媒介地理學”在內的十個領域或話題。
③ [加]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譯者序言。
④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頁。
⑤ 英譯本見Michel Foucault,OfOtherSpace,Diacritics,vol.16,no.1,1986,pp.22-27.
⑧ Bo Lenntorp,Gunnar T?rnqvist,OlofW?rneryd,Sture?berg,TorstenH?gerstrand1916-2004,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Human Geography,vol.86 issue 4,2004,p.325.
⑨ 參見Tuan,Yi-Fu,Topophilia:AStudyofEnvironmentalPerception,AttitudesandValue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74.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工程師,澳門科技大學傳播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