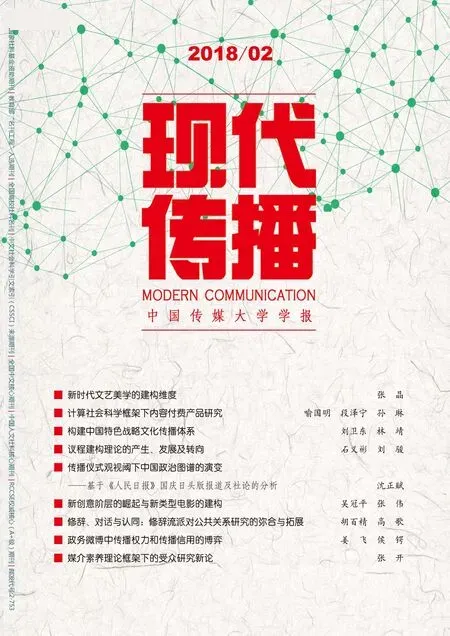海外民族志:中國民族志紀錄片新視野*
■ 王慶福
民族志是一種寫作文本,是人類學的獨一無二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建立在參與觀察的基礎上,用來描述文化,以此來解釋社會現象并提出理論見解。用民族志的方法進行紀錄片創作形成民族志紀錄片。近年來,伴隨著“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中央電視臺相繼推出了《魅力肯尼亞》《絲路,重新開始的旅程》《與全世界做生意》等一系列記錄海外不同國家民族風情、經濟生活的紀錄片。由于其取材內容與表達方式與傳統的民族志紀錄片完全不同,因此如何認識這類紀錄片的價值就成為本文的重點。
一、東方視角審視他者
他者乃自我以外的存在,在民族志紀錄片中,他者是與自我相異的文化,民族志紀錄片的創作不僅僅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相遇,同時也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對話。作為文化的持有者,紀錄片人必須將自身的文化理念融入其中,借助影像形成對他者的審視。遍查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可以發現“和而不同”與“生生不息”兩種文化理念。
1.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最早出現于《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在為人處世方面,正確的方法應該是拒絕茍同,在相互爭辯中達成共識。在創作中,這一觀念被紀錄片人所吸收,并呈現于作品中,如紀錄片《魅力肯尼亞》第一集《大地的呼吸》開篇:
肯尼亞馬賽馬拉國家公園機場,職業導游彼得正在等待切爾西和布萊德,一對來自英國的情侶……
仔細閱讀這一段落就會發現,相校于西方人拍攝的民族志紀錄片,這里的主客位置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西方民族志紀錄片無論是《北方的那努克》、還是《一個叫做蜂的部落——研究亞諾瑪米人》都將拍攝者設定為第一敘述人,通過“我”的講述去發現被講述者的世界,伴隨著“我”的講述,觀眾如同拍攝者一樣,被設定為文明人去發現被拍攝對象的原始與神秘,進而產生好奇心。這種視角本身就是建立在殖民者對自我身份反思基礎上的,西方人類學家拍攝這些紀錄片的目的在于將“他者”的世界當作“我者”世界的對立面,并以“他者”世界為鏡,去發現“我者”世界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因此他們作品中的“他者”,總是一個基于自我意圖的“他者”。而在《大地的呼吸》中,則是當地人彼得以這片土地上主人的身份,迎接來自英國的情侶切爾西和布萊德。影片通過切爾西和布萊德的游歷,呈現出非洲大草原上人與自然和諧的壯觀場景。“他者”與“我者”的易位,使原來被視為弱者的民族具有了真正的話語權,從而為民族志紀錄片建立起更為平等的對話機制。
2.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來自中國的古代哲學,指變化的發生和新事物的產生。①中國人認為,世間萬物之所以存在,乃陰陽互相,化育天地而生生不息。用“生生不息”的原則看待世界會發現生命是一個綿延過程,作為發展的一個階段,任何形式的文化都有著自身存在的價值。以這一理念指導創作,將不同文化收入作品,使紀錄片具有展示多元文化的魅力。如“魅力世界”系列中,紀錄片《魅力津巴布韋》記錄現代化的大學與古老的繪畫;紀錄片《魅力肯尼亞》中呈現鉆木取火與現代化的劃艇;特別是紀錄片《魅力斯里蘭卡》講述斯里蘭卡的宗教文化,更是通過 “遍查”與 “細描”②,呈現出綿延千年的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生生不息”。如作品對一次佛牙節的影像表述,在呈現了佛牙節的盛況之后,緊接著是花市上一對賣花夫婦的生活,在介紹睡蓮在斯里蘭卡人心目中的地位的同時,讓慢速移過的睡蓮鏡頭與賣花人微笑的臉互相切換,使花與人的關系生動呈現。通過“遍查”與“細描”,展示出這個國家佛教的歷史以及佛教與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聯系。
“和而不同”與“生生不息”不僅出現在《魅力肯尼亞》《魅力斯里蘭卡》《魅力印度尼西亞》這些弱小民族國家的題材,也出現在《魅力希臘》《魅力西班牙》《魅力葡萄牙》這些西方發達國家題材中。從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可以將這一現象解釋為:無論西方文化,還是東方文化,都各有所長,文化交流的最終目的不是建立仇恨與敵對,而是尋求和諧與共生。“和而不同”與“生生不息”最終達到的是“美美與共”的境界③,即無論文化之間有著怎樣的不同,總能找到彼此的相似點,進而求得共同發展,一種文化的存在不能以取消另一種文化為前提。“和而不同”與“生生不息”為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紀錄片賦予與西方民族志紀錄片不同的東方視角。
二、海外華人新形象
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在呈現海外各民族文化、生活的同時,也將海外中國人的身影呈現于熒屏,從而完成海外華人形象的重塑。紀錄片中處于支配地位的海外華人形象是由西方媒體塑造的,由于西方媒體具有強大的傳播優勢和話語權,其通過反面海外華人形象歪曲與丑化中國形象的消極作用就會更加明顯,因而如何通過海外華人形象的重塑傳播積極正面的國家形象就成為中國電視對外宣傳的首要任務。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海外民族志紀錄片順勢而生。細讀當下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可以看到,其主要在如下三個方面完成海外華人形象的塑造:
1.積極進取的海外華人形象
積極進取的海外華人形象主要出現在《絲路,重新開始的旅程》《對望——絲路新旅程》《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人在非洲》《與全世界做生意》等紀錄片中,他們分別是打拼意大利的女老板金小青、在吉爾吉斯坦戈壁荒原上建起煉油廠的朱強、將中非友誼紡織廠起死回生的馬千里,把中國電視節目引進到非洲的四達時代董事長龐新星,奔波于米蘭、紐約等各大時裝周的模特劉雯、王詩晴等。這些人物形象共同的特征是不懼困難、積極進取。他們身上都繼承了前一輩海外華人的“打拼”精神,卻有著前輩所沒有的品質——樂觀自信,如《與全世界做生意》中的張仁武面對美國合作方繞開自己單獨和國內伊犁溝通的行為,果斷終止其對美方的供貨業務,最終迫使對方回到談判桌上。他說,伊犁看重的是“我張仁武這塊牌子”。樂觀自信是新一代海外華人與老一代海外華人相區別的顯著標志。
2.合作共贏的海外華人形象
合作共贏的海外華人形象出現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國人在非洲》《對望——絲路新旅程》《與全世界做生意》等作品中。代表人物為投資美國牧草的生意人張仁武、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中方負責人魏建青、扎根非洲農村的農業技師萬叢新、跨境電商的倡導者廖旭輝、在非洲從事貿易的90后王封齋以及中科院非洲研究所的中國科學家們。這些人物形象作為中國人在海外的典型案例,以生動鮮活的事實回擊了西方媒體的“中國威脅論”。如關于中國人對非洲的影響,BBC紀錄片通過對當地居民的采訪,塑造出一個威脅當地人生存的中國人形象。而《中國人在非洲》則通過中非蘇伊士經貿合作區由建立到繁榮的曲折歷程形象地呈現了這一經貿合作區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來自湖北的農業技師老萬在非洲實驗新的農業耕作方式,并以實際的收獲成果打消了當地人的疑慮。由中國企業投資興建的蘇丹卡土木煉油廠正在改變著蘇丹落后的工業面貌。合作共贏的形象還呈現在以姚明、黃鴻翔為代表的環保主義者身上,正是通過他們在非洲大草原上保護動物的行動,改變著外界對中國人的負面評價。
3.東方天使與國際主義戰士
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紀錄片中,還出現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如《中國人在非洲》中的烏干達魯揚子學校校長王麗紅、中國援非醫療隊的女隊員、聯合國維和部隊里的中國女兵們。其中烏干達魯陽女子學校校長王麗紅是一位來自中國的北京女性,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是愛情讓她遠嫁非洲烏干達,三十年的生活,使她逐步適應了這片土地,并將自己的生命融入這片土地之中,與當地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她是非洲爺爺眼中的“東方天使”。中國援助醫療隊為中國政府應非洲國家政府邀請派出,在以往的媒體中,對其的報道多偏于政治宣傳,很少觸及醫療隊的真實生活。紀錄片《中國人在非洲》通過一系列個人經歷,講述了醫療隊員如何應對艾滋病、艾博拉疫情的威脅,令人印象深刻。而對聯合國維和部隊里中國隊伍的女兵的呈現,則將女兵與當地兒童的互動、通過這位來自重慶的中國女兵采訪,將自己童年的經歷與目睹的非洲兒童經歷的對比,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一細節讓一個既充滿愛心、又堅強剛毅的中國女兵形象躍然于屏幕。
一系列具有新視野與新氣質的海外華人形象是中國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對海外華人族群的貢獻,這些形象的塑造,改變了國際社會對海外華人作為邊緣群體的認識,從而為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華人賦予新的責任與義務。
三、跨越國界的文化認同
全球化時代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資金、物流、人流的全球性。伴隨著信息的全球化,國家之間的邊界被打破,不同語言、不同膚色的族群可以自由交往,從而逾越地理的距離,突破心理的疆界,建立起全新的文化認同。中國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就形象地呈現了這一現實,典型的作品是《世界上的另一個我》。這部紀錄片在寫文化上的貢獻如下:
1.“直播式”文化體驗
不同于傳統民族志紀錄片,《世界上的另一個我》呈現的是一種全新的文化體驗,這種體驗首先是通過多角度、伴隨式拍攝實現的。如第一集《年輕就要出發》開篇,伴隨著對影片內容的介紹,不同文化背景的90后主人公影像以爆炸性的方式呈現。其次,每一集的敘事,都是以不同角度、不同景別的騎行鏡頭做導引,這種類似電視現場直播式的鏡頭設計,讓觀眾產生對異國文化的全方位體驗,極大地滿足了觀看者的好奇心。
2.分享人類學的敘事方法
分享人類學的概念由法國人類學家讓·魯什提出,并在創作中加以實踐。魯什在對《瘋狂的靈媒》總結時說,“3年后,我回到索科漁民們居住的小島,給他們放了新拍的這部彩色電影。他們第一次明白我一直用拿在手上的那個奇怪機器干了些什么。他們在電影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他們看懂了電影語言,他們看了一遍又一遍,突然他們開始提出批評,告訴我哪兒不對頭。這是一種分享人類學的開端,我們之間突然出現了一種關系。我把我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寫的一本關于他們文化的書送給他們,他們拿來卻毫無用處。可我只用一個屏幕、一臺放映機、一臺發電機回顧一個民族時,就真正走入了他們中間”。④紀錄片《世界上的另一個我》的拍攝過程就是一個走入被拍攝對象、共同分享彼此世界的過程。如《離去與重生:為愛歸家》一集,采訪帕特里西婭關于父親的內容中插入了楊帆手持攝影機拍攝的畫面,之后是車上帕特里西婭與楊帆關于舞蹈的對話,為楊帆參與帕特里西婭的健身舞鍛煉做鋪墊,健身舞一段,楊帆的拍攝讓觀眾跟隨鏡頭看到攝像師的工作,而楊帆與被拍攝對象共舞又讓觀眾暫時忘掉攝像機,跟隨主人公全身心投入舞蹈的過程。通過分享人類學,民族志紀錄片為觀眾建立起開放的、辯證的觀影方式。
3.重返式的拍攝方法
“重返式拍攝”是由美國紀錄片先驅弗拉哈迪首倡的一種拍攝方式。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重返式拍攝,其一,重返式拍攝是一種對素材價值的再思考,紀錄片的本質在于記錄,但所有的紀錄并不能保證記錄的真實性,而重返式記錄就是對原始素材的反思,通過重返式拍攝,使紀錄片對真實的探索更進一步;其二,重返式拍攝彰顯紀錄片的記錄功能,使紀實的素材價值得以延伸,通過重返式拍攝,紀錄片真正實現影像的見證力量。《世界上的另一個我》中有兩集分別使用了重返式拍攝,一次是《90后媽(下)》,這一集和上一集的拍攝時間相隔兩年,此時的主人公巴森扈即將成為第二個孩子的母親,時間將兩集的內容連接起來,也使這一人物形象變得立體、豐滿。一次是歐洲季中的《失戀女孩冰湖重生》,這一集和兩年前的《紫色女孩》擁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公——漢娜。兩年的時光,讓楊帆和漢娜擁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此時的漢娜正身陷于失戀的苦惱之中,是楊帆的再次到來讓她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氣,并找到自己新男友。重返式拍攝讓攝像機見證了一個歐洲女孩從青澀到成熟的整個過程,為這部紀錄片賦予一種時間上的厚度。
通過“直播式”文化體驗、分享人類學的敘事方法、重返式的拍攝方法,以《世界上的另一個我》為代表的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將對于文化的書寫由國內少數民族拓展到海外各民族,從而建立起跨越國界的文化認同。
四、結論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當下中國主流媒體制作的“魅力世界”系列、“一帶一路”系列及“海外華人系列”紀錄片,代表了當下中國紀錄片發展的新趨勢。這些紀錄片以東方視角審視他者,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呈現“美美與共”的境界,形成不同于西方民族志紀錄片的鮮明特色,在寫文化的深度上,突破了商業紀錄片的框架,進入影像民族志的層次,同時也應當看到,當下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在“寫文化”的深度方面依然欠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創作者大都為媒體記者,記者的新聞敏感與敘事特長為民族志紀錄片賦予看點,但因缺少學者對文化的洞察力而無法深入文化的本質。另一方面,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在呈現方式上還只是欄目紀錄片,而真正的民族志紀錄片應該是反欄目的。中國的海外民族志紀錄片在滿足大眾的商業趣味的同時,依然需要人類學的滋養以積淀其文化內涵。
注釋:
① 《周易·系辭上》,“生生之謂易”。參見曾繁仁:《生態美學導論》,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20頁。
② 馬嵐:《從解釋社會學到解釋人類學——謹以此文紀念人類學家格爾茨》,《廣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③ 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上)》,《群言》,2005年第1期。
④ 魏國彬:《分享人類學述評》,《內蒙古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