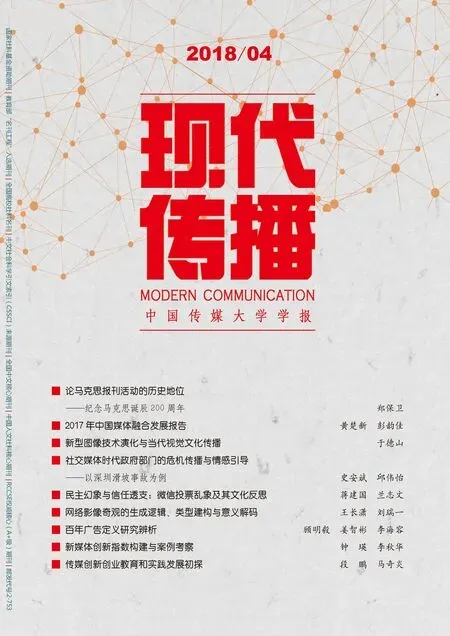民主幻象與信任透支:微信投票亂象及其文化反思*
■ 蔣建國 蘭志文
網絡技術所帶來的虛擬現實,不僅對日常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也對人們的政治生活產生影響,馬克·斯勞卡(Mark Slouka)認為,數字革命的深層核心,是與權力相關的。①投票作為一種政治技術,具有民意表達、凝聚社會力量、強化共同情感氣氛的作用,是民主實踐的重要手段。作為現實民主的網絡鏡像,微信投票的功能更加豐富。但就目前而言,微信投票淪為一種營銷工具,各方利益的博弈使朋友圈被塑造成“拉票圈”、微信群成為“拉票群”。公平正義和朋友情感在“拉票”過程中不斷被侵蝕。朋友情感異化成商品,被不斷消費;公平正義被潛規則所替代,規則成了“花架子”。本文主要探討被商業利益裹挾的微信投票行為,分析微信投票背后的游戲規則,以及“拉票圈”亂象所帶來的情感疏離和信任危機。
一、微信投票的熱鬧與隱憂
媒介技術對民主制度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網絡自誕生之日起就被賦予了培育民主的重要使命。對民主的再定義離不開對公共領域問題的探討,凱斯·桑坦斯(Cass R.Sunstein)認為,網絡“已經比街道、公園成為更重要的表達活動的競技場”②。互聯網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并以其開放性和平等性確保交往主體的獨立性,網絡將成為繼傳統公共論壇之后一個全新的、充滿活力的公共空間,其對民主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使用公共領域這一范疇去評估互聯網民主,他認為“民主,作為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制度,肯定比歷史上的其他選擇更優越。現存的所謂的民主形式肯定不能實現自由和平等的愿望”③,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有利于構建一個更新、更完善、更先進的公共領域,它加強和鞏固了民主的進程。然而,民主的表現方式也日益多元,它常常被具化為一系列的政治技術,如選舉、投票、座談會、民主協商等。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終端設備的普及,民主實踐形式更為豐富,從以網絡論壇、網絡博客為主的“鍵盤民主”,到網絡投票為主的“鼠標民主”,直至手機投票為主的“拇指民主”。常態邏輯下,網絡投票被視為民主的一種形式,而微信投票是網絡投票的一個分支,網民可以通過微信平臺進行民主實踐。
媒介是人的延伸。手機的智能化、便捷化,使其成為一個“綜合性器官”,通過手機,人類可以隨時隨地接入虛擬世界,實現現實與虛擬的無縫對接。簡言之,手機使現實虛擬化,虛擬現實化,它是“對空間依附的象征性的‘最后一擊’”④。隨著微信社交的流行和微信用戶的快速增長,建群、入群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偏好。通過主動“邀請”或被“邀請”入“群”可以延伸現有的關系網絡,“朋友”數量呈幾何式增長,擁有一個或多個百人大群已成為常態,入“群”已成為“社會交往的重要方式,也是新型社會化的象征行為”⑤。根據親緣、地緣、趣緣、業緣和物緣構建的大量微信群,使越來越多陌生人能夠迅速地產生互聯,微信群可以由親友關系、朋友關系組成的強關系網絡轉向由陌生人組成的弱關系網絡,微信社交夾雜了熟悉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的諸多特征。換言之,微信滿足熟人鏈條的溝通之后,轉而進入一個泛社交化時代。泛社交化的微信空間不斷創造出新的社會關系,并突破地理空間的限制,擴展網絡民主實踐場景。
毫無疑問,投票的本質是一種社會選擇,因此微信投票具有社會選擇的某些特征。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的動物,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偏好和評價標準,這些內在的價值體系具有差異性,甚至是沖突的,這種沖突往往導致個體更加孤立、分散,集體決策難以形成。社會選擇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主要關注個人偏好和集體選擇之間的關系,“其核心在于把個人的偏好變成社會的偏好,把個人的選擇上升為社會的選擇”⑥。投票是一種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沖突矛盾的有效方式,被現代民主國家廣泛采用。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戈登·塔洛克認為,投票是民主決策的主要組成部分。⑦個人偏好、投票交易策略、投票人擁有的信息狀況等影響投票結果及相關決策的形成。在民主國家,作為一種政治舞臺劇,投票劇目在國家公共生活中周期性上映。作為政治象征儀式的一部分,投票具有表達和聚合的作用,換言之,它“既成為理解自身的途徑,也成為理解社會的橋梁”⑧。通過投票活動,政黨和政治人物獲得民眾的支持。總之,投票對民主國家的延續至關重要,被政府、商業機構、宗教等所掌握和運用。隨著技術的發展,投票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斷變化,以微信投票為代表的網絡投票因其便捷性、互動性的特點,深受政治團體、商業機構、社會組織、網民的喜愛,各種“名義”的微信投票在微信社交圈廣為流行。
在微信時代,泛濫的毒雞湯、無孔不入的微商、層出不窮的拉票,無不體現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惡俗”。許多商家利用微信投票進行品牌營銷,間接地將情感轉化為利益。商業化的微信投票披著民主的外衣,做著品牌營銷的勾當,主辦方隱蔽地利用微信用戶實現營銷、漲粉的目的。商業化的微信拉票被冠以“友誼檢測劑”“情感潤滑劑”“社群凝結劑”的名號,一切為了友誼、為了團結,民主在微信中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態勢,但其背后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和人情變異,是商業利益引導下的“人情綁架”。虛高的票數并不能真正反映候選人的實力和水平,這種榮譽流于虛浮,是惡俗的表征,也對網絡民主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與現實社會的選舉相比,微信投票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首先,微信投票具有強烈的功利性。現代社會是一個流動的社會,生活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未來常常被簡化為當下的利益,“成名的渴望”蒙蔽了許多網民的“理性之眼”。很多微信投票被冠以“最美”“最佳”“最萌”“最具影響力”等稱號,參與者被外在的名利裹挾前行。其次,微信投票易受資本的控制,為發起者的利益服務。某網友敏銳地分析道:“商家只不過是想借用這樣的活動賺取知名度,我們這樣的都成了給人家免費打廣告的了。”商家利用微信投票,將親朋好友之間的感情轉化為利益。再次,從投票的規則來看,微信投票人情第一,規則第二。傳統投票有特定的時間、地點、人群,有明確的投票規則和投票秩序,依靠“選民”進行理性選擇。微信社交圈則是圈子文化的象征,依靠人情和面子進行投票是微信投票的“潛規則”之一。如為孩子、為朋友、為朋友的朋友等拉票行為源源不斷,各種“該投票了”的指令在微信朋友圈橫行霸道。民主秩序和規則在微信投票場景中變得雜亂無章。最后,微信投票過度消費情感,帶來新的人際關系焦慮。微信投票以人脈(即關系)為紐帶,一次微信投票就可以麻煩到許多親朋好友。海量的投票信息,一點一點地消耗朋友間的互助、關愛和理解,無形之中增加網民在朋友圈的壓力。部分微信用戶不堪微信投票、拉票所產生的人情重負,紛紛“逃離”朋友圈,開始隱姓埋名。
總之,微信投票從熟人關系入手,通過朋友之間直接或間接聯系,從熟人社會延伸到半熟人社會甚至陌生人社會,培育了新的“選舉”模式和交往文化,對網絡公共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公共領域是民主發育的重要場所,網民通過微信投票可以對一些社會事件進行評價,對于凝聚社會共識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網絡選舉幾乎沒有門檻,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可以在網絡上發起評比活動,尤其是利用微信群投票和公眾號投票極為便捷,這就導致微信投票泛濫,而轉發投票信息者都有明顯的“指引”,要求群內成員投指定的候選人,從而使投票行為受制于各種“明示”,參與者并沒有真正了解投票目的、候選人信息,以致于出現了“已投”的告白,來表示自己的立場。而資本和商業利益的入侵,激發候選人和投票者的私欲,功利性的投票行為,遮蔽了“票選”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并淪為形式上的民主——空洞的、無意義的“拇指運動”,并不能真正體現民意。
二、微信投票的人情、面子與象征性支持
新技術無法消除面對面、書信和電子廣播交流所建立起來的權力關系的記號。⑨微信社交圈以熟人關系為基礎,因此微信社交行為難免帶有現實社會中人際關系準則的影子,這正是微信投票中“人情票”“面子票”產生的根源之一。毫無疑問,民主的本質是自由、平等、普遍地參與,不應受到人情、面子的制約。而在微信投票中,參與投票的網民,在人情、面子的束縛下,機械、象征地進行投票,網民并未深入了解候選人,顯然背離了自由表達、公平競爭、體現民意的“選舉”意義。
黃光國認為,人情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有三層含義:個人遭遇不同生活情境時的情緒反應、社會交易時可饋贈的資源、人與人相處的社會規范。⑩簡言之,人情是一種社會交換模式,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禮尚往來。中國是一個講人情面子的社會。給誰投票或不給誰投票,背后是傳統的人情法則在起作用。以自我為核心的差序性“關系網”和這個關系網當中的其他人的差序性“關系網”,共同構成了復雜的人際關系網絡,進一步來說,由血緣和地緣關系構成的差序性“關系網”,決定了人們關系的親疏遠近。人情便是植根于熟人社會的土壤當中,雖然“人人心頭都有頭秤”,但是情誼或親密的程度決定了是否“做人情”給對方,即是否給“請托者”投票。在微信交往當中,面對微信好友的“投票”請托時,微信好友會遵循人情法則,盡可能調動自己的資源去幫助朋友。
面子是個人社會聲望或地位的象征,“面子功夫”影響網民的投票行為。為了能夠“控制他者的行為”,一個行為者在共同的行為處境中就必須認識到他的行為對每一個互動伙伴的意義。由于了解到“面子”對于他人的重要性,在面對私戳或群發要求“投票”的時候,人們會不顧麻煩投上寶貴的一票。投票表示對彼此之間關系的確認,對其社會地位的肯定,尤其是在面對領導或上司群發投票信息時,微信群內就變得十分喧鬧,各種“已投”加截圖表示自己給上級“面子”,領導或上司掌握他們職業升遷的權力,因此群內成員表現得異常熱情。在面對魚龍混雜的投票信息時,既不愿意投票,也不愿意損壞別人的“面子”,那么“拖”的策略便被運用到微信社交中,對朋友群發或私戳的投票信息不予理睬,或者用“已投”來掩飾自己的立場。
“刷微信”是一種消遣娛樂的方式,這種“習性”引導下的“民主”實踐,具有娛樂化的傾向。現實社會中的投票活動信息比較公開,人們對投票宗旨、標準、目的以及候選人信息了解比較充分。在微信投票中,多數人對候選人的信息幾乎不了解,投票者只是根據請托者給予的投票規則和說明進行投票,如“投票方法:四組各投一個,不過請認準第3組34號”“請投某某某,他是我舅舅!”等,在選完指定的候選人之后,投票者會“隨意”投一下其他人,以達到投票提交的要求。不難看出,微信投票是缺乏想象力和價值判斷的,請托者將“候選人”的“姓名”“編號”“代碼”等置于最突出的“指向”下,投票者只是按照要求完成一個指定的動作。投票過程中,投票者以一種游戲的心態完成既定的任務,休閑、娛樂的心理需求多于對民主的需求。五花八門的微信投票,培養了一種娛樂化的政治參與,而這種認知圖式的輸出,勢必會影響到現實社會當中的政治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投票者所付出的“人情成本”遠高于所獲取的交往報酬。在微信投票中,投票者所獲得的報酬是朋友的感謝或微薄的紅包收入,而候選人的報酬,也不外乎是榮譽、獎品、少量金錢。在具有競爭性質的微信投票中,投票者和候選人均獲得了短暫的快感和愉悅。但是,情理社會在人情往來上的非對等性,在于期望彼此因為情的產生而使交換的關系不是一次(或若干次)性地完結,或結束一次重新開始下一次,而是期望發生了一次之后就能連續性地循環下去。微信投票者往往會不顧某些麻煩而為朋友指定的候選人投上一票,然而微信投票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一天多投”“每天都能投”的規則已見怪不怪,投票時間短則幾天,長則一個月甚至幾個月,朋友不斷地麻煩其他“朋友”,形成一條“投票鏈”。但在一段時間內,可供交換的“人情”資源總量是不變的。因此,投票者的“人情”存在被過度消費的風險,進一步來看,一旦“人情”被過度消費,參與者便從主動投票陷入到被“道德綁架”的投票困境中。此時,人們的投票是被迫的,行為是不自由的,投票的結果自然顯得不公正。而對于拉票者而言,為了獲得這種短暫的收益,不經意間就陷入高企的“人情債”當中。如某網友便吐槽:“有了投票以后,我周圍的小伙伴都問我是不是被傳銷了;有了投票以后,隨時感覺友誼變得就像工具一樣,不得不幫忙,也不得不去做;有了投票以后,我被好多人嫌棄。”
邊際效應理論認為,消費者所獲得的收益隨著消費的增加呈遞減趨勢。隨著微信投票的增多,參與者從“投票”中所獲得的社交報酬不斷減少,從而減少或者終止繼續投票。于是,“面具人格”被引進微信社交當中,“偽裝”成為網絡社交新技術。網絡社交本身就是帶著面具的社交,匿名性可以讓人更輕易地偽裝自己,更好地適應周圍的環境。用沉默掩飾,用“已投”偽裝,成為應付微信群拉票的有效方式。如面對同學群轉發的投票信息,大多數人保持沉默或者以“已投”的告白來偽裝自己。微信群或朋友圈列隊回復“已投”已然成為一種新的社交語言和例行表態,它能夠有效地營造出積極參與的假象,讓請托者有“面子”,讓朋友圈顯得“和諧”。這種偽裝既可以免于得罪親戚、朋友、領導,還能維系和擴展既有的社會資本,這種所謂的“共贏”策略正被廣泛運用。雖然這種策略對雙方都是無害的,但正如布勞所言,“偽裝會使贊同失去意義”,“已投”表面上是對朋友的支持,但這種支持是一種投票者的自我偽裝,并不能起到強化友誼的作用,偽裝的面具戴久了,人們就會習慣,這種習慣將會影響到日常生活中的交往。除了“已投”這種新興的社交語言之外,象征性轉發也成為對付拉票的舉措之一。毫無疑問,象征性的投票與轉發行為,違背了投票作為了解他人、溝通社會的本質特征,從而淪為空洞、無聊、形式上的拇指運動。
正如讓·波德里亞(Jean Baudriltard)所言,“象征”是一種交換行為和社會關系,它終結真實,它消解真實,同時也就消解真實和想象的對立。由于各種象征性的支持或表態替代了真實的民意,回應與感謝也變得機械和虛偽。許多商家利用技術創造了一場“投票游戲”,通過榮譽、獎品等吸引候選人參與到投票中,將投票者的關系資源視為利益來源。候選人通過人情、面子進行拉票,并通過“紅包”刺激投票者參與其中,制造所謂的民意。投票者營造出一種民主參與的假象,民主被擬象創造出來的“超真實”所取代,看似同意,實則幻象。一些參與投票的“候選人”常常在朋友圈用請客吃飯等俗套忽悠朋友,友情在投票中變得虛偽與功利化,感謝也變得十分肉麻、庸俗。
三、微信“拉票圈”亂象的“贏取同意”與文化反思
微信投票所帶來的金錢、物質和聲譽,誘使候選人將投票信息分發到各自的微信社交圈,微信拉票的現象層出不窮。盡管政治選舉當中也存在拉票行為,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和認可,政治候選人會關注選民提出的問題,站在選民的立場上制定有吸引力的政策。選民的投票行為,是根據候選人提出的施政方案與自身需求的鍥合度而展開的。而在微信拉票過程中,商家巧妙地將利益個人化,將商業競爭轉化為個人競爭;候選人的拉票行為則受商業資本的操控,具有較強的被動性;投票者的價值判斷被人情、面子所壓制,缺乏民主的想象力。在利益的驅動下,候選人忙于一場“趕工游戲”——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多的票數。拉票成癮,像流行疾病一樣,感染著許多候選人,他們為了名利而廢寢忘食、患得患失。不斷變動的數字與相互競爭讓候選人內心緊張,票數便是成敗的標識,刺激著候選人不斷轉發與求助。在投票的過程中,群體被候選人的個體利益所蒙蔽,被“投票”所產生的利益所操控。而微信朋友圈在“選舉假象”籠罩之下,追求意義就會被追求手段所取代,朋友圈的正常交流也會受到“投票”的沖擊。
微信拉票對個人利益的過度關注,不斷消解人際互動的意義。從微信交流的角度看,“微”小的“信”,起到了溝通情感的作用。而隨著微信社交的泛化,微信群的交流越來越少,“巡視”群組,但不發言已成為常態,偶爾“刷一下存在感”,但回應者寥寥無幾。隨著微信的情感交流功能被弱化,許多微信群里僅剩下“幫忙”“投票”的功能。據《成都商報》報道,郭先生因為反對同學一直在班級群中發其女兒表演節目的拉票信息,而被同學投票移出微信群。而當同學再次邀請郭先生進群時,郭先生拒絕了。正如網友Justso_CN所言,“老同學的用處,就是給同學的女兒選美投假選票的。”當情感被抽離出微信群時,微信好友就變得越來越類型化、工具化。為了彌補“朋友”在投票過程中所消耗的時間和精力,拉票者會發微信紅包“回謝”,或者以搶紅包的形式來激發微信群成員的投票熱情,微信紅包成為激發成員投票的動力,有些微信群成員直接表示,“要不是領了紅包,就不投了”,這種以“紅包”交換票數的行為在微信社交圈十分流行,功利化的選擇替代了純粹的朋友間的交流,“要投票,先發紅包”的“索賄”標語不時出現。“當‘友情’元素淡出朋友圈時,這個軀殼般的圈子很容易會發生異化,被赤裸裸的‘利益’元素填充。”“一票不投,就拉黑”“票都不愿意投,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當朋友圈被各種利益關系所牽制、污染,商業利益、私人利益壓倒一切,集體意義的共識與團結就成為空話。
信任是交換和交流的前提,而微信朋友圈“接龍式”的拉票,正在消解微信社交互動的信任基礎。傳統意義上的投票行為,具有凝聚情感和社會團結的重要作用,“拉票”是候選人自我展示、爭取信任的過程。而在微信社交圈,有媒體總結了朋友圈拉票“四大真”:商家主導拉票大戰、孩子變成營銷工具、花錢買票自欺欺人、消費友情評選變味。可見,微信拉票并不是為了增進了解、促進團結,而是商家利用人的虛榮心,通過網民的人際關系網絡進行的一場營銷活動。網民拉票,不是真實的自我表露,不是為了爭取他人的信任,而是為了獲得他人手中的選票而已,這是“惡俗”的表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微信社交中的人際信任,在投票鏈接中植入病毒,一些網民被騙后賬號被盜,從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毫無疑問,網絡人際信任的主體是ID或昵稱,但實際承擔后果的是現實社會中的個體。由微信投票帶來的網絡人際信任危機必然會影響到現實的人際信任,不利于線下主體間的交流。從而使一些網民對朋友圈的拉票行為保持警覺,并遠離各種網絡投票活動。
“微信刷票”使微信朋友圈的信任基礎受到沖擊。微信群、微信公眾號是網民社交的主要場所,是網絡共同體建構的主要載體。而“共同體是基于信任而生的”,換言之,信任產生于一個團結、友愛、合作的共同體內部,共同體成員對準則的遵守也能夠有效保護人際信任,增強人際互動,同時也能增強共同體的黏合度。個體投機、市場逐利以及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利益爭奪,會消解信任的基礎。尤其微信的過度商業化運營,使微信投票也“商業化”了。通過百度搜索檢索“微信投票”,可以顯示有幾百萬條相關信息,其中諸如“投票吧”“投票網”的推廣信息,具有明顯的營銷動機。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投票的泛濫還帶來了一個新的“產業鏈條”——微信刷票,各類刷票公司、刷票插件、刷票軟件風靡“拉票圈”。“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得第一名,花了4000元刷到第一名”“家長朋友圈發1.5萬紅包幫娃刷票,發現第一名用了買票軟件”等新聞頻見于媒體。各種離奇的網絡投票數據,導致了公眾對投票結果的質疑和批評。大量的刷票行為,正在腐蝕網絡社交的信任基礎,許多網民對拉票行為甚為厭惡,取消關注公眾號、關閉朋友圈、拉黑好友等切斷關系網絡的自我保護行為屢見不鮮。
當微信群成了“拉票群”,朋友圈成了“拉票圈”,“公德”的缺失便直接影響到公共交往的價值。微信群和朋友圈作為社交場所,是網民情感交流的“屋檐”,每個人都有義務去維護公共空間的秩序,如不隨意轉發投票信息和盲目拉票等。但是從微信群的拉票信息來看,很多用戶“缺德”甚至“無德”,他們不顧“評比”的真實性和有效性,每天刷屏、大量轉發,即使群內成員已經做出善意的提醒,他們仍然熱衷于在各種微信群拉票,生產大量的信息垃圾。對于泛濫的微信拉票信息,用戶很難當場清理,而“已投”的社交語言又以“霸屏”的形式沖淡了交流的意義。
總之,社交媒體的發展擴展了民主實踐的場域,有利于網民廣泛地表達個人意見。但在市場化、商業化導向下,微信投票成為商家的營銷工具,成為一種典型的“惡俗”現象。在微信投票博弈過程中,功利性交流取代了情感性交流,投票的溝通功能被不斷消解,民主成為一種幻象。然而,“惡俗的現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俯首聽命于惡俗的擺布,不再追求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因此,為了讓網絡民主真正運轉起來,應強化微信投票的監督機制,制定投票規范,嚴厲打擊刷票等不誠信行為。提倡“網絡公共道德”,自覺維護網絡社會秩序,從而體現“誠實守信”的網絡公共精神。
注釋:
①[美]馬克·斯勞卡:《大沖突:賽博空間和高科技對現實的威脅》,黃锫堅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頁。
②[美]凱斯·桑坦斯:《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黃維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
③⑨[美]馬克·波斯特:《互聯網怎么了?》,易容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195頁。
④[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前言第16頁。
⑤蔣建國:《金錢游戲與社交幻象:微信搶紅包亂象的倫理反思》,《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⑥張曙光:《現代經濟學的最新發展》,《經濟學動態》,1999年第8期。
⑦[美]戈登·塔洛克:《論投票》,李政軍、楊蕾譯,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⑧馬敏:《政治象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頁。
⑩黃光國:《人情與面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85年第3期。
(作者蔣建國系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蘭志文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