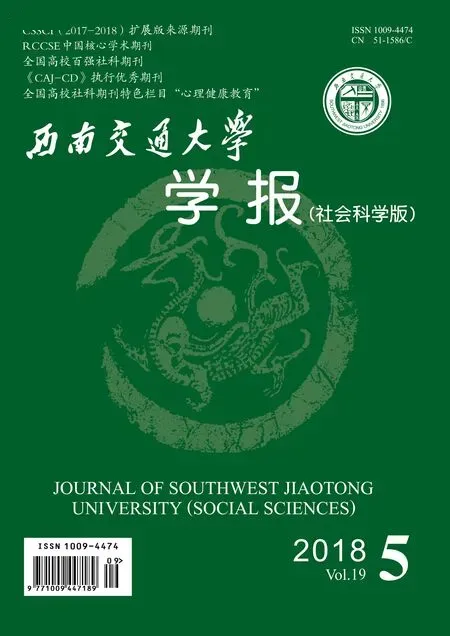社會比較理論視角下媒體從業人員日常交談研究
——基于成都市的調查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近年來媒介技術的迅猛發展進一步加劇了傳媒業的“不確定性”風險,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便是媒體從業人員面對的是一個競爭異常激烈、變化更加迅速的從業環境。有學者指出,當下媒體從業人員所處的從業生態總體呈現灰色狀態,表現為工作壓力大、工作穩定性差、職業倦怠指數高、職業滿意度與忠誠度下降、身份認同渙散等〔1〕。超強的身份模糊感與較低的職業認同度導致媒體從業人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渴望與上級領導、同事以及同行展開交談。通過日常性的交談活動,媒體從業人員不僅能夠獲取有利于他們開展新聞生產活動的有效資訊,而且能夠通過交談維持工作中和生活中的良性互動,從而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系,利于今后工作的開展。本文借助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通過對成都市媒體從業人員展開分析,聚焦并考察發生在媒體組織內部以及媒體同行之間的日常交談活動。
一、理論視角與問題意識
語言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重要媒介,通過語言不僅能夠交換資訊,而且能夠維系社會網絡中各個社會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交談作為口頭語言交際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和人際傳播的一種重要方式,是指經語言或其他符號將一方的訊息、意見、態度、知識、觀念甚至于情感傳至對方的過程。
組織是由無數個體所組成的社群,交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組織中的交談現象無處不在,屬于組織溝通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學者在研究組織中的人際交談活動時發現,日常人際交談具有友情建立、影響力、社會交往和促進組織效能等功能〔2〕。此外,也有學者指出,日常人際交談具有一項重要功能,即與他人之間無意識地進行一種社會比較,當公開地比較自己與他人時,所獲得的資訊可以讓人們減少尷尬與危險〔3〕。
社會比較理論最早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Festinger提出,他認為人們對于評估自己的意見與能力有著基本的渴求,當社會的客觀存在無法滿足個人評估自我的需求時,人們會無意識地利用他人作為比較的尺度來進行自我評價〔4〕。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社會比較理論的內涵和邊界不斷被拓寬。從廣義上講,所有個人自我角色與他人互相比較的過程,皆可稱為社會比較。
目前學界對于社會比較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比較類型和社會比較動機兩大層面。關于社會比較類型,學者們通過不斷探索提出了多種理論假說和模型。社會比較中最常見的比較類型是平行比較(similar comparison),即當社會情境不明確的時候,人們往往會選擇相似的他人作為比較的對象。除平行比較以外,上行比較和下行比較也是社會比較中較常出現的兩種比較類型。Suls等人較早地提出了上行比較(upward comparison)的觀點,該觀點認為,上行比較的目的在于尋找到與優秀個體之間的差距,從而滿足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進的動機〔5〕。Collins隨后對上行比較進行了進一步拓展,提出上行比較基于預期目標的不同可能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應:對比效應(contrast effect)和同化效應(assimilation effect)〔6〕。與上行比較不同的是,Wills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全面、系統的下行比較(downward comparison)理論,他認為當人們感知到外界和內在受到威脅時,會傾向于與比自己差的人進行比較,努力讓自我威脅感降到最低并從中獲取成就感〔7〕。
除了平行比較、上行比較和下行比較之外,內群體比較(in-group comparison)與外群體比較(out-group comparison)也是社會比較中另外兩種常見的比較類型。Tajfel和Turner將群體界定為“一些個體的集合體,這些個體把其自身覺知為同一社會范疇的成員,并在對自身的這種共同界定中共享一些情感卷入”〔8〕。內群體和外群體則是依照人們的歸屬感對自身所在的社會群體作出的一種劃分。群體內成員通過與群體外成員的日常交談,可以比較得出自己在群體中處于何種位置以及自我所在的群體是處于何種地位。與此同時,群體間的社會比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或削減群體間的身份認同。當內群體與外群體之間相似度高時,有效的身份認同就建立了,反之亦然。另外,當社會比較結果是我屬群體(one’s own group)優于外群體時,群體中的成員往往會更具有優越感,自尊感往往較高;反之,群體中成員就會更加沮喪,自尊感往往較低。
在社會比較動機方面,目前學界較為公認的三大動機分別是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和自我改進(self-improvement)〔9〕。自我評價是自我意識的一種形式,是指個體要認知、評價自己的能力、特點以及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總是需要自己與相似的人進行比較后才能更好地得出結論,換言之,自我評價的目的在于自我了解以及自我界定(self-defining);自我提升又被稱為自我增強,是指個體有著積極看待自我的基本愿望,在此訴求驅使下,通過下行社會比較能夠產生一種積極的自我覺知,滿足比較者自我提升的訴求;自我改進是指人們企圖利用上行社會比較讓自我變得更好的心理歷程,通過“力爭上游”促使自我效能感得到有效提升。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試圖引入社會比較理論作為理論分析視角,并主要探討以下問題:(1)媒體從業人員在與媒介組織內部的同事以及與同行展開日常交談過程中,是否有意識地進行著一種潛在的社會比較?這種社會比較有哪幾種基本類型?能夠滿足其何種動機需求?(2)媒體從業人員借由日常交談進行社會比較時,在話題選擇和比較策略上有何特點?(3)媒體從業人員的日常交談活動以及社會比較行為會對他們所從事的新聞生產活動產生何種影響?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取社會科學質化研究中深度訪談法這一方法,此方法雖然獲取的樣本數量較少,但對于初探性研究來說,概念性的問題可以不受限制,反而能得到更多樣性的答案。在抽樣方式上,本文選擇非概率抽樣中滾雪球抽樣這一方法,最終選取成都市內媒體從業人員共20位,囊括了平面媒體記者、編輯,電視臺記者、編導和網站編輯等各媒介類型。在20位受訪者中,男性共14位,女性共6位,其平均年齡為31歲。其中,媒體從業經歷最長者從業年限達21年,最少為1年。
三、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將從社會比較的類型、動機、話題選擇、談話策略、結果等方面對成都市媒體從業人員日常交談中的社會比較行為進行探討和解讀。
(一)比較類型:通過平行比較獲取資訊,內群體與外群體比較時態度截然不同
研究發現,在媒體從業人員通過日常交談所進行的社會比較中,平行比較這一比較類型的數量最多,其主要目的是通過平行比較來獲取新聞生產活動中有用的資訊。通過日常交談,媒體從業人員能夠獲知同行日常新聞處理的方式、其他媒體組織的內部組織規范以及各種八卦消息等。與此同時,通過平行比較能夠有利于自我工作的有效開展。
“我平時交流的比較多的就是和我報社關系比較好的同事,然后就是和自己跑同一口子的其他報社的朋友。和他們交流我可以知道他們最近在關注哪些新聞,還有什么可以做的,特別是關于我們口子的新聞,一有什么消息大家都會互通信息。”(受訪者3)
“我經常問我朋友他們報社最近有什么新的要求,比如什么內容不能觸及,什么內容該采取什么樣的要求去報道。通過和他們溝通,我就發現其實大家面臨的形勢都差不多,你懂的,現在的新聞太不好做,除了宣傳任務還是宣傳任務。”(受訪者19)
此外,當內群體與外群體進行比較時,媒體從業人員態度往往截然不同。內群體和外群體比較常用于區別自身所在組織,同時也通過社會比較強化自身組織認同,維護組織形象。Tajfei指出,組織認同是指組織內成員意識到他(她)屬于某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意識到作為組織成員帶給自身的情感和價值意義〔10〕。在交談過程中,交談者往往不會過多奉承外群體,對于內群體的評價多以正面態度為主,組織認同度較高。
“每周一的例會,部主任都會對每周的同題新聞進行點評,雖然偶爾還是會表揚其他報社這個題目做的比較好,但大多數情況都是肯定自己的屬下,我們做得相對更好。”(受訪者14)
另外,研究還發現,媒體從業人員在與內群體以及外群體通過交談進行社會比較的過程中,比較的話題也不盡相同。在與內群體比較時,同事間往往會選取工作層面的話題,比如對新聞的處理方式,對某些選題的看法。而在與外群體進行比較時,話題的選擇往往來源于生活中的一些瑣碎事情,比如稿費、生活福利、同行八卦等。
“我們同事之間或許會聊最近捕捉到的比較有做頭的專題,但一般不會給其他網站的朋友聊,畢竟存在一個獨家新聞的考慮,萬一他們比我們先做,我們就吃虧了啊。而與外面的人聊得更多的是同事和同行間八卦、福利、待遇等話題。”(受訪者10)
(二)比較動機:通過交談強化自我改進和自我提升的動機
研究發現,當媒體從業人員有自我改進需求的時候,他們會傾向于與能力和經驗優于自己的同事或同行前輩進行上行比較。通過日常交談,他們可以間接地找出差距,以便今后努力地向優秀的同事或前輩靠攏。
“你看華西今天做的稿子沒?”
“沒有啊,怎么了嘛?”
“今天又被主任批了,說華西那個記者稿子又做的比我好,人家采訪的就更扎實。”
“哈哈,你又不是第一回挨批,人家那個記者好多年你才好多年嘛!”
“再批我個人都莫得面子咯,你說我咋個就沒得人家寫的那么好呢?”
……
(根據訪談對象會話進行整理)
以上談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當人們具有自我改進的動機時,往往傾向于選擇與比自己優秀的人進行上行比較以達到“同化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傳媒業是工作壓力極大、競爭異常激烈的特殊行業,高負荷的工作量會導致媒體從業人員的職業倦怠感,在這個時候往往需要不斷給自己以正面暗示,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途徑就是經由日常交談并采用下行比較的方式來實現自我提升這一動機。研究證實,下行社會比較是媒體從業人員日常應對壓力的重要方式。在下行比較中,比較者往往比被比較者在心理上更有優勢,常帶有一種驕傲或輕視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往往導致日常交談變成一種負面的、情緒化的交談,其體現為通過負面評價他人,樹立一種自身優越感和自我認同,這種情況在資深媒體從業人員身上尤為普遍。當談論起新進記者或者實習生的表現時,資深媒體從業人員會帶著一種輕視的語氣或表情,比如其中一位受訪者就表示:
“老記者們往往會在一起時,就會討論現在的記者水平一代不如一代,從而凸顯出‘他們’這個群體的優越感。”(受訪者3)
(三)比較話題:組織強制性話題更能引發交談
研究發現,組織強制性話題在所有交談話題中更能引發媒體從業人員的日常交談行為。有受訪者表示:
“媒體從業人員因為工作性質的原因,工作時間長且面臨各方面的壓力,一般不太會主動地展開交談,除非是在編前會、例會和閱評會等場合。”(受訪者9)
組織強制性話題之所以能夠引起交談并且進行社會比較,是因為在組織強制性話題討論中個人可以找出自己在內群體或者外群體中的位置,從而進行自我評價。另外,組織強制性話題在客觀上傳遞著一種組織規范,而媒體從業人員在面對這一組織規范時表現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認同和抗拒。特別是表現出抗拒態度時,媒體從業人員更傾向于通過交談來達成共識并采取抵制行動。
“比如某天某條新聞,我們大家都覺得那個記者處理得不錯,可上面偏偏覺得不行,要求重新寫不然就不給發,我們聽了都不以為然。”(受訪者7)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嘛,天天上頭給我們說這個新聞不能報,那個新聞該怎么報,在私下我們都會吐槽。”(受訪者10)
由此可以看出,強制性話題往往能夠引發媒體從業人員討論,并且通過比較對組織規范進一步加深認同或者產生抗拒心理。
(四)比較策略:以自我保護性策略為主
研究發現,媒體從業人員在日常交談中不可避免地進行著社會比較,而社會比較的結果往往又不盡如人意。在社會比較進行過程中,如果其中一方處于劣勢的時候,交談時處于劣勢的一方往往會采取保護性的交談策略來維護自尊,這些保護性的策略主要包括逃避比較、選擇新的比較維度與反向性自我維護三種方式。
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自己曾經在不同場合使用過逃避比較這種保護性策略。受訪者4表示:“每當交談的一方有意或者無意地談論自己取得的成就多么突出,表現多么不錯的時候,交談另一方一般會選擇轉移交談話題從而逃避比較。”Brickman和Bulman指出,當談話雙方在某一個維度上進行比較時,其中一方如果意識到自己處于劣勢,通常采取回避比較的策略來應對負面的、消極的情緒體驗,以降低負面情緒帶來的困擾〔11〕。
選擇新的比較維度是進行社會比較過程中保護自我的另一種常用策略。這種策略主要是通過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即重新選擇與受到威脅領域無關的其他重要的自我價值來進行比較。Steele等人曾指出,個體在社會比較過程中一旦感知到自己處于劣勢或受到“威脅”時,就會逃避應對并優先考慮選擇自己比較擅長的領域,重新設定比較維度,達到維護“自尊”的目的〔12〕。
此外,反向性自我維護機制也是被受訪者所頻頻提及的一種保護性策略。在Alicke等人看來,當個體在應對消極的社會比較過程中,他們往往會通過反向維護的方式,即通過夸大他人的能力,貶低自我來達到維護自尊的目的〔13〕。這種策略的使用往往是在感知到他人明顯地優越于自己,而且不容易否認社會比較信息的有效性的情況下個體所采用的維護自我概念的一種有效機制。
“我們媒體行業,論資排輩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一般有老同志在我們面前‘炫耀’自己的時候,一句‘是是是,向您老人家學習的東西還太多’就敷衍過去了,反正尊重老前輩也不吃虧嘛。”(受訪者15)
(五)比較結果:強化職業身份認同,增強職業互動與同行競爭
Kroger認為,認同是一種心理活動,代表著人們和他人比較后對于自身印象的描述與肯定〔14〕。身份認同是個人對于自己歸屬于某個群體的心理認知活動,這是自我概念中十分重要的一個面向〔15〕。個體與群體內其他成員基于對群體成員身份的知覺,以相近的方式認同和評價自身。群體成員對“我們是誰”、“我們擁有什么樣的特征”、“我們應如何與其他群體成員互動”以及“我們和其他群體的區別”等一系列問題有著相同的感知,正是這種群體成員身份體現了集體自我的建構——“我們”與“他們”〔16〕。媒體從業人員作為一群特殊的從業者,必須長期面對超長的工作時間、同行競爭的壓力以及社會輿論的不理解。因此,媒體從業人員是各個職業工種中發生日常交談行為最為頻繁的群體之一。媒體從業人員通過日常交談能夠了解同行與自己工作的相似性,并且能與一群處于類似情境中的人展開比較,從而讓自己更了解自我職業特性,達到形塑職業身份認同的結果。
研究發現,受訪者如果整日處于緊張焦慮的工作狀態時,多數受訪者會通過日常交談來降低自我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感,不過前提是他們只會與同行中這種處于類似工作情境的人進行討論。
“你知道我們記者的工作性質嘛,真的就是新聞民工的命,特別是剛剛踏入媒體這個行業時非常不適應,每天晚上我都會回家和大學同學在QQ或者微信上聊天、吐槽。當得知朋友那邊也是差不多的情況時,我好像沒那么壓抑了。對于我們這種新記者來說,不僅在報社內部受到老記者們的‘另眼相看’,甚至有的時候采訪對象看到我們是新人都會給我們氣受。”(受訪者7)
受訪者7是剛剛工作半年的記者,在這半年時間中歷經了從最初的不適應到逐漸適應的過程。訪談時,受訪者7表示:“我職業身份認同的強化就是通過與同樣是從事媒體工作的同學展開日常交談而實現的。”此外,在接受訪談的所有媒體從業人員中,大家不約而同地表示通過日常交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區別出“我們”這個特殊群體的身份特征,從而進一步強化“我們”之間的職業身份認同。
研究還發現,媒體從業人員通過日常交談和社會比較,不僅增強了人際互動,而且導致了同行間競爭的加劇。具體來說,媒體從業人員這個特殊群體需要與同業人員展開交流獲取有利于今后工作開展的資訊,而且與不同媒體間從業人員維持互動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也有利于日后工作的開展。然而,傳媒業是一個充滿高度競爭的行業,因此媒體同行間在日常交談和社會比較的互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關乎彼此利益的話題,當交談話題涉及到自己和自己所在單位核心利益時,交談行為就會終止。比如,有受訪者通過跑獨家新聞的例子進行解釋:
“記者都有這個經歷,每次通過交談得知哪個同事和同行又跑到了‘獨家’時,是又嫉妒又不服氣,有時候會覺得為什么我碰不到這樣的好新聞呢?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當我們和同行聊最近哪些新聞可以做時,如果覺得這條新聞可以變成我的稿子,那我就不和你聊這個了,一般會選擇重新換個話題。”(受訪者1)
由此可見,媒體從業人員在掌握到獨家線索時,就會特別小心翼翼地避談這部分,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同行間競爭無處不在。
(六)通過社會比較,對新聞生產活動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如前所述,通過日常交談和社會比較,媒體從業人員能夠強化職業身份認同。眾所周知,媒介從業人員本身作為傳播活動的傳播主體,他們身份的特殊性影響著其所從事的新聞生產活動,媒體從業人員間的日常交談活動,可以被視作一種傳播者的“再傳播”行為。通過日常交談和社會比較,媒體從業人員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對媒體行業從業生態的認知和評價,初步形成一種“共識”,且這種共識往往是負面的。這種負面情緒迅速地在媒體從業人員中擴散,繼而形成一種反制的力量并對新聞生產活動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通過與20位受訪者訪談,大致可以歸納出這種負面影響的三個表現:
(1)影響工作效率。通過日常交談,媒體同行能夠彼此獲取和交換資訊,當得知自己所處的境遇更加糟糕時,往往會采取更加消極的方式來表達不滿,如開小差、裝傻賣呆、暗中破壞、消極怠工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聞生產活動的效率和新聞產品的最終呈現品質。“每次和其他報社跑同一口子的記者聊天時就發現,我們每次寫得也差不多,為什么他稿分就比我高得多,再下次我收到任務時我就會故意寫差一點,等編輯給我改,反正我付出的也和我得到的沒有成正比,何苦讓自己那么辛苦”。(受訪者11)
(2)懷疑角色價值。角色價值主要包括權利、名聲、收入和專業自主權等。國內一位名記者曾經這樣寫道:“記者在中國是很難作為一種終身職業,媒體人周而復始的動蕩和流動使記者成為一個吃青春飯的職業。”〔17〕同時,加上近幾年來對“新聞民工”現象的探討不絕于耳,媒體從業人員的職業歸屬感和榮譽感淡薄,頭頂早已沒有“無冕之王”的光環了。有受訪者表示:“每次我們幾個跑同一個口子的記者約出去吃飯,談論的往往不是哪篇稿子做得好,最近又發生了什么大新聞,而一般常談論的是你這個月又拿了多少稿分,電視臺的某某某又買了好車好房子,而你我都還在掙稿分。”(受訪者13)另外,有學者指出,“年輕化”和“流動快”是當下媒體從業人員隊伍最顯眼的兩個特征,很多記者、編輯都以“新聞民工”自嘲〔18〕。以上的這些表現與媒體從業人員間進行的社會比較不無聯系。一位有15年從業經驗的主任記者這樣描述道:“每次我和同行的那些同輩或前輩聊天時就不禁感嘆,如果我們當時轉行不做新聞,現在該是怎樣,那些早就跳槽的人里面,一個二個都比我現在混得好。”(受訪者9)
(3)加深職業倦怠感。研究發現,社會比較對媒體從業人員職業倦怠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媒體從業人員由于工作特性,每天與不同媒體記者朋友處在同一個時空,共同采訪報道新聞事件,不經意間總是處在與同行進行社會比較的氛圍中,如交換工作上的資訊、收入、家庭信息等,所透露的資訊往往會激發彼此間進行社會比較的需求,再加之個體傾向于與自己有著重要社會聯結的他人進行比較。因此,媒體從業人員間的日常交談活動往往存在著社會比較這一有趣現象。本文發現,越負面的社會比較越容易導致職業倦怠感的產生。
四、總結與不足
媒介組織作為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面臨著媒介體制和政治環境的雙重制約。“和其他社會組織類似,媒介組織內部也有科層結構、勞動分工和生產流程,因此,傳播活動貫穿于這些結構、分工和流程之中,并且具體演示了這些結構和流程”〔19〕。本研究發現,面臨著諸多管控的媒體從業人員往往渴望通過與媒體內部人員(上司、同事)以及同行展開交流來獲取利于他們發展的資訊、維持互動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甚至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規避風險和釋放壓力。通過日常交談,采取多種社會比較方式,媒體從業人員在強化職業身份認同、增強職業互動、與同行競爭的同時,本身就作為傳播者的媒體從業人員間的“再傳播”行為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所從事的新聞生產活動,如影響工作效率、懷疑角色價值和加深職業倦怠等。
毋庸諱言,作為一項初探性研究,本文還有很多不足。首先,由于本研究受時間和經費的限制,僅僅選取了20名成都市內媒體從業人員進行訪談,樣本數量較少,且訪談對象中平面媒體從業人員居多,這就直接導致樣本多樣性不足,研究結果是否能夠推廣到所有的媒體組織還值得商榷。其次,由于研究時間比較短,準備不夠充分,以深度訪談作為本研究的起點,在研究路徑上可能也存在一定問題。最后,在研究設計上,未來是否可以聚焦到一個更為典型、更加微觀的新聞生產場域,通過更為直接的參與式觀察、田野考察獲取一手資料,這都是后續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