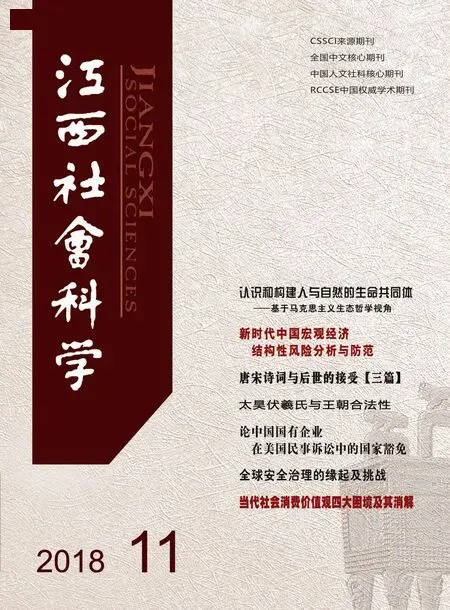《理想國》的認知結構與教育理念
《理想國》是哲學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作品。在該書中,柏拉圖以追尋正義的本質為線索,以辯論的形式,構建出一個完整的理念世界,并提出理想城邦的設想。在理想城邦的設想背后,是柏拉圖對世界本質、靈魂和教育的認識。在柏拉圖看來,人類認識真實世界需要靈魂進行一次關鍵的轉向,理想城邦的建設則需要靈魂進行第二次關鍵轉向,而教育則是實現靈魂兩次轉向的關鍵所在。
柏拉圖于公元前428年出生在雅典的一個貴族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大約20歲時,他跟隨老師蘇格拉底投身哲學。當時,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那場伯羅奔尼撒戰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雅典在戰爭中和戰后經歷了一連串的政體改變,在寡頭制的少數人統治和民主制的大眾統治之間頻繁更替。在民主制復辟的內戰中,柏拉圖的舅舅和表兄最后都被民主派殺死,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也在民主制雅典被判處死刑。蘇格拉底的死在哲學和政治兩個方面對柏拉圖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在哲學方面,他一生都在探尋事物的本質,并由此發展出“理念論”;在政治方面,柏拉圖試圖尋找出一種完美的政治制度,并得出了“哲人王”的論斷。哲學與政治的結合,不僅是柏拉圖在《理想國》里給出的終極方案,也是柏拉圖一生想要努力實現的政治抱負。
本文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正義本質的認識的三個階段為線索,歸納其在構建理想城邦過程中展露的教育思想,并探討教育和靈魂轉向之間的關系。
一、柏拉圖的正義本質
(一)對事物影像認識的想象的正義
在柏拉圖看來,在現實世界之上還有一個理念世界,這個理念世界是神創造的真實世界,是本質的世界。我們現實中感受到的世界其實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并不是真實的世界。現實世界中的藝術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是“對影子的模仿”。通過藝術來認識世界,無疑遠離了真實和本質。這個階段的認知,就是對事物影像認識的想象。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通過“床”的例子具體闡述什么是對影子的模仿。制作床的人有三種,創造床的原理的神、制作床的木匠和繪制床的藝術家。神創造的是理念世界的床,是床最真實的本質部分;木匠根據原理,制作出一張現實世界的床;藝術家則通過臨摹現實世界的床,畫出床的形狀。因此,若通過“對影子的模仿”去認知世界,無疑是南轅北轍。[1](P20-55)
格勞孔在《理想國》第二卷提出的正義契約論無疑屬于在這一層次的認知上對正義的理解。按照格勞孔的說法,對人來講,最理想的情形莫過于隨心所欲,做任何事情都不用承擔后果,這是專屬于“最強者”的待遇;最壞的情形莫過于遭受欺凌,受到傷害,忍受無妄之災而無力反抗,這是“最弱者”可能遭遇的不公平的境遇。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弱者不得不聯合起來反抗強者,要求按照一套名為“正義”的規則辦事,約束強者,保護弱者,正義不過是“強者的妥協”。在正義的“契約”下,社會上的每個人都遵守契約,權益得以保障,秩序井然,儼然是一個理想型的社會。但是。這種認知背后隱藏的觀點是,人性本惡,只是因為不想受到懲罰,才按照正義的規則辦事,正義是被動和妥協的結果。
柏拉圖將這種正義的認知比喻為“牧羊人的神話”:呂底亞人古各斯的祖先是一個牧羊人,在機緣巧合下在一道深淵中發現了一枚可以使佩戴者隱身的戒指,這使得他可以作惡而不被發現。于是,他就想方設法為自己謀取利益,獲得權力,并勾引王后同謀殺死了國王,最終取而代之。所以,柏拉圖說,無論一個人看起來多么善良,多么正義,只要他能夠做了壞事不受懲罰,那么,他一定會這么做的。[1](P60-65)
(二)對事物本身認識的信念的正義
在柏拉圖看來,現實世界之上還有一個神創造的真實世界,現實世界不過是這個真實世界在現實中的投影。但是,由于我們并不能直接接觸真實世界,想要弄清楚真實的本質,必須從現實世界的投影進行倒推和反證。他同時認為,要搞清楚真實世界的投影是什么其實并不容易,因為詩歌和神話描繪的世界,都是對“影子”的二次模仿。在《理想國》書中,這種思想的具體化,就是通過探索城邦中的正義來追尋靈魂的正義。城邦中的正義,就是對事物本身認識的信念。探索城邦中的正義,有一個基本的假設:本質具有“不變”和“持久”的性質,“正義”是“善”的尺度上最好的那一部分,必然存在于最好的城邦之中。
蘇格拉底認為,城邦的出現,是出于提高效率的需要。隨著人類的發展,個體逐漸無法實現自給自足,于是出現了分工與合作,再通過產品交換,就能更好地滿足所有人的需要。最初級的城邦,只需要滿足人們對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城邦中以農民、建筑師、裁縫、工匠、牧人、商人和醫生共七種主要職業,可以稱之為“健康的城邦”或是“豬的城邦”。隨著城邦的發展,香料、藝術、珍寶開始在城邦中流行,“發燒的城邦”開始出現,欲望的需求取代了生存的需要。在這樣的城邦中,軍人作為一種專門的職業出現,人們對資源的占有和爭奪引發城邦之間持久不斷的戰爭,城邦陷入無休止的混亂。由于“豬的城邦”和“發燒的城邦”各自的缺陷都非常明顯,所以,柏拉圖進一步借蘇格拉底之口提出“美麗城”的設想。在這座“美麗城”中,有三個階層,分別是最高層的統治者、中間層的守衛者和最底層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人們按照不同的天賦能力在不同的階層工作和生活,每個人的作用都被最大化,能夠對內保證秩序,對外保障安全,這就是理想城邦的樣子。在這個認知層次上,柏拉圖提出城邦正義的定義:“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1](P76)換言之,各安其位,即是正義。
柏拉圖用一個“關于高貴的謊言的神話”作為這種正義的基礎。人類實際上孕育于地球,地球是人類的母親。所以,人們一定要對出生地念念不忘,衛國保鄉,御侮抗敵,團結一致,有如親兄弟一般。但是,他們雖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神在鑄造人時,卻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黃金,因而這些人是最可寶貴的,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所以,各行各業的人應當忠于自己的本行,各盡所能。
(三)關于純粹理念的理性的正義
在柏拉圖看來,人們通過感覺器官來理解現實,得到的是“對事物影像認識的想象”和“對事物本身認識的信念”,它們都是理念世界在現實世界的“影子”。在此基礎上,只有通過理性的方式,才能夠得到對理念世界的認知。從現實世界到理念世界的認知,正是人類認識從低級到高級、從易到難、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過程。柏拉圖在《斐多》(Phaedo)中將這種飛躍描述為從大地逐漸上升,穿透云層,最終進入空靈之境。人們只有完成這種認知上的飛躍,才能接觸到世界的本質。[2](P39-45)在《理想國》中,蘇格拉底便是通過理性的方式,以“對事物本身認識的信念(城邦的正義)”為起點,推導出“關于純粹理念的理性(靈魂的正義)”。[1](P49)
若要透過城邦的正義來尋找靈魂的正義,首先要證明的就是它們之間的關聯。理解靈魂的本質,一直就是哲學中的難題。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靈魂的存在,可是它又看不見、摸不著,難以觀察,因此,只能通過理性的思考和邏輯推理來描述它的特點。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提出靈魂的三分學說。他提出一個基本原則:同一個東西不可能同時、在同樣的方面、相對于同樣的東西做相反的事情,如果出現同時、在同樣的方面、相對于同樣的東西做相反的事情,那么,它一定不是一個單一的東西,而是一個復合體。[3](P45-52)柏拉圖以在現實世界中人們時常會陷入左右兩難境地為例,證明了靈魂是一個由理性、意氣和欲望組成的復合體。
柏拉圖借助“關于靈魂的馬車”的比喻,闡述了為什么正義是對靈魂的褒獎:靈魂是一架兩匹馬拉的馬車,其中一匹溫順,另一匹頑劣。那匹溫順的白馬愛好榮譽,謙遜而節制,車夫不用鞭子教訓它,只用輕聲的勸導就使它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而那匹黑馬則桀驁不馴,驕橫放縱,車夫必須用長鞭逼迫它就范。因此,車夫駕馭這輛馬車并不容易,但只有同時駕馭住這兩匹馬,靈魂才能達到正確的地方。
至此,城邦的正義便和靈魂的正義確立了對應關系,理性的車夫對應著城邦中的統治者,意氣的白馬對應著城邦中的護衛者,欲望的黑馬對應著城邦中的生產者。靈魂中的正義就是理性、意氣和欲望這三個部分在理性的統領之下各司其職、各安其位。由此,柏拉圖最終得出結論,正義的本質是保證靈魂的有序和健康,正義的回報是對靈魂的褒獎,至此對正義的“契約論”也作出了回應。[4]
二、認知的結構和靈魂的轉向
(一)認知的結構
在《理想國》中,對于認知結構體系的構建是由三個著名的隱喻來完成的。[5]
在“太陽喻”中,柏拉圖向我們揭示整個認知結構的兩個層次,即可以感受到的現實世界和需要通過理性認識的理念世界。世界萬物之所以具有可見性,我們的眼睛之所以具有視力,都是因為有太陽的存在。太陽的光線不僅僅使我們能看見世界,還讓萬物生長。而理念世界中的“善”,則發揮太陽的作用,給予我們認識理念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我們才能夠探索事物的本質和分類,才能夠有了解真實世界的可能。
柏拉圖將一條線段分成不相等的兩個部分,分別代表著“可感世界(現實世界)”和“可知世界(理念世界)”。然后,再按照同樣的比例把每一條小線段分成兩個部分,劃分出四個從低到高的知識等級,分別稱之為 “對事物影像認識的想象”“對事物本身認識的信念”“對數理對象認識的理智”和“關于純粹理念的理性”。[1](P182)在他看來,在可感知世界里認識的對象是一些變化無常的東西,我們只能通過感覺器官來感受;而在可知世界里的認識對象則是實在的永恒事物,需要通過理性才能夠了解他們的本質。[6]
“線段喻”以“太陽喻”的兩個認知結構層次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出關于兩個世界的新型結構,通過線段的格式闡述認知的四個階段,并提出它們之間的演進關系。
在“洞穴喻”中,生活在黑暗的洞穴世界中的囚徒都已經習慣被囚禁,他們身后的高處,點著一團火,這是整個洞穴里唯一的光源。囚徒每日看著墻上恍恍惚惚的陰影,卻從未想過這些陰影是從何而來,是誰創造了這些陰影,甚至認為陰影就是真實。他們早已失去了離開洞穴、探索真理的勇氣和能力。突然間,有一個囚徒被松開了捆綁,被迫站起來并回過頭去觀看那團火光,認清雕塑與影子之間的區別,之后又被強迫走上那條通往洞口的崎嶇的上坡路,走出洞穴,看到了真實的世界中的動物和植物。最后,他終于看到了真正的太陽。
柏拉圖將“線段喻”中提出的四個認知階段通過洞穴模型進行了遞進的展示,最初囚徒看見的影子就是“對事物影像認識的想象”,起身后看見的火把和雕像是“對事物本身認識的信念”,走出洞穴后看到的花草樹木是“對數理對象認識的理智”,最后看見的太陽是之前看到所有事物的本質和起源,也就是“關于純粹理念的理性”。
(二)靈魂的轉向
這些囚徒,實際上就是人類被囚禁的靈魂,囚徒走出洞穴的過程,從可見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過程,就是靈魂走向健康和完美的過程。走出“洞穴”的起點就是關鍵的第一次轉身,第一次看到陰影背后的火把和雕像,開始對可知世界產生疑慮和困惑,眼睛“因為初見光亮”而產生不適,柏拉圖稱之為“靈魂的轉向”。在《理想國》的第七卷,蘇格拉底對格勞孔說:“于是這方面或許有一種靈魂轉向的技巧,即一種是靈魂盡可能容易盡可能有效地轉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靈魂中創造視力,而是肯定靈魂本身有視力,但認為它不能正確把握方向,或不是看在該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設法努力促使它轉向。”[1](P193)
靈魂的第一次轉身,是一個十分艱辛的攀登過程,正如《理想國》書中所闡述的,需要有“金”的天賦,從小接受最好的教育,經過層層篩選,學習算術、幾何、天文等迫使靈魂接近真理的學科,再通過數十年哲學辯證法的訓練,才能夠經過重重考驗,艱難走出洞穴,獲得靈魂的正義,探索世界的真理。《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對這種艱苦的描述是:“靈魂對學習中的艱苦比對體力活動的艱苦是更為害怕得多的,因為這種勞苦更為接近靈魂,是靈魂所專受的,而不是和肉體共受的。”[1](P173)教育是“靈魂轉向的技巧”,但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人解放、喚醒、提升理性的痛苦過程。在走出洞穴,見識了真實世界的遼闊和壯美后,柏拉圖卻認為這個靈魂還應當以教育家的身份再次轉身,回到洞穴中,幫助這些被囚禁的靈魂走出洞穴,完成靈魂的第二次轉向。對于剛剛走出洞穴的靈魂來說,重回洞穴無疑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柏拉圖認為,走出洞穴的靈魂會因為“正義”而轉身,重回洞穴,回報培養的他的城邦。[7]
在靈魂的兩次轉身中,教育貫穿于始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因為教育,靈魂向外轉身;又因為教育,靈魂向內轉身。
三、柏拉圖的教育理念
在追尋正義的本質的過程中,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構建出一套完整的教育體系,并分別對教育的階段、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目的進行了論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系統。
(一)教育的階段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提出,公民的教育可以被概括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幼兒教育、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他認為,教育3-6歲的兒童,應當以講故事、做游戲、學音樂為主,但是,在內容的選擇上要進行嚴格的審查,選用健康的音樂、能夠激發勇敢正義的故事和有助于遵守規則的游戲,因為“凡事開頭最重要,特別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階段,最容易受陶冶,你把它塑造成什么型式,就能成什么型式”[1](P231)。到6-16歲這個階段,所有人都要接受普通教育,以個人的天賦和愛好為依據,分別進入不同類型的學校進行學習,培養情感和道德。具有“銅”“鐵”天賦的人們畢業后進入社會的第三階層,成為勞動者。具有“銀”天賦的人接受進一步的體育教育和音樂教育,培養靈魂中的意志和勇敢,成為一個優秀的守衛者。“金”天賦的人則進入高等教育階段,學習天文、幾何、算術等“通向真理”的學科,并通過長達數十年的哲學訓練,成為“哲人王”。
(二)教育的方法
在《理想國》中,有三個重要的教育方法貫穿始終。
第一個重要的教育方法是建立教育的“審查制度”。柏拉圖要求必須將諸神之間的爭吵、天神對人類無故的懲罰、英雄人物的悲傷情緒和冥府中的陰森可怕排除在教育的內容之外。再用這些經過審查的教育內容讓受教育者相信神是絕對正義的,神性是完美至善的,為城邦和朋友死于勇敢是光榮的,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8]只有這樣,城邦中才能實現最好的秩序,城邦中的公民才能實現最好的生活。
第二個重要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按照他把人的天賦分為“金”“銀”“銅”“鐵”,每個人都應當接受和自身天賦相適應的教育。比如“銅”“鐵”天賦的人們應當通過接受關于閱讀、書寫、體操、騎馬等的教育,形成節制的品格,進入社會做一個順從的勞動者。“銀”天賦的人應當接受文藝教育和體育教育,文藝教育培養其對內的友善溫和,體育教育訓練其對敵人的兇猛勇敢,最終培養為一名優秀的護衛者。
第三個重要的教育方法是關于如何通過學習算術、幾何、天文學獲得真理的。柏拉圖認為,任何一種通向真理的學科,是能夠迫使靈魂使用純粹理性的學科。算術是一切學科的基礎,幾何的對象是永恒的事物,天文學研究天體運行背后的規律,這三門學科的研究對象都是不可見的,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它們的存在,這與柏拉圖對真理的定義何其相似。因此,柏拉圖認為,學習算術、幾何、天文學是通向真理的正確方法。
(三)教育的目的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提出的教育的整體目的是打造一座正義的理想城邦,使不同天賦的人能夠各安其位,進而使城邦井然有序,良性發展。個體教育目的終點是培養出一位能夠認知“理念世界”,具有高貴的品德修養,愛國愛民的“哲人王”統治者。通過建立“審查制度”,規范教育的內容,使用音樂和游戲培養幼兒,利用音樂教育和體育教育培養護衛者,開展以算術、幾何、天文等學科為主的高等教育,并不只是為了培養受教育者對音樂的欣賞,提升受教育者的體能,也不是為了在戰爭中能夠取得人口素質的優勢,而是通過不同的教育階段,采取一系列的教育方式,將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逐步轉化為對理念世界的認知。
四、結 語
從《理想國》完成的時代背景來看,當時雅典的政治體制在戰爭中經歷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寡頭制、民主制、僭主制中反復。無論是在建立理想城邦的過程還是在構建靈魂正義的過程中,柏拉圖都是以城邦和人整體的健康和發展作為最終的目標,理想城邦中的人和靈魂,是為了整個城邦和完整的靈魂服務的。城邦中有著嚴格的分工,人們依據天賦接受適當的教育,從事適合的工作。可以說,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追求知識本身就是學習的目的,進而倡導去功利化的教育等關于靈魂和教育的觀點至今仍在煥發著蓬勃的生命力。